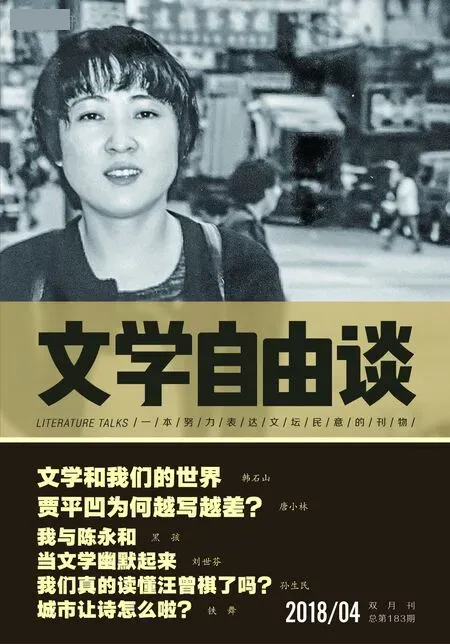我與陳永和
黑 孩
給一個(gè)朋友打電話聊天,她問(wèn)我是否知道微信,我說(shuō)不知道。朋友說(shuō)我一定活的十分孤獨(dú),微信早已經(jīng)是無(wú)人不知無(wú)人不曉,連小學(xué)同學(xué)都能幫你串起來(lái)。我問(wèn)微信是什么?朋友說(shuō)是一個(gè)軟件,下載后就可以使用。說(shuō)起來(lái)或許沒(méi)有人相信,這是去年的事。
加了微信后,電話號(hào)碼將一大群人串起,于是我知道在日本有一個(gè)用中文寫(xiě)小說(shuō)的圈子,還有一個(gè)用中文寫(xiě)小說(shuō)的筆會(huì)。圈子里浩浩蕩蕩幾十個(gè)人,消息也多的不得了,如此我得知有二十年未見(jiàn)的陳永和也在寫(xiě)小說(shuō)和散文,并且寫(xiě)得不錯(cuò)。
約好了在我家見(jiàn)面,我去車(chē)站接她。她笑著向我擺手,看上去無(wú)憂無(wú)慮,二十年好像被她的一擺手就擺掉了。
之后又見(jiàn)了三次面,我們談到好多事。與陳永和聊天,我發(fā)現(xiàn)她對(duì)自己對(duì)他人似乎不添加她自己的眼光,說(shuō)好聽(tīng)了就是隨和。但是談到我好多年不寫(xiě)作的情況時(shí),陳永和卻讓我感到隱藏在她內(nèi)心的熱烈。她這樣對(duì)我說(shuō):黑孩,你要相信自己,走出自己,你可以重新寫(xiě)的,你不該放棄。她的這些話清晰地印在我的腦子里。本來(lái)我以為寫(xiě)作是過(guò)去了的事情,過(guò)去了的事情就讓它過(guò)去好了。陳永和對(duì)我的鼓勵(lì)像遠(yuǎn)方的閃電,一瞬間讓我看見(jiàn)遠(yuǎn)方的一條小路。
與陳永和見(jiàn)面后,我還真寫(xiě)了幾篇散文。《寅次郎的故事》在北京文學(xué)》雜志發(fā)表后,陳永和說(shuō):黑孩,你邁出了第一步,接著走。《話說(shuō)西湖》《富士山和生魚(yú)片》在《中國(guó)文化報(bào)》、《閉上眼睛》在《上海文學(xué)》雜志上發(fā)表后,陳永和比我還高興,她對(duì)我說(shuō):黑孩,你走得挺好,堅(jiān)持下去。顯而易見(jiàn)我應(yīng)該感謝陳永和。昨天寫(xiě)出長(zhǎng)篇的第一行,我發(fā)微信給她,說(shuō)無(wú)法接受這個(gè)開(kāi)頭,還說(shuō)早年一天寫(xiě)一萬(wàn)字,現(xiàn)在一千字都難。陳永和回話說(shuō):堵塞了那么多年,哪能一下子就嘩嘩地流啊,寫(xiě)作是生命,要慢慢來(lái),將生命寫(xiě)到最好。原來(lái)她憧憬文學(xué)至此。我感動(dòng)到無(wú)語(yǔ),覺(jué)得一生一世都可以跟陳永和用一個(gè)鼻孔出氣。我本來(lái)在日本的區(qū)政府工作,很穩(wěn)定,重新寫(xiě)作后,我開(kāi)始猶豫要不要辭去這份工作。看到我猶豫,陳永和就說(shuō):你有這么多東西可以寫(xiě),你辭職寫(xiě)啊,再不寫(xiě)就沒(méi)有體力寫(xiě)了。我怕寫(xiě)不好,即使寫(xiě)出來(lái)也未必有人要讀,陳永和就說(shuō):一天二十四小時(shí),總得用什么方式打發(fā)時(shí)間啊,不要考慮正在寫(xiě)的東西有沒(méi)有人讀,你就寫(xiě)好了。我二話不說(shuō),立即把區(qū)政府的工作辭掉了。
我讀了她的長(zhǎng)篇《一九七九年紀(jì)事》。小說(shuō)里寫(xiě)了好多種人,好多種愛(ài)情。所謂下筆如有神,小說(shuō)的神在細(xì)節(jié)。陳永和筆下的細(xì)節(jié)看起來(lái)非常真實(shí),推測(cè)出她的長(zhǎng)篇都是經(jīng)過(guò)長(zhǎng)期準(zhǔn)備的。福建是她的故鄉(xiāng),福建也是她心中的故鄉(xiāng)。在一篇?jiǎng)?chuàng)作談里,陳永和這樣說(shuō):小時(shí)候,媽媽常常牽著我的手到城里三坊七巷走親戚。那時(shí)候,坊巷間鋪的全是石板路,大約走了幾百年,也就走出凹凸不平來(lái),下雨天會(huì)積點(diǎn)水,平日腳踩在上面會(huì)發(fā)出好聽(tīng)的響聲。后來(lái),到了“文革”,沒(méi)有時(shí)間走親戚了。忘了是哪一年,又開(kāi)始走時(shí),才發(fā)現(xiàn)坊巷間的石板路已經(jīng)沒(méi)了,全變成了水泥路。于是很感嘆。沒(méi)想到過(guò)了幾十年后又變回來(lái)了。現(xiàn)在的坊巷間,又全鋪上了石板路。石板路很新,走上去不響,也不積水。于是就想,還要再走上幾百年,才會(huì)變成我小時(shí)候走過(guò)的,會(huì)響、會(huì)積水的石板路吧……小時(shí)候的走,常常會(huì)走到心底,像白布被染上色,一輩子再也無(wú)法褪掉。于是,不知不覺(jué),就被這種褪不掉的色彩控制了。年紀(jì)越大,就越發(fā)覺(jué)自己被它控制。
文字靜寂而清新,似音樂(lè)淌過(guò)心間。《一九七九年紀(jì)事》的讀者也許會(huì)將她筆下的人分成好人壞人,將她筆下的愛(ài)情分成幸福的,貧窮的,高尚的,庸俗的,粗暴的,柏拉圖式的,放蕩的,甚至是盲目與極端的。但是,雖然小說(shuō)充滿鬼氣,文字后的她卻像跟我談話一樣,對(duì)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持有主觀評(píng)判,該發(fā)生的就自自然然地發(fā)生了,唯有一股綿綿不斷的力量是屬于她自己的。陳永和的故事肯定萬(wàn)物,視無(wú)常為命運(yùn),有對(duì)一個(gè)時(shí)代的所有的一切的尊重和理解。陳永和的隨和是謙順的,誠(chéng)實(shí)的,達(dá)到一種境界。陳永和非常善良。我時(shí)常情緒低落,跟她聊天后覺(jué)得她大徹大悟,所以總是打電話給她,好像她是我的漢方藥,可以為我解毒。陳永和會(huì)說(shuō):人都有這樣的時(shí)候,很正常。我?guī)缀醯昧岁愑篮鸵来姘Y。優(yōu)秀的作家看人、寫(xiě)作的時(shí)候,會(huì)去掉私心,陳永和做到了,所以我想說(shuō)她是優(yōu)秀的,她的優(yōu)秀與她本人有關(guān)。
關(guān)于陳永和的另一部長(zhǎng)篇《光祿坊三號(hào)》,她說(shuō)她的《光祿坊三號(hào)》可以稱為IDEA小說(shuō)。與其他小說(shu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IDEA小說(shuō)一定都有一個(gè)眼,或者說(shuō)一個(gè)想法。這個(gè)想法不那么普通,甚至相當(dāng)奇特,但都具有很強(qiáng)的生命力,有深度與厚度。整部小說(shuō)就建構(gòu)在這個(gè)眼這個(gè)想法之上,包括人物設(shè)計(jì)、情節(jié)走向、結(jié)構(gòu)規(guī)劃,都服從這個(gè)眼、這個(gè)想法,順著這個(gè)眼、這個(gè)想法走。總之,想法貫穿整部小說(shuō),離開(kāi)了這個(gè)想法,小說(shuō)就不成其為小說(shuō)了。陳永和說(shuō)在《光祿坊三號(hào)》中,這個(gè)眼就是三份遺囑。不僅如此,小說(shuō)的背景是她的老家福州。作家陳希我和陳永和有過(guò)一次對(duì)談,陳希我說(shuō):在陳永和這里,本土題材不再是被廉價(jià)提取的資源,她提供了故土敘事的新的可能。陳永和本人也說(shuō):我之所以總喜歡把自己小說(shuō)的背景放在福州,或許就因?yàn)楝F(xiàn)在年紀(jì)已經(jīng)足夠大,大到能讓褪不掉的色彩在心里充分發(fā)酵,使它足夠成熟,使它從心溢出到身體,再?gòu)纳眢w溢出到文字吧。陳永和說(shuō)這一類(lèi)小說(shuō)的代表作,她看過(guò)的有日本作家三島由紀(jì)夫的《金閣寺》、德國(guó)作家帕特里克的《香水》和美國(guó)作家雪佛蘭的《戴珍珠耳環(huán)的少女》。我告訴陳永和,除了《金閣寺》,其他的兩本我還沒(méi)有看過(guò)。于是她再來(lái)我家的時(shí)候就帶了幾本書(shū)來(lái),里面就有香水》和《戴珍珠耳環(huán)的少女》。陳永和希望我繼續(xù)寫(xiě)小說(shuō),就這兩本書(shū),比什么都能證明她的一番心意。
話說(shuō)回來(lái),我每每提起陳永和小說(shuō)的好處,她都說(shuō)她沒(méi)有感覺(jué)。她說(shuō)她的小說(shuō)自有它自己的命運(yùn)。為此陳永和不太在乎對(duì)她的小說(shuō)的評(píng)價(jià)。陳永和的淡泊,是一個(gè)作家的個(gè)性。心情不好的時(shí)候,跟她聊幾句就會(huì)病愈。這樣的人并不多見(j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