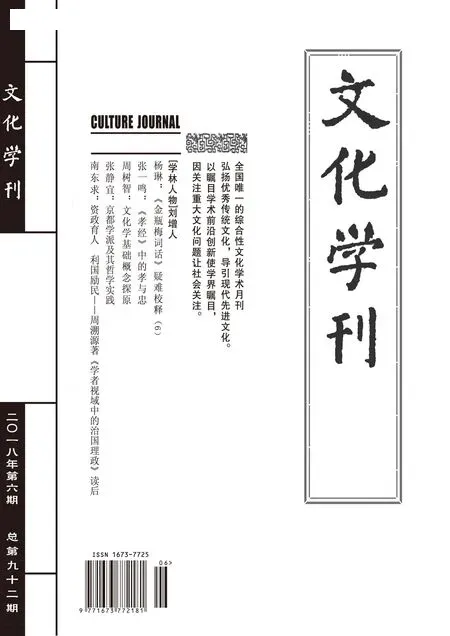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理論評析與反思
江 曼 徐燕峰(華東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一、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概述
在民事訴訟領域中,證明標準對于案件的處理有決定意義,證明程度的高低與相應案件事實能否通過現有證據得到認定有直接聯系,但在實踐生活中,對與證明標準有密切聯系的證明責任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證明標準,因而證明標準的理論體系尚未有效構建起來。盡管我國在民事訴訟相關立法中試圖確立多級證明標準,但在實踐中并未起到預期作用。在設立證明標準之初,法學界對其寄予了厚望,證明標準確立以后,對于法官、當事人及整個社會都具有重大意義。[1]
(一)法官層面
對于法官而言,證明標準的確立有助于法官認定舉證責任人提交的證據所指向的案件事實。一旦標準確立,法官即可基于已達證明標準的證據認定相應事實,以其真實存在為裁判的依據之一。除此以外,確定的證明標準能夠為法官在認定案件事實階段提供統一的規則,并且可幫助法官準確地判斷當事人的事實主張是否已得到證明。例如,對于不能證明的部分,法官可以其并未達到證明標準為由而作出不予認定的裁判;在發生訴訟爭議的情況時,法官可依該標準作出有法理依據且為當事人所接受的相關解釋。在法官威信度較低的社會現狀下,確立的證明標準可有效制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并最大程度防止法官錯判誤判。
(二)當事人層面
對于當事人而言,當證明標準已明確時,當事人可依據該標準預測民事訴訟的結果,亦可根據已掌握的證據來判斷其是否有足夠證據可以提起訴訟。當事人對一審裁判不服,認為一審法院并沒有按照民事訴訟證明標準認定證據的證明力是否合乎標準時,其可以此為由提起上訴,要求二審法院以一審認定事實不清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對于申訴案件亦可以此為由。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對于司法活動的良性進行有諸多益處。
(三)社會層面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明確的證明標準對提高整個社會的法治觀念及促進立法目的的實現有重要意義。我國是一個成文法國家,有大量系統化、明確化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對于社會一般人而言,法言法語相較于日常生活用語晦澀難懂,并且對法官具有較大自由裁量權的相關法律法規難以作較為正確、客觀的理解,以至于在裁判作出后,當事人對判決有諸多異議,直接導致了我國上訴率較高這一結果的產生,這無疑浪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且對于我國司法機關所作裁判的公信力和司法權威都是極大的挑戰。[2]而明確的證明標準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這種不足,繼而從個人層面和法官層面出發,促進社會的發展。
二、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理論基礎
根據《證據規定》第二條的規定,在當事人不能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情形下,舉證責任人承擔不利后果。此處對于“足以”的判斷便是證明程度高低的問題。對于需要達到怎樣的證明程度才能從法律層面接受當事人的主張,學界尚未有定論。
(一)客觀真實說
“客觀真實說”在我國民訴證據理論界中一向占有主導地位。持有這種學說的人認為,在兩大訴訟中,都必須將案件事實盡數查出。以此為基礎,當事人在案件事實的證明上也必須達到這一標準最低限以上,從而滿足法院對證明的認定要求。否則,其證明將不被采納,其主張亦得不到滿足。
筆者認為不然,認定案件事實時,如必須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大多數民事案件會因無法查明而無從裁判,這顯然有失訴訟法律本意。不可否認的是,民事糾紛案情復雜多樣,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可以還原案件全部事實的,而以客觀真實說為證明標準實屬嚴苛,根本不具有操作可能性。因此,筆者認為不應將其確立為民事訴訟法定證明標準。
(二)蓋然性說
“蓋然性說”在兩大法系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置喙。蓋然性程度雖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均屬不要求完全證明,只需具有一定程度可能性即可。除此之外,大陸法系亦明確規定了自由心證為其證明標準之一。自由心證,即只要獨立作出判斷,心有所證即可,而要使法官形成“內心確信”,不一定要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只需其具有十之八九的可能性,即高度蓋然性即可。[3]
三、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反思重構
民事訴訟領域中要義之一是證明,與證明相對的則是證明標準,證明標準是對證據本身的證明力大小所立判斷標準。我國屬兩大民訴證明標準并行制:一是高度蓋然性;二是排除合理懷疑。立法機關學習國外立法,試圖建立層次化證明標準,但其忽視了該標準所適用的外部環境、正確的規則及相應適當的司法體制,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不能有效運用到司法實踐當中這一后果的產生。
在筆者看來,上述兩大標準均難以滿足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要求,因此,當下亟待走出的困境是制定一個更加符合民事訴訟證明要求的體系,以期更好地應對民事訴訟要求。大陸法系明確規定了自由心證為其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從適用該標準的國家與地區看,成績斐然。該標準要求證據證明力必須達到一定程度,但不需要其達到確定無疑的程度,將其作為民事訴訟法定證明標準是未來民事立法的趨勢。
(一)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反思——兩大標準之不足
1.“高度蓋然性”
《民訴解釋》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標準,這也是該標準在法律上的資格認定來源,其要求人民法院基于相應證據對相應事實予以認定時必須達到高度蓋然,即可能性。與此同時,法官必須在該尺度上進行蓋然性判斷,并因此得出極有可能如此的心之所證。也就是說,其與客觀真實說的要求相差無幾,這也是其在司法實踐中難以得到有效適用的根本原因。
在筆者看來,單設高度蓋然性為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沒有必要,從民訴解釋第一百零八條以及證據規定第六十四條可知,所謂高度蓋然性,依舊是為法官作出心證所服務,將其與最終理論置于統一且對應的理論高度是不適當的,明顯違背了法律邏輯學的相關要求。因此,無需單設高度蓋然性為民事訴訟證明標準,但應當保留并且將其作為法官達到內心確信所需的理論工具。
2.“排除合理懷疑”
我國《民訴解釋》第一百零九條明確規定了排除合理懷疑制度,這也是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的法源,其為排除合理懷疑制度在民事訴訟領域的適用賦予了法律資格。
依筆者之拙見,“排除合理懷疑”作為民事訴訟法定證明標準之一是不得當的。以一般人的角度看,涉及到排除合理懷疑首先且唯一想到的是刑事立法。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無論在案件性質,還是證據規則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4]:第一,兩者案件性質完全不同;第二,兩者的訴訟程序不同;第三,兩者的法律后果和效果不同。更重要的是,前者的社會危害性和不良影響持續期間遠不如后者。在民事領域內,當事人的民事權利受私法管轄,公權力不應過多介入,否則會使得公法和私法界限混亂,不利于法治化進程的有序進行。適用“排除合理懷疑”標準,對當事人而言過于嚴苛,這不利于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亦不能兼顧民事訴訟的效率價值。
(二)民事訴訟證明標準重構——“內心確信”標準
《證據規定》第六十四條的規定,可以成為“內心確信”標準在我國的法律引證來源。按照該條劃定可知,審判人員必須遵照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要求,遵守職業道德,在周全且嚴謹的審查全部證據以后,基于已有證據,自行判定,從而產生內心確信,并且基于此作出相應裁判。內心確信在我國民事訴訟領域已經得到實際應用,將其法律地位提升至民事訴訟一般證明標準是必然且必要的。
毋庸置疑的是,法官在適用內心確信的標準之時,已將蓋然性標準融會其中,若相關證據無法達到該標準,法官如何會產生內心確信?“蓋然性標準”指代的是一類標準,無論是哪一個,或哪幾個,均是形成內心確信應有之義,但僅以其中的一個標準或者幾個標準作為民事訴訟證明標準,顯然是不周延的,不能滿足當下復雜的社會生活需要。社會生活變化多樣,“一刀切”式的法定證明尺度,留給法官自由裁量的幅度是有限的,因此,在實踐中,我國經常會出現適用法定證明標準而顯失公平的案件。筆者認為,基于我國當前司法現狀和法治化進程的需求,應當構筑以“內心確信”為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證明體系。
第一,內心確信具有可預見性。法官將內心確信標準貫徹于審理案件的整個過程,最終基于現有證據形成內心確信,從而作出相應裁判。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在此并非作為某一特定且特別的群體而存在,其形成內心確信必須是基于法律的基礎及社會一般人的角度,這也就說明社會一般人是可以預見到裁判可能結果,一旦其擁有該預見可能,訴訟的神秘面紗便被揭開,這對于普通人民群眾法律意識的提高及訴訟意識的增強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內心確信誕生于羅馬法系。通說認為,我國是一個大陸法系國家,而內心確信標準為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所選擇和適用,其中尤以德國為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印度法系等其他四大法系的最大區別在于其屬于成文法系,以成文法規范為主,而在民事領域,大量成文法規范的適用必須通過訴訟,這就意味著必須將事實與成文法規范聯系在一起,而作為這之間橋梁的便是確定且適宜的證據標準。在這樣的要求下,事實應當是確定無疑的,而非是可能或者很可能存在的,那么只有法官形成內心確信才能成為作出裁判的依據。
第三,內心確信是自由裁量權良性行使的應有之義及重要保障。內心確信標準不同于其他列舉式的法律規范,其自由裁量的幅度更大,法官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作出分析和判斷,但其幅度又是有限的,法官不能想當然地作出裁判,而應將其形成確信的過程以說理的形式呈現在裁判文書當中。當事人可以根據裁判文書來監督和指正法官作出適當裁判,以免當事人上訴或者申訴,降低訴訟效率。
基于前文所述可知,當下我國民事訴訟證明標準與司法活動嚴重脫軌,普適性極低。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多重,筆者認為,首要原因應當是其未與社會發展的步伐保持一致,以致于既有的證明標準無法滿足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從而出現了法定證明標準不適用,內心確信標準逐漸走上民事訴訟舞臺這一現象的產生。這既是司法實踐的選擇,也是民事訴訟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重筑一個更加適用于我國司法活動實際需要的證明標準尤為重要,這不僅有利于民事司法活動的良好進行,更有利于民事訴訟立法體系化的構筑。筆者認為,基于大陸法系的實質,應當以“內心確信”為我國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以提高我國訴訟活動的質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