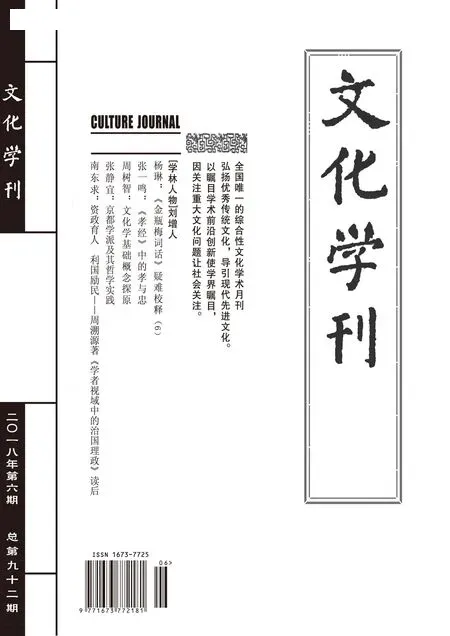《孝經》中的孝與忠
張一鳴(中國人民大學,北京 100872)
前言
后世在解讀孝忠關系時,多以由《孝經》中文句化成的“移孝作忠”“以孝事君”將孝與忠同一化、政治化。然而,“移孝作忠”與“以孝事君”雖語出《孝經》,但就《孝經》自身而言,忠孝關系本身并未表現出“忠孝無別”或是“以孝作忠”的特點。*作者按伏亮先生所作《孝的傳承與重建——以<孝經>為中心的考察》中認為《孝經》的身份并不僅僅是一部倫理書,還具有更高層次的義理。同時認為對于《孝經》只談論其中“五等之孝”的階級性、“移孝作忠”的落后性和“孝治天下”的專制性的這種理解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孝經》本身的義理。見以及陳壁生先生的《古典政教中的“孝”與“忠”——以<孝經>為中心》中從《孝經》古注出發認為“忠孝無別”的現象實發生于明皇注孝經后,《孝經》文本本身實是強調忠與孝的分離。而“移孝作忠”同時根據敦煌所出皇侃之注可推出“移孝作忠”只針對士這一階層的說法。《孝經》中“孝”觀念的特殊地位使“孝”處于“天之經,地之義”的地位,忠孝關系也因“孝”獨特的主導性而使關系的雙方——“忠”與“孝”既有所關聯又相互獨立。
牟宗三先生在說明中國哲學獨有之“強度的真理”時即舉“孝”為例,認為“孝”作為具有強度的真理,在其真理范圍內有著無所不包的特性,和如同彈簧般可變通的真理性,是可以與西方哲學“廣度的真理”可媲美的真理。[1]“孝”觀念確然像牟宗三先生言,在“孝”限定于是子女對父母行為時的表現多種多樣*作者按《論語·為政篇》中孔子在向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四人解釋孝時回答截然不同,說明孝的表現形式并不單一,實現孝的形式因人而異。。但是“孝”觀念的內核在多樣的表現中始終沒有發生改變——被評價為“孝”的行為始終內含對主體對象父母的愛敬之心,而當愛敬之心被認證為“孝”觀念最精髓的內核時,“孝”可以實行的主體對象就不再局限于父母,“孝”可作用的關系也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展。*作者按可證明孝的主體性多元化的典型案例即是《禮記·祭義》中“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的記載。孝實現了從主體對象為父母向主體對象多元的轉化。
“孝”觀念因主體對象的多元化而使自身得到擴展,至于《孝經》內部更是把“孝”觀念置于五等之內,將孝分為: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孝經》中獨有的“五等之孝”的說法體現了時位化的特點*作者按楊慶中著《周易解讀》的導論內容,周易的時位確定了一爻所處的特殊環境,即時位觀。:即具體提出不同身份的人居處于不同時位之時,可以盡己所能,以愛敬之心來達到的“孝”行,而“孝”觀念終于因《孝經》中“孝”體現的時位化的特點,擴展為“天之經,地之義”的無所不包的存在,《孝經》中的忠孝關系也因“孝”觀念最終的擴展而愈加明朗和清晰。接下來,筆者將從主體對象為父母的“孝”觀念談起,逐步揭開根植于《孝經》文本中的孝與忠的關系。
一、主體對象為父母的“孝”觀念
今天我們說起“孝”,自然而然會想到“孝”是子女對待父母的行為評價。而諸多文本對“孝”亦有相似的定義。《尚書·酒誥》中有:“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的說法[2];《詩經》有:“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3]《尚書》和《詩經》中的“孝”都被圈定于子女與父母關系之間。《說文解字》云:“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4]《爾雅·釋訓》云:“善事父母為孝。”[5]從下定義的角度來看,“孝”是“善事父母”當沒有什么疑問。在這里,“孝”是一種子女對待父母的行為描述,孝行為的主體對象是父母。同時,“孝”對這種行為描述還包含了評價和判斷——必須“善”事父母,才稱之為“孝”。換言之,在這個“善事父母”的對“孝”的定義中,如果“孝”僅是“事父母”的行為而沒有“善”的對待態度,便不能稱為孝;同理,僅有“善”的對待態度而沒有“事父母”的行為,也不能稱為“孝”。《禮記·祭統》就完整的從“善”和“事”兩方面中詮釋“孝”:“孝者,蓄也。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6]其中“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體現“孝”作為“事父母”行為的一面;“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則體現的是孝作為一種行為,其背后對待父母的愛敬之心自然生發出的“善”的態度(由觀察判斷態度)。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孝的內涵包括了可以于外界直接可見的行為,和需要去觀察才能辨別出的內心的態度。因此,主體對象為父母的孝本質上是心與行的統一:這種定義下的孝強調了子女對根植于直系血緣關系的父母所懷有的愛敬之心,并且憑著愛敬之心對待父母時,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外在表現。簡單來講,對父母的愛敬之心自然而生發出來的一系列行為,在品德上即可被定義為孝。有心無行或是無心有行皆不可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孝。真正的孝體現了文質彬彬。
限定于主體對象是父母的“孝”本身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以《論語》為例,《論語》中有四人向孔子問孝,孔子所作的回答皆不同。孟懿子問孝時,孔子答:“無違”[7]孟武伯問孝時,孔子答曰:“父母唯其疾之憂。”[8]子游問孝時,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9]子夏問孝時,孔子答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孔子對孝的回答不一樣的并不是說“孝”觀念的不確定,而是孔子根據問孝之人的自身情況進行因人而異的回答,來使子女實現自身情況允許下最大程度的孝。孔子對孝的回答雖有不同,但是可看出的是:這四種重點不同的孝依然強調“善”與“事”、心與行的統一。“無違”是孔子要求對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10]對父母從生到死的以禮相待是為人子愛敬父母之心的外化。“父母唯其疾之憂”的回答則更多的體現了“心”的層面,以己之心體貼父母愛己之心,懼怕父母擔憂而對自己身體多加照顧。“色難”和“不敬何以別乎”雖然是行為上的要求,但是這兩種行為更需要真正的有愛敬自己父母的心情才能心甘情愿的做到。若人沒有通過愛敬之心的外化來要求自身,那么“色難”與“敬”是很難做到的。或者即使做到了,也終有露出破綻的時候。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孝的概念(在主體對象是父母時)因其外在表現的多種多樣而得到擴展,而這種擴展雖然依然圍繞主體對象是父母展開,但是,此時“孝”的核心得到了印證——如此多種多樣的表現都可稱之為孝,不在于其外在行為的統一,而在于子女對父母的愛敬之心的同一。由于我們沒有辦法通過非行為或非觀察(觀察也是一種行為)的其他手段來判斷子女是否懷揣愛敬之心,因此與心結合的行為、或是心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行為只得靠精微的細節和外界的觀察來判別是否蘊含著愛敬之心。
二、主體對象多元化下的“孝”觀念
通過上述對“孝”觀念的分析,我們實質上看到了“孝”觀念對主體對象的偏離。雖然“孝”是對生育我們的父母由自然的愛敬父母之心生發出的行為,但是在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為“孝”時,子女的行為是否體現愛敬之心成為主要的判斷標準,而其孝行是否針對的主體對象是父母這一判斷標準則被削弱。當然,這種以判別心本身是否具有愛敬來判斷其行為是否稱之為“孝”也有其局限性。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一個人只能確定自身的心靈狀態,對他人的心靈狀態只能通過觀察或分析才能無限趨近,而如果對于周公和王莽的假設成立,那么我們更無法從對他人的觀察和分析進行正確的心靈狀態的判斷。這雖然使孝的定義和判斷標準得到更加具有向錯誤的方向擴散的可能,但卻是無法避免的。畢竟一切的目的論最終都要從結果去探知與發現——如同我們亦以精微的側面的觀察來評判人子之孝,雖然依然可能會有判斷錯誤的時候,但這已是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方式。
除了《論語》里展現的“孝”觀念的擴散,其他經典涉及到孝主體對象是父母時也有類似的擴散。如《禮記·曲禮上》:“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11]這是以否定的形式來規定人子稱孝時應做到的方面。這種否定式的定義方法導致“孝”在被定義時得到了內容上的擴散。《荀子·大略》中:“曾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悅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12]荀子直接將具備由愛敬之心外化出孝行的孝子歸入道中,將“孝”觀念與道相合。
“孝”的標準和判斷在實際表述中形成的偏離以愛敬之心外化的行為為核心,而依然可將每種不同表現形式的“孝”歸結于“孝”,但是這種擴散和偏離的趨勢很快就以“孝”的主體對象不再單純指向父母而越發顯現。
《禮記·祭義》云:“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親,敢不敬乎?’”[13]這里“孝”的對象即發生前所未有的擴大,不單單僅止于主體“善事父母”——即主體對象為父母的“孝”觀念的層面。雖然曾子強調“孝”的對象擴大是因為身為父母之遺和害怕災及于親,但客觀來講,人子在對象是非父母時應做到的行為判斷已經納入了是否稱之為“孝”的判斷中。孝的主體得到了擴大。但此時,“孝”的核心依然是強調愛敬之心的外化,也仍然存于曾子的表述——對父母的愛敬之心表現于對待非父母對象的行為引發的結果是否會危及雙親。而《中庸》:“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14]這里的孝就已將對象轉移到“人”身上,而不再只局限于主體對象父母了。
三、《孝經》中時位化的“孝”觀念
主體多元化的“孝”觀念打破了主體對象為父母的限定,而在《孝經》中進一步體現了《周易》時位化的特點。《周易》之中影響各爻行為判斷的即是時位。有時哪怕是輕微的時位的不同也會導致截然相反的占辭。最淺顯的例子即是一卦六爻處于相同的卦時,處于不同的爻位會明顯表現出有不同的選擇傾向。而“孝”也受到這種時位化特點的影響。
就于人所居處時位的不同,要做到的“孝”的偏重點也有所不同。如《禮記·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為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15]在這里曾子提到了君子孝,認為君子之孝不能單純的直養。《禮記·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16]從孔子在《坊記》中的這段話也可看出孔子有對待小人之孝與對待君子之孝的區別。
“孝”觀念的時位化特點不僅體現在君子之孝與小人之孝的區別,還體現于《孝經》的“五等之孝”中。《孝經》中的“五等之孝”,將“孝”分為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和庶人之孝:
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17]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18]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19]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 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20]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21]
這里明顯可以看出,《孝經》在五等之孝的描述中,所處之位越高,越在表面與孝的原初觀念“善事父母”相比附加的內容更多。這種類似于職位劃分的“孝”一方面有其歷史原因,《禮記·表記》:“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22]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 “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諸侯之制。”[23]《左傳·桓公二年》:“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24]可見孔子作《孝經》*按陳壁生《孝經學史》第16-21頁,《孝經》是孔子所作當無疑問。時宗法雖已遭破壞,但仍有血緣親疏。
而另一方面,《孝經》將“善事父母”中隱藏的愛敬之心用于不同時位,使得“孝”由事親延伸出無所不包的特性。這意味著無論在任何存在“下上”的關系中甚至不存在“下上”關系的關系中(如朋友)關系中的任何事情,“孝”都可以作為行為好壞的衡量標準。即:《孝經·開宗明義章》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25]此時的孝雖然表面以主體對象為父母出發,以主體對象為父母為終,但實質上“孝”成為了以子女對父母的愛敬之心連接了人居于世間由生到死的一切行為——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因此《孝經》中言“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就是因為《孝經》中的“孝”涵蓋了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而“孝”觀念也因這種無所不包的特性在其內部形成了眾多的層次。《孝經·廣至德章》云:“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26]這里第一個“孝”是已經是主體多元化、時位化的“孝”觀念,而第二個“孝”則是具體而狹義的“善事父母”之孝。《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有云:“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于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各有分。分中委曲,名眾于號,號春大全。曲有名。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是故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27]“孝”觀念的無所不包下設了五等之“名”,而五等之“名”又各順于天而成德道;“孝”觀念在《孝經》“五等之孝”的廣闊性由斯可見。
四、《孝經》文本中觀念擴散化的孝與忠
有了如此廣闊的“孝”觀念,當我們再來看《孝經》中有關忠孝關系的表述時就不會有后世認為《孝經》中蘊含所謂忠孝對等、子事父完全同于臣事君,以至于認為忠孝同一化、政治化了。我們先來看一下《孝經》中表忠孝關系的原文:
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后世矣。
可以說明的是,擴散化了的孝觀念作為一切之根本,既是一切之原因,又是一切之結果。其雖與忠有敬相通,雖“事親孝”可移于“事君忠”但這不意味著“孝”與“忠”的對等和完全轉換,而意味著“孝”無所不包而衍發出“忠”,“忠”被視為“孝”的延伸道德。另一方面,孝的內核,即子女對父母的愛敬之心,如果沒有特定的主體對象和沒有固定的時位限定,那么一個懷揣愛敬之心的人子無論他被安置于哪里、服務于誰都可以完全的勝任而無所障礙,把他放在君臣關系中自然而然的可以做到“忠”的程度。因此《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28]由此,“忠”可以被認作是“孝”的愛敬之心表現在特定于君臣關系時的別名。
但“忠”的另一內核使“忠”與“孝”又有所區別,使得“忠”相對于“孝”有相當的獨立性,這個內核就是義。忠孝之分別主要表現于:“孝”觀念下要求人子在父母行事不正時的諫諍與“忠”觀念下要求臣下在君主行事不正時的諫議是不同的。鄭注:“父子之道天性”為“性,常也。父子相生,天之常道。注“君臣之義”為“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義合耳。三諫不從,待放而去。”[29]而子女諫諍父母時雖也有義的成分——“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30]但由于“愛敬出于天性,自然相因”諫諍的選擇就有所不同。《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31]《禮記·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里,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2]如果諫的對象是父母,那么即使父母最終沒有采納意見也要委身服從,而如果諫諍的對象是君,如果臣三諫之后仍不被采納,那么臣就可以選擇離開。簡言之,“孝”畢竟是血親的延伸,而“忠”終究有義的成份。忠雖是“事君之孝”的別稱,但在“事君之孝”中君臣關系是由義主導的。事父母之孝根于血親,別無選擇,故諫而順之;事君之孝根于義,乃有自主性,是以三諫不從,當舍棄之。從孝到忠也就體現了孝的割恩從義而成乎忠。
五、結論
綜上所述分析,我們可以大致看到忠孝關系在“孝”在《孝經》中占主體地位時的表現。“孝”因其自然屬性在“孝”觀念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擴散為以愛敬之心為內核而無所不包的品德概念,而“忠”則成為“孝”在君臣關系中作用時的別稱。同時,“忠”與“孝”又因形成基礎不同——孝由自然屬性而成,忠則由“義”成又顯現出極大的差別。忠與孝作為兩個獨立而又相關的品德觀念在《孝經》中的關系由斯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