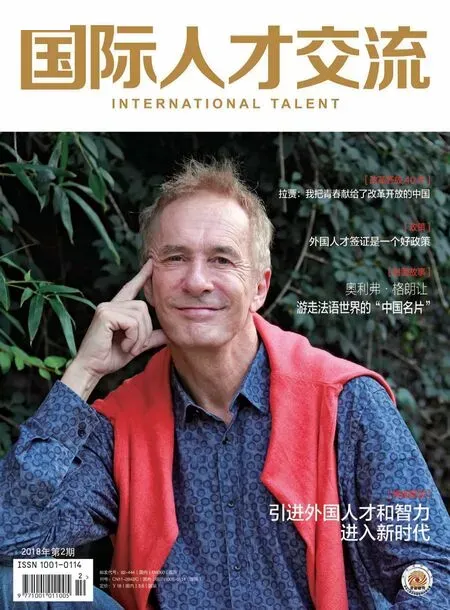黃河與未名:英國院士的中國緣
文/何明璐

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著名的環境流體力學專家艾利斯克·波斯維克(Alistair Borthwick)
當談到北大近年令人印象深刻的變化時,艾利斯克·波斯維克(Alistair Borthwick)開玩笑地說:“校園內建筑的變化太快了!盡管我每年都來,卻仍常有迷路的危險。好在,北大還保留了未名湖。”
這位風趣、隨和的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大名鼎鼎的環境流體力學專家,在二十年前與黃河、與北大結緣,二十年間,在中國的環境問題、環境工程領域的國際交流和人才培養方面都付出了諸多心血,也與中國的學者和學生們結下了深情厚誼。黃河與未名,見證了他同中國的故事。
“我從沒研究過這么長的一條河流”
“1998年,北京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的倪晉仁教授以訪問學者身份來到牛津,當時我負責接待他,”波斯維克教授回憶說,“顯然,中國派來了一位很有才華的學者。”
1982年,26歲的波斯維克取得了環境工程領域的博士學位;此后三十余年間,他的研究興趣涵蓋環境流體力學、洪災風險管理、河岸工程以及海洋可再生能源等多個方向,發表論文130余篇,獲得了多項專利,成果斐然。1998年,倪晉仁到牛津進行學術交流,結識了當時在牛津任教的波斯維克,并向他介紹了黃河的主要環境問題,包括洪災風險、下游斷流等等,激發了波斯維克研究黃河的濃厚興趣。
黃河太特別了。作為中華文明的搖籃,它享有盛譽;可同時它又喜怒無常、洪災頻發。作為僅次于長江的中國第二長河,它攜帶了全球河流泥沙含量的6%,居于世界河流泥沙含量之首;而依賴黃河獲得飲用與生活用水、灌溉、航行的人口又是如此之多,以至其帶來的環境挑戰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都不容忽視。這些都吸引了這位英國河流專家的目光,他笑言:“和黃河相比,英國的河流都太小了——正是這一點讓我對黃河問題有了濃厚的興趣,在那之前,我還從沒研究過這么長的一條河流。”
當時,波斯維克的研究團隊正在建立淺灘流量的量化研究模型,北京大學的研究團隊來了之后,雙方模擬研究了黃河潰堤的情況,又對黃河水量、泥沙量的特征進行了觀察。這些研究,不僅讓波斯維克堅定了對黃河進行深入研究的想法,更讓他與倪晉仁教授結下友誼,也同北京大學因此結緣。此后每年,波斯維克教授都會來到中國、來到北大,對黃河的研究也從最初的水量、泥沙量擴展到了更廣泛的領域。回憶起這些研究的發展歷程,波斯維克感慨頗多。
“起初這些研究遇到過一些困難,”波斯維克說,“問題之一就是可用數據不足,常常出現各研究機構都只掌握一部分數據的情況,就好像醫生只能看到病人的一只胳膊,而不見其他部分。這給我們建立研究全景帶來了一些障礙。”不過,在這十來年間,中國對于相關研究的開放程度逐步提高,研究者們也有機會接觸領域更廣泛、時空上更全面的數據,涉及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數據記錄也讓研究者們能夠用一種量化方式估測河流的“健康狀態”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具體某一因素對于河流整體造成的影響,而這些成果也幫助了中國作出河流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決策。
不僅如此,黃河相關統計數據的逐步開放讓研究者們獲得了更寬廣的視野——不僅從中國的角度看待黃河,更從世界的角度研究黃河。波斯維克提到,隨著對在更長歷史時期——早至15世紀的黃河流量數據的觀察,研究者們十分驚奇地發現,黃河的流量變化甚至與北極震蕩現象(天氣現象,造成北半球出現氣象顛倒,致使北半球的北美洲、歐洲和亞洲地區出現寒冬)也呈現相關性!這讓波斯維克進一步看到了黃河環境問題的重要,也激勵他在這個領域深耕。現在,波斯維克和倪晉仁正開展黃河對于全球性生態平衡影響的研究,在黃河三角洲碳通量(生態系統中通過某一斷面的碳元素總量)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
從最初開展對黃河的研究至今已近20年,波斯維克對黃河的興趣依然不減。這條孕育了中華文明的長河,讓這位優秀的學者與北大、與中國相識、相知、相“戀”。
三校攜手,為“水”而來
波斯維克同中國的緣分起于黃河,卻并未局限于黃河,也并未止步于北京大學——多年以來,波斯維克還在中國災害帶狀分布情況檢測、污水處理的生物降解技術、納米技術等方面與倪晉仁展開合作;2010年,在倪晉仁的倡議和波斯維克的推動下,新加坡政府、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聯合成立了“SPORE”(Singapore-Peking-Oxford Research and Enterprise)項目,促進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在研究和人才培養兩方面的交流發展。
SPORE涉及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新加坡教育發展董事會出資約6000萬美元投入這項以水生態環境為核心的研究項目;具體來說,該項目基于兩位教授多年來對黃河生態的研究,又涉及水凈化系統、城市污水管理、中國河道修復、水資源合理分配等方面,波斯維克所在的牛津大學在工程和化學領域為該項目提供智力支持。三所名校的優秀學者和研究人員,為解決世界性水資源稀缺、水環境可持續發展共同努力,并取得了多項研究專利。
除了研究之外,SPORE還關注人才聯合培養。來自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的碩士生,同時接受新加坡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和牛津大學三所學校教授的指導,并在畢業時獲得本校和其他兩所學校的碩士學位證書。談到博士生的培養,波斯維克舉例說:“一名博士生主要在牛津開展研究,同時接受我、理查德·達頓教授、北大的倪教授和新加坡的李教授的指導;在研究期間,這名學生也多次到北京大學訪學。”
作為該項目牛津大學的聯絡人和推動者,波斯維克認為這種交流合作對于三所學校都有重要的意義。“三所學校不僅有了分享研究經驗的平臺和機會,也受益于彼此的優秀學者和有才華的學生,更建立了促進友誼的網絡。”波斯維克表示,“這樣的國際交流通過友誼發揮作用——從我本人的經歷看,友誼堅固,諸事大順。”
懷抱這種信念,這位國際交流促進者,帶著對北大的欣賞,推動了北大與多所名校結下良緣——在他離開牛津大學、先后任職愛爾蘭考克大學土木環境工程系主任、愛丁堡大學應用流體力學系主任的過程中,也促成了北大與兩校的合作交流。
傳道授業,桃李滿天下
“2016年的春節,波斯維克請組里所有的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到一家中國餐館過年。那天也正好是他60歲的生日。餐館的桌子鋪著大紅的桌布,昏黃的燈光照在上面。大大小小的盤子里有宮保雞丁、紅燒肉等菜品。恍惚間,我像是坐在了家中擺著年夜飯的桌子旁,波斯維克則是家里的長輩。他用睿智而慈愛的眼光看著我們。待大家都安靜下來,他舉起酒杯說:‘Kan-Pei!’(干杯!)”畢業于北大、2015年到愛丁堡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現已任職于武漢大學的岳遙回憶起這位慈愛師者在異國他鄉給予的關照,流露出滿懷的感動和幸福。波斯維克的中國學生們提起他,都對他的親切、友善和隨和印象深刻;而他在學術問題上的一絲不茍、認真負責,也讓他們受益良多。

博斯維克教授(中)與倪晉仁教授(右)討論學術問題
近二十年來,每年波斯維克教授都會來到北大,除了會議、報告、考察研究工作之外,他常與學生一對一單獨討論學術科研的進展,在指導學生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現在任職于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許楠回憶說,因為波斯維克每次討論起學術問題來都追根究底,常常要討論整整一個下午,所以每次討論之前,學生都如同臨考一般。除此而外,他還指導學生們的英文論文,減少語言問題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因為工作日程太滿,他甚至經常熬夜為學生們看論文。作為師者,他不僅授業解惑,更傳遞給了學生們為師者之“道”。
說起自己的中國學生,波斯維克并不吝于表達對他們的欣賞。“他們勤奮、聰明、肯鉆研,都有全面的素質。和他們相處令人很愉快。”二十年來,這些年輕的研究者都在成長,有的離開“象牙塔”、走向商業領域,成為優秀的工程師;而更多的人現在已成為專家、教授,甚至中國高校的系主任。這些學生的成就,讓看重教育的波斯維克教授十分欣慰。
“我見證了很有才華的學生的成長。我認為,年長的學者正應該擔負這樣一種角色,在下一代研究者事業起步的時候幫助他們。好的教學,能夠激勵頂尖學生成為下一代的研究者和教育者,這是一種良性的循環。我在念本科的時候,接受了一位當時已經70多歲卻仍熱情洋溢的教授的指導,這讓我認定流體力學是我的未來,并從未后悔過這一選擇。我的教學經驗是:要充滿熱情,為學生提供支持,用‘蘇格拉底式’的辯駁式提問方法與學生交流。”
培養更多思考者
二十年來,波斯維克教授對黃河問題的理解日益深入,見證了北大的發展和無數學生的成長,更見證了一個更加開放、國際交流更加頻繁的中國。盡管中國環境問題錯綜復雜,波斯維克仍對未來充滿信心——這些年來,研究者可以接觸到更完備的數據,應對污染挑戰的技術不斷進步,更重要的是,人們正逐漸培養起保護環境的意識。波斯維克教授認為,未來解決環境問題的途徑將是“混合”式的,需要社會科學、工程、基礎學科、經濟學的共同努力,也需要針對污染管控更強的全局意識和更有效的統籌管理。而在此過程中,同時承擔著“科研”和“教育”兩重任務的大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是,對于大學里的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而言,“科研”和“教學”之間存在的張力十分明顯;科研壓力很有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教學的興趣和投入。談到未來如何緩和這種矛盾,達到兩者間健康的“平衡”,波斯維克教授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未來,也許我們需要一些與教學有關的評價方式,從教學角度對研究者予以鼓勵。
訪談結束前,回顧自己四十年的治學經歷,這位跨越大洋、行于河邊,卻一直心系教育、從未離開過“象牙塔”的科學家總結道:“學生和教師之間的相互激勵很有益處;而培養學生成為具有自信心、獨立性、批判性思維的思考者,對于一個領域的未來發展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