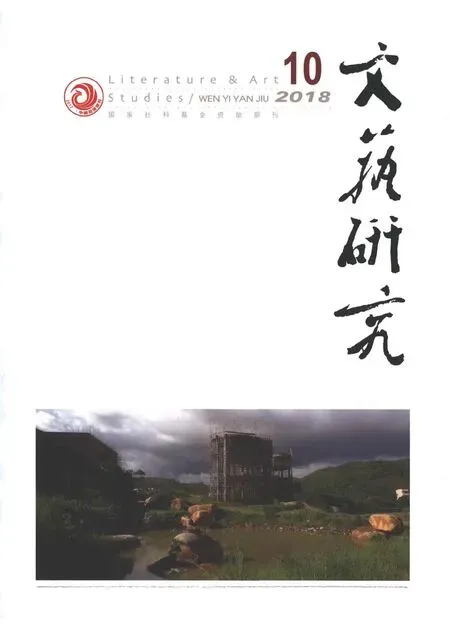袁枚的詠史詩創作與性情人生
馬 昕
袁枚作為清代中期杰出的詩壇領袖,既有大量詩歌作品傳世,又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性靈”理論,主張抒發率真性情,堅持書寫平凡生活。但在其《小倉山房詩集》所收的4461首詩中卻有236首屬于詠史題材,占比約為5.3%。這個比例比同屬性靈詩派而又是著名史學家的趙翼還要高一點①,足見袁枚對詠史詩有相當濃厚的興趣。但問題是,詠史題材與袁枚的整體詩學追求構成一定的“矛盾性”,這是其他題材所不具備的。一方面,寫作詠史詩要立足于一定的史學修養,素材也源于書本,難免要以典故敷衍成篇,這種“以學問為詩”的做法容易禁錮人之性情,也正是袁枚所一再反對的。另一方面,詠史詩所描寫的歷史事件多屬帝王將相主題,又與袁枚的性靈詩學所崇尚的對平凡生活的書寫習性相差太遠。換句話說,詠史題材最不應該是性靈派詩人的專長,在袁枚身上卻恰恰相反,這當然值得我們關注。筆者認為,必須將袁枚一生所作的二百多首詠史詩,與其瀟灑率性的人生經歷對應起來,才能體察其內在聯系,看到其詠史詩如何突破學問和書本的隔膜與阻礙,直達詩人的性情內核。
袁枚的一生,經歷了縱橫南北的漫游、在翰林院的學習、基層官場的歷練以及在隨園的隱居生活,生活狀態并不相同,其詠史詩的創作風格也有所變化。在34—36歲這三年,也就是初次歸隱期間,袁枚只寫了一首詠史詩,是其詠史詩創作歷程中的一段空白。在這段空白期的前與后,袁枚的人生遭遇和詠史詩創作風格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因此,我們以34—36歲初次歸隱為界,將其詠史詩創作歷程分為前、后兩期,分別討論。
一、袁枚詠史詩創作的前半期(21—33歲)
(一)漫游南北與流落京城時期
《小倉山房詩集》的收詩起點是乾隆元年(1736),袁枚21歲。這年正月,他受父命,到廣西桂林投奔當時身處金幕下的叔父袁鴻,希望借金之力謀得進身之階。這是袁枚第一次出門遠行,人生閱歷得到極大擴充。他路經浙江、江西、湖南等省,途中參訪了不少歷史遺跡,寫下10首詠史詩,集中表現了青年才子對功名的期許。例如他行經浙江桐廬嚴子陵釣臺時,寫下《釣臺》一詩,詩中充盈著“為念故人重,轉覺天子輕”②的豪氣;又在《書子陵祠堂》一詩中寫下“何況赤伏符,可無王者師”③二句,似乎在想象著自己也能有睥睨帝王的能力。可見,袁枚從嚴子陵的事跡中,擷取的并非隱士的恬淡與孤獨,而是能與君王同榻而眠的優越感,甚至是可為帝王師的榮遇,我們從中能感受到一個年輕才俊那顆正在蓬勃躍動的雄心。到長沙,他參觀孫策廟,作《吳桓王廟》一詩④,只寫孫策的英雄意氣,卻無一字提及其英年早逝的悲劇結局。到賈誼祠,又作一首《長沙謁賈誼祠》。他寫賈誼,重點不是悲其“不遇”而是羨其“懷才”,用“屈子堪同調,相如敢比肩”⑤這樣的話來追捧賈誼。這些都可看作少年才子的心性表達。
袁枚在這年九月試于保和殿,卻不幸落選,不得不暫滯京城,狼狽地過了一年多。這段時光里,他只寫出兩首詠史詩,都與京城附近的遺跡有關。其中一首是《黃金臺》,袁枚并不依尋常意見去歌頌燕昭王之禮賢下士,而是作起翻案文章。他說:“回問當年豪舉心,果然值得黃金否?”甚至質疑燕昭王“不報仇時臺不筑”⑦。這樣的翻案立場,很難不被人懷疑是一種“酸葡萄心理”。
總結袁枚在這一時期的經歷與詠史詩作品,可以發現:袁枚的性情變化幾乎纖悉無遺地表露在其詠史作品中。對英雄先輩的崇拜,對功名之念的執著,對書生價值的自信,都是他應試之前的正常心態;可一旦首戰失利,自暴自棄與憤世嫉俗的思想就以詠史翻案的方式暴露出來,也使我們看到這位青年才子脆弱和敏感的一面。不過所幸,他這段低谷期并不是很久。乾隆三年(1738),袁枚中進士,以庶吉士身份開始了三年的翰林院生活。他的詠史詩創作也出現了新的主題與風格。
(二)翰林院時期
袁枚在翰林院師從史貽直學習滿文,卻并不專心,而是對史學議論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常與友人蔣和寧談史論古,“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堲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幾叫呼,以故益相得”(《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⑧。“國家治亂、人才臧否”,可作清談之資,也可為詠史詩提供素材,但他對史學的興趣顯然是膚淺的,并不能像趙翼那樣埋首史籍、沉潛考據,而不過是一副坐而論道式的清談做派而已。他在此時所寫的《意有所得輒書數句》之二中說:“形為萬卷累,亦非達士懷。不聞古神仙,識字居蓬萊。書堆三萬卷,轉使我意乖。束之良可惜,讀之不能該。吾欲法祖龍,一舉為灰埃。終日仰屋梁,不樂胡為哉!”⑨袁枚將萬卷書視作束縛,寧愿一把火燒掉。這種束書不觀的習慣發展成一種游談的氣質,使他在乾隆六年(1741)集中寫出了16首頗見新意的詠史詩。這些詩都是七言絕句,也都寫歷史上的女性人物,在詩集中連續編排,應是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的。女性主題恰好很容易寫出新意,而七言絕句的體裁也適合寫出杜牧式的翻案議論。只不過不同詩篇的“新意”中包含著思想認識上的矛盾。
矛盾的一頭是:袁枚對這些女性的悲劇命運報以深沉的同情,認為她們不過是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只能受男性權力的擺布,一切對她們的批評和責難都過于苛刻。比如《玉環》之一就說:“緣何四海風塵日,錯怪楊家善女人。”⑩袁枚認為楊玉環本是個單純、善良的女子,為何要將國家動亂歸罪于她呢?《西施》之一又云:“吳王亡國為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詩中細致刻畫了西施的內心矛盾:她一方面是越人,為越國的復興承擔重大使命;另一方面又是女人,面對夫差這位對自己寵愛備至的男人,又懷有深深的負罪感。這樣的矛盾與撕裂,是她不能改變的宿命。總之,玉環嫁給玄宗,西施進入吳宮,都不能自己決定命運,顯然居于被動地位。因此,對她們二人報以同情,都在情理之中。但像妲己、褒姒、張麗華這樣的女子,歷來都是一副純粹的負面形象。袁枚《張麗華》之二卻說:“可憐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傳里人。”?認為褒姒、妲己之流能受到圣主的陶冶而轉變成為賢妃,其實暴露了他思想中的某種“局限”:看似要為女子鳴不平,但仍然以將女子置于弱勢地位的妥協方式來為這份同情心尋求依據。如果袁枚一直保持這種態度,我們不過說他終究還是個俗人。問題是,他的思想中還存在另一面。
矛盾的另一頭就是:袁枚還時常賦予女人以強勢地位,讓她們在男權體系中展現女人的力量,甚至具有超越男權的資格。例如《上官婉兒》云:“論定詩人兩首詩,簪花人作大宗師。至今頭白衡文者,若個聰明似女兒?”?后世對上官婉兒的功過是非充滿爭議,或譏其淫亂宮闈,或批其干亂朝政。但袁枚只推重她的文才,認為即便今日執掌文衡之輩也難以與其比肩。這番議論未必高明,但至少顯示出袁枚的立論勇氣。而且,袁枚對女性地位的抬升,不僅表現為贊美,還可以表現在批評當中。例如《潘妃》云:“玉釵生自劈《楞伽》,尼子歸來步步花。爭不荊條加苦手,教人好好作官家。”?潘妃對南齊東昏侯蕭寶卷的荒淫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袁枚卻希望她能“荊條加苦手”,教導蕭寶卷做個好皇帝。這當然高估了潘妃的情操和能力,但正是這份高估暴露出袁枚對女性承擔社會責任的較高期待。
學術界研究袁枚的女性觀,多將乾隆六年所作的這批詠史詩視作重要依據?,但都忽略了以上所揭示的這重矛盾。袁枚對這些女子的評價中隱藏著他對女性權力自相矛盾的兩種認識。但有一點一以貫之:他同情玉環、西施的宿命,為褒姒、妲己、張麗華開脫,是因為前人總在批評她們;他贊美上官婉兒對文學的貢獻,是因為前人總在夸大她那些宮闈隱私;他批評潘妃不勸諫君王,是因為前人根本未寄希望于她會為國家帶來積極影響。如果因為袁枚對幾位女性人物表達了同情或贊美,就說他對女性的尊重是從這一時期已注定,那顯然是忘記了他在這批作品中的其他幾首詩里也暗示了對女性的貶低。這些詠史詩中并沒有袁枚一以貫之的女性觀,而只有一以貫之的翻案手法而已。翻案技巧無疑能讓年輕的詩人發泄他對歷史議論的狂熱,顯示出他在清談中高人一籌的所謂“識見”。
(三)南京候任時期
袁枚在翰林院學習滿文并不用心,所以散館時被授以末等,只能出放縣令。失落至極的他灰溜溜來到南京,準備接受任命。在此期間,他至少寫了24首詠史詩,但《小倉山房詩集》只保留了其中5首。不過,袁枚早年編刻了一部《雙柳軒詩集》,暴露了他在此階段更加真實的創作情況。陳正宏考證,《雙柳軒詩集》所收245首詩,創作于乾隆七年至十年(1742—1745)間。中年歸隱后,袁枚自悔少作,將書板焚毀,但仍有110首詩出現在《小倉山房詩集》中?。就詠史詩而言,《雙柳軒詩集》保存了袁枚從北京回南京途中以及在南京候命期間所作的22首詠史詩,其中竟有19首沒能編入《小倉山房詩集》,而剩下3首也全都被徹底重寫。這樣嚴重的刪改簡直是專門針對詠史詩的,因為其刪和改的比例都大大超過其他題材類型的作品。這使我們懷疑,袁枚晚年編定詩集時對這一階段的詠史作品有所避忌。那么,他在擔心什么呢?
研究的突破口是遭到嚴重篡改的那三首詩,其中有《金陵懷古》二首?,在收入《小倉山房詩集》時將詩題改為《抵金陵》?。第一首被完全重寫,第二首也只有頷聯得以保留,修改幅度之大令人咋舌。修改之后,“山頭日已斜”“金城淚落”一類氣氛陰郁的景物描寫都被刪掉;“傷心世世帝王家”變成“一片長江六帝家”,“廷尉山頭日已斜”變成“輦轂規模大道斜”,傷心的情緒被替換為壯闊、恢弘的氣象。原作末句以庾信流落異國自比,在改作中卻替換成“手揮羽扇問年華”,儼然一副釋然與淡定的模樣。可見,原作與改作的最大區別是情感基調與詩人形象的變化,詩人從一副落魄的模樣化身為“手揮羽扇”坐看滄桑變化的智者形象。看來,袁枚并不想讓讀者知道他被外放之后這段時間里的真實心境,擔心那會使自己苦心塑造的孤傲自賞的才子形象和淡泊名利的隱士形象大打折扣。
再將那些被刪的作品與收入《小倉山房詩集》的同題作品作比較,更能看清袁枚的這層擔憂。比如《雙柳軒詩集》中有《孫策》一詩,《小倉山房詩集》未見。該詩專寫孫策英年早逝的悲劇結局,與上文所述《吳桓王廟》的情緒基調恰成鮮明對照。再比如袁枚還刪掉一首題為《昭君》的七絕,《小倉山房詩集》卻保留了袁枚在即將抵達南京時所作的《明妃曲》。《昭君》云:“君王不愛傾城色,賤妾無心怨畫工。”?這個王昭君完全是一副自暴自棄的樣子,不被君王寵愛也就罷了,竟然對畫工都無心怨恨。而《明妃曲》卻寫得慷慨激昂,末二句說:“寄言侍寢昭陽者:同報君恩若個多?”明妃不但不自傷,反而以能報君恩為無上榮耀。這樣充滿“正能量”的作品最終被晚年的袁枚精心保留下來。
在南京候任的這段時間,袁枚的內心世界里籠罩著一生中最陰郁的一片愁云,這使他滿腹牢騷、滿腔怨怒,寫下了一些任性而又輕佻的作品。這也可能是他最不想回首的一段歲月,所以他后來一辭官,就開始自悔少作了。
(四)任職江寧時期
乾隆七年至九年間,袁枚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陽等地擔任知縣。乾隆十年春,又奉命調任江寧知縣。這時他已經適應官場規則,甚至在沭陽任上還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政績,儼然一個標準的循吏。《小倉山房詩集》卷四、卷五有21首詠史詩,都寫于袁枚在江寧任職期間。詩中的價值觀逐漸向官場所能夠接受的方向靠攏,也就是對“臣則”極盡推崇,甚至出現一些過于諂媚的表達,都有點讓人難以看清這到底是詩人的真心還是假意了。
例如他在乾隆十二年(1747)寫了《詠史》6首,都是五言古體?。第一首寫漢武帝和汲黯。袁枚先用八句鋪陳武帝的文治武功,接下來竟以近乎咒罵的方式指責汲黯是“老匹夫”。汲黯曾認為當縣令是一件恥辱的事,還感嘆自己過去的部下都如“積薪”一般后來居上。袁枚對此表示不滿,甚至說:“當時竟殺汝,如鼠投沸湯。”漢武帝對汲黯異常尊重,甚至當汲黯覲見時,皇帝定會衣冠整齊,“不冠不見”。袁枚卻說:“不冠而見之,于帝更何傷。”我們聯想一下袁枚在幾年前剛剛被外放縣令時是何等的牢騷,已經做了六年縣令的他,不但不對汲黯以做縣令為恥的說法表示出同感,反而橫加指責。也不知袁枚這種對皇權的一味維護,是否發自內心?
第二首寫東漢初年的桓譚。桓譚擅長彈琴,頗受光武帝劉秀欣賞。但他所演奏的琴樂多是新曲,近于“鄭聲”。宋宏對此非常不滿,便勸說光武帝罷免了桓譚的官職。沒過多久,桓譚又因為勸諫劉秀勿信讖緯而被貶為六安郡丞。這兩件事,桓譚先是過佞,有如優伶;后是過直,有如莽夫,都違反了臣則。最終,袁枚贊成宋宏那樣“自重立臣則”。他雖然批評桓譚彈琴近乎優伶,卻又為劉秀開脫,說:“君王愛泛聲,一彈奚足責。”單從這兩句詩來看,袁枚骨子里也夠“佞”了。
其他幾首大致也是類似的主題,都蘊含著對臣則的鼓吹和對君權的逢迎。我們不禁會懷疑:這還是那個十年前高吟“為念故人重,轉覺天子輕”的袁枚嗎?不過,再看他在此階段寫的《嚴助》?,就發現袁枚內心深處的牢騷終究還是掩藏不住。這首詩將張湯小人得志后的丑態生動描繪出來,儼然就是一幅諷刺官場生態的漫畫。看來,袁枚對臣則的鼓吹,多半也不是真話,而很可能是長久壓抑之下的一種自我開解;也可能是反話正說,跟后人開了個冷幽默的玩笑。
乾隆十二年,尹繼善舉薦袁枚升任高郵知州,卻被吏部阻撓。袁枚已經在知縣任上苦守七年,卻被這件事激怒,決定辭官歸隱。次年冬,他來到隨園,開始隱居。但時間不長,由于經濟日漸窘迫,入仕的想法再次萌生,他又走上入京的路途。
二、袁枚詠史詩創作的后半期(37—82歲)
(一)二次出仕時期
乾隆十七年(1752)正月,袁枚離開隱居了三年的隨園,北上入都。他本以為還能在南京做地方官,這樣就能做官、歸隱兩不誤,沒想到消息傳來,卻是命他去陜西上任。這一年里,他先是在二月入京候命,三月就離京赴陜,五月到達西安,又在西安周邊游覽一圈。可是官還沒做幾天,就在這年的九月,父親的亡訊傳來,袁枚只能南歸守孝。所以這所謂的二次出仕,多半時間都在路上,說是出仕,不如說是游覽。而他所游覽的地方,主要是歷史遺跡異常豐富的關中地區,少不了登臨懷古,詠史詩自然就沒少寫。《小倉山房詩集》收錄了他在這期間的46首詠史詩,是袁枚詠史詩創作最為鼎盛的一次高潮。這些詠史詩展現出兩個新特點:一是以帝王主題集中表現的“英雄氣”,二是批判性的回歸。
袁枚從南京入都的路上經過了漢高祖歌風臺、周世宗慶陵、光武帝原陵、秦始皇陵、武后乾陵和唐太宗昭陵,這些帝王都可謂雄主。袁枚在這些地方所寫的詠史詩里,再次澎湃起他在少年時代有過的英雄氣。只不過,將帝王寫成英雄人物,有不同的側重點。有人專寫帝王的文治武功、煊赫業績,但這樣難免千人一面。袁枚的關注點很獨特,多寫鐵漢柔情,把帝王寫出了風流才子的味道。比如寫歌風臺,就最能寫出劉邦率真的一幕。因為這是一代開國帝王衣錦還鄉、高唱《大風》的地方,威儀赫赫的君王變成了一位可愛的醉漢。所以袁枚在《歌風臺》二首中專寫他的醉態,說:“有情果是真天子,無賴依然舊酒徒。”“千秋萬歲風云在,似此還鄉信丈夫。”?
剛盛贊過劉邦沒幾個月,詩人又來到光武帝原陵,這時他卻說:“人道蕭王遜高祖,我道蕭王較英武。”認為與劉邦相比,劉秀更像個英雄。因為“未必中興輸草創,生來天性勝高皇”,贊劉秀“天性”更好。比如“掃除四海凈風沙,遂得初心陰麗華”,他取得天下之后,對陰麗華這位糟糠之妻初心不改,可見是個有情人;不像劉邦,先是辜負呂雉,后是保護不了戚夫人使其受虐而死。又比如“一時馮鄧皆師友,殊勝爭功半鷹狗”(《光武原陵》)?,為劉秀立下汗馬功勞的功臣馮異和鄧禹,最終都和劉秀保持亦師亦友的關系,得以善終;不像劉邦,勝利之后就開始屠戮功臣。總而言之,袁枚對“英雄”的定義,并不是看那些外在的功過成敗,而是特別看重人的心性,看他是不是一個有真情、有血性的男子漢。從中我們發現,此時的袁枚突然褪去了前幾年那副令人作嘔的官僚氣質。雖是稱頌君王圣德,卻多從真情熱血著眼。如果再對帝王做些批判,那么袁枚就真是和官僚做派漸行漸遠了。下面就來說一說這一時期袁枚詠史詩批判性的回歸。
上文提到過,袁枚在南京候任時期寫過一首《明妃曲》和一首《昭君》,前詩說昭君自表有功漢室,后詩則說昭君自怨自艾甚至無心怨恨畫工,無論表功還是自傷,都處于心理上的弱勢地位,也都沒有對君王的昏庸行為展開批評。但袁枚在陜西時又寫了一首《昭君》,詩云:“陰山月落夜啼烏,放下琵琶影更孤。知道君王終遣妾,將軍不賜賜匈奴。”?此詩假借昭君口吻,說漢元帝既然不能寵幸自己,為何不將自己賞賜給將軍而要便宜匈奴呢?實則批評元帝對敵國的軟弱立場。袁枚此時還寫了《馬嵬》四首,第二首云:“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袁枚在翰林院期間寫了兩首《玉環》詩,主要是為楊玉環開脫,但這首詩卻認為,與李、楊的愛情悲劇相比,普通百姓的離別苦難要更加深重,直指玄宗誤國。《昭君》《馬嵬》二詩都對古代君主發出責難,這與他在江寧任職時對臣則的宣揚構成鮮明對比。
(二)隨園隱居時期
袁枚37歲時經歷了短暫的二次出仕,旋即因為南歸丁憂而作罷,此后開始了長達四十余年的歸隱生活。他在43歲這年,一口氣創作了13首七絕詠史詩。詩人寫這些詩的時候,并不處于外出壯游的狀態,所以都是書齋寫作。雖然缺少江山之助,卻并不意味著這些詩缺少靈機,反而在詩酒田園的生活狀態下,英雄氣質與批判精神都得到進一步發揚。在此之前,袁枚的性靈詩學理論已見雛形?。再看這13首詠史詩,多寫古人性靈之事,恰是袁枚性靈思想的縮影。
例如《朱買臣》云:“采薪歌罷雪花飄,五十登朝氣轉豪。殺得張湯刀筆吏,一行功已敵蕭曹。”?此詩寫朱買臣為給朋友嚴助報仇,不惜犧牲性命,也要害死張湯。《張禹》云:“羽衛傳呼謁太師,九重請訓萬人知。先生開口君王拜,床上深深托女兒。”?此詩寫張禹為能經常見到女兒,竟然請皇帝將女婿調任到離京城更近的地方。《陶弘景》云:“樓上三層道氣濃,永明求祿枉匆匆。先生綠鬢方瞳意,可在烏紗骨相中?”?此詩寫陶弘景雖享無上恩寵,卻仍堅持歸隱山中。這些都是七言絕句,篇幅有限,便只寫他們一生中最見性情的事跡,正體現出袁枚對真情熱血的青睞與推崇。
(三)晚年時期
乾隆四十三年(1778),袁枚63歲始得一子,自此之后重新開始外出漫游。次年春,攜幼子回杭州故里游覽。四十七年(1782),約詩弟子劉霞裳同游天臺、雁宕。四十九年(1784)又作遠游,南下兩粵。袁枚在這三次出游中,尋訪了不少名勝古跡,共寫下四十余首詠史詩。隨著年齡的增長,詩中的熱血逐漸衰歇,但真情并未泯滅。隨著袁枚閱歷日豐,對世事看得越來越透,熱血戰斗的激情轉變為冷靜反思的力量,從批判別人轉變為批判自己,這也使其詠史詩的思想內容老而彌醇。
上文已述,袁枚在21歲去往桂林的路上曾路過嚴陵釣臺,對嚴子陵表達了少年人常有的歆羨與仰慕。但在乾隆四十七年他67歲時,又一次來到嚴陵釣臺,寫下《重登釣臺》和《再題子陵廟》三首,卻表達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觀。《再題子陵廟》之二云:“未必無心助文叔,巢由兩個誤狂奴。”袁枚認為嚴子陵本來有意出仕輔佐劉秀,卻為巢父、許由所“誤”,看來他對嚴子陵歸隱的抉擇已經不以為然,與之前迥然有別。如將此認定為“性靈派詩人一大慣技”?,恐怕會大大誤解隨園老人的深意。其實所謂“誤”,在袁枚早有所感。《隨園詩話》卷九云:“鄂公拈香清涼山,過隨園門外,指示人曰:‘風景殊佳,恐此中人,必為山林所誤。’有告余者。余不解所謂。后見宋人《題呂仙》一絕曰:‘覓官千里赴神京,得遇鐘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誤先生。’方悟鄂公‘誤’字之意。”?袁枚對自己是否真為山林所誤,是有過反思與省察的,并非一味以歸隱高節自我標榜。他對隱士行為的反思,實際也是對自我人生的反思。他在自己年逾花甲之時,去推翻這樣一個曾帶給他最多榮耀的身份,該是何等艱難。但他不但做到了,還做得很絕。再看《再題子陵廟》之三:“牛牢高獲俱同隱,只有斯人事獨彰。惹得鄴侯還艷羨,也思一枕共君王。”?牛牢和高獲跟嚴子陵一樣,都是劉秀的舊友,也都在劉秀取得天下之后歸隱,但只有嚴子陵獨享盛名。照此推理下去,嚴子陵的成名實則包含多種偶然因素。《重登釣臺》又說嚴子陵是“圣世辭官易得名”?,這也完全可用來說袁枚自己。他對自己之所以能夠成名,看來也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并沒有首先歸因于自己的才情和智慧。
到嘉慶二年(1797),袁枚82歲,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個年頭。他的最后一首詠史詩是《讀孔子世家》,詩云:“尼山道冠千秋處,妙在平生不著書。”?詩人認為孔子的偉大,恰在于“述而不作”。這對于已經留下四千多首詩和幾十部著作而且還常常憂慮著述湮沒不存的袁枚來說,不啻為生命最后的自我反思。
三、袁枚詠史詩的性情追求
本文開篇提出性靈詩學與詠史題材的兩點“矛盾”:一是抒寫性情、慎用典故的主張,與詠史題材立足史學、“以學問為詩”并且難免要使用典故的特征相抵牾;二是對平凡生活的關注,與詠史題材常見的帝王將相主題相去甚遠。那么,袁枚大量創作詠史詩的行為,是否對他的性情抒發構成障礙,又是否與其性靈理論形成真正的矛盾呢?筆者持否定態度。
首先,雖然袁枚在基本立場上反對以學問填詩和在詩中堆砌典故,但并未將學問、典故與性情抒寫完全對立起來。總體來看,他的立場是折衷而開放的,所以,他一邊說詩歌“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一邊又說“萬卷山積,一篇吟成”,“曰‘不關學’,終非正聲”?。關于這一矛盾,袁枚解釋道:“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圣《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發,如拆襪線,句句加注,是將詩當考據作矣。”?可見,袁枚不是在詩中排斥一切學問,而是認為詩中不應注入與詩情、詩性嚴重不合的考據之學;他對典故也沒有一味反對,而是反對典故太生和太多,給讀者造成閱讀隔膜,不利于性情的傳達。如像李商隱那樣,既可運用典故,又能驅使才情,豈不兩全其美?
袁枚曾經頗為自得地介紹自己創作詠史詩的經驗:“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他在作詠史詩前遍搜典籍,當然是限于既有閱讀量的不足以及過往閱讀記憶的缺失,才要尋求書本的幫助,獲取更多創作素材,但卻不把書本知識直接化為典故填入詩中,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詠史詩具有特別的自信,這份自信或許正源于他認為自己的詠史詩是富于性情與靈機的。袁枚確實有一些詠史詩不用典故,單憑詩人自身注入的情感取勝。比如他21歲出發去桂林之前所寫的《錢唐江懷古》:“江上錢王舊跡多,我來重唱《百年歌》。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五代十國時期的吳越王錢镠是顯赫一時的江南霸主,看到錢塘江潮洶涌而來,竟命三千弓弩手向涌來的潮水萬箭齊發。這固然是一種英雄氣概,但袁枚卻奉勸錢镠不必怒射江潮,而應將矛頭對準真正的敵人——那個在汴梁建都稱帝、讓錢镠也不得不俯首稱臣的朱溫。這首詩雖有典故,卻不依賴典故,單憑他這副臧否人物、指點江山的派頭,青年才子胸中那股昂揚奮發之氣就已躍然紙上。
在袁枚的詠史詩中,典故常能形成絕好的隱喻,只要典故不生僻,就能保證詩人的性情既順暢又不失雋永地表達出來。例如袁枚在參加博學宏詞試途中,經過河南開封,想到這是戰國時期魏國的都城,就寫了一首《大梁吊信陵君》。這首七言歌行一共32句,袁枚先用大量筆墨書寫信陵君竊符救趙之始末,末尾卻一筆宕開,冷冷拋出這樣兩句:“張耳滅秦封王聲赫赫,原是郎君門下客。”?張耳在秦末亂世中重建了趙國,后來又助劉滅項,被封為常山王。這樣一位聲名赫赫的人物,其實早年也只是信陵君門下一個普通的食客而已。這類底層人物逆襲成功的案例,最能搔到袁枚當時的癢處,所以他對信陵君的歌頌雖然長達二百多字,卻根本不像這兩句才真正道出詩人的心里話。可以說,袁枚正是通過這個典故,使我們了解到他當時羞于明言卻又不吐不快的真實心境。總而言之,在詠史詩中,典故不一定是性情的敵人。
其次,帝王將相主題與袁枚的性情抒發也不形成真正的矛盾,因為袁枚掌握到了調節矛盾的良方。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歷史記述以帝王將相的事跡為主,后人對他們的評價雖然也會出現個別分歧,但總體來說史書記載俱在,以主流的倫理觀念和政治立場評價古人,往往會得出趨同的看法,進而形成寫作套路。從積極角度講,這些詠史套路反映了古人的“集體無意識”,其中的思想代表了群體的思想,其中的情感也屬于群體的情感,當然有助于我們研究古人的思想史和觀念史。但袁枚所建立的性靈詩學恰恰不能容忍這種詩人主體性與詩歌個性的退卻。袁枚認為詩中不能沒有平凡生活的真性情,實際是說詩中不能沒有一個“我”。而他偏偏又作了那么多詠史詩,歌詠對象也確實都是些帝王將相,那么他將如何避免詩人主體性的消失呢?筆者發現,他至少有兩種辦法。
第一,將帝王將相的政治運作和權力游戲“平凡化”“生活化”。袁枚只做過最基層的地方官,后來又長期在野,因此和權力中心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使他論及帝王將相時,可以在士大夫群體意識之外融入平凡生活的成分,也就是以一介布衣的平凡之心看待帝王將相的內心世界,甚至重構其行為邏輯。比如上文談到他為二次出仕而游歷中原、關中,途中寫了很多帝王主題的作品。當他歌詠劉邦時,發現開國雄主竟也有卸下面具的時候。當我們想象到劉邦那副臨風高歌的醉態,才猛然發現,原來身為帝王,也有酒后的放縱,也有欲訴的衷腸,也有一時乍現的溫情,也有難以排遣的寂寞。而當袁枚將劉邦和劉秀作比較時,再度放棄了傳統的政治標準,而是特別看重劉秀對妻子與戰友的溫情。再比如袁枚晚年所作的《讀淮陰侯傳》:“滅楚身提百萬師,知公含笑了無奇。英雄第一開心事,撒手千金報德時。”?袁枚認為,即便是親率百萬雄師亡項滅楚的功績,對韓信來說,都不過置之一笑而已;真能令韓信快意之事,是他功成之后終于能以千金報答漂母。以帝王將相的政治邏輯來看,“滅楚身提百萬師”才是韓信留給歷史的深刻印跡,但一個平凡小民,卻更容易被“撒手千金報德時”的情節感動。“快意恩仇”從來都不是一個成熟政治家該有的情操,但卻滿足了平凡小民的性情釋放。稍能理解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政治的游戲會如何扭曲心靈、摧殘人性,不能以尋常百姓的生活情感取代帝王將相的生存法則。但袁枚偏不這樣,他偏要把帝王請下龍椅,將英雄看作平民,這何嘗不是他對平凡生活觀的一種堅持?
第二,將帝王將相化為詩人自我的“隱喻”。平凡的人生也都有喜怒哀樂,帝王將相的情感有時只是將平凡的情緒夸張、放大而已。袁枚表面是在歌詠古人,實則要將古人看作自我的化身。所以,當21歲的袁枚從杭州南下廣西之時,寫下了那首洋溢著英雄豪情的《吳桓王廟》。當年孫策的南下便如同眼前詩人的南下一樣,雖然一位是開拓江東六郡的霸主,一位還只是前途未知的后生,但詩內與詩外的兩個人是同樣的意氣風發,也同樣在努力為自己的人生開拓全新的格局。37歲謀求二次出仕時,袁枚剛剛離開隨園的詩酒溫柔,又一次燃起建功立業的理想之火。這時他寫到了謝安這樣一位在淝水之戰中指揮若定、功勛卓著的英雄人物。英雄有大功,卻常有小節之失,謝安就總在游覽山水時攜妓同行。袁枚自己就很喜歡狎妓,所以對謝安這樣放誕的行為也相當寬容。《卮言》之三就說:“奇物取大節,瑕瑜不相蒙。謝安游江左,挾妓東山東。”?與謝安相比,杜牧也很擅長軍事指揮,不僅給《孫子》作過注,還獻計平虜,取得過大勝。同時,杜牧也是個風流情種,所以袁枚在《杜牧墓》一詩中專寫他的風流,并且還頗有幾分歆羨之意。所謂“高談澤潞兵三萬,論定揚州月二分”?,就把杜牧在戰場和妓館中的兩番英雄舉止概括出來了。其實,袁枚是將杜牧化作自己的“影子”,讓杜牧在詩酒與功名這兩個舞臺上都為自己充當替身。展開這些隱喻的時候,詩人得到了一種角色代入的權力,仿佛穿越到別人的時代里,走了一遍別人的路,但其實隱隱約約走的還是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用別人的人生證明了自己的選擇。以歷史人物為替身,這確實使性情的抒發變得曲折而又隱晦,但唯其如此,詩人才更敢于抒寫真情,因為以隱喻為偽裝,反而比直陳心志的時候更加敢想敢說。
去除了“以學問為詩”和帝王將相主題這兩重干擾,也還難以真正理解到袁枚詠史詩與其性情人生的全部關聯,因為它們都屬于詩歌本身的形式或內容特征,沒有觸及詩人的性格特質。既然詩寫性靈,那么詩中真性情的展開方式必然在根本上為詩人的人格氣質所決定。詩人內心真誠,詩才能寫出性情;詩人內心虛偽,詩就會遮蔽性情。進一步講,詩人內心天真,則詩中性情往往簡單率直;詩人內心老練,則詩中性情每每復雜雋永。這個道理在袁枚的詠史詩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上文前兩部分的論述,運用了最為常規的“知人論世”之法,將袁枚的詠史詩創作歷程與其人生起伏相對應,而人生起伏的背后正是袁枚的一部性情成長史。我們將其人生以初次歸隱為界分為前、后兩期,也正是以其性情的成長狀態為依據。在前半期,他或是天真幼稚得可愛,或是虛偽詭譎得可怕,都沒有達到最佳狀態;到后半期,生活給了他更多的自信與悠游,其性情才變得富于魅力,可謂壯而益真、老而彌醇。
具體而言,袁枚在參加博學宏詞試之前,走在漫游南北的路途上,是那樣簡單而真誠,在對古代豪杰的歌詠中也寄寓了自己的理想與自負。但年輕人的心志宣泄雖然樂觀向上,卻又容易千篇一律。因為即便歷史上命運最為悲慘的詩人,通常也都有一個青春無敵的少年時代。這時的性情雖然真誠,但未必令我們欣賞。尤其是當青年才子遭遇博學宏詞落榜和外放知縣這兩輪打擊的時候,不論是他流落京城還是在南京候任,詩中性情都迅速蒙上陰影。什么豪情,什么壯志,全都被現實打敗,我們才發現他之前的青春激情是何等幼稚。而幼稚,作為真性情的敵人,通常不易覺察,因為它總是偽裝成樂觀豪邁的樣子,使人們誤以為那就是他的本真自我,覺得他未來的性情人生都在少年時代埋下了伏筆。不要忘記,青年才子們除了高唱美好未來,還特別喜歡炫耀自己的小聰明,所以袁枚在翰林院期間沾染了清談的風習,也總愛寫一些充滿翻案意味的作品。炫耀聰明這件事本身就帶點兒虛偽的色彩,因此我們很難說那種為翻案而翻案的詠史詩真正符合性靈詩學的宗旨。他的“靈機”不發端于他的“性情”,就會變成虛偽的抖機靈。但比幼稚樂天和炫耀機智更可怕的,是他對性情詩的徹底背叛。他在任職江寧時期所寫的《詠史》六首,對汲黯的咒罵,對桓譚的嘲笑,讓我們讀過之后,背后隱隱發涼。如果這些觀點出于小人之手,我們也還能接受;出于袁枚之手,你才會發現生活的詭異和人心的荒誕。我們不禁會問:當初那個青年才子是如何在官場重壓之下變成這副模樣?所以,幼稚樂天、炫耀機智和徹底背叛這三者,都屬于性情尚未完善的狀態。真正使袁枚的性情完善起來的,是他初次歸隱的那三年。很多研究者會低估這三年的意義,但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作的分析,二次出仕時的袁枚已經和江寧時期判若兩人。
在二次出仕和隱居隨園時期,袁枚的詠史詩充滿批判性,也喚醒了真性情。批判性使其徹底有別于官場的虛偽做派,而此時的真性情又被自信和自由的心滿滿地滋潤著,因此真有了一種手揮羽扇、氣定神閑的樣子。唯一令我們失望的,是他在此階段刪改了南京候任時期那些抑郁陰暗的作品。以他一個中年人的心智,當然會對自己當年的幼稚不滿。但一個徹底具有真性情的人,不應去遮掩自己的過去。真正令筆者佩服的真性情,應是他老年時期的心態,是那種對自己一生做出反思的勇氣。王昶曾評價袁枚的詩,說他“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斗捷,不必盡遵軌范”,這大概能對應袁枚初次歸隱之前的狀態;又說袁詩“清靈雋妙,筆舌互用”,意思是袁枚還能擺脫簡單的逞才,而達到雋永的高度,這很符合他初次歸隱之后的狀態;而王昶評語的最后一句則說袁詩“能解人意中蘊結”?,這就最符合袁枚老年時的心靈境界了。
袁枚講詩中要有性情,那么我們讀袁枚的詩,怎么能不研究他的性情成長史呢?因為對一個真正的性靈詩人來說,他的人生便是他的性靈,他的性靈便是他的詩。以人生況味來衡量性靈詩作的水準,才是比較符合詩學規則的鑒賞手段,至少從詠史詩這個維度來看是這樣。
① 筆者統計《甌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得知趙翼存詩五千余首,其中詠史詩有240首,占比不足5%。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袁 枚 :《小倉山房詩文集》,上 海 古 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頁,第1頁,第2頁,第4頁,第12頁,第17頁,第1826頁,第34頁,第33頁,第31頁,第33頁,第34頁,第32頁,第43頁,第80—82頁,第86頁,第153頁,第163頁,第168頁,第171頁,第306頁,第306頁,第307頁,第737頁,第736頁,第1063頁,第1頁,第12頁,第628頁,第172頁,第177頁。
? 宋致新:《袁枚的思想與人生》,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192頁;賈君:《袁枚詠史懷古詩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第17—18頁。
?陳正宏:《從單刻到全集:被粉飾的才子文本——〈雙柳軒詩文集〉、〈袁枚全集〉校讀札記》,載《中山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 袁枚:《雙柳軒詩集》,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新編》第16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第14頁。
? 王英志:《袁枚暨性靈派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 張健:《袁枚詩新論》,(臺灣)文津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頁。
???? 袁枚:《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303頁,第326、146頁,第146頁,第20頁。
? 劉衍文、劉永翔:《袁枚續詩品詳注》,上海書店1993年版,第16頁。
? 王昶:《湖海詩傳》,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