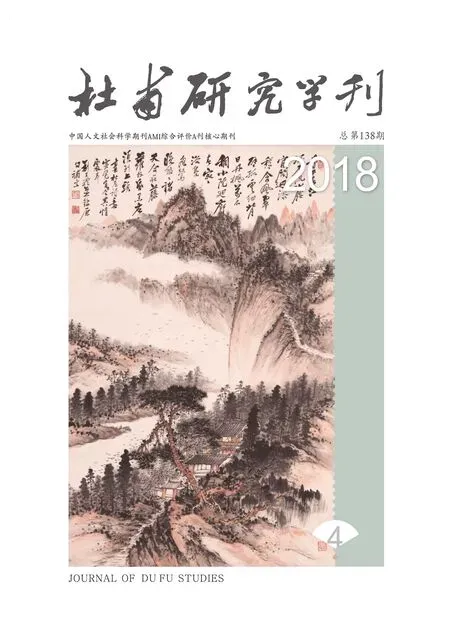杜甫《兵車行》與唐代政治、思想和文學
陳麗琳
《兵車行》一詩與《悲陳陶》《悲青阪》《哀江頭》《哀王孫》四首收錄在郭茂倩《樂府詩集》卷第九十一的“新樂府辭二”之“樂府雜題二”之中。此詩不僅可作為杜甫的第一首“新樂府”,也可以看作是其“詩史”創作的開端。通過分析詩歌內容與當時之歷史史實,筆者發現,《兵車行》不僅在杜甫的創作史中具有重要意義,于唐之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學史,亦具有重要地位。《兵車行》從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天寶十載前后,唐之政治、思想與文學所發生的一系列的轉折性變化。本文便將從《兵車行》與唐代之政治、思想與文學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兵車行》與唐代之政治
《新唐書·杜甫傳》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若論及杜甫寫實傾向的詩作,常常將之與“詩史”相關聯。“善陳時事”所指向的正是杜甫以詩歌這一形式反映歷史史實。《兵車行》以詩家之言補史家之筆,從特定的角度將處于歷史轉折之際的唐代政治史實進行了敘說。茲錄全詩于下: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驅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托于漢以刺玄宗也。”關于本詩之題旨為諷刺唐玄宗窮兵黷武,古來并無多少異議。但關于此詩的創作背景,卻頗有爭議。王嗣奭《杜臆》之中認為此詩之背景,當為天寶八載哥舒翰拔石堡城之役:
注謂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是已。然未詳。按《唐鑒》: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俟釁取之。”帝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取石堡,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蓋以愛士卒之故。延光過期不克。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所以有“邊城流血”等語。

又有論者以此詩當作于天寶十載唐與南詔之戰,《杜詩詳注》下所引有黃鶴之論,即作此說。清代錢謙益《唐杜少陵先生甫年譜》中,于天寶十載下列《兵車行》,在其《錢注杜詩》有具體論述:
此詩序南征之苦,設為役夫問答之詞。君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驛騷,不獨南征一役為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賦役。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詔,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聞,君不見,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于其詞。若不為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錢謙益認為“君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驛騷,不獨南征一役為然。”即《兵車行》的創作背景當為天寶十載唐朝與南詔之戰。此詩中雖未言“南詔”,但卻借南詔之戰將此前發生的一系列開邊戰爭進行了批判。通過分析當時之歷史,筆者認為錢氏之說較為合理。《兵車行》被諸多論者認為所敘為征討吐蕃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在詩中出現多處明確指向與此相關的內容,包括“北防河”、“西營田”、“青海頭”等。錢氏所言“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或并不準確,但若將此詩放在征兵之時所作,那么杜甫所敘有關吐蕃的殘酷史實,其用意應當是要告誡正在籌備征討南詔的統治者。事實上,《兵車行》中潛藏著大量唐代的政治社會史實,若單單將本詩與某一具體戰役對應反而限制了杜甫要表達的內涵。
首先,“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兵車行》敘寫的征人長期鎮守邊境的情況,反映了玄宗朝之軍事制度。唐代開元十五年,還存在征關中兵萬人防秋的兵役制度。“唐代前期自邊境要地設置軍鎮,改變了分散軍弱的傳統鎮戍制度。為了適應新的邊境形式,為了鞏固邊防避免調發之煩,需要有常備的邊防軍,還需要有常任的統帥本地區諸軍鎮的軍事長官。”從開元二十五年起,朝廷所招募的“兵防健兒”便已經開始常駐邊疆,這些士卒受鎮守邊境的節度使統領,不再實行“征發制”和“番代制”,府兵制在其時已被廢除。但青壯勞動力常駐邊境,國內無勞動力進行耕作,于是就出現了“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的情況,而國內也不可避免地演變為“千村萬落生荊杞”的衰敗之景。
而發生戰事之時,邊鎮防御外敵所用之戍卒便是各節度區的常駐士兵。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石堡城,其兵力便“出自河隴及河東、朔方以及突厥阿布思部”。在史書之中,開元二十五年之后就未記載有大規模的征兵事件。但《兵車行》言“點行頻”,其中之“頻”字,實際上指出了雖然在這期間未發生大規模的征兵,但“邊庭流血成海水”,邊境戰爭中所消耗的兵力必然需要從國內征兵進行補充。那么實際上征兵現象一直存在,只是有著規模大小的區別。直到天寶十載,唐與南詔爆發戰爭,《資治通鑒》載:

為了與南詔對抗,楊國忠下令強行征發戍卒,以至于出現“分道捕人”的情況。“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的場景是當時突然發生大規模征兵的寫照。而天寶十載,杜甫正在長安城中,“分道捕人”之事也當為杜甫親眼所見。



二、《兵車行》與唐代之思想
《兵車行》與唐代政治史相關之外,也反映了天寶中后期士人思想的變化。



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復皆杖死。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卽貶所賜皇甫惟明、韋堅兄弟等死。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過殺遷謫者,郡縣惶駭。排馬牒至宜春,李適之憂懼,仰藥自殺。至江華,王琚仰藥不死,聞希奭已至,即自縊……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霅,杖死于河南府。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

這一年無疑是玄宗朝極為黑暗的一年。正月,李邕被杖斃。天寶四載的歷下亭之游還令杜甫難忘,而僅僅兩年之后,這位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前輩就已被奸人所害,對于杜甫而言,必然讓他對當時的朝廷感到失望。宰相李林甫在朝廷之內大肆鏟除異己,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之中所贊揚的李適之,屈死于李林甫黨派之手,就連試圖為父伸冤的李霅,也被李林甫誣陷致死。房琯亦于這一年被貶。杜甫所推崇的前輩被李林甫迫害得七零八落,這樣的現狀對他所造成的沖擊不言而喻。在同一年,玄宗“廣求天下之士”,這場考試本應是杜甫大展才華的機會,但因李林甫的弄權而截斷了杜甫進入朝廷的路徑。這無疑對杜甫是一個更為沉重的打擊。






天寶十載,玄宗朝已出現崩潰的先兆,士人思想也隨之發生著變化,儒家價值逐漸開始受到重視。在整個唐代思想變動之中,杜甫的獨特之處正在于其儒家思想發生的轉變。杜甫的儒家價值觀由早期的追求“治國平天下”,逐漸轉變為更為深沉的“仁愛”思想,《兵車行》一詩便是他儒家思想轉變的例證。
三、《兵車行》與唐代之文學
杜甫所創作的《兵車行》,對應了唐代之政治與思想的轉折。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此詩的創作也反映了唐代文壇的復古與變革。


唐代對漢魏文學的復古,以樂府詩的創作為代表,這種復古伴隨著唐人的創新。陳廷焯曾言:




第三,除了杜甫對漢魏樂府語言上的繼承,題材上的開拓,更為重要的是杜甫在詩中的個人情感的注入。《白雨齋詩話》評《兵車行》曰:




小 結
《兵車行》是杜詩中一首具有典范意義和轉折意義的詩作。此詩被后世歸為杜甫的“新樂府”,在杜甫的詩歌創作史中具有轉折性的價值。同時,此詩與唐代之政治、文學和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系。若以“史”而論之,則在唐代之政治史、思想史與文學史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以詩歌的形式反映了歷史轉折之際的玄宗朝在這三方面的特征。本文由此從這三個方面進行論述。首先,《兵車行》一詩的寫作背景當為天寶十載唐與南詔之戰,杜甫所見應為楊國忠下令分道捕人之事。杜甫創作此詩的目的,應當是對正在籌備征討南詔的統治者的勸誡。詩人站在百姓的立場來看戰爭,對戰爭的性質進行了反思。除此之外,此詩反映了當時之軍事制度與底層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史之亂爆發前唐代社會的衰敗在《兵車行》之中已有顯現。其次,《兵車行》對應著唐代思想的轉折。天寶六載之后,杜甫在政治抱負無法實現之時,將目光放在了下層百姓的生活,以儒家情懷敘寫當時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杜甫的儒家思想中,更加深沉的“仁愛”思想逐漸上升。而《兵車行》正是這種思想轉變完成后的詩作,杜甫的思想轉變在唐代思想史之中獨樹一幟。最后,《兵車行》不僅是杜甫創作史的轉折,也反映了唐代文學的復古與變革。《兵車行》作為杜甫的新樂府創作,復古與變革交織。在杜甫筆下,以樂府體裁反映史實具有更為深刻而廣泛的內涵,其中更蘊含著杜甫個人深厚的情感。《兵車行》不僅可看做是杜甫的第一首“新樂府”,也可作為杜甫“詩史”創作的開始。
注釋
:①(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二百一,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38頁。

③(宋)蔡夢弼會箋:《杜工部草堂詩箋》,(清)黎庶昌輯《古逸叢書》本。
④(明)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5頁。
⑤(清)劉鳳誥:《杜工部詩話》卷二,載張忠綱校注:《杜甫詩話校注五種》,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⑥(清)錢謙益箋注:《唐杜少陵先生甫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1頁。
⑦(唐)杜甫著,(清)錢謙益箋注:《錢注杜詩》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頁。此論又見錢謙益之《讀杜二箋》。(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8-2189頁。
⑧⑨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華書局2011年,第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