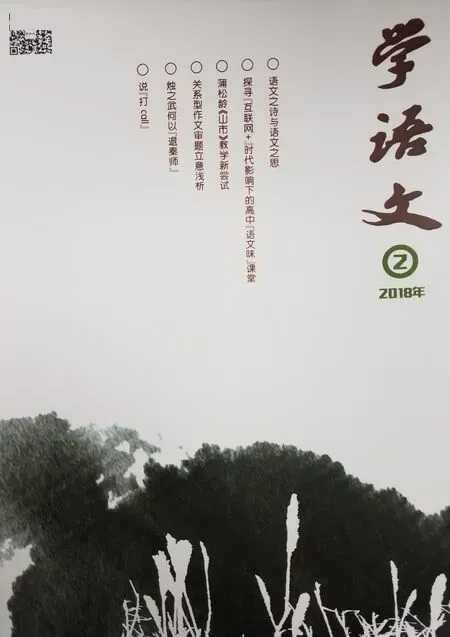從語言表達得體角度重新審視焦仲卿和劉蘭芝
《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自掛東南枝”,劉蘭芝“舉身赴清池”。千百年來,人們扼腕嘆息他們的遭遇。多數人認為焦母是罪魁禍首,劉母和劉兄是幫兇,封建家長制害人匪淺。焦仲卿懦弱,劉蘭芝美麗溫順,有情人“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如今重讀文本,卻有新的發現,新的感悟。
詩從蘭芝對仲卿的一番傾訴開始。蘭芝覺得自己在焦家生活很是悲苦,原因有三:一是常守空房,相見日稀;二是辛苦勞作,不得休息;三是婆婆嫌棄,故意刁難。面對蘭芝的傾訴,仲卿既沒有安慰,也沒有責怪,而是找母親詢問。他原本是去求情的,結果非但求情不成,反而更加激怒了母親。細究其因,除了焦母專橫易怒以外,焦仲卿的語言表達實在欠妥,實屬不得體。
俗話說“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焦仲卿說話的對象是強勢專橫的母親,對蘭芝懷忿已久的母親,養育自己多年的母親。他沒有顧及母親的感受,直言相問:“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其實是在指責母親蠻橫無禮,明顯偏袒妻子,這令焦母情何以堪!勢必讓焦母以為:自己二十年養大的兒子,兩年時間就被另外一個女人搶走了。焦母有錯,仲卿按《禮記·內則》,應當“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然而詩中焦仲卿語氣強硬,還語帶威脅之意,等于是火上澆油,以致焦母“槌床便大怒”:“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母子鬧僵,事情再無挽回的余地。再看焦仲卿“堂上啟阿母”的話:“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發同枕席,始爾未為久”,也會使母親傷心失望憤怒。在焦母的心中,焦仲卿“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換句話說,焦母對兒子寄予厚望,她望子成龍,希望兒子有美好的前程,自己也能母憑子貴,可仲卿卻如此貶低自己,就是粉碎了母親的美夢,豈不令母親失望!焦母嫌棄蘭芝至極,焦仲卿卻說“幸復得此婦”,等于在和母親唱對臺戲,站在了母親的對立面。他傳遞給母親這樣的信息:蘭芝是上天賜給我的,我前途已經無望了,絕不能再失去她。你要休她,我就讓你絕后。試想:如此強勢的焦母怎能忍受兒子為了一個無禮、不聽教訓的女人自毀前程?仲卿過激的言語加重了焦母對蘭芝的怨忿。倘若仲卿聽到蘭芝的牢騷后,先安慰她幾句:“吾母年已高,汝勿生母氣,母行有偏斜,請汝多擔待”,再去安撫母親:“蘭芝尚年輕,令母多費心。勤心相教導,令其感母恩。吾不長居家,蘭芝養汝身”,或許,事情還有緩和的余地。
求情不成,仲卿便遣蘭芝回娘家,臨別時告訴蘭芝:“且暫還家去,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蘭芝被休,仲卿認為只是回娘家暫住幾天而已,他想象不到蘭芝回娘家后的尷尬和難堪,顯得極其幼稚。當蘭芝說“我有親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時,仲卿依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有擔憂,也沒有安慰,就那樣輕易撒開了手,只留下幾句海誓山盟的空話而已,其愚拙可見一斑。聽聞蘭芝要重新嫁人了,仲卿才“因求假暫歸”。當蘭芝傷心訴說變故后,仲卿無計可施,不是好言相勸,真心祝福,而是醋意十足,以語相激:“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這段過激的話直接把蘭芝引向一條不歸路。如果不是仲卿以言語譏諷,蘭芝或許不會走向絕路。
作為家中唯一的男人,已經成家立業的焦仲卿本應是家中的棟梁,為母親,妻子,甚至妹妹撐起一片天。但焦仲卿心智不成熟,他不能留住心愛的女人,也不能庇佑自己的至親。他雖已在官府工作多年,但智商情商都不太高,沒有能力,沒有擔當。工作上,他只是一個小吏;生活上,家庭支離破碎。語言表達上,他更是偏激幼稚,愚不可及。他選擇死亡,是在逃避責任。他解脫了,年邁的母親無人贍養,年幼的妹妹無所依傍,焦家今后的日子將會是何種艱難!這些仲卿都不管,他愚拙的走向絕路,無能的選擇逃脫。
蘭芝是作者極力謳歌的對象:“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朝成繡夾裙,晚成單羅衫”,她多才多藝,美麗動人,頭腦清醒,個性鮮明,似乎無可挑剔。但仔細品讀她的語言,發現與其說她溫順,不如說嬌縱任性。她很自愛,卻不能自立;她要自尊,卻難以自強。她需要寵愛,但焦仲卿給不了她,焦母也不給她。她既沒有中國傳統女性的溫婉和順,也沒有現代女性的獨立自強,她極力張揚個性,彰顯自我,缺乏忍耐,最終走向毀滅。
焦仲卿一回家,蘭芝就抱怨:“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守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這段話有三層意思::一是埋怨仲卿重工作輕感情,二是指責焦母蠻橫,三是自請遣歸。試想:如果不是恃寵而嬌,蘭芝怎么敢在仲卿面前指責焦母?倘不是任性,怎能自請遣歸?這顯然是有違禮法的。她抱怨焦家生活悲苦,說明她不適應媳婦的身份及焦家的生活,已出嫁的女兒豈能還依戀娘家美好?不管娘家如何美好,那都是過去,自己的生活要自己面對,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但蘭芝沒有成功實現由姑娘到媳婦的蛻變。
從詩中,不難發現劉家的富裕非比尋常。蘭芝離開焦家時交代仲卿她的嫁妝是“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再嫁準備嫁衣時“移我琉璃榻”,可見她的物品豐盈,而且華貴。她能接受那么多的教育,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做到的。在娘家時,母親對她疼愛有加,又加上錦衣玉食的物質生活,劉蘭芝應該是嬌生慣養的。在她被休之后,母親沒有責怪她,也認可蘭芝無錯,及至媒人提親,蘭芝不愿改嫁,母親也是聽之任之,可見劉母對女兒愛護之甚。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劉蘭芝,勢必會養成嬌縱任性的品行。從詩中她敢于對抗兄長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嫁到焦家之后,劉蘭芝離開了溫和柔順的慈母,迎來了強勢蠻橫的焦母;放棄了錦衣玉食、無憂無慮的生活,過上了日夜苦辛、獨守空房的日子。娘家的溫暖富足和婆家的冷漠凄苦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這樣鮮明的反差,一個嬌慣成性的嬌嬌女怎能適應?所以她才會有那么多的抱怨,才敢自請遣歸。她的自請遣歸,既是清醒的認識,也是任性的舉動。倘使她不那么任性嬌縱,而是放下身段去誠心誠意侍奉焦母,以真誠博取焦母歡心,少些抱怨,多些行動,或許焦母會改變態度。但蘭芝豈肯摧眉折腰?
蘭芝離開焦家前,嚴妝打扮自己,與其說是維護自尊,體面地離開,不如說是向焦母示威以彰顯自己。品讀蘭芝別焦母的話:“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富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這段話看似有禮有節,實則柔中有剛,綿里藏針,話中帶刺,語含譏諷。劉蘭芝對焦仲卿傾訴苦楚時,自認為有教養,無過錯,是焦母蠻橫無理,因而她不可能真心誠意向焦母認錯。與其說是認錯,還不如說是變相譏諷。這些內容可能只是平日里焦母批評她的,她拿來維護自己,反擊焦母而已。“念母勞家里”,言外之意是:既然你對我不滿意,我干脆不做你的兒媳了,今后你就自己干活吧,我再也不看你的臉色了。一番不軟不硬的話使“阿母怒不止”,也無可奈何。可以想象,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個縮影而已。平常生活中,焦母何止一次這樣被噎著。蘭芝是善言的,而且言語犀利,似刀子,如匕首,直指焦母。
蘭芝任性,最怕人激,亦不喜人責。婆婆嫌棄,她針鋒相對;兄長怒斥,她仰頭回擊;仲卿奚落,她以死相許。她以嬌縱的性情,完成了最后的任性之舉:“舉身赴清池”。我們扼腕嘆息蘭芝悲劇命運的同時,也應反思:如果蘭芝少一分嬌縱,斂一分任性,事情或許是另外一種結局。
焦仲卿和劉蘭芝就像兩個任性的孩子,渴望自由,卻不能自我強大;非常自我,卻未能蛻變成熟,注定是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