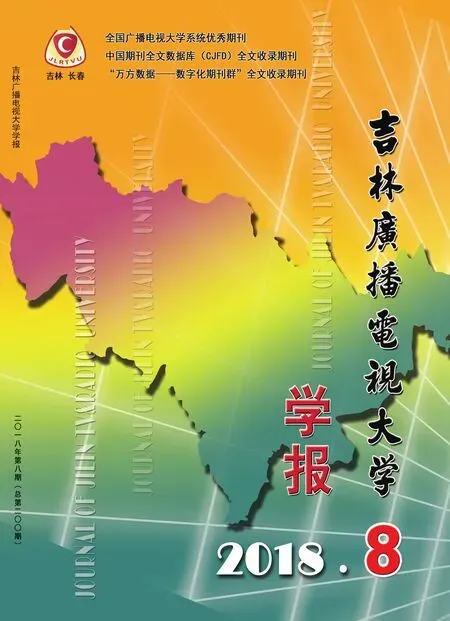論《爵士樂》中的母性缺失與自我構建
李可一 劉曉露
(明德天心中學,湖南 長沙 410004;長沙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03)
作為美國當代黑人女性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作品始終強調主體自我獲得承認、肯定和愛的需要,始終關注黑人主體是如何在以白人文化為主宰的美國文學中被構建起來的。在一次關于小說《爵士樂》的訪談中,莫里森指出女主人公維奧萊特其實是在沉睡的狀態中死去。“沒有什么能讓她復生,除了那個擁抱生命的靈魂或精神,那個當我們說“我”時所意味的東西。它是如此被忽視,如此沉默,如此不被統治世界的力量所接受……那是自尊誕生或毀滅的地方……我們需要釋放,以自我的那部分為榮……這對人類而言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尋找那種人、那樣的理念和思想構成了我的大部分作品。”自我必須獲得愛和認同,用莫里森的話說,就是得到尊重和釋放。當我們無視或疏于照顧真實的自我時,我們會丟失、忘記我們原本的樣子,就會像維奧萊特那樣陷入沉睡。
莫里森指出自愛取決于自我首先被另一個自我所愛。在一個孩子學會愛自己之前,他必須經歷自我被愛,從而證明自我是有價值的,是值得這份感情的。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強調了母愛對一個孩子情感健康的重要性,因為正是母親首先愛孩子,賦予他一種被愛的自我認知。那些被遺棄的,從未得到母愛關懷的孤兒,在成年后通常有心理創傷。失去母愛的孩子從未學會如何去愛他們自己,沒有這種自愛,自我會迷失、被遺忘。因此,正確的過程是母愛——自愛——自我。莫里森的第六部小說《爵士樂》即講述了一群母愛缺失的孩子們的故事,他們沒能完成從母愛到自愛的旅程,因此也從未真正認識自我。
一、維奧萊特與羅絲·蒂爾:源自母性之殤的裂縫
《爵士樂》以二十世紀初美國大遷徙運動為歷史背景,講述了黑人夫婦喬與維奧萊特離開南部鄉村融入北方城市的經歷。敘述者用“頭腦里的裂紋”“黑暗的縫隙”“粘得很糟的接縫”來描述維奧萊特主體意識的分裂和破碎。她很小的時候,母親羅絲因為無法忍受生活的重擔而自殺。小時候,外婆總是給她講一個金發小孩的故事。這個金發小孩叫戈爾登·格雷,是白人路易斯小姐和一個黑人小伙所生的兒子。從外婆關于金發男孩被溺愛被崇拜的故事中,維奧萊特得知擁有白皮膚和成為男性,就能獲得愛和快樂。她同樣從那些故事中得知她的母親,外婆的其中一個女兒,在外婆追隨主人路易斯小姐去巴爾的摩時被留在了身后。本該屬于女兒們的母愛被慷慨地贈予了長著黃色卷毛的白人男孩。可外婆并不恨這個把她從女兒身邊奪走的男孩,相反,她愛這個“美麗的年輕人”,這個讓外婆忘了自己女兒的男人也同樣迷惑了維奧萊特的心,并且毀掉了她的自我價值。她的欲望不僅僅是得到戈爾登的愛,更是要成為他。小說結尾,維奧萊特告訴費莉絲她的腦子里住著一個愛耍花招的金發小孩,她又是如何把生活搞了個一團糟:
“現在我想做我媽媽沒能活著看到的女人。那一個。她會喜歡的那一個,我以前也喜歡的那一個……我外婆老把一個金發小孩的故事灌給我。他是個男孩,可有時我把他當作一個女孩,當作一個兄弟,有時當作一個男朋友。他活在我的腦子里,像顆痣一樣沉默。可直到我來到這里才知道。我們兩個,必須擺脫它。”
……
“你是怎么擺脫她的?”
“殺了她。然后我把那個殺了她的我也殺了。”
住在腦子里的金發小孩是導致維奧萊特心理創傷和伴隨而來的自我錯位的根源,也是死去母親的替代品。美國學者黛博拉·麥克道爾(Deborah McDowell)指出對死去母親的回憶是小說《爵士樂》的原動力,更確切地說,文本的原動力是對替代母親的追尋。一系列錯位,一系列替代推進著維奧萊特的敘事。無論是對金發男孩戈爾登的迷戀,還是對丈夫喬的愛,亦或是后來對死去女孩多卡絲的著迷,對母親的饑渴像重錘敲打著她,她試圖填補因母親去世而產生的自我空洞。
維奧萊特對母親身份的抗拒也與母親的缺失有關。“維奧萊特從中得出的重大教訓,最大的教訓,就是永遠永遠不要孩子。不管發生什么,決不要有一雙小黑腳疊在一起,一張饑餓的小嘴叫著:媽媽?”維奧萊特后來經歷的三次流產,“與其說是喪失,還不如說是不便。”流產似乎是自我誘導的,象征著維奧萊特對母親身份的抗拒,更確切地說,她拒絕變成她母親那樣。
盡管維奧萊特拒絕母親身份,她卻不斷地把自己置于母親的角色。小說中,維奧萊特“盯著小孩子看,在圣誕節展銷的玩具前面躊躇不前……漸漸地,熱望變得比性愛更難對付了:一種令人心跳氣短、不能控制的饑渴”。維奧萊特用一個藏在床下的娃娃安撫自己,甚至企圖把別人的孩子抱回家。日常生活中,她也表現出與其她女性的母性認同。維奧萊特靠給人燙頭發謀生,燙頭發代表了一種母性行為,顧客是她的替代孩子,她從未有過的女兒們。通過打扮這些女士,維奧萊特獲得了母親身份,向她的孩子們提供養育和咨詢。一看到多卡斯的照片,她就想要把她的發角修修。就如那些顧客是她的女兒們一樣,鳥也是,喬曾對鄰居瑪爾芳抱怨“維奧萊特對她的鸚鵡比對我照顧得更好”。
試圖通過養育別人找回失去的自我——對多卡斯、洋娃娃、抱走的孩子、做頭發的顧客、鸚鵡——維奧萊特實際上試圖成為她失去的母親。更重要的是,通過像母親一樣撫育他人,她渴望發現作為女兒的原來的自己。她把自己投射在她照顧的人和動物上,這樣,成年的維奧萊特撫育了作為孩子的維奧萊特。她自己撫育了自己。通過這種養育,維奧萊特既可以成為她失去的母親,也同時是曾經作為女兒的自己。
最終在年長女性愛麗絲的開導下,維奧萊特認同了她的母親羅絲,理解了母親的人生。維奧萊特終于理解母親為什么沒有養育她。羅絲當不了女兒的母親,因為她自己從未被當作女兒養育過。維奧萊特意識到了母親身上缺失的母愛,這種認識使女兒—女兒之間的認同成為可能,反過來又強化了母女間的聯結。當維奧萊特記起作為母親、作為女性、作為女兒的媽媽時,維奧萊特也找回了自我。她心中死去的那個女孩復活了。用莫里森的話說,“她現在就在這兒,活生生的。我看到她,命名她,索要她——她是一個多么好的陪伴啊。”與母親的認同將維奧萊特帶回她的自我,內心里狹窄、黑暗部分關閉了,粘得很糟的縫隙得以修復,自我變得圓滿完整,在尋找母親的秘密花園時,她找到了自己的花園。
二、喬與“野女人”:追尋母親的痕跡
《爵士樂》中另一個缺席的母親是“野女人”(Wild)——喬的生母。“這人腦筋徹底毀了,連最差勁的母豬都能辦到的事也不會做:給自己下的崽子喂奶。”戈爾登第一次看到野女人是在樹林中,他描述她是“一個莓子一樣黑的裸體女人,渾身粘滿了泥漿,頭發里凈是樹葉”。她的肚子又大又緊,他被嚇住了,他想這不是一個真的女人,而是一個幻影。野女人居住在一個典型的女性空間——子宮一樣的洞穴中,存在于法律、秩序、理性的男性世界之外。她是閣樓上的瘋女人,是粗暴、原始、被放逐的女性自我。野女人嚎叫、大笑、撕咬、歌唱,但她從不說話。當喬第一次聽到野女人唱歌時,他錯誤地認為她的歌是天地奏出的音樂,是流水和高高的樹中間的風共同發出的聲音。當喬在灌木叢中尋找野女人以確認她就是他的母親時,他所想要的只是一個信號,“他不需要語言,甚至沒想過要語言,因為他知道語言是會說謊的,會燒得你熱血沸騰然后就無影無蹤了……她要做的只不過是給他一個表示,把手從樹葉中間一下子伸過來”。野女人通過觸摸交流,用后現代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說,她是用身體寫作。通過笑聲、歌唱、觸摸,野女人講述了前俄狄浦斯母性空間的前話語語言。
法國后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家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了主體表達在表意過程中出現的符號界(the semiotic)和象征界(the symbolic)兩個階段之間的互動關系。在她那里,象征界是指語言學家所認定的意義本身,而符號界則是語言中的動力因素,它與節奏、音調等相關,是非語言或先于語言的,不能化約為語法和邏輯結構。這種用于母親和孩子之間的前俄狄浦斯語言,是一種特別的標志、痕跡和索引。澳大利亞女學者伊麗莎白·格羅茲(Elizabeth Grosz)把這種符號定義為“前指義的能量。”她認為符號界是內在性沖動無序無形的循環,以無束縛的方式在孩子的體內循環。這種多形態的,不合常情的沖動無視現實法則,僅靠自身的力比多驅動。符號界在象征界中爆發,它表現得如同中斷,是文本的不和諧音,是不受文本邏輯和敘述控制的節奏。這種記號既是象征界功能的前置條件,又是不受控制的放縱,可以為話語使用,但不能發聲。
野女人代表了符號界不受控制的放縱。她的大笑、歌唱、觸摸構成了符號界敘述語言。克里斯蒂娃解釋了符號界是如何打斷象征界并以節奏、文字游戲、曲調、大笑等形式回歸。野女人同樣存在于象征界之外,用她女嬰般的笑聲,指甲的輕敲瓦解了作為象征界的男性世界。克里斯蒂娃把符號界定義為痕跡,同樣的,野女人的兒子給自己取了“特雷斯(痕跡)”這個姓。野女人的家也是作為前俄狄浦斯母性空間而呈現的。她住在如同子宮般的洞穴里,喬第一次尋找母親時,他“找到了石洞的入口,卻無法從那個角度進洞。他得爬到它上面,再從它的口里滑進去”。幾年后,喬再次試圖進入洞穴,他“爬進了一塊低得能擦到他頭發的空地……他不能夠在里面轉身,就拖著整個身子一路爬出去,好讓頭朝前再進來……然后他看見了那個裂口,他屁股著地滑進去,一直滑到了底兒。就好像掉進了太陽里面”。這里描述了回歸母體的場景。喬順著產道,穿過子宮頸,進入子宮,嬰兒的出生通道被反轉過來,一個成年男性尋求重新進入母親的子宮。喬進入了“野姑娘那間金色的房間”,回到了初始之地。喬渴望發現他來自哪里以便他最終可以知道他是誰。對光線的指代,“就好像掉進了太陽里面”,顛覆了柏拉圖洞穴的黑色虛無。這個通道暗示了黑暗是光,洞穴——子宮——則是原點之錨。
不同于同時代男性作家的“父愛饑渴”主題,莫里森的《爵士樂》則講述了一個關于男性的傷痕和治愈完全不同的故事。喬遭受的不是父愛饑渴,而是作為一個得不到母愛的孩子的憂傷。母愛缺失導致了喬的心理創傷。喬從未哀悼到時生物學上父親的缺席,事實上,喬從未想知道親生父親是誰,文本也沒有推測他父親的身份。
喬曾三次動身尋找野女人。喬想證實“她千真萬確就是他的母親,就算得到證實將讓他感到恥辱,他還是會成為弗吉尼亞最幸福的孩子……是。不是。兩者都行。其中一種也可以。但不要這樣一聲不吭啊”。當他的乞求得不到回應時,他帶著憤怒和恥辱轉身跑了。“那種內心空虛,從此被帶在了身上”。喬不斷從一種身份轉向另一種。“在認識她(多卡絲)之前,總共改變過七次”。多年后,情人多卡斯的出現填補了喬內在的空虛。喬在多卡斯身上找到了他從未見過的母親,她臉頰上的雀斑成為尋找母親的痕跡:
她要我買的護膚品我都買了,可令人高興的是沒有一樣管用。把我臉上那些小蹄印去掉?一點痕跡也不給我留下來?在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唯一的東西,就是找到那條路,決不放棄。我在弗吉尼亞追蹤我的母親,那條路引著我找到了她。
在喬的意識中,野女人和多卡斯合二為一,因為多卡斯“頭腦冷靜,甚至很野”。喬開槍射殺移情別戀的多卡斯,敘述者承認“直到此時此刻我也拿不準他的眼淚到底為了什么而流,不過我敢肯定那不僅僅是給多卡絲的。當時,他頂風冒雨地滿街亂跑,我一直以為他是在找她,而不是找‘野姑娘’那間金色的屋子”。
野女人才是那個被喬打中的女人,是她的死讓喬哀悼。作為一個男孩,喬從未和母親的達成和解,他費盡一生試圖忘記他的母親,試圖成為別人而不是自己母親的兒子。當他第二次失去母親時,喬重新經歷了作為孩子被否認、被壓抑的痛苦和缺失。只有當喬真正承認并體驗到失去母親的情感傷害時,治愈才成為可能。隨著多卡斯的死,喬最終能夠哀悼母親的死,并學會和過去和解,重新找回曾經丟失、錯位的自我。
三、結語
法國哲學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認為語言永遠地把我們從母體分離。語言是無限衍義之鏈,無止盡的差異運動,從一個能指滑向另一個,尋找著想象中的自我完整和統一。美國學者麥迪龍(Madelon Sprengnether)在《幽靈母親》中寫道:欲望永遠無法獲得它的客體,能指無法捕捉或包含所指;主體必須永遠對他和她自己保持未知。這種欲望創造了語言。我們不斷地更換替代物,用隱喻替代隱喻,卻從未能恢復我們想象中的純粹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完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是語言把我們從母體分離,喬不斷變換的身份和對母親的追尋模仿了替代物無限衍義的過程。正如《寵兒》以數字124作為開頭,《爵士樂》用聲音開始敘述:某個聲音——女人穿針之前添濕手上的線時嘴上發出的動靜。這樣,我們不是通過語言進入文本,而是通過非語言、前話語的聲音,這個聲音是舌頭和嘴唇接觸時發出的,是身體原始、本初的語言,在話語之外循環。《爵士樂》的敘述以典型的母性話語開始,把喬和維奧萊特對失去母親的記憶聯結在一起。《爵士樂》肯定并贊美了母性。沒有得到母愛的孩子身上深刻的心理創傷提醒讀者母愛對自我認知和情感健康是多么重要。孩子回到母親身邊,治愈才有可能發生,自我改變和重生的希望開始于母親。也許那雙推動搖籃的手不會統治世界,但它們卻能帶我們回到過去,并為我們指明未來的道路。在追尋母親的秘密花園時,我們找到了我們自己的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