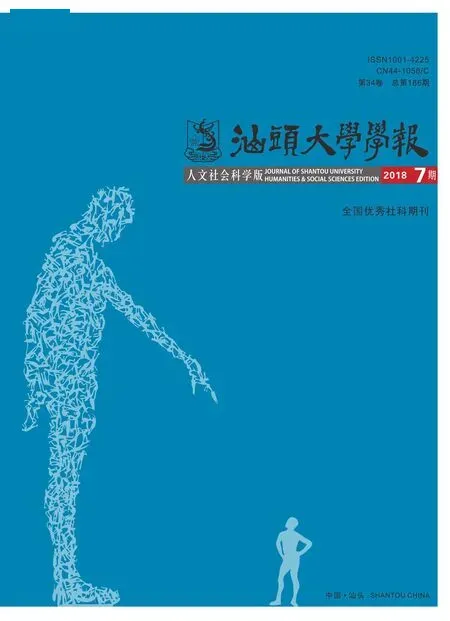《詩經》“男艷女素”服色特點的審美意蘊
楊為剛,肖潤秋
(汕頭大學文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已有研究均有注重《詩經》女性服裝色彩,而男性服裝色彩研究相對較少。實際上,《詩經》中,男性服裝色彩較女性更為艷麗多彩,以黑、紅為主,另有黃、綠、花紋等服色。先秦時期,夏商周部族有各自的色彩崇拜,《禮記·檀弓上》記載:“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1]179黑色稀有而珍貴,且難以制作,“尚黑”象征尊貴和莊嚴,亦包含“天玄地黃”的敬天觀念,多用于夏后氏男性貴族服色,具有神秘、質樸、莊重的審美特征。與后人的“白色忌諱”相反,白色服裝在所有性別和等級中均有存在,且為女性主流服色,代表尊貴、美、純正與品德高尚。殷人以白為尊,白色的女性貴族服飾適用于重大場合,而地位卑賤的妾媵主要著彩色女服。[2]86紅色多用于男性軍隊將領、朝廷命官、貴族的服裝,代表權力和地位。另外,狩獵時代和采集時代的審美遺留,是先民使用有色獸皮和黃綠色布料的原因。在《詩經》時代,社會推崇男性審美,“美人”無性別色彩,是當時社會審美觀的一大特征。本文從服色角度來審視《詩經》時代“男艷女素”服色審美所體現的顏色審美差異、審美原因,及文化心理。
一、尚黑、尚白、尚赤的服色審美
先秦有“尚黑”、“尚白”、“尚赤”的服色審美傳統,男性和女性服色審美有共通之處,但男性服色較女性服色更豐富、鮮艷,體現了《詩經》中“男艷女素”的服色審美特點。黑色多用于男性貴族禮服,代表尊貴和莊嚴。白色多用于女性貴族禮服、日常服裝、平民服飾、婚服以及男女性的內衣,代表了尊貴、美、純正和高尚的品德。赤色多用于男性服飾,如軍服、朝服等,象征權力、地位。從時間上看,黃綠色染料是采集時代的審美遺留,有色獸皮制衣是狩獵時代的審美遺留。從空間上看,顏色崇尚體現了部族個性特色。
(一)男性服色的“尚黑”審美及其文化內涵
“尚黑”多體現為男性貴族服色,《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3]743這里的“青”指黑色,象征有才之士。“尚黑”原因有二,一是“天玄地黃”的敬天觀念,《周易·系辭下》有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4]300“天在未明之時為玄色,故上衣像天而服色用玄色,地為黃色,故下裳像地而服色用黃色,這種上衣下裳的形制以及上玄下黃的服色,就是由于對天地的崇拜而產生的服飾上的形和色。”[5]86黑色是先民對黑夜的直觀印象,在原始巫術中表現為“順勢巫術”,也稱“模擬巫術”,主張“同類相生”原則。施行巫術時,通常用目標物的類似物為替代來達到巫術目的。[6]21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與“黑”意義相近的“幽”、“玄”,并且與祭祀相聯系。[7]帝王禮服上玄下黃,以象征天地,這有以黑色作為媒介而與天地發生感應的巫術意識,也正是由于黑色與夜晚天空的顏色相同,因而導致了先民對它的避諱或崇拜,將其納入溝通天地的巫術儀式;二是黑色布料染制的過程復雜。《周禮·考工記·鐘氏》記載:“鐘氏染羽,以朱湛、丹林,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箋》:“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8]1117,“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9]278“緇”要經過七道染色工序才能獲得,物以稀為貴。
“尚黑”象征尊貴和莊嚴。“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鄭風·緇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鄭風·子衿》)“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幽風·七月》)孔穎達疏:“玄黃之色,施于祭服。”[8]499“緇衣之宜兮。”(《鄭風·緇衣》)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8]100鄭《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8]100“又何予之?玄衰及精。”(《小雅·采藏》)“王錫韓侯……玄袞赤易。”(《大雅·韓奕》),“玄袞”,畫有卷龍的玄衣,賜之以表示帝王恩寵。
“尚黑”的文化內涵另有佐證,《禮記·月令》“成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10]543《周禮·春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8]549鄭《箋》:“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除天子,一般貴族祭服也為黑色。”[9]897公卿大夫也常著黑色冠服,《論語·鄉黨》:“緇衣羔裘……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11]100《儀禮·士冠禮》:“巫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縪。”[12]5《禮記·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13]892《春秋谷梁傳》也有“天子丹,諸侯黑,大夫蒼,士黃”[14]88的記載。毛詩以為,此詩是一首“言武公作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的贊頌之詩,“言武公于此緇衣之宜服之兮,是言其德襯其服也。”[4]100
(二)女性服色的“尚白”主流審美及“尚白”的文化內涵
《管錐編》提到:“衛、鄘、齊風中美人如畫像之水墨白描,未渲丹黃。”[15]92“尚白”在所有性別、所有等級的服色中均有體現,在社會中具有審美共鳴,是女性服色的審美主流,如“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鄘風·君子偕老》)磋,玉色鮮明潔白貌;縐絺,細葛布做的單衣;“紲袢”,夏天穿的白色內衣。鄭玄注:“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縞衣綦巾,聊樂我員。”[4]188(《鄭風·出其東門》)毛《傳》:“綦巾,蒼艾色,女服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召南·羔羊》)“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齊風·著》)“碩人其頎,衣錦褧衣。”(《衛風·碩人》),朱熹注:“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姜孽孽”,毛《傳》:“孽孽,盛飾。”陪嫁女子與素衣莊姜對比,素雅代表尊貴。白色在男性服裝里并非主流,《詩經》中只有少數例子:“庶見素衣兮。”(《檜風·素冠》),“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曹風·蜉蝣》)
先秦時期的白色審美與后人的“白色忌諱”相反,“古人多素冠、素衣,不似今人以白為喪服而忌之也。古人喪服唯以麻之升數為重輕,不關于色也。”[16]153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以此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周代貴族婦女禮服多有白色,結婚時身披白紗。周代王后有六種禮服,其中晨衣為白色,用于朝見天子、接待賓客、祭祀、節日等盛大的歡慶活動等重要場合。[4]188
“尚白”審美蘊含尊貴、美、純正、品德高尚的文化內涵。《冠子·學問》道:“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陸佃注:“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17]322,“素絲紕之”“素絲組之”“素絲祝之。”(《鄘風·干旄》)毛《傳》:“《鄘風·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9]206“素絲五紽。”毛《傳》:“上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4]84《周易·正義》:“傳知素絲不為線,而為飾者,若線則凡衣皆用,非可美,故素絲以英裘,非線也。”[4]85《文心雕龍·情采》:“賁象窮白,貴乎反本。”[9]347“賁”是絢爛的美,而“窮白”則是絢爛又復歸于平淡,即所謂極飾反素也。殷商文化中,以白為尊,這是女性地位較男性更為尊貴的表現之一。夏代時期東夷部落盛行太陽崇拜,殷商繼承了這一宗教信仰傳統,白色成為殷商時代的天授之色。《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18]29《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鄭《箋》:“天之諸神,唯日為尊”,反映敬天意識。[19]795《禮記·檀弓上》:“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1]179《史記·殷本紀》:“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20]109《淮南子·齊俗訓》:“殷人之禮……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服尚赤。”[21]789女性的彩色服色僅見于貴族婚嫁時,《大雅·韓奕》記韓候迎親的場面描寫:“諸娣從之,祁祁如云。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其中陪嫁妾媵服飾比較鮮艷,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地位卑賤女性的服色特征。
(三)男性服色“尚赤”的主流審美及其文化內涵
“尚赤”,主要體現于男性服色,主要用詞為“赤”“朱”。《周易·說卦》:“乾為天,為圜……為大赤。”孔穎達疏:“為大赤,取其盛陽之色也。”[4]330《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個,乘朱路,駕赤馬。”孔穎達疏:“色淺曰赤,色深曰朱。”[19]482
《詩經》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曹風·候人》)“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小雅·采菽》)“素衣朱襮,從子于沃。”(《唐風·揚之水》)“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豳風·七月》)“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小雅·斯干》)“公徒三萬,貝胄朱綅。”(《魯頌·閟宮》)“大車啍啍,毳衣如璊。”(《王風·大車》)“璊”為紅色的玉,一說谷之一種,苗為赤色。[22]134“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蔥珩。”(《小雅·采芑》)方叔征伐楚國時,身穿朝廷命服及紅色敝膝。“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奭,赤貌。”[23]157“載驅薄薄,蕈茀朱鞹。”(《齊風·載驅》)“傳:鞹,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是路車有赤飾也。”[24]391“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小雅·斯干》)“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小雅·瞻彼洛矣》)《說文·赤部》:“赩,大赤也。”[25]491毛《傳》:“韎韐所以代韎。”韐是士所佩的韎,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9]855此外,裘衣也選用了赤色獸皮,“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秦風·終南》)
《左傳·桓公二年》:“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杜注:“尊卑各有制度。”[26]140《白虎通·紼冕》:“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27]271根據黃盛璋[28]45、楊寬的研究,在先秦時期,君王將不同的紅色衣物按照功德的高低賞賜給不同諸侯,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對不同階級進行分類,紅色被當做社會分類的標志與工具,在西周社會中起到了聚合與分離的功能,這與西周“錫命”與“冊命”禮有關。[29]479一方面體現了紅色在男性服色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從側面體現了奴隸社會日漸成熟和男性地位的提高。因此,紅色服色是周代階級高低的重要表現,作為禮的媒介和象征體系,有效地維護了王權的威信。赤色在較長時期內被推崇,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審美心理。
二、男性服色艷麗的特點及其審美原因
(一)從時空角度看男性服色
除黑、白、赤色之外,男性也常著綠衣黃裳和帶花紋的衣服。女性的彩色服色主要用于妾媵的服裝,在其他場合尤其是重要場合中,女性服色均以白色為主。
從時間上看,《詩經》時代的流行服色,受采集時代和狩獵時代服裝材料的影響:先民在采集時代中形成的認知,及“天玄地黃”的敬天觀念影響了人們的審美,代表植物與生命的綠色與代表大地的黃色成為了人們所推崇的服色;“綠兮衣兮,綠衣黃里。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邶風·綠衣》)“大車檻檻,毳衣如炎。”(《國風·王風·大車》)“毳”,是一種以細毛制成的衣服。“炎”,初生的蘆荻,“炎”衣的顏色為嫩綠。綠受到人們的青睞,原因有二:一、綠色代表生命;二、采集時代的審美遺留。“青,生也,象物之生時色也。”(《釋名·釋采帛》)[30]。玄與天同色而為上衣,黃色與大地同色而為下裳。“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31]383黃色經常用來作下衣,《周易》中有“黃裳,元吉”的說法。[32]6“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小雅·都人士》)。“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豳風·七月》)
“裘”等男性貴族服飾選用狐、虎、羔、貉皮等材料,體現了狩獵時代的審美。其中天子著狐白裘,諸侯著狐黃裘,大夫、士著狐青裘。[33]27當羔裘與狐裘同時出現時,以羔裘為貴。[9]391“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小雅·都人士》)“羔裘豹飾,孔武有力。”(《鄭風·羔裘》)人們對獸皮的審美可以追溯到狩獵時代,先民多從自然界中獲取動物皮毛、獸齒、獸骨等來制作、裝飾服裝,由于材料的限制,服色也有限,質量上乘可供保暖的狐皮、羊羔皮、豹皮便成為貴族冬衣的首選材料。《詩經原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34]140《周禮·天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鄭《箋》:“功裘,人功微粗,謂狐青麝裘之屬。”[35]172“狐裘蒙戎”(《邶風·旄丘》),狐皮紅中透黃,貴族男子崇尚紅黃色澤。“羔裘豹祛”,“羔裘豹褎”。(《唐風·羔裘》),“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小雅·大東》),“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豳風·七月》)
從空間上看,先秦男性服色中,黑色在夏代服色中較為流行,商代紅、黑兩色較為流行,周朝紅、黑、白三色均流行,黃色等其他彩色被用于官服。
北京平谷劉家河商代中期貴族墓出土黑紅色衣衾[36];滕縣前掌大晚商大型墓出土織物為紅黑白三色彩繪圖案[37]176。總體上看,商代墓葬遺跡,紅、黑兩色較為流行。
除此之外,男性常穿有色花紋服裝。“玄袞赤舄。”(《大雅·韓奕》)“袞衣繡裳。”(《豳風·九罭》)袞衣,衣上繡著龍,繡裳,是繡有花紋的裙子。《周禮》言五彩備謂之繡[32]214。“玄袞及黻。”(《小雅·采菽》)“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大雅·文王》)“黻”,是黑白相間斧形花紋。[9]855在重大場合中,人們用黑白兩色以示莊重。范曄《后漢書》:“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麻,觀軍羽。翟之文,榮華之色,用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38]3661
(二)先秦男性審美的歷史淵源
《詩經》時代是一個注重男性審美的時代,與后世“男素女艷”的服色審美不同,女性以素淡為美,男性以艷麗多彩為美,這不僅是對大自然的模仿,也是原始母權至上傳統文化的遺留。
先秦社會“猶保存母權時代之孑遺”[39]10,女性沒有完全從屬于男性,她們仍保留了一定的社會地位,持有一部分社會資源,一直到晚商之前,女性在政治生活中仍有一席之地,這是原始時代母系氏族文化的影響。男性地位較女性低,為爭取繁衍后代,男性通過將自己打扮得艷麗來吸引女性的注意,這種原始文化審美遺留影響下的服色審美,是《詩經》中“男艷女素”服色審美特點形成的主要原因。
《國風》以“美”中贊頌女子的作品有:“云誰之思?美孟姜矣。”(《鄘風·桑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鄭風·有女同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鄭風·野有蔓草》)“彼美淑姬,可與晤歌。”(《陳風·東門之池》)“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陳風·澤陂》)
以“美”贊頌男子的作品有:“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風·叔于田》)“盧令令,其人美且仁。”(《齊風·盧令》)“美無度,殊異乎公路!”(《魏風·汾沮洳》)“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唐風·葛生》)“誰侜予美?心焉忉忉。”(《陳風·防有鵲巢》)“抑若揚兮,美目揚兮。”(《齊風·猗嗟》)其他贊頌男性之美的有“其人如玉”(《小雅·白駒》)“公之媚子”(《秦風·駟馬鐵》)“燕婉之求”(《衛風·新臺》)
《詩經》中“美人”可同指男性與女性“美人”一詞最早考自《邶風·簡兮》“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鄭《箋》:“彼美人,謂碩人也。”[40]“美人”指身材高大的男性樂官。又如《陳風·澤陂》:“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云:“美人以指貞臣正士,非指女子之言也。”[41]130姚際恒解釋“美”:“‘西方’,西周;美人,西周王者。鄭氏以上‘美人’為周室之賢,下‘美人’謂碩人,非也。美人者,美德之人,猶言圣人、彥士之稱。后世以婦人色美,故稱美人。”[42]63《集傳》曰:“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故以美人目其君也。循后世之說,反謂以婦人指,可謂循流而忘源矣。《靜女篇》‘美人之貽’,謂美其人之貽也。”[43]25
“美”有相貌美麗的含義。《詩經》中的男性審美觀既對身材、五官有要求,也重視儀表修飾,服飾與儀容相得益彰,是體現君子美好品德的象征。通過外在美來幫助規范內在美,與周代等級制度的規范相符。在后世文獻中,“美人”已從“貞臣正士”變為“婦人色美”,這也從側面表明,無性別色彩的“美人”是專屬于《詩經》時代的特征之一,與后世相比,當時的女性更為大膽地歌頌男性之美,男性修飾儀表時也更為細致。“多彩”實則折射出周禮的莊嚴與規范,與社會上普遍推崇內外兼修的道德風尚。
結 論
綜上所述,較之女性服色,男性服色更加豐富且艷麗,這是《詩經》時代的審美主流。《詩經》中“男艷女素”的服色現象絕非偶然,作者意在通過描述不同等級、不同性別的服色差異來表現周代等級制度的秩序、規范以及審美意蘊。周人視品德的善高于服飾之美,《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叔孫氏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44]1127《禮記·表記》:“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發明而無其行。”[45]1477提出了君子服飾與儀容、言談、舉止的和諧。因此,《詩經》的服色代表著周代注重外在美和內在美統一的審美追求,體現了周代人平和、崇尚自然、理性、規范有序、推崇美德的文化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