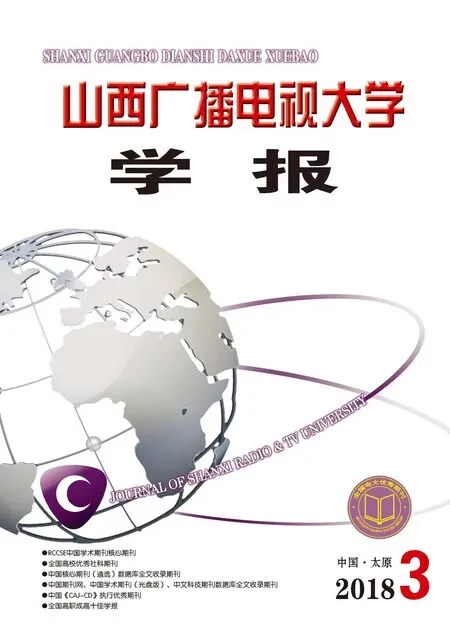試論離合法在宋詞中的運用
□藺若晨,霍慧玲
(山西廣播電視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7)
離合藝術是宋詞創作的一種藝術手法,歷代詞學家對此提出不同的見解。清代著名詞學家周濟說詞應,“講離合,面片斷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然而詞學家們對離合的藝術手法并沒有統一的定論。什么是離合?怎么才算是離合藝術手法的運用?對此疑問,眾說紛紜,側重不同,使得離合藝術手法成了一個復雜的問題。直至清代著名文藝學家毛先舒道出了詞的離合藝術 “不特難知,也難言”。知道離合藝術很簡單,但如何運用好離合藝術手法,卻很難用語言表達出來。因此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商量。縱觀歷代詞學家對宋詞離合現象的解析,大體可以概括為,離合法在宋詞中的巧妙運用,即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上,不應刻板,不應純客觀復制,而應有多種變化,有跳躍性。要做到:似虛又實,化實為虛,虛實相生、層層鋪述,情景交融,脈絡分明、點染結合,中鋒突破,側翼包抄、結構嚴謹,而又動蕩開合,呼應靈活,首尾照應、“物物而不物于物”,使客觀景物帶有作者本人的風格和個性、思想和感情,但又不能歪曲對象的面目,讓駿馬充分有騰躍的本領。離合藝術手法在宋長調慢詞中運用尤為突出,它可以利用長篇鋪述、記敘的優勢,發揮其一步一態,一態一變,層層深入的特點,不僅豐富了詞的內容,而且曲折回旋,意蘊深遠。離合藝術手法在宋代詠物詞和寫景抒情詞中的運用,就本人淺知,略談一二。
一、離合法在詠物詞中的運用
離合是詞的藝術傳達的一種技法,詞的體性特征對詠物的要求是曲折、蕩漾、唱嘆有情。離合技法即植根于此。劉熙載在《藝概》里說:“詞要放得開,最忌步步相連;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遠。”收縱自如,才能饒有蘊藉,不板滯。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劉熙載《藝概》稱起始“似花還似非花”句,可做全詞評語,蓋不即不離也,說出了這首楊花詞離合技法的典型性。的確,它不離題,又不死扣題目;既不脫離楊花,又不局限于楊花。寫楊花是“即”,也就是“合”。從開頭寫到“欲開還閉”,一直在寫楊花。“似花還是非花”花還是非花,開頭一句跳出了物象之外,因為它既像花兒卻又不像花兒,先用事實證明她那“非花”的一面,沒有人會對他的墜落產生憐惜之情,任由他離開本家在大路上隨風飄泊,假如真是個花,就不至于如此了。挽回一筆:雖然是非花,不過仔細想來倒是無情還有情,所以又不完全是“非花”,他也有自己的情思。想象它是一位閨中少婦,在暮春的天氣里,她因思念遠人而柔腸縈結,因天氣倦人而嬌眼欲開還閉。用楊花的紛亂,春愁無限比作楊花的紛亂;用楊花漫天飛舞,輕佻撩人,比做人慵懶,百無聊賴的情緒。“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暗合楊花,緊扣題目。“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這三句是離,接上面想象,寫這位少婦,如今正在入夢,夢見自己去找尋夫婿,不料還在中途,就被可厭的黃鶯兒吵醒了。“楊花”,即思婦,楊花仿佛就是思婦,隨思婦夢魂隨風飄蕩、乍去還回、欲墜仍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不恨與恨把傷別又擴大到傷春,是離而不離。(不恨是不止恨,恨是更恨,是進一層的寫法) 楊花非花,所以不必怨恨飛盡,但是此花飛盡,卻說明春光已逝,西園里的繁華從此紛紛飄零了,那確實很可惜的,又是離而不離。“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又回到了楊花,是即。原本是鋪天蓋地的輕盈花絮,經一場春雨后,便消逝殆盡,他們跑去哪兒了?思來想后無果,看見池塘里滿是細碎浮花,“柳絮如水化為萍”,原來他們被雨水沖刷成這樣,這便是他們的最終去處。如果以柳絮代表整個一個春天,那么春天的的三分之二,已經變成塵土,剩下的三分之一成為流水,一去不返。結拍“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即是楊花,又是離人淚,或說楊花變成了離人淚,是又離又即。回應上文閨中少婦那一段,只有思婦和游子的眼淚,才如此漫天蓋地,葬送了大好的春光!
我們以姜夔《疏影》詠梅詞為例,全詞為不犯本佳作。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全詞明明暗暗用典故,為梅花的姿態進行勾勒。“客里相逢…自倚修竹”,句中遞入作者自己。“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是借一個具體的古代美人比擬梅花,為什么要拿王昭君來比擬?問題很簡單,梅花是因寒而開的,使人很容易想象它是一位在嚴寒的北方呈現特有豐姿的美人;而昭君正是遠嫁匈奴,生活塞外,所以便拿來比附,以梅關合人,人又有梅花的特點,似離而不離。姜夔因為是詠江南的梅花,為了牽合眼前事實,所以用了“昭君胡沙”之后,立即筆鋒一轉,說昭君是“暗憶江南江北”,而且“月夜歸來”以后,便“化作此花幽獨”。花和美人結合成為一體了,合而不離。下片開頭用了另外一個梅花典故:“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梅花飛到翠眉附近,那是宋武帝女兒壽陽公主的故事。據說這位公主人睡在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在額上,成五色花,拂之不去,直過了三天才能洗掉,以后官女就學著在額上作梅花妝了。這是常見的梅花掌故,似離又合,由人想到“梅花妝”。“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意說梅花開在寒冬,春天本來不去管它,可我們卻不要象春風那樣。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是形容美人的風采。“早與安排金屋”——因為已連用兩個宮中美人的典故,這里就索性再用漢武帝“金屋藏嬌”的故事(又是一個宮中美人)來表示對梅花應該特別珍惜,由人又關合到梅花,由美人逝去的憐惜,而關合對梅花逝去的惋惜之情。以下,又由壽陽公主梅妝而想到梅花的飛墜。“一片隨波去”,寫出梅花逐水漂流,“玉龍哀曲”,因梅花墜落而想及《落梅花》曲,最后,轉到畫幅里的梅花,意思是說,等到梅花落盡,枝頭上看不見它了,假如要尋覓它的蹤跡,那只有到小窗上的橫幅之中,畫著梅花的畫圖,細細欣賞它那幽艷豐姿了。人和梅花,梅花墜落,《落梅花》曲,畫幅中的梅花等,都是由“梅花”引起,人與花、物與情在不即不離之間,詠物而不滯于物,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按照此詞思路我們可以知道,詠物詞中所謂“托物言志”和“無言志”,其實就是一種離合關系。詠物而不滯于物,言情而不拘于情;物中有情,情中寓物。讓人看出物外有興,物外有寄托,即“離”,而物外象,物外意,又注入作者的精神血肉,并且沒有脫離物的特點,兩者渾然一體,情由物生,寫物含情,運化無跡,即“合”。
二、離合法在寫景抒情詞中的運用
離合是一種離題旁涉與緊扣題目結合的表現手法。如果直寫主題(感情),內容就會顯得局促,太質實,沒有意境;蕩開筆墨,內容又會偏離題目,有離題之嫌。而離合技法就是要講究直寫與旁寫、正寫與側寫的和諧,側寫、旁寫都要做到服務于正寫,服務于主題,從而使詩詞意脈相連,似斷實續,搖曳多姿。這種手法在寫景抒情詞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以柳永《戚氏》詞為例,可見端倪。
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疏,井梧零亂,惹殘煙。凄然,望江關,飛云黯淡夕陽閑。當時宋玉悲感,向此臨水與登山。遠道迢遞,行人凄楚,倦聽隴水潺潺。正蟬吟敗葉,蛩響衰草,相應喧喧。 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凈,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綿綿。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 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留連。別來迅景如梭,舊游似夢,煙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長縈絆。追往事、空慘愁顏。漏箭移,稍覺輕寒。漸嗚咽,畫角數聲殘。對閑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
全詞共分三片。“念名利,憔悴長縈絆。”是全文感情基調。柳永早年赴汴京應試,“多游俠邪”與歌妓交往甚多,又精通音律,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于世,于是盛傳一時”,然而,這種生活卻給他進入仕途帶來挫折。因他在《鶴沖天》詞所寫到“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傳說,這首詞被宋仁宗看到了,這位“留意儒雅,物象本道”的帝王很不高興,在一次進士放榜時,一見到柳永的名字便一筆勾掉,說什么:“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便從此落第,直至年近花甲,才登進士第。于是,柳永四處漂泊,浪跡江湖,足跡遍當時大半個中國。此詞為羈旅行役詞,“念名利,憔悴長縈絆。”是全文感情基調。頭一篇寫景寫作者白天的所見所聞。第二篇寫情,寫作者“更闌”的所見所感。第三篇寫意,寫作者對往事的追憶,抒發了自己的感慨。開始“晚秋”天以下六句,寫的是靜景。晚秋季節,天下著小雨,菊花蕭疏,梧桐葉落,炊煙飄散,彌漫著。描寫近景關合著漂泊羈旅的凄涼心境,似離而合。“望江天”七句,寫作者登高遠望,展現在作者面前的曠野秋景,點明自己落寞情緒。遠景又關合著他凄楚的心情,似離又合。遠遞道上的行人是凄楚的,隴頭道旁的潺潺流水聲,也無心去聽,為什么凄楚和倦聽呢?“正蟬吟敗葉,蛩響衰草,相應喧喧。”蟬在樹上叫,蛩在地下鳴,發出的都是悲戚的叫聲。從眼前凄楚的景色,行走在遠道的行人,擴大到所有途徑此道之人亦是和我一樣的心情,似離而又不離。作者抓住微雨、蕭菊、敗葉、殘煙、飛云、夕陽、遠人、近水、鳴蟬、叫蛩這些看似“離”的物象,處處關“合”著漂泊羈旅的情懷。第二篇重點寫情。“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一個人孤獨客舍度日如年,苦悶極了。風冷了,露結成了霜,一直愁悶挨到夜靜更深。直接續寫羈旅情懷。“長天凈,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綿綿。夜永對景。”在屋內愁悶難挨,出外一看,長天凈如水洗,天河清澈見底,一輪皓月美麗動人,引人思緒綿綿。月圓人未圓,長夜難眠,我怎么能忍受的住呢?對月懷人,寫出了因為漂泊羈旅,未與心愛之人團聚的苦悶心情,層層深入,情思切切。似離又合。“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回想過去,名未立,祿未得,明為,在綺陌紅樓中,即生活在煙花柳巷,一年又一年混日子。續寫羈旅情懷,心情苦悶之由,似離又未離。第三篇,寫意。“帝里”以下九句,進一步回憶在帝京(即京城汴京)時候風光美好,與狂朋怪侶,在一起飲酒作樂;別后時光流逝,舊游似夢,好像是很遙遠的過去了。既然回不到過去,那就回想過去。因為厭倦了漂泊羈旅和過去歡情形成鮮明對比,似離又合。“念名利,憔悴長縈絆”,把他仕途失意,漂泊無著,旅況離愁,以及受名利思想侵擾的內心情懷,赤裸裸地揭示在讀者面前:“追往事、空慘愁顏。”回憶過去,更加愁苦,于事無補。過去一去不返,現實終究是現實,仿佛飲酒澆愁,愁更愁。又離又合,又合又離,渾然不分。“漏箭移,稍覺輕寒。”時間在推移,意識到有些冷意。畫角叫了幾聲,表示天要亮了。“對閑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回到房舍,熄了燈,仍是不能入睡。意味深沉,一步深似一步,令人不禁泣訴難禁。這首《戚氏》詞,成功地運用了離合手法。離,描摹景物、記敘時空之語;合,就是總題,是核心:“念名利,憔悴長縈絆。”點名這是本詞的要害,是主要意念,圍繞這個中心,寫秋色,寫“微雨”、“蕭菊”、“井梧”、“殘煙”,寫“行人”、“隴水”、“蟬吟”、“蛩響”,寫“長天凈”、“絳河淺”、“皓月娟娟”。因為追求名利,數年歲月,走遍名川大山,沒有盡頭,對羈旅行役生涯有切身體會,寫來景真、情真、意真,有了“念名利,憔悴長縈絆。”使得每一個片段之間都有了邏輯的鉤連所接,所以長篇直敘,無拘無束,舒卷自如,旖旎入情,娓娓動人。
吳文英的長調則常常被清人視為離合之典范。其《鶯啼序》(殘寒正欺病酒)一闋,就被清人譽為“通體離合變幻,一片凄迷”。全詞二百四十字,茲引如下:
殘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說春事遲暮。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 羈情、游蕩隨風,化為輕絮。 十載西湖,傍柳系馬,趁嬌塵軟霧。溯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倚銀屏、春寬夢窄,斷紅濕、歌紈金縷。暝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 幽蘭旋老,杜若還生,水鄉尚寄旅。別后訪、六橋無信,事往花萎,瘞玉埋香,幾番風雨?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楫桃根渡,青樓仿佛,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淡塵土。 危亭望極,草色天涯,嘆鬢侵半苧。暗點檢、離痕歡唾,尚染鮫綃,亸鳳迷歸,破鸞慵舞。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遼海沉過雁。漫相思、彈入哀箏柱。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
全詩共四段。第一段從傷春敘起,“殘寒”點出晚春時節,“病酒”點出自己眼下的境況。第二句,接著說:就在那還有寒意的時候自己害了病就因病而怕冷,因此把門扇都關起來。“畫船載” 到“吳宮樹” 是作者憶想之詞,是設想中的西湖景色,由追想西湖景色又遞入自己,輕輕把西湖和自己那段經歷虛籠一筆。似“離”又“合”。“念羈情、游蕩隨風,化為輕絮。”說自己天涯羈旅的愁情徘徊著,游蕩著,給風一吹,仿佛化成萬千飛絮漫天蓋地,簡直不知如何收拾了。此句是全篇之骨,即全詞之情感基調也。第二段,因“念羈情”:追溯西湖舊游、當時艷遇,時為往昔之十年,這十年中,時時系馬在柳蔭底下,感趁那湖上美好風光,期間偶遇女子“錦兒”,兩人話很多,情誼深厚。似離又合,因“念羈情”關合出一段往事。第三段敘寫別后情事,尤為交錯。“尚寄旅”寫今,說他不久就離開了杭州到了一個水鄉,而且在這里寄予了一段較長的時間;“訪六橋無信”到“幾番風雨”寫重返杭州。他再回杭州,到西湖舊地找她,她已經不在,訪來問去,毫無信息。過去的愛情就像落花萎地,原來的她已埋骨在西湖邊上,墳頭的花草不知經歷了幾番風雨。“青樓仿佛”三句,則回到現在,他記起了,那回分手時,他在壁上提了詩,以表惜別之情。此段地點變換多次,“水鄉”、“六橋”、“青樓”錯雜。時空、景物如此錯綜跳躍,此謂之“離”也,但萬“離”不變其中,始終關合著“念羈情”,念與佳人的情愫。第四段“危亭望極,草色天涯,嘆鬢侵半苧。”他站在湖亭上極目遠望,青草一直伸展開來,似乎直到天邊。那草色又使他回憶起她衣衫上的顏色,“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遠望望到的情景,又使他聯想到所思之人,離而有合。“暗點檢…破鸞慵舞”,感情又進一步擴展,他私下里想,身上還藏著她送的手帕,那上面既有別時的眼淚,也有歡情的唾痕。“殷勤待寫…彈入哀箏柱。”寫自己的哀情不知如何抒發。“傷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結拍表示深層的哀悼,并點出譜寫這首長調詞的用意。縱目那遙遙千里的江南,盡是傷心之情,盡管我可以譜寫一曲哀歌,像《楚辭 招魂》那樣,引來她的靈魂,讓她復活,然而,他的靈魂在還是不在呢?要是在,又在何處呢?全詞在敘事寫景上前后照應,更主要的是有“念羈情:念佳人。(與佳人約會、別后思念、悼念佳人)”這根主線貫穿全詞,使得每一個片斷仿佛一個畫面,每個畫面無論是景,無論是人,無論是物,將他們勾連起來,形成一部完整的故事,此謂之“合”也。陳洵稱此詞“通體離合變幻,接下來一片凄迷,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正與毛先舒所言本同末異。
由此可見,在寫景抒情類的宋詞中,所謂“離”,就是看似極盡描寫景物,極盡描寫時空變幻,或兩者交織描寫,極盡變化曲折;所謂“合”,就是情脈貫通全詞,把情寫到景物里,讓景物染上主觀色彩。“語離情合”可以說是對此類詞離合之法的概括。
三、離合與不犯本位
詞是否犯本位,也是“離合”問題。所謂犯本位,是清人劉熙載在《藝概》中提出來的。他說:詞以不犯本位為高。蘇軾《沁園春》:“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至君堯舜,此何事難。”語詞悲慨,充滿自信。然《蝶戀花》“墻里秋千墻外道,墻外行人,墻里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尤為含蓄。劉熙載說寫詞如果直截了當地把感情表白出來就是犯本位,用比興手法含蓄地抒情就是不犯本位。蘇東坡《沁園春》中說“此何事難”,即沒有得到朝廷重用,對于“至君堯舜”這一偉大功業,他還是充滿這信心和希望,希望像杜甫那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實現自己的“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的政治理想,這都是議論式直言其事。而在《蝶戀花》里,用比興的手法借“佳人”曲寫胸中郁結之情,說自己對朝廷一片忠心,卻落得遠謫嶺南的下場,這不正是“多情卻被無情惱”嗎?而他的境遇也正像被風雨摧殘的柳絮“枝上柳綿吹又少”,“也無人惜從教墜”,希望得到朝廷重用,從而“再使風俗淳”。
劉熙載主張,寫詩詞都不應該直說,不應該從正面直寫,應該從旁、烘托、應旁敲側擊地抒情,不可直言其事,這就叫做不犯本位。如:辛棄疾《木蘭花慢·可伶今夕月》和《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兩首詞都是曲折表達自己在政治上壯志未酬的苦悶,而沒有正面直截了當地寫自己的情緒。《木蘭花慢》全詞用比興手法,用一輪滿月象征大宋江山,面對中秋明月而對大宋江山表現出惆悵滿懷。“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瓊樓”,作者想象月宮被長鯨破壞,暗含對猖獗的黑暗勢力迫害國家而表現出極度憤慨。結尾“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兩句,描寫烏云散去,月亮光明如初。實則提出,蕩清黑暗勢力,還清明世界。全篇以月發情懷,寄托遙深,含蓄蘊藉。《水龍吟》上篇寫登臨之感,通過寫景抒情,表現出滿腹悲憤,但沒有回答引起悲憤的原因,只是營造種種引起悲憤情緒場景,側面描寫,層層深入。這就叫不犯本位,而有離合之妙。同樣的思想感情,到岳飛的筆下,卻犯了本位。《滿江紅》上闕直接敘寫自己:我滿腔熱血,感到怒發沖冠,我靠著欄桿,看著風雨瀟瀟,以后又停止了,這個時候,我抬起頭來遠望,同時還仰天長嘯,我雄壯的胸懷再也壓不住了。三十歲了,功名還未立,我已不在乎了。我渴望是晝夜趕路,馳騁沙場,功成名就,不要讓少年頭輕易變白了,到時候只能空悲切…全詞直寫其意,明白如話,沒有曲折,沒有隱匿,這就是犯本位,即無離合之妙。
宋詞中的離合藝術手法的運用,不止用于詠物和寫景抒情類詞中,它是運用是多方面的,宋詞詞家根據寫作情況,明確主題,靈活變換形式,采用各種離合寫作手法曲折表達自己情感,不一而足,從而使詞的表現手法豐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