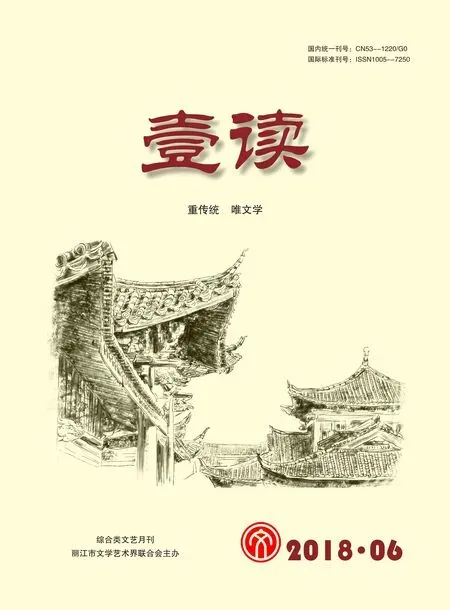住在群山之中(組詩)
李永天
曠野
這么大的地方
騎馬也跑不到盡頭
種上玉米
種上燕麥
爺爺高興得合不攏嘴
種上草烏
種上續斷
有病的人欣喜
我說由于它荒涼
讓野兔無人侵擾
身后有笑聲傳來
回頭不見人
此時此地
什么都是自由的
住在群山之中
我喊媽要小聲點
我吹口哨要小聲點
我喚狗要小聲點
我累了
嘆息要小聲點
我向你表白要小聲點
大聲了
回聲不斷
整個群山都知道
還以為我瘋了
山居筆記:臘月
魚一輩子困在河邊魚塘
酸菜干了依然酸
甘庶可以烤出酒
一條土狗
名字叫黛安娜
有人朝一棵老樹磕頭
在老樹上獻上肉和飯
樹是神
樹是一個逝去的老人
頑石奏樂
石頭
你們幾個
自己壓著自己的身影
沒有腳
卻說好了
一起去大海
在山頂時
在鷹的腳下
高過山
不說一句話
有的住著神
有的藏著獅子
有的包裹著一幅畫
等著石匠開鑿
一起蹦出來
這么安靜
是不是在準備
一起奏一曲
天麻
我去哪兒找你呀
植物界的
地下工作者
不長苗
不開花
羊吃不到
阿芝遠嫁你不知道
村里死了人也無法通知你
在地下
兒孫滿堂你不聲張
爛掉也不露聲色
草。你要一年年的長
核桃樹的影子
壓不彎河水
風一陣陣地吹
在一生的時光里
塵埃終會落下
我有沒有告訴你
草。你都要一年年的長
讓我的高原綠著
我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在你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
母親汗流滿面
從她背回的柴上
抽下一把山茶花
叫我找個舊瓶子插上時
我看到一個遼闊的高原
兒子在沙中
堆出他的城
讓外星人有房子時
我看到一個異度空間
我夢見月亮哭著
要照到陰山時
我看到蒼穹的力不從心
你失望地轉過頭時
我從你的眼神里看到我自己
一只沒有家的鷹
在天空孤單地流浪
鴻門口
江水有巨大悲哀
只是把巨石
在江底翻滾
沒有聲響
那年一船人被江水吞了
頭發都不見一根
只有翠翠的嫁妝
一床紅被面
在幾公里外出現
漂過木頭的江
沙里有黃金的江
我畫下這個金沙江廢棄的渡口時
加了一條
破舊的小木船
船頭的鳥
睡著了
素描:母親
年輕時最冷的天
敢赤腳走過河
用沒底的竹籃
在羊坪水庫淺灘捉魚
在方家村,能用大斧頭
砍倒大樹
我們記得
在松腦子火塘邊
老爸說
風濕痛的時候
就要變天了
我們只看電視上的
天氣預報
老爸的天氣預報
媽媽一個人
篤信
我們記住
媽服侍三個老人
二十幾年
直至他們進入墓地
一個是奶奶
另外兩個是孤寡老人
媽不會唱山歌
偶爾喝一口酒
吸一支煙
棗紅馬
留下一片荒野
讓棗紅馬
跑得汗流浹背
踏過最軟的草
走過最硬的石頭
仰天長嘯
趕馬的外公罵
這牲口
站著做夢的棗紅馬
不進村投宿的苦行僧一般
固執地站在遠處
寒風中
拒絕靠近
暗淡
此刻暗淡的
除了遠處的老松
還有父親的眼神
身后長滿野草的路
是夕陽丟在大地上的繩
沒有說一句話
暮色中
遠處小河的悲傷
沒有聲響
有蝴蝶的井
水的父親告訴剛從石頭上
滴下的水
以其游走
不如一頭撲在一個地方
汲取大地的清幽
冬天不結冰
于是有了一口井
有蝴蝶在井欄停歇
十萬火急時
可以沉溺其中
獲得另一次生命
井就人一樣活了
井看見
丟了耳朵的人
唯有愛情
才能縫合他的耳朵
對鷹吹笛
俯看
一只野兔
一個人
都是一個黑點
鷹啊!今夜你睡在
哪里
吹一曲舞曲
鷹抖動翅膀
像極了
一個孩子在學跳舞
對鷹吹笛
不需要顧及
人的皮囊與靈魂
鷹不想聽
馬上飛開
你只能看
鷹擊長空
錯亂的時鐘
亂撥時針
隨意停駐
看到一只狗
銜著樹枝
朝一個方向
狂奔
錯亂的時鐘
把一個正午叫做清晨
時鐘錯亂的間隙
沉默的老人
看著一只槍
仿佛只要老人示意
槍會突然
響一聲
誰在拉住時鐘
指向自己的青春時光
望遠鏡
幾個人正在
虔誠地搬運自己的影子
看到說話的姿勢
聽不到聲音
讓遠處模糊的驢
清晰一些
我的望遠鏡
讓我望見了
愛情是一個
懷抱牛奶
奔跑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