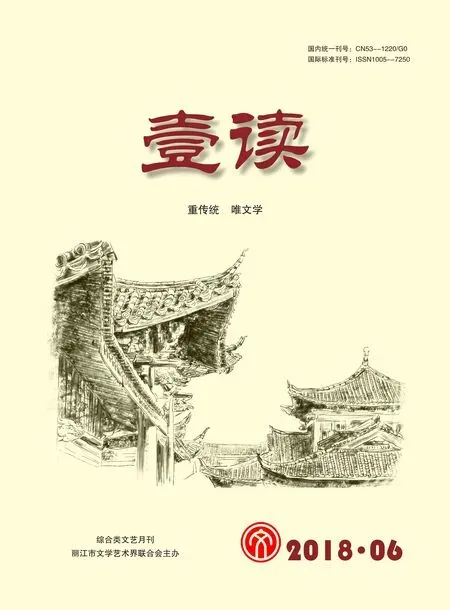遇見王祥夫
羅開華
相遇是緣。
一次與他的普通相遇,竟然在我的生活中濺起朵朵浪花,讓我心動、喜悅。他時髦的形象、燦爛的微笑、詼諧的話語、總是在我耳邊縈繞。于是,我記下了和他相遇的過程。
2016年12月 25日,在歡迎“全國著名作家永勝行”的晚會人員中,就缺王祥夫。之前,我似曾見過他,但不了解他。
第二天,我與隨行人員去六德他留山采風,吃中午飯時,一陣“嘩嘩”的掌聲響后,他出現在了我眼前。他著一件黑色長衫,面料很粗糙,或許是純棉的。他最吸引我的,不是圍在脖子的紅色圍巾,也不是紅撲撲的臉蛋,而是高鼻梁上架著的墨鏡。那圓圓的、小小的、漆黑的鏡片后面,好像藏著一雙“色咪咪”的小眼睛,有點兒逗人發笑。好家伙!我的大腦里突然閃現:電視劇、上海灘、黑老大等字眼。
“對不起大家,我遲到了,先罰一杯”。說完,他雙手舉杯,向大家致歉。接著,“咕嘟”一聲,一杯他留人(云南少數民族,彝族支系)的自釀酒就下了肚。他左手拎著酒壺,右手拿著酒杯,向每一個喝酒的人敬酒。當他來到我身旁向我敬酒時,我只是禮貌性地呷了一小口,他卻“咕嘟”一聲,又下肚了。知道嗎,那一杯足足有一兩多呢!他喝酒的動作是那樣地優雅、別致、瀟灑。
午飯后,我們繼續到永勝瓷廠采風。走在瓷廠的大道上,他留烈酒(他留人自釀的白酒)把他醉得步履蹣跚,以至于要人駕著才能行走,早已沒了剛喝酒時的瀟灑形象。
我盡量把照相機的焦點從他身上挪開,生怕他那“丑陋的形象”(當時我就是這樣想的),侵占我的內存。
我們參觀、交流、采訪。從一個車間走向另一個車間。當來到展示大廳時,瓷廠廠長已經準備好筆墨紙張靜候多時了。聰明人,就是能夠提前預知、提前準備、提前行動的人。瓷廠廠長就是這樣一個人。原來,他早已準備好筆墨宣紙,要請名家們為瓷廠題詞了。只見他恭恭敬敬地用雙手把毛筆遞給云南著名詩人雷平陽,雷平陽欣然寫下了“山城瓷都”四個字。一陣掌聲后,王祥夫也在眾人的簇擁下也出場了。我挪開照相機,靜靜地等待這個“醉漢”怎樣弄出“笑話”來。
只見他從雷平陽手中接過毛筆,顫顫巍巍地來到桌前,用左手按住紙的一角,在潔白的紙上寫下了“瓷都之光”四個大字。他筆勢雄勁、姿態橫生,字跡既像脫韁駿馬,又像蛟龍飛天,哪有酒醉的樣子呀!我從一陣又一陣的掌聲、喝彩聲、歡呼聲中驚醒,急忙把照相機的焦點對準他,便“咔嚓咔嚓”地按下了快門……
于是,我重新認識了他。
第三天,按日程安排,我們上午先去程海螺旋藻廠參觀。坐在去程海的車里,他那以眾不同的形象總在我腦海里閃現,我感覺,似乎之前在哪里見過他。我拿出手機,在百度搜索框里輸入“王祥夫”三個字,“王祥夫簡介”便躍入眼簾: “王祥夫,男,1958年生,遼寧撫順人,中共黨員,大專文化。歷任大同市照相館攝影師,中共大同市委黨校講師,山西文學院專業作家,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云岡畫院院長,當代畫家。” 嚇著我的,不是這么多頭銜,而是他的文學作品。如長篇小說《米谷》《生活年代》《百姓歌謠》《屠夫》《榴蓮 榴蓮》等七部;中篇小說集《顧長根的最后生活》《憤怒的蘋果》《狂奔》《油餅洼記事》等五部。散文集《雜七雜八》《紙上的房間》《何時與先生看山》等六部。短篇小說集就多得無法一一列舉了。他的獲獎作品同樣多得嚇人,如散文《荷心茶》、中篇小說《顧長根的最后生活》分別獲得第一、二屆“趙樹理文學獎”散文獎和中篇小說獎第一名;他的短篇小說《上邊》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第一名。長篇小說《種子》英譯本還獲得了美國丹佛爾獎。總之,他的文學獲獎作品多得難以一一累述。
突然,行進著的車變得顛簸起來,我只好收起手機,把目光投向車窗外。我把記憶的“膠片”在大腦里進行幾次回放,終于想起來了,原來,在“2014國際·麗江大家高峰論壇”上,他為我們作過報告。車繼續顛簸著前行,不知不覺中,已經駛向了通往程海保爾螺旋藻廠的土路上。
我們來到保爾螺旋藻廠,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從生產車間到深加工車間,從包裝車間到銷售平臺。最后,在會議大廳傾聽程海保爾集團董事長譚國仁詳細介紹產品情況。由于我是這次活動的攝影師,必須用影像記錄活動的全過程,所以,我只能走在整個隊伍的最前面。奇怪的是,在隊伍前面,很難見到他的蹤影,不知藏哪兒了。離開程海保爾螺旋藻廠,我們又趕往清水古鎮,去那里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了解一下邊屯的那段歷史。清水古鎮,勘稱“麗江第一村”。歷史上的清水村是重要的交通驛站,歷史資料記載,明永樂二年時,云南布政司在瀾滄衛設驛站,一個設在衛城北勝,另一個就設在清水驛,使這里成為麗江唯一一個官方鄉間驛站。從邊疆沃土拓荒之早,中原漢文化積淀之深,清水古鎮都堪稱云南邊屯文化重鎮。一村四進士就出自這里。在參觀“土司所”時,他似乎很喜歡古式木結構中的“雕龍畫鳳”,特別是對那幾塊雕刻古文字的踏步石很感興趣,一邊彎腰仔細觀察,一邊還和作家們議論著什么,好像在尋覓中原文化留下的遺跡。在行至一段土胚圍墻時,他又被上面長滿的植物所吸引,連連問隨行:“這是什么、這是什么?” 隨行只能搖頭說不知道。他卻拉起一串仔細觀察,如癡如醉,不愿離去。有位本土作家告訴他,那叫“爆竹花!”聽后,他稱贊說:“這名好!紅彤彤的,喜慶、形象!”
離開清水古鎮,是去“永勝·云南邊屯文化博物館”參觀。在“毛氏宗祠”里,他對毛澤東祖先從江西、湖南充軍到云南永勝毛家灣的過程了解得特別詳細,總是緊緊跟隨講解員認真聽講,還時時向講解員提問。
程海湖,又名黑伍海,是永勝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滇西第二淡水湖,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世界上天然生長螺旋藻三大湖泊之一。由于自然條件得天獨厚,對它的開發與保護一直困擾著當地政府。把全國著名作家邀請到這里,是請他們來出謀劃策的。走出“邊屯文化博物館”,作家們在程海湖邊吃完有程海魚的中午飯,大家興致勃勃地登上程海管理局的巡邏快艇,環湖繞一圈,以加深對程海湖的印象。
藍天、白云、溫柔的陽光、碧波蕩漾的程海湖,時時有海鷗從巡邏艇上空掠過。這么迷人的景致,讓作家、詩人如癡如醉。他們紛紛登上二層船沿,要我幫他們拍照留影,在云南,在永勝留下他們美好的一瞬間。盡管拍留影讓我忙前忙后,我卻時時留意他的動向。但在二層船艙和甲板上,總是尋不到他的蹤影,他好像就待在一層船倉里。本想在船上與他合影留念的,只能留下遺憾了。
下午四時,我們來到了三川翠湖村。三川,因有盟川、匯川、濟川三條河流流經壩子而得名。翠湖,是因芮官山腳下九股泉涌出相匯而形成的。這里最美的季節是夏季,萬畝荷塘碧波萬頃,紅白蓮花隨風搖曳,不是江南,勝似江南。明代郡人羅俊明詩云:“九龍潭水靜無波,堤畔人家總種荷。霞映一灣朝日淺,花香十里千風多。沙明藻綠青蒲間,鷗宿魚游白鷺過。一副吳宮新制錦,數聲越女采蓮歌。”
翠湖的田園風光,小橋流水特別美,作家詩人們來到這里便三三兩兩分散開來,讓我的拍照記錄無從下手。于是,我索性丟下相機,也去“自由”活動了。走出“農家樂”不遠,我卻看見他正和幾個在河里洗蓮藕的婦女說話。他說: “這藕真白呀,我從未見過。”
“還可以生吃的!”一婦女說著便拋了一根給他。他接過后,先是看了看,然后又聞了聞,最后真的生吃了起來。還連連說:“甜,好吃,真好吃!”
離開洗藕的婦女,他朝荷塘走去。他走到荷塘邊,對著大片大片的殘荷發呆……
晚餐時,他被翠湖農家樂里的“荷花宴”驚呆了,連連稱贊:“好看、好香、好吃!”那晚,他好像又喝多了。
12月28日一大早,他又神采奕奕地站在了出發前的車子旁,絲毫沒有“醉”的樣子。
我們一起又去了魯地拉電站、濤源的“金江古渡”等地參觀。下午,我們回到了永勝縣城,并在賓館會議室參加了由永勝縣委宣傳部組織召開的座談會,作家們對四天的永勝行進行了總結性發言,他在總結會上也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寫文章就是寫自己,寫作是一門科學,是一門深奧的學問。作家要把自己當作最普通的人深入民間、深入生活。寫作一定要接地氣……”座談會結束,“全國著名作家永勝行”活動圓滿完成。
對于永勝,我在后來他寫的《永勝散記》中看過這樣的描述:“永勝真是個好地方,這里的土地好像有無窮的力量,一路走來,割過的稻田里都已經長出了青青的蠶豆,雖說是在云南的永勝,但眼前的一切卻實實在在讓人想到江南。這就是永勝給人的一種錯覺。或者說永勝這個古老的地方藏著一個江南。雖然時間已經是十二月的時光,而這里,觸目都是一片青翠。”
12月29日,我與作家們一起去麗江。根據麗江市文聯的安排,由我繼續陪同作家們在麗江的日程。中午12點,我們抵達了麗江。
在麗江,沒有官方安排活動計劃,而是受云南詩人雷平陽之邀,直接驅車去參觀他原在單位“云南建工集團”在麗江的承建項目“文海水庫建設”項目。
文海,位于麗江玉龍雪山主峰西南麓,平均海拔3180米,是云南麗江拉市海高原濕地省級自然保護區的片區保護區之一。面積676公頃,其中,水域(文海)僅160公頃。麗江沒海,有很多人沒見過海,于是,把湖都稱作海,如程海、拉市海、文筆海、九子海等。其實,它們只不過是很小很小的湖,有些只是小水潭而已。
文海由古老的冰蝕湖演變而成。湖水有點奇怪,秋冬季為豐水期,春夏季卻為枯水期。這里也是麗江的旅游景點之一,春夏季有很多種呼不出名兒的野花盛開,芳草茵茵,引來很多游客。兩年多來,經工人的建設,堤壩升高了,蓄水面積一直朝雪山方向延伸,給人一種拉近了雪山的感覺。
作家一行來到壩堤,一個個和雪山合影,和雪山下的圣水合影。唯獨不見王祥夫。我四處尋覓,想和他合影留戀,可還是見不到他。
12月末的文海,因受雪山的影響,氣溫已經很低了,即使是在大白天,也只會在4-5度的樣子。由于太冷,我們在大壩上沒堅持多久,只好往回趕。
我們來到云南建工集團麗江文海水庫建設項目部,那里的工作人員已經發燃炭火,等待我們吃燒烤了。他和工人一起忙著為我們準備吃的。只見云南著名詩人老六樂呵呵地跑到我們面前說:“大家一定要多吃點多喝點哦,這可不是普通牛肉,是高原牦牛肉哦!”我們按照喝酒的類別不同分別坐下,我和喝啤酒的坐在一起,他和喝白酒的坐在另一邊。
我們吃著、喝著、聊著。寒冷的只不過是季節,而人情和心境卻是溫暖的。大家吃飽喝足后,三三兩兩圍著炭火繼續閑聊。他卻隨著夕陽向東不斷前移的光,獨自退到了房檐下,感受著即將消失的溫暖。他的眼神似乎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又從我眼前閃過。于是,我聽到了他的招呼聲:“攝影的,你過來。”聽罷,我朝他走了過去。
他招呼我坐在他身邊,并和我聊了起來:“其實,我也很喜歡攝影,在一家照相館待過很久。”
“那您的攝影技術一定很棒?”我說。
“也不一定,攝影和畫畫,我更喜歡后者。”他說。
我們倆就這樣聊著,除了攝影和畫畫,聊得更多的就是文學。他說寫文章雖然沒畫畫賺錢,但也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生活的日常。他說他還喜歡收藏,特別喜歡奇石、怪石。喜歡養花、種草、還喜歡小動物……
我被他的勤奮所感動,更為他豐富多彩的生活日常喝彩。
夕陽躲進了西山,失去陽光的高原不僅僅只是寒冷,而是孤寂、疼痛、恐懼。
天空很快暗了下來,我們匆匆離開文海。
回到麗江古城,氣溫升高,大家都有了精神,于是,一起去古城里喝茶。
古城里的燈光很亮,雖然不是白天,但有些地段的光亮還是顯得十分地刺眼。古巷里的行人不少,但步履匆匆。
我們選定一家離大石橋最近的小酒吧,這樣,既可以看到橋上行人的模樣,又可以傾聽到潺潺的流水。喝著啤酒、普洱茶;聽著音樂、磕著瓜子。讓生活的節奏慢些慢些再慢些。
他喝啤酒的頻率十分的緩慢,與喝白酒判若兩人。他點了一首慢節奏的歌。我無暇聽,只是看他嗑瓜子的樣子:拿起瓜子,先慢慢剝殼,一粒、兩粒、三粒,然后再一粒一粒丟進口里慢慢咀嚼,再后就是呷上一小口啤酒,給人一種特別享受的感覺。
嘩啦啦的雪山清泉穿過大石橋,在我們身旁流淌,像電視連續劇《木府風云》里的動人故事,又像是忽必烈與阿良“夜分手”的惜別話語。總的看來,它好像在訴說著麗江納西族五千年來的歷史變遷。
第二天,在麗江的告別午宴上,他又和大家一起相互敬酒,說著五天來,在麗江、在永勝的各種真實感受、說著惜別的話語……
午宴結束,我送他到了麗江機場。在機場VIP候機室里,由于酒的原因,他靠在沙發上睡著了。我拿來毛毯蓋在他身上,候機室里,立刻響起了他并不刺耳的鼾聲。
大約三十分鐘后,他醒來了,我們又聊起了關于人生、關于家庭、關于文學、關于書法、關于繪畫等話題。接著是握手、是擁抱、是揮手,是藏在心里還來不及傾訴的話語!接著是匆匆離去的腳步、是漸漸消失的背影、是飛機起飛時的轟鳴。接著是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一直縈繞在耳邊的他寫的《永勝散記》中那句:
“永勝,比如此刻,我很想遠遠喊它一聲,就像喊我的一位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