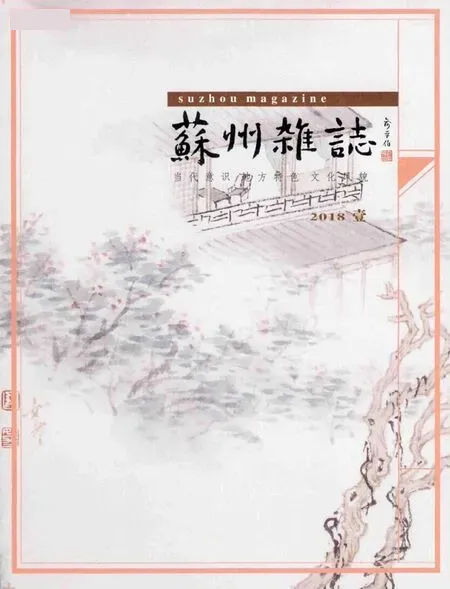望子成龍
李正
幾把母親留下的壺,卻也留下了一些抹不去的記憶。
這是些幸存的茶壺,幸存的原因也許因為它們都不是什么大家珍品,所以能遺留下來。就像蘇州的“冷水盤門”一樣,當初為人冷落,卻能完好地保存至今。
我的母親是攻文武老生的“角兒”。除了在臺上演戲,她老人家幾乎沒什么其他的嗜好,最多的時間就是花在品茶上。因此,家里林林總總的錫罐里,放著她從各地巡回演出帶回來的各類名茶,品種可謂繁多。但是最多的就是皖、浙、閩一帶的特產,什么六安的“瓜片”、黃山的“毛峰”,西湖的“龍井”,安西的“鐵觀音”,卻很少看到她喝云南的名茶“普洱”的。她泡茶不但用水講究,定期讓人到深山裝回幾桶清澈的泉水,還嚴格實行“一壺一茶制”,泡過“猴魁”的壺,她絕不會拿來再泡她年老時唯一愛喝的“茉莉花茶”。這還不包括她專門喝參湯的壺、喝中藥的壺。因此,她擁有的各類壺具就特別多。
然而,母親的茶壺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大多數都是她的“粉絲”們送的。她每到一個場口一了解當地的戲迷喜歡聽“馬派”的,她就演《失空斬》;喜歡聽“高派”的她就上演一出《轅門斬子》;喜歡看“麒派”的,她就來一出《徐策跑城》。戲路廣也給她招來了人緣之廣。同樣,戲迷們也在了解她,知道她愛品茶,便往往在喝彩謝幕之后到后臺送上一把壺,以表敬意。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名家制作的精品之壺。
也許是“角兒”的緣故,她所用之壺總是先揀一些有名頭的好壺。每每上場演戲,她的“跟包”大寶子總捧著把茶壺在下場口等著。這茶壺除了“跟包”之外,是斷然不允許其他人動彈的。即使我的姐姐妹妹包括我如果渴了去啜這么一口水,那她馬上就會當眾摔了這把壺;“跟包”一時半會兒地離開了那把壺,她也會一砸粉碎。哪怕是楊彭年、陳鳴遠制作的壺她都在所不惜。這也許就是所謂的“角兒脾氣”吧。可是除了摔壺之外,很少看見她會發雷霆之怒的。舞臺之下,她幾乎整天架著一副眼鏡在看書,手里總離不開一把壺,儼然就是一個涵養到家的“老夫子”,待人謙恭有禮,是看不到她摔壺時的那股橫勁的。后來才知道,她是怕有人毀了她那“一句一個好”的亮嗓門。她拖兒帶女,得生存。
有一次,我想喝茶,于是很識相地自己擎著一只杯子問正在看書的她:“娘,我想喝茶,您說我泡哪種茶最好呢?”
她微低著頭,眼睛從鏡框上端越過來注視著我半晌,才打趣道:“你也快三十歲的人了,是該捧個茶壺擺出個爺們樣了。”說罷,她朝壺架上一指:“別拿玻璃杯泡,去揀把茶壺吧。”
我順從。揀了把紫砂加彩的壺端在手中,等待著她回答。她看著我手上的茶壺,微微點頭:“這把壺泡過太湖西山的茶,你先試著品品‘碧螺春’吧。”
我徑自找著“碧螺春”的錫罐。
而母親卻兀自嘆息:“都知道蘇州的‘碧螺春’如何有名,卻哪里知道早在唐朝末年時,洞庭西山還出過一種叫‘吳郡金’的貢茶,可惜我也只喝過這么一回,它竟匯集了‘大紅袍’的回甘雋永、‘龍井’的香馥如蘭、‘碧螺春’的味鮮生津、‘毛峰’的滋味醇甜……真能讓人回味無窮啊……”“吳郡金?”本來就對茶文化一無所知的我,自然一片茫然。
她放下了書本,又像平時那樣,一旦跟我講起那些歷史上的趣聞軼事就興趣盎然:“那是一種紅茶。我記得當年他們告訴我,原料也是洞庭西山上‘碧螺春’的(清)明前嫩芽。可是采摘下來時正好碰上唐代末年天下大亂。莊園地主忙著逃難,于是就叫家丁把金銀細軟和茶葉兒都藏在一口千年古井深處井壁旁的暗窖里。這暗窖用蛋清、香糯、松花粉砌成,既阻斷了濕氣,又保住了清涼。到了端午節前他們回家拿出這些茶葉兒一看,居然嫩鮮如初,當下就想烘焙炒制。誰知從林屋山來了一個老道阻止了他們,說:“這茶葉產于兇時,幸而藏于與第九洞天相連的通靈之處,才戾氣全無,若能放在端午節正午之時,外以雄黃繞工場四周,中以麝香屏之氣味,傭工以冰片凈手揉制,必定清香撲鼻,滋養五臟,祛除百毒,即使一葉一金亦在所難求”。”
“嗯……怪不得,它產于吳中,所以取名‘吳郡金’。”我恍然大悟。
母親微微頷首,又嘆了一口氣:“可惜,這茶稱得上是天下一奇,但生不逢時。后來五代十國戰亂不已,它雖然歲歲進貢朝廷,卻記載全無,只留下了一個傳說。”
“那……您又是怎么喝到這種茶的呢?”
“緣分。那年還沒你呢,娘帶團到洞庭西山演出,有兩茶農都是戲迷卻又沒錢,我還是讓人把他們請進了劇場。他倆看了我的戲后第二天大早又來了,足足在劇場外等了幾個時辰說要見我,還說有東西要當面交給我。你知道娘起床晚,洗漱完后人家告訴我有這么回事,我也納悶著,但還是出去見了他們。那其中的一個漲紅了臉,從懷里掏了半天,才掏出了丁點大的一包‘吳郡金’,千叮嚀萬囑咐地告訴我這是用祖傳秘技制作的好茶,還你一句我一句地說了那個故事。唉,農民老實啊,也不知他們是否還有傳人……”母親說到這兒戛然而止,兩眼炯炯:
“你知道娘跟你講這個故事的含義嗎?”我茫然,惶恐不安地試探:“母親是要兒去鉆研‘吳郡金’制作的絕技?”
母親搖首:“你錯了。天下名茶這么多,你能學得過來嗎?所有的‘名、特、優’,都是人家自己努力打造,打造自己的名、自己的品,要能讓別人翹首以望,就像那一壺‘吳郡金’一樣,要留給別人一種想頭,這就是價值。自然,學只是其中的一步,關鍵是要有自己的、別人不可替代的獨特建樹,這當然談何容易。但是一個人要有志氣,不管干哪一行都要出人頭地,即使像娘這樣當個演員,記住:一定要站在舞臺的中間!”
“娘,兒子記住了。”我鄭重地點了點頭。
但母親卻仿佛意猶未盡,繼續著她難得一次用心的訓誨:
“三十而立。這種‘立’絕非是泛泛而談的自立生活,自己一點賴以養家糊口多弄幾張鈔票的所謂家業。而是要立出自己的名聲,立出自己的品牌!要有這樣的氣概——‘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
我無語。我知道母親這是在“望子成龍”。
……
又是三十年快要過去了。我沒有“成龍”,但也沒有“成蟲”。然而,回首檢討我確實在努力了。如今年近花甲,甲胄全解,也只得自詡為過著野鶴閑云的生活。于是,我只得將母親的這番教導連同她老人家留下的那幾把并不值錢的壺,傳給了我的兒子。
還是一樣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