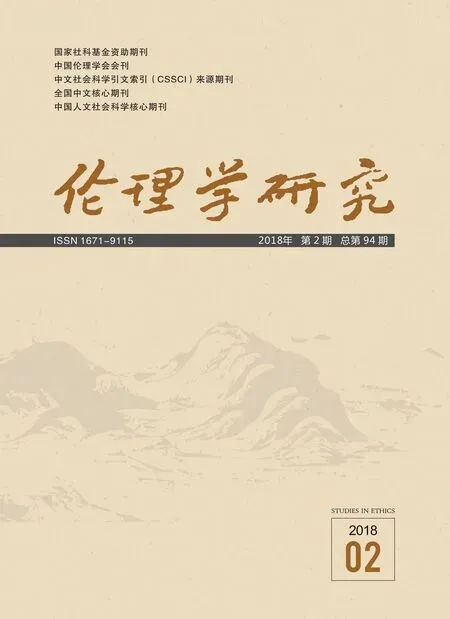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的基因信息隱私問題及其倫理方面
呂耀懷,曹 志
一、基因信息及其大數據樣態
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條件下,基因信息以數據的形式被保存在各種各樣的數據庫中,呈現出所謂“大數據”的樣態。當然,基因信息不完全等同于基因數據,例如,人們往往通過信息與數據之間的關系來區分二者:數據是未經加工、未經處理的信息,而信息則是為使其能夠為其接受者所用而進行過處理的數據[1]。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對基因信息與基因數據往往并沒有給出或沒有必要給出清晰的、有效的區分。因此,本文中的基因信息概念與基因數據概念是在大致相當的意義上使用的。什么是“大數據”呢?國際數據中心IDC是研究大數據及其影響的先驅,其在 2011年的報告中,對大數據給出了這樣的界定:“大數據技術描述了一個技術和體系的新時代,被設計于從大規模多樣化的數據中通過高速捕獲、發現和分析技術提取數據的價值”。對大數據的這種界定突出了大數據的4個顯著特點,即海量 (volume)、多樣(variety)、高速(ve loci ty)和價值(value)。在已有的相關文獻中,這種被簡稱為“4Vs”定義的使用較為廣泛[2]。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上述以“4Vs”為特點的大數據定義,那么,以此為依據,就可以將基因信息納入大數據的范疇,即基因信息整體上呈現出大數據的樣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由基因信息構成的數據庫,完全具備大數據的上述幾個特點。
首先,基因數據庫的數據量特別大(volume)。分子生物學、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促進對基因精細化的認識、多種組學的進步,從而產生海量數據[3]。人類基因組堿基對信息量約為3G,實際分析中疊加環境等因素后,個體數據均在TB以上[4]。1986年,美國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杜伯克率先提出了人類基因組計劃(HGP),旨在闡明人類基因組上3×109核甘酸序列,破譯人類全部遺傳密碼。自1990年啟動以來,經過美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國科學家十多年的努力,人類基因組計劃取得重大進展,提前和超額完成了遺傳和物理作圖,現已進入大規模測序階段。有關HGP的研究成果和數據幾成指數增長[5]。
其次,數據多樣化(variety):由于測序儀器種類繁多(比如常見的高通量測序儀器CG測序儀、Il lumina的 Hiseq、Roche 454、Lon Tor rent等),產生的數據格式也各不相同。同時,利用不同的基因信息分析軟件或分析流程處理得到的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
第三,價值高(value):隨著基因研究的深入和基因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有價值的信息從各種各樣的基因數據庫中挖掘出來,這些價值不僅體現在基因科研領域,而且逐漸在農業、健康和醫學等領域中嶄露頭角。應當指出,“4Vs”中的value有時也被解讀為“價值密度低”,即:數據量呈指數增長的同時,隱藏在海量數據的有用信息卻沒有相應比例增長;相反,價值密度的高低常常與數據總量的大小成反比[6]。但即便如此,人們也無法否定海量基因數據的總體價值仍然很高。
第四,高速(velocity):基因數據增長的速度非常迅速。這里,以華大基因的數據增長為例。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2013年6月,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僅原始的測序相關的數據量就達到12PB,并且以每月60TB的速度增長,預計未來幾年內每月的原始數據增量會超過2PB[7]。Velocity也意味著流動速度快。當處理的數據由PB級代替了TB級時,“超大規模數據”和“海量數據”是快速動態變化的,數據流動的速度快到難以用傳統的系統去處理[6]。
受益于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基因信息也得以數據庫化并表現出大數據的“4Vs”特點。而呈現為大數據樣態的基因信息,則既可能具有一般大數據所內蘊的隱私問題,又可能附帶有與基因信息或基因數據之特殊性相關的一些隱私風險。
二、基因信息的隱私蘊含及其風險
基因隱私是有關基因信息方面的隱私,基因信息之所以可能成為隱私是因為:“個體基因信息是關于個體的基因組成,基因組內是否有致病基因、缺陷基因存在;致病基因、缺陷基因有多少及這些致病基因、缺陷基因將可能導致何種疾病的信息”[8]。個體的基因信息不僅可以揭示致病基因、缺陷基因與個人疾病、個人缺陷之間的內在關系,而且可用于解釋個人的品格、智力尤其是某種潛在的素質。因此,基因信息作為決定和表征個體特征的重要信息,是個人信息的深層次內容[9],將其中個人不愿意公開的部分歸之于隱私范疇也就是理所當然的。
在大數據背景下,基因信息不僅遭遇到與其他類型的大數據同樣的隱私風險,而且還因基因自身的特性而可能生成某些特殊的隱私問題。
已有研究者指出,大數據的巨大潛力使得別有用心者可以從一大堆雜亂的數據信息中精準捕獲個人的隱私信息,甚至能夠做到預測人們的隱私行為,從而使得我們的身份、行為、喜好等個人隱私信息有隨時被暴露的風險[10]。
劉雅輝、張鐵贏、靳小龍、程學旗等人具體揭示了大數據時代對個人隱私保護的6個挑戰[11]:(1)個人隱私保護的范圍極難確定;(2)侵犯個人隱私的行為難以認定;(3)隨著信息技術的應用變得越來越普遍,乃至整個社會變成了信息社會,對個人隱私信息的管理也就變得更加困難;(4)個人隱私保護的技術挑戰;(5)構建多維的、靈活的個人隱私保護政策面臨著極大的挑戰;(6)大數據的數據來源成為隱私研究者的研究障礙。
這6個對個人隱私保護的挑戰中,(1)—(5)實際上揭示了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所面臨的風險,而其中的(6)則似乎不是個人隱私所面臨的風險,其僅僅是隱私研究的障礙,故嚴格講來,其并不是對個人隱私自身的挑戰。如前所述,基因信息具備大數據的“4Vs”特征,從而呈現為大數據樣態。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基因信息及其所內含的隱私,也就面臨著與其他大數據同樣的隱私風險。這就是說,此處所謂大數據對個人隱私保護的挑戰中,至少前5種也是基因信息隱私所面臨的風險。
在大數據背景下,由基因信息的特殊性所決定,其還可能有一種與個人隱私不一樣的隱私風險,即所謂群體隱私的風險。
有論者曾經指出過基因信息的這樣兩個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不可變更性。一個人的基因信息是終生不變的,一旦某個人的基因缺陷被公布于眾,與此基因缺陷或基因病相關的羞辱、歧視等不利因素都將終生陪伴著他。其二,家族或種族相關性。個人基因信息的暴露不僅可能使人聯系到其家人、后代和家族,甚至還可能聯系到其種族,從而可能造成“基因下層階級”或基因弱勢群體[8]。這里所說的第一個方面的特殊性即不可變更性,是使得基因信息成為個人隱私的原因之一,基因信息因此而屬于個人不愿公開的信息。這里所說的第二個方面的特殊性即家族或種族相關性,則導致了一種特殊的隱私問題:群體隱私的風險。
群體隱私是一個與傳統隱私概念不同的新隱私概念。在傳統的隱私理論中,其所謂的隱私通常指的是個體的隱私。傳統隱私理論的這種隱私概念,源自War ren和Brandeis合寫的《隱私權》一文,其主要探討個體的隱私權問題[12]。在War ren和Brandeis的《隱私權》一文發表之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許多西方學者也主要專注于對個體隱私的研究。隨著社會的變化和隱私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需要重新對隱私概念予以界定,以往僅僅與個體相關的隱私概念必須擴展為能容納群體隱私的概念。研究隱私問題的著名西方學者Westin曾經將隱私界定為個體決定有關他或她自己的什么信息可為他人獲知的權利要求,但后來他修改了這一界定,將社會群體和社團方面的隱私要求也納入其中[13]。
Bloustein對群體隱私問題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在《個體隱私與群體隱私》一書中,他將群體隱私界定為“人們在其與他人的結合中所尋求的一種隱私形式”[14](P124-125)。他認為,“‘群體隱私’是在一個群體中相互結合的個體的屬性,而不是群體本身的屬性”[14](P124-125)。他的這一觀點,表明西方學者通常是根據個體及其行為和關系來分析群體隱私的。他進一步指出:“群體隱私是個體隱私的擴展。通過群體隱私而得以保護的利益,是人們為了實現其目標而交換信息、分享情感、制定計劃及采取一致行動的結合需要和愿望。這要求人們在彼此之間相互披露信息——突破他們的個體隱私——并且取決于他們為了將披露的信息保持在群體中而所要結合在一起的那些人。因此,群體隱私所加以保護的對象是人們的外在空間而不是他們的內在空間,是他們的合群的本性而不是他們的完全獨處的愿望”[14](P124-125)。群體隱私與個體隱私的這種區別,也導致這兩種隱私有不同的形成機制:“人們的個體隱私的形成,是通過控制自我的信息是否將被分享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被分享;群體隱私的形成,則是通過控制分享信息或結合的過程”[14](P124-125)。由于群體隱私與個體隱私有這樣的不同,故即使個體隱私得到了很好的保護,群體隱私也未必就處于同樣水平或同樣程度的保護之中。或者說,當存在著群體隱私時,即使個體隱私方面沒有什么問題,也不能保證群體隱私就不會有問題。基因信息隱私的風險,有很多就屬于這樣的情況。
Sheri A.Alpert這樣指出:“在任何情況下,所有基因信息不僅與任何一個個體有關,而且與他或她的血親有關,還可能與他或她所在的種群(ethnic membership groups)有關”[15]。這樣的話,“任何群體(如這里所界定的)中一小部分人的信息都可以(正確地或不正確地)包含有該群體所有成員的信息”[15]。
作為群體隱私的基因隱私,從大的方面看,有家庭隱私與族群隱私這樣兩種情況。
在基因技術迅速發展與普及的當代社會中,家庭隱私面臨著十分明顯又極其特殊的挑戰。“家庭中隱私面臨的挑戰同樣十分強烈,而且往往在情感上讓人更痛苦,因為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基因效應。特別是就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如舞蹈病,患這類病的個體遺傳了一個變異的基因和一個正常的基因)而言,決定做基因檢測可能對所有家庭成員都會有深重的影響”[14]。既然所有家庭成員或大多數家庭成員都攜帶有某種致病的共同基因,那么,如果有某個家庭成員同意進行基因檢測即其自愿披露自己基因方面的隱私信息,就意味著實際上其他家庭成員即使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基因隱私信息也無濟于事。
Sheri Alper t曾經說到這樣一件事:Rabbi Moshe Tendler是一位生物學家和倫理學家,他反對最近對基因研究中德系猶太人的關注。他說,“為什么你們僅僅關注德系猶太人,給全世界留下我們都有壞基因的印象?……(其他人)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我已經被確認為攜帶有壞基因的德系猶太人社區的一分子。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對我”。在Sheri Alper t看來,Rabbi Tendler的苦惱代表了對基因背景中群體隱私問題上的許多擔憂[14]。此處的群體隱私,顯然就是基因信息隱私中的族群隱私。
三、關于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倫理探討
隨著基因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在社會上的廣泛應用,基因信息隱私也日益成為人們普遍擔心的一個現實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法律、技術和倫理三個方面尋求相應的對策。
技術上的對策,已經有不少技術方面的專家在進行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果。有學者指出,現有的隱私保護技術分為3類:數據擾動技術、數據加密技術和數據匿名化技術,而個人隱私數據經歷收集、存儲和使用過程(使用包括數據的二次使用、數據共享以及數據發布),因此,應該實施數據的多級安全保護。他們結合大數據的特征,從數據層、應用層以及數據展示層對個人隱私保護技術和相關的工作進行敘述[11]。雖然似乎還沒有出現針對基因信息隱私的專門保護措施,但這些一般大數據背景下保護個人隱私的技術手段,顯然也適用于對基因信息隱私的技術保護。
在法律領域,包括中國法學界在內的各國法學學者們為應對基因信息隱私的風險即保護基因信息問題上的隱私權,早就開始了相關的研究,迄今也取得了不少讓人感到振奮的成果。趙震江、劉銀良在2001年就曾指出:個人信息被認為是個人隱私。由于個人基因信息具有廣泛用途并可能會帶來可能的基因歧視,因此亦被認定為個人隱私,應受到法律保護。基因信息的權利根據大致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基因信息的憲法保護;第二,基因信息的民事法律保護[8]。這之后許多學者進行的基因隱私的法律保護研究,雖然日益細化、越來越深入,但似乎仍然是沿著這兩個方面展開的。
雖然技術方面和法律方面對于基因隱私之保護的研究十分重要,但僅有技術、法律方面的努力仍然不夠,而且本文的關注重點是倫理方面,故以下主要從倫理角度論述基因隱私的保護問題以及基因隱私問題的倫理對策。
為什么要保護基因信息隱私?或者說,基因信息隱私因何而值得保護?回答是,基因信息隱私蘊含有重要的倫理價值,這樣的價值至少包括:自由、尊嚴、公正。
基因信息隱私蘊含自由價值,這樣的價值由基因主體在基因問題上的自主、自愿、自決所構成。只有在具備基因隱私的條件下,基因主體才可能有對于自己基因信息的自主權、對于基因信息能否被采集和被利用的自愿同意以及相應的自決。如果缺乏基因隱私的保護,那么,基因主體就無法控制自己的基因信息,就難以避免自己的基因信息為他人所非法獲取或利用。這種情況,表明基因主體已經失去其在基因問題上的自主、自愿與自決,基因主體在這個方面的自由即不復存在。
尊嚴是人之為人的重要屬性,是人們普遍承認的價值之一。作為基因主體的人,其尊嚴的保障之一,就是基因信息隱私的存在。如果沒有基因信息隱私的保護,那么,基因主體自身基因的信息就可能隨意為他人所知,就會被他人肆無忌憚地利用。這樣的話,所謂的基因主體就淪為了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其作為主體的尊嚴蕩然無存。
基因信息隱私保護,具有公正的價值。這是因為,如果沒有基因信息隱私保護,那么,就可能給某些自私自利者提供了獲取和利用他人基因信息的可乘之機,而這些自私自利者出于其自私的本性卻又千方百計地防止自己的基因信息為別人所知。在這樣的狀況中,既形成了與公平相對立的不平等,又違反了行為尺度始終如一的公正要求。如果形成了有效的基因信息隱私保護機制,則這樣的不平等或不公平現象就難以出現,而公正的價值就得以實現了。
以上關于自由、尊嚴、公正的討論,實際上涉及的是基因信息隱私保護的價值依據。針對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技術措施和法律規范,都需要有相應的倫理支撐。但是,僅僅說明基因信息隱私保護為什么具有應然性或為什么基因信息隱私值得保護還不夠,作為倫理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針對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倫理探討還必須給出具體的倫理對策。與針對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技術解決途徑和法律規范途徑相比較,倫理對策有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具體來說,倫理對策可在不同環節對與基因信息有關的行為予以規范,以鞏固和完善對基因隱私的保護。與基因隱私保護所要實現的價值相對應,針對基因相關行為的不同環節,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倫理對策主要考慮如下三項:
第一,高度重視基因數據收集中的知情同意。在收集基因數據時,采集者是否獲得基因主體的知情同意至關重要。因為如果沒有獲得基因主體之知情同意,那么,這種采集基因主體的基因數據的行為就踐踏了基因主體的自由,也是對基因主體之尊嚴的漠視和否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于2003年10月16日通過了《國際人類基因數據宣言》(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n Human Genetic Data),其第8條明確要求:人類基因數據、蛋白體數據或生物檢體的采集,以及隨后的處理、使用和保存,無論是由公共機構還是私人機構來進行,均應在不以經濟利益或其他個人利益加以引誘的情況下,事先征得當事人自愿的、知情的和明確表示的同意。除非有極為重大而能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能由符合國際人權法精神的國內法律,對此項告知后同意原則做出限制。而且,當事人應被告知有撤回其同意的權利,且不得因其撤回同意而對其造成任何不利益,但若當事人的數據已無法回溯辨識、無從追蹤時,則得例外地無法撤回其同意[16]。該條所說“在不以經濟利益或其他個人利益加以引誘的情況下,事先征得當事人自愿的、知情的和明確表示的同意”,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知情同意的基本條件。只有切實執行知情同意的這些要求,才有可能避免對基因主體的強制,才能使得基因采集行為及其結果與基因信息隱私保護的倫理價值保持一致。
第二,努力強化基因數據存儲中的安全責任。基因數據往往包含有豐富的隱私信息,一旦其進入數據庫而又沒有安全存儲的保障,那么,這些包含有隱私信息的基因數據就可能被泄露或被盜取。如果基因信息隱私因未有安全存儲而被泄露或被盜取,則這些隱私信息的原主體即基因主體的自由、尊嚴都因此而受到侵犯,基因信息隱私相關的公平、公正也就不復存在。因此,基因數據存儲的安全責任實在是一種道德責任,是道德上可以提供正當性證明的責任。沒有這樣的責任,與基因信息隱私相關的一些重要倫理價值都會隨之跌落或喪失。而通過強化基因數據存儲中的安全責任,嚴守此類數據進出的關口,就為維護與基因信息隱私相關的倫理價值設置了一道道義防線。
第三,全面落實基因數據利用中的平等共享。負載著隱私信息的基因數據之所以被采集及儲存,是因為這樣的數據可被利用來產生利益。如果不存在任何利益生成的可能性,那么,人們也就無任何必要去采集和儲存基因數據。然而,在利用基因數據方面,卻可能有不公平問題的發生。《國際人類基因數據宣言》第16條規定:除非取得當事人新的自愿和知情的情況下明確表示的同意,原本基于某特定目的所采集的人類基因數據、蛋白體數據和生物檢體,不得用于與最初的同意不相符合的其他目的[16]。這一規定是前述知情同意要求在基因數據利用中的重申,由此可見,對基因數據主體的自由與尊嚴的尊重,不但是基因數據采集的價值前提,而且也是基因數據利用的要求。但就基因數據利用而言,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基因數據的平等共享。HUGO倫理委員會(2000)建議,利益分享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回報”可以是任何形式,甚至簡單的一句“謝謝”——但是公司應當考慮從凈利潤中提取1%~3%用于公共衛生基礎建設或其他人道主義事業[17]。這種建議,體現出對利用基因數據而獲得的利益的分享要求。應當說,無論采取何種方式或選擇何種分享比例,利益分享在大方向上總是符合相關倫理價值取向的正當要求的。進一步的要求,是這種分享應當成為平等的分享。這就是說,分享因基因數據產生之利益的人們,無論是什么出身或社會地位、無論有否遺傳疾病、無論其貢獻多少,都是平等的分享主體,都具有平等的分享權利。《國際人類基因數據宣言》第19條規定:藉由使用為醫學和科學研究目的而搜集的人類基因數據、蛋白體數據或生物檢體,所研發得到的利益,應根據國家的法律或政策及國際協議,將其成果與整個社會及國際社群共同分享[16]。這里的共同分享,具有平等性,即全社會及國際社群的每個成員都具有平等的分享權利。這種平等,其實就是公正的體現,即內蘊于平等中的公正或表現為平等的公正。如果某個國家或少數幾個國家獨占基因數據庫甚至掠奪其他國家的基因資源,這就不是國際社群的共同分享,而是前者的基因霸權及對后者的基因剝削;如果某個社會中只有少數人能利用基因數據庫,這就不是整個社會的平等共享,而是少數人的獨享;如果含有隱私信息的基因數據只能為市場主體所利用而非市場主體不能從中受益,這就否定了非市場主體作為利益共享之平等主體的權利。這三種“如果”的情形一旦發生,那就顯然會導致更多、更大的社會不公平或非正義。
以上三個方面的倫理對策,是針對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一般倫理對策,即適應大數據特征的普遍化對策。除此之外,還應當有基因信息隱私問題的特殊倫理要求,即針對基因隱私不同于其他大數據隱私問題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專門要求。這樣的特殊要求主要包括:
第一,認清基因信息隱私問題上個體與群體的倫理關系。雖然沒有個體就不會有群體,但群體的存在也與個體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一個現實的社會中,群體往往是個體生長的搖籃及其發展的外部條件。沒有相關的群體,個體甚至都不可能存在,更談何發展。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相互支撐,是其倫理關系的本質方面,不容人們忽視或遮蔽。在這個意義上,群體中的個體隱私與群體隱私也是不能相互隔離的,個體隱私的狀況勢必影響到群體隱私的狀況,而群體隱私的問題也必然是個體隱私的問題。基因信息的采集者或利用者,在采集或利用家庭、族群之類群體的基因信息時,就不能因其中個體基因與群體基因的相關性而只重視群體中的某個個人或某些個人的權利,從而導致對整個群體的忽視及對該群體其他成員的不尊重。
第二,平衡由基因信息隱私而形成的不同利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宣言、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近年來一再強調研究者及產業界應讓參與基因數據庫研究的民眾所屬的社會或族群得到“利益共享”。按照這一要求,應可適度平衡“要求民眾基于公益而提供檢體”以及“產業界勢將參與并將衍生商業利益”兩者間疑似呈現的矛盾,可以符合分配正義及互惠的要求,并可促進公眾的信賴與支持[18]。一般地說,所有基因信息提供主體與基因數據采集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都可以依據這一要求而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決。就基因信息隱私的特殊性而言,特別需要強調家族基因信息隱私和族群基因信息隱私中家庭和族群作為權利主體的重要地位及其隱私利益的公平分享。根據這一要求,因共同基因而產生的利益,即使其源自群體中某個個體或某些個體的基因隱私的自愿提供,也應該在群體中得到共享。
第三,把握同為基因主體權利的個體權利與群體權利的關系。基因信息隱私在家庭中表現為不同家庭成員的共同隱私,在族群中則是不同族群成員的共同隱私。家庭或族群的個體基因中有負載群體共同基因的部分,個體成員的隱私也就包含有群體的共同隱私。因此,基因信息隱私方面的權利就不完全是單純的個體權利,基因信息隱私也就成為了群體權利的對象。群體中的個體固然有個人的隱私權,但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個人隱私權與群體隱私權的相互關聯,群體中的個人在行使其隱私權時,其實受到群體隱私權的一定限制。這就意味著,群體中的個體在隱私方面的自由權利其實也是有限的,其行使不能構成對群體之自由權利的侵犯。根據這一要求,在采集或利用家庭、族群之類群體的基因信息時,采集者或利用者就不能僅僅滿足于獲得群體中的某個個體或某些個體的知情同意,而是必須將基因信息視為群體權利的對象,為了尊重群體的權利,就必須征得群體的知情同意。
[參考文獻]
[1]Heeks R,Stanforth C.Technologic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 ries: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process using actor-network theory[J].Development Studies Research,2015(1).
[2]李學龍,龔海剛.大數據系統綜述[J].中國科學:信息科學,2015(1).
[3]任思沖,周海琴,彭萍.大數據挖掘促進精準醫學發展[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5(23).
[4]楊夢潔,楊宇輝,郭宇航,王家亮.大數據時代下精準醫療的發展現狀研究[J].中國數字醫學,2017(9).
[5]方向輝.基因數據庫的分析和利用[J].情報雜志,2003(7).
[6]劉曉曙.大數據時代下金融業的發展方向、趨勢及其應對策略[J].科學通報,2015(5-6).
[7]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7%89%A9%E5%A4%A7%E6%95%B0%E6%8D%AE/15689146.
[8]趙震江,劉銀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法律問題研究[J].中外法學,2001(4).
[9]劉仁忠,代薇.基因隱私的倫理和法律基礎[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4(9).
[10]董軍,程昊.大數據技術的倫理風險及其控制——基于國內大數據倫理問題研究的分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7(11).
[11]劉雅輝,張鐵贏,靳小龍,程學旗.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保護[J].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5(1).
[12]Samuel War ren,Louis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J].Harvard Law Review,1985(5).
[13]Alan F.Westin.Soci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Privacy[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3(2).
[14]Edward J.Bloustein Individual&Group Privacy[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 ishers,2003.
[15]Sheri Alper t.Protecting Medical Privacy:Chal lenges in the Age of Genetic Information[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3(2).
[16]劉宏恩.人群基因數據庫法制問題之研究——國際上發展與臺灣現況之評析[J].律師雜志,2004(303).
[17]Ruth Chadwick.基因數據庫:個人選擇和社會利益[J].鮑貽倩,譯.中國醫學倫理學,2004(1).
[18]劉宏恩.基因數據庫研究中的公眾信賴、商業介入與利益共享[J].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0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