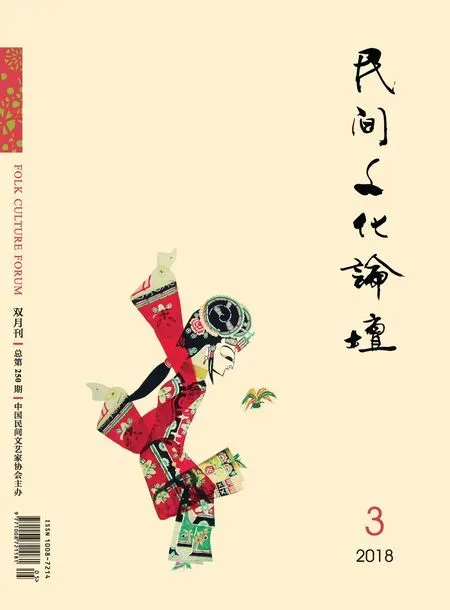民俗的承啟關系:暗示與啟示*
[美]丹·本-阿默思(Dan.Ben-Amos)著 張舉文 譯
引言:描述性民俗學
幾年前,被一位前輩學者打上“年輕的突厥人”標簽的一群民俗學者,②理查德·道爾遜(Richard M. Dorson)在《民俗與民間生活概論》(Folklore and Folklife: An Introduction,1972, 45-47)。(“年輕的突厥人”原文是young Turks。“突厥人”(Turks)現在一般指土耳其人。有關“突厥人”的文字記錄最早的是公元前200年的中文文獻。本文中所用的意思是指這些年輕人敢于創業,又因為他們多是中東猶太人或猶太后裔,也可理解為“不安現狀的年輕人”——譯注)。倡議要提出民俗學新觀念。③參見 《邁向民俗學的新觀念》(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 1972)。有關蘇維埃的觀點,見 Zemlianova, L.M. Sovremennaia Amerikanskaia Folkloristika (Contemporary American Folkloristics)(1975), pp. 269-273. 感謝Dana Howell (Todes) 提供這個參考。其實,并非如這個標簽所暗示的,他們既不是要謀反,也不是要反叛。他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試圖將民俗置于社會生活的現實中來審視作為社會互動中的象征的敘事、歌謠和諺語。他們持有一個共同觀點:民俗是社會生活的真實過程,也因此試圖拓寬民俗研究的經驗基礎。“承啟關系”(context)這一概念,無論從表面還是內含意義,成為產生新的邏輯概念的大框架。當然,這個概念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他們這些人特指的。①近年來,“承啟關系”成為學科新概念之一,Susanne Langer在其Philosophy in a New Key(1942)一書中有討論。雖然不一定是“歷史上的一個有啟發的思想”,概括了一代人的哲學,但是,承啟關系已經成為幾個學科的核心思想。在對《圣經》的研究中,Hermann Gunkel 早在1906年就運用了“Sitz im Leben”(生活環境)這個概念,見,"Die israelitische Literatur", Die orientalischen Literaturen, P.Hinneberg, Ed. (Kultur der Gegenwart I/7, B.G. Teubner, Leipzig, 1906), pp. 53-112. Gunkel也在后來的寫作中發展了這個概念,關注的是對《舊約》中出現的口頭傳統在成文之后的不同闡釋,特別是有關這些傳統在人民生活的地位作用,識別出獨特的韻文與詩歌類型,將它們與具體環境聯系在一起。他的傳記作家們支持Gunkel本人創造了口頭傳統中的“生活環境”這個概念,參考了當時的民俗學研究。參見Werner Klatt, Hermann Gunkel (1969), pp. 106-148. 有關《舊約》的新近研究,見Martin J. Buss, "The Study of Forms", Old Testament Form Criticism, John H. Hayes, Ed. (1974), pp. 1-56;Jay A. Wilcoxen, "Narrative", ibid, pp. 57-98; Klaus Koch, The Growth of the Biblical Tradition: The Form-Critical Method (1969); Rolf Knierim, "Old Testament Form Criticism Reconsidered", Interpretation 27,435-468 (1973); D.A. Knight, "The Understanding of 'Sitz im Leben' in Form Criticism",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74 Seminar Papers Vol. l, George MacRae, Ed. (1974); Burke O. Long, “Recent Field Studies in Oral Litera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Sitz im Leben”, Semeia 5, 35-49 (1976).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在他的有關民族志語言理論中也構建了“承啟關系”這個概念。他將以詞語聯系起來的文化現實的承啟關系與賦予特定語言以意義的場景承啟關系做了區分,但在他的寫作中,他將兩個概念混合使用了。見他的著述,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The Meaning of Meaning,C.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Eds, (1923), pp. 296-336, and The Language of Magic and Gardening: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ume II (1965), pp. 3-74. 弗思(J. R. Firth)將馬林諾夫斯基的場景承啟關系概念運用到語言學和意義的問題上,見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1957). 有關場景的承啟關系的討論,參見 D. Terence Langendoen, The London School of Linguistics: A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of B. Malinowski and J. R. Firth (1968), and R. H. Robins, "Malinowski, Firth and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Language (1971), pp. 33-46. 承啟關系的概念對人類學有著核心的意義,比馬林諾夫斯基和弗思所運用的更廣泛。拉德費爾德(Robert Redfield)引用 Milton Singer,建議 “人類學研究是基于承啟關系的:涉及到的一些大傳統的元素,如圣書、故事元素、老師、儀式或者超自然物等,并將這些聯系到普通人,作為人類學家眼中的日常生活的承啟關系”,見The Little Community/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1956, 1960 ), p. 51. 但是,目前在民俗學中所使用的這個概念沒有將“承啟關系”與“文本”做出區分。正如鄧迪斯所提出的,可以是平行的研究(見Alan Dundes in "Text, Texture and Context", Southern Folklore Quarterly 28, 251-265 (1964)),或是如鮑曼所明確提出的可以是彼此的延伸(見Richard Bauma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290-311 (1975). 近來有關民俗的承啟關系的研究主要依靠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著作,特別是,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Style in Language, Thomas JL Sebeok, Ed. (The M.I.T.Press, Cambridge, 1960), pp. 350-377, 以及海姆斯(Dell Hymes)的有關民族與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如"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Anthrop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Eds., T. Gladwin and W.C. Sturtevant(1962), pp. 13-53; "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vi, pt. 2. Special Publication: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ds. John J. Gumperz and Dell Hymes(1964), pp. 1-34;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Eds. John J. Gumperz and Dell Hymes (1972), pp. 35-71. See also Dell,Hymes,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Ethnographic Approach (1974). 除了這些將承啟關系作為核心概念的研究外,民俗學家也發現與這個思路一致的是有關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發展起來的“框架”概念的分析,見"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1972), pp. 177-193,以及戈夫曼(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1974). 承啟關系這個概念在文學研究中也很顯著,延續了形式主義和符號主義的研究,Michael Holquist提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對現存文本的不同方面的新關注,是基于其他各種著作的發展,是對‘有關文本的語境’的反抗”("If Language is the Only Way to See Meaning, Then Narrative is Blind ..." paper read at the 1976 Annual Meeting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 in New York, pp. 15-16. )但是,因為民俗的承啟關系涉及到公共表演,因此,有種或明確或含糊的假設,即承啟關系,如果文本一樣,是有受規則和規律制約的。因此,出現了社會中的民俗運用是受到描述關系的制約的思想,民俗學家和關注比較研究的人類學家都面臨兩難境地,如Julian Pitt-Rivers所表述的,"Contextual Analysis and the Locus of the Model", Archives Europeen de Sociologi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 15-34(1967)。目前,“承啟關系”已經成為語言學、審美學、哲學和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諸如“交際”②參見 Dan Ben-Amo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 3-15 (1971).、“表演”③參見 Roger D. Abrahams, "A 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 to Gossip", Man 5, 290-310 (1970); "Folklore and Literature as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75-94 (1972). Richard Bauma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290- 311 (1975); Dan Ben-Arnos and Kenneth s.Goldstein, Eds. Folklore: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1975).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Form in Performance, Hard-Core Ethnography, Eds. Marcia Herndon and Roger Brunyate (Austin, 1975).、“規則”④參見 Elli Kangas Maranda,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iddle Analysis",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Eds. Americo Paredes and Richard Bauman (1971), pp. 51-60.和“語法”①參見 Dan Ben-Amos, "Analytical Genres and Ethnic Categories", Genre 2, 275-301 (1969).等術語被用做描述性概念來分析作為社會行為的民俗。對故事和歌謠在其場景性的承啟關系中的再發現,揭示說明了民俗是有其系統性的,如同宗教、意識形態②參見 Clifford Geertz, “Religion as a Cultural System",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1973), pp. 87-125,193-233. These article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1966 and 1964 respectively.,以及藝術③參見 Anthony Forge, Ed. Primitive Art and Society (1973), pp. xiii-xxii.。由此,有可能將民俗構想為一個文化系統,其自身具有可被發現和分析的融合機制。④參見 Dan Ben-Arnos, "Folklore in African Society",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6, 165-198 (1975).
上面提到的“新觀念”代表了從歷史性和比較性民俗學向描述性民俗學的過渡。如同語義學向語言學的過渡,所改變的不只是方法,而更有意義的是理論方面的。描述性民俗學滿足了漢森所提出的成為一個理論的標準,因為它是“對所觀察的資料的一個條理清晰、有系統性的概念模式。其模式的價值在于其融合多種現象的能力,而如果沒有理論,那些現象就顯得或是令人驚訝、不可思議,或是徹底被忽視”⑤參見 Norwood Russell Hanson, Patterns of Discovery: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ce(1969), p. 121.。歷史民俗學派關注的是不同時代的相同之處;比較民俗學派審視跨文化的可比性;對承啟關系的描述所分析的是在特定社會中民俗表演如何被融入一個藝術性交際體系。描述民俗學是建立在基于結構主義和符號學所產生出的理論框架之上的。描述民俗研究也認同“完整論、變遷論,以及自律論”⑥參見 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1970), p. 5.。然而,描述民俗研究不是聚焦于某一個獨立文本或單一類型,而是全社會范圍的民俗交際。“新觀念”的目標是去發現某社會的成員的民俗表演所體現出的可能的和可接受的變異,以及自律論可解釋的現有民俗的異同;同時,參照社會結構、文化宇宙觀和象征符號,以及普遍的口頭行為。
描述性民俗研究仍處于其初始階段。目前只有極少數的研究文章,⑦參見 Richard Bauman and Joel Sherzer,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1974); Dan Ben-Amos and Kenneth s. Goldstein, Eds. Folklore: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1975);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Ed. Speech Play: Research and Resources for Studying Linguistic Creativity (1976).包括(4-7篇)綱要性短文,以及博士論文。⑧以下是部分博士論文,注明外,都是賓夕法尼亞大學大學的:Michael J. Bell, Running Rabbits and Talking Shit: Folkloric Communication in Urban (1975); Allessandro A. Falassi, "Stasera a Vegalia":Structure and Contexts of the Tuscan Folk Narrative (University California, Berkeley, 1975); Bert H,Feintuch, Pop Ziegler, Fiddler: Study of Folkloric Performance (1975); Michael K. Foster, Beyond the sk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Four Longhouse Iroquois Speech Events (1974); Gregory Gizelis,Narrative Rhetorical Devices of Persuasion in the Greek Community of Philadelphia (1972); Juidth T.Irvine, Caste and Communication in a Wolof Village (1973); John H. McDowell, The Speech Play and Verbal of Chicano Children: An Ethnographic and Sociolinguistic Study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Austin, 1975); Herminia Q. Menez, Folkloric Communication Among Filipinos in California (1973); Peter I. Seitel, Proverbs and Structure of Metaphor Among the Haya of Tanzania (1972).正如勞里·航柯和維爾莫斯·沃格特所指出的,這個趨勢有著重要,但尚未完成的諾言。⑨參見 Lauri Honko, "Genre Theory Revisited", Studia Fennica 20 (1976), p. 22; Vilmos Voigt, "Semantics and semiotics of Works of Art in High/Folk Literature", 1976年布達佩斯的國際比較文學研究會第八屆大會。盡管如此,深入地從其文化和場景的承啟關系中觸及敘事、歌謠、俗語和謎語,已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民俗學的基本概念框架,重新構建民俗與其他口頭交際體系(主要是文學)的關系。“新觀念”的影響深遠,難以言表,顛覆了曾經是有關民俗、文化以及進步的理論根基。那些思想是隨著現代的系統論思想,以及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知識而產生的,可能并沒出現批評的意識,便被融入現代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
文學與民間文學
有關民俗的思想(即使不是這個術語本身),是作為啟蒙運動的黑暗面發展起來的,對立于那個時代所激發的新思想。理性主義“對民眾及其創造物,特別是文學,嗤之以鼻,視為粗野、無知、不懂措辭、缺少精細思辨和升華的思想。對民間文學的這種貴族態度是理性主義運動的代表特色”①參見 Martin Schutze, "The Fundamental Ideas in Herder's Thought", Modem Philology 19 (1921), p. 118.。那些贊美理性主義者所鄙視的具有詩意的浪漫主義者,顛覆了對民眾及其文學的態度和價值審視,但是,他們沒有拒絕文學與民間文學內在的根本二元對立論。創用了“民間文學”“民間詩歌”和“自然詩歌”等詞的赫爾德,②同上, p. 117.從政治、社會、教育和歷史角度來考試“民眾”(Volk)。“民眾”是一個民族中被統治的,而不是統治的,并且常常被用作“民族”這個概念的同義詞。民眾是一個民族中很少受到教育的、也是古代和現代都沒有達到適當的文明程度的人。其中最后表述的特征尤其重要,因為這也暗示著“民眾是一個不同于哲學家、詩人和演說家的一個階層;一個不同于賢人的階層。天生不明智沒學識,他們一定是那些人為的文化培養方法難以奏效的人,而同樣的方法對哲學家、詩人和演說家則行之有效。所以,他們更接近于自然人”③參見 Georgiana R. Simpson, Herder's Conception of "Das Volk" (1921), p. 9.。作為盧梭的追隨者,更是他的老師哈曼(Hamann)的信徒,赫爾德將自然人理想化,羨慕其詩性的表現。對他來說,民間文學在個體作家的性格、主題,及其本土受眾的集體性格或當地環境之間達到了很高的和諧度。因此,他認為,民間詩歌是所有詩歌的最高級類型和終極標準。④參見 Martin Schutze, op. cit. p. 119.
這樣,赫爾德建立了一個概念框架,由此確定了文學與民俗的二元對立關系。盡管浪漫派贊美理性主義所斥責的特質,但是,在他們之間,就這兩種文學的基本特征而言,并沒有爭議。對創造文學和民間文學的討論充滿了“高與低”的比喻用法。⑤參見 Max Luthi, Volksliteratur und Hochliteratur (1970).無論是從歷史、進化論、社會、文化,還是藝術角度,民俗都被視為文學的丫鬟,有著無法擺脫的低級出身和素養。
如此之關系概念已扎根于文學和知識的社會基礎。無論是在古代,中世紀歐洲,還是處于現代發展中的社會,每當介紹文學功能時,它都是作為區分社會階層的要素之一。它劃分出富裕階層和貧窮階層,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⑥參見 Samuel Noah Kramer,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 (1963), p. 231.一旦獲得識字能力,它也會永遠固化社會地位。由此而導致的社會階層結構又成為判斷其結果之價值的比喻:有文化和沒文化的人的創造力與他們各自的社會地位相對應。作為窮人階層特有范疇的口頭藝術需要其演說者自己賦予其意義。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將他們從“地球上可憐的人”中所看到的粗陋擴延到他們的語言和口頭藝術。即使是那些羨慕民間文學的人也將其簡樸、天真和自發性單獨挑出來,作為他們所最喜歡的特質,如約翰·格林威所說,“要求民歌有文學價值就是否定其民間的唯一特性——不世故的直來直去。民眾中有許多不很有條理的詩人,但是幾乎沒有像彌爾頓那樣的啞人;想在民歌中發現彌爾頓式的水準就是要把民歌提高到有意識的藝術的水平。”⑦參見 John Greenway, American Folksongs of Protest (1953), pp. 18-19.
承啟關系中的民間文學
這個謬論的前提已經深深根植于民俗的概念之中。對此,我直到去年在尼日利亞的貝寧市進行實地調查時才明白過來。①在此感謝古根海姆基金會對我在貝寧的研究的贊助。我當時要做的是運用從民俗學的“承啟關系派”所產生出的原理,將特定文化的交際事件作為其社會生活模式和口頭行為的一部分去加以檢驗。在貝寧,有兩種場合是凸顯講故事活動的,一個是“依波塔”(ibota),另一個是“歐克波彼”(okpovbie)。依波塔主要是家庭場合,孩子、年輕人、婦女,以及家長都參與。歐克波彼則是更具有節日性的事件,有許多客人或來訪者參加,通常是因為有婚禮、守靈或是其他儀式活動而聚集一群人。兩者的主要區別是參加歐克波彼的專業藝術家的打扮。現在,在歐克波彼上,有當地的樂人表演,但是在過去,專門講故事的人講貝寧的歷史,自己彈著一種七弦的低音琴作為伴奏。②參見 Dan Ben-Amos, Sweet Words: Storytelling Events in Benin (1975).
貝寧的專門講故事人是獨自謀生的,不同于那些屬于傳統行會的藝術家和藝人,③參見 Paula Ben-Amos, Social Change in the Organization of Woodcarving in Benin City, Nigeria (1971).也不同于吟誦王族世系傳統的本巴拉(Bambara)和沃羅夫 (Wolof)的結盟的游走詩人。④參見 Dominique Zahan, La Dialectique du Verb chez les Bambara (1963), pp. 125-148.貝寧的故事人常常是處于邊緣的個體地位,不屬于職業行會或酋長社會。貝寧是個有明顯階層結構的王國,圍繞王族人物及其宇宙觀有許多社會組織,但專門講故事的人則沒有社會地位。這樣,住在鄉下的講故事的人屬于本村的同齡群體,但當他們進城表演時,他們又是陌生人。
有一個這樣的講故事人,叫阿米耶凱本·歐格貝波爾(Aimiyekeagbon Ogbebor)。⑤參見 Dan Ben-Amos, "Two Benin Storytellers", African Folklore, Richard M. Dorson, Ed. (1972), pp.103-114.1966年,當我在貝寧做實地調查時我認識了他,并在好幾次的歐克波彼上對他進行了錄音。當我在1975年11月末返回到貝寧時,正好看到他躺在停尸臺上。
歐格貝波爾是貝寧最受歡迎的講故事人之一。在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去貝寧之間,他的名聲影響到了大眾媒體,一家當地的錄音公司出了四張他說唱故事的唱片。⑥參見 Akpata Music, Vol. I, No. 6386045; Akpata Music, vol. II, no. 6383046; Aimiyekeagbon Ogbebor and His Group, No, 62590102E; Aimiyekeagbon Ogbebor and His Akpata Group, No. 6361125.受唱片的時間限制,那些故事都很短。他在實際的歐克波彼上講故事時,一個故事就可能持續一兩個小時,包括敘說,唱歌,還有吟誦。他在1966年給我講過的一個故事是關于一個貝寧國王(Oba Ewuakpe)的生平和業績,他在18世紀初時在位,依據的是推測的歷史年表:⑦參見 Jacob Egharevba, Short History of Benin (1968) , pp. 37-39.
國王的母親去世了,國王把許多人作為陪葬送她到精神世界。這讓下面的酋長們感到很不滿,就謀劃造反,也不再帶著進貢的東西去朝拜他了。國王很孤獨,也開始沒吃的了,就決定回到他母親以前的村子去。回家的路很遠,可一路上只有他最忠實的王后陪著他。他來到河邊時,擺渡的劃船人不載他,盡管他不斷說自己是國王。最后,那個擺渡人答應了,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允許他強奸王后。無能為力又別無選擇,國王忍受了這樣的羞辱。
之后,當國王快走進他母親的村子時,遇到一群清理道路的人。他說,“我是國王。我要回到我母親的村子。”他們說,“要是你不幫我們清理道路,你就過不去。”
國王只好被迫像他曾經命令過的下層人那樣親手干起活來。他就這樣一次次被羞辱,但終于安定下來,并開始開墾一片土地了。慢慢地,國王重新積累了財富,并決定回到貝寧城里。
可是在城里,情況沒有變,酋長們還是反抗他,不斷有騷亂。王后也陷入絕望,只好去見一個占卜人。那個人說,國王應該把王后活埋了,然后在宮殿周圍放些空籃子和火把。盡管國王反對,可是王后堅持讓他把她活埋了。他就照辦了。
悲劇發生不久,當國王正坐在宮殿里為死去的王后和自己的不幸悲傷時,有個酋長偷偷往院子里看了看,發現了空籃子和火把。他認定這是個信號,是別的酋長違背了他們共同的約定,并在晚上給國王送來了貢品。他害怕自己是最后一個歸順國王的酋長,馬上跑回家,帶著禮物和貢品送到國王的宮殿,并請求饒恕。隨后,別的酋長也都效仿,一個個都朝拜了國王。于是,國王重新得到國王的寶座和權力,報復了他的敵人,使貝寧人得到了和平安寧。
這個故事講了近兩個小時。那是1966年5月3日晚上。故事情節廣為人知,貝寧的許多人,哪怕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能講這個故事。至少有兩個貝寧的作家將這個故事編出了戲劇,①參見 Emvinma Ogieriaikhi, Oba Ovonrarnwen and Oba Ewuakpe (1966); Osarenren Omoregie, Oba Ewuakpe.Mimeograph. n.d.都保持了歐格貝波爾所講的情節。可是,歐格貝波爾講的時候,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是按照故事線索講的。整個故事中穿插了許多歌和吟誦的詞語。唱歌是這種敘事場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當他要平靜一下自己的難過情緒時,他就唱起來,或是當描述到儀式事件時,他就唱那時該唱的歌。他吟誦的短語中有適于那種場合和貝寧傳統的諺語和典故。場景性引用語(situational references)包括問候語、感激語、以及向主人、貴賓和普通人說的祝福語。傳統性引用語(traditional references)包括諺語,對別的故事和典故的概要性引用,以及涉及到貝寧歷史上重要事件的人物和地方的詩句。
場景性引用語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的,可是傳統性引用語中的典故則只是有些人懂,有些人則模模糊糊不清楚,要看每個人的受教育程度。我為了弄清楚這些典故、諺語和引用語,不得不拜訪一些年紀大的人。貝寧的高級酋長歐瑪瑞吉是闡釋傳統最好的人。
對這些文本的完整翻譯和分析還處在整理的初級階段,可能需要幾年才能完成。在此,我無法提供對該表演中的非敘事部分的背景的完整和系統的分析,也無法深入解析他在故事中所引用的主題和人物。但是,即使是初步的審視也可以揭示,那些對聽眾來說似乎隨意和點綴性的傳統性引用語,其實有著鮮明的統一性,用了貝寧人的整個敘事傳統中可抽用的類比和對照來襯托主題。這些典故,還有諺語,發揮了“亞敘事”(meta-narrative)的作用,使得敘事人能引領他的主人公,評述他的舉止,憐憫他,并將敘事場景中的情況與他個人的境況相類比。作為藝術家,歐格貝波爾并不只是講述,也不是象海姆斯和鮑曼所建議的那樣將故事表演出來②參見 Dan Ben-Amo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olklore in Contex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 3-15 (1971).,而是將國王的故事置于貝寧口頭歷史的承啟關系中,形成了他自己對故事的態度。文化史、敘事性場景,以及講述場景,通過講述人所選擇的引用語和典故,融合在一起。歐格貝波爾構建出一套“文化意識流”程式,從中,人物和事件快速閃現出來,然后消失在背景之中,將舞臺讓給別的人物,而他們又都是被隨時提到,似乎顯得無序,但這一切都圍繞一個特定的故事,將其最獨特的方面以講述人所構想的方式展示出來。不知不覺,不認字的歐格貝波爾循序了T.S.艾略特的規則:將自己個人才能置于他自己的傳統的承啟關系中。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他展現了諾斯羅普·福瑞所遵循的準確性:作家在直接或間接暗示給他的,先前已經存在的文學主題和人物的承啟關系中進行再創作。①參見 Northrope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1957).
盡管貝寧的故事講述人明顯不是作家,但是,他們是口頭詩人和敘事人;他們沒有西方的文學背景,但是有他們自己文化、城市、村子,甚至個人世界的背景。對口頭表演敘事的這些特質的認識,要求我們必須修正我們現有的對“民俗”及其與文學的關系的觀念。依此邏輯,口頭詩人在本質上等同于文學作家。
民俗的簡單直白存在于外人的眼里。從文化角度看,一個民間故事、一首歌和一條諺語可以具有任何一位學識淵博的作家所創作的作品所具有的復雜的概念意義、內涵,以及深遠意義體系。格林威所認為的民歌缺少深奧性②參見 Samuel Noah Kramer, Sumerian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Character (1963), p. 231.,及其對其他民俗形式的如此推理,絕不是民間文學的內在特性。借助口頭言語的創造性,口頭敘事與任何其他言語創作都具有同樣的表達能力、意義、多重性,及其關系的復雜性。
當然,如此論斷需要一些限定條件才能成立。首先,有必要警惕浪漫派的態度的逆轉:將深奧世故性,而不是簡單直白性,賦予民俗的各種表達形式,并堅持認為它們在本質上優越于其他各種口頭言語藝術。其次,我們必須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民俗表達形式都具有那些在貝寧專業講故事人的敘事中所能辨認出的特質。許多敘事和歌謠具有其他特質,因講述者的年齡、表演中的承啟關系,以及民俗的類型而定。認識到如此潛在的多元性是進一步發展民俗學對承啟關系研究的一個關鍵。置民俗于其文化和場景的承啟關系之中來審視,這使得我們能夠解釋各種口頭言語藝術能力之間的差異,及其在不同表演中達到目的的不同表現。換句話說,民俗學中的承啟關系論的研究是描述性的,但是它有潛力將民俗研究超越描述,并為民俗的多元性提出一個理論解釋。
承啟關系論的民俗研究模式
承啟關系論的民俗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可能具有以個人、社會,以及口頭言語為坐標的三個維度。個人坐標代表的是個人在其社會中的成長及其運用民俗時的不同身份轉換;社會坐標代表的是在個人成長的每個階段,對每個人都是已知和開放的交際事件與民俗表現形式的多元性;口頭言語坐標關系到將任何一個現實方面,包括想象的現實,轉換到口頭言語表達形式的能力。
對此模式的進一步的表述可能要運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歷時性可用來說明某個人一生的變化,而不是口頭言語形式的變化;共時性用來說明交際事件與口頭言語形式的同時性,不只是因為它們共存于社會之中,而且還是因為,特別是就此例而言,它們可以讓每個人參與。換言之,目前的模式試圖將心理學的認知因素融入各種民俗形式的表演,作為對此提供解釋的新維度。盡管在承啟關系論的民俗研究框架內的分析是側重社會和文化層面的,但是,目前的模式則試圖強調分析角度的必要性,即需要有一個能將個人及其變化能力包容到一種民俗理論的分析角度。
通過對在個人、社會和口頭言語表達坐標上發現的變量及其準確關系的理順,可以解釋民俗形式的簡單性或復雜性。與浪漫派——無論是新發展的還是歷史上的觀點相反,簡單性不是民俗形式的內在特質,而是取決于說話人的個性,以及說話或歌唱時的社會環境。兒童歌謠很可能被視為本質上是“簡單的”,但是,這個特質不能歸于口頭表演的本性,而只能歸于個人有限的經歷、心理語言運用能力,以及口頭言語創作能力。
有序與無序
為了避免對口頭藝術和寫作文學的結構等級做出評價和判定或構建,我們可以采用一套并非獨創的判斷標準,將社會中的口頭言語創造性視為以言辭確立有序和無序的努力。口頭言語表達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關系到說話人的文化、社會、宗教,以及語言現實。在表演中,每個人都有兩個選擇:有序性的,即,以某種有序性表現他個人的,或是想象的或是真實的經歷和敘事,試圖以言語的形式復制出現實;無序性,即,改變現實,將其反映在現實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系列關系中。個人可以自己創造出這些選擇,也可以從他自己的文化中已知的民俗類型里選擇某種說唱類型。
創建秩序是為了要在觀念上復制口頭表達的現實,“如實”講述歷史,以仿佛親歷的方式敘說各種經歷,并將幻覺以仿佛親眼見過的方式表述出來。在這些情況下,現實的邊界是由所處文化和個人狀況來決定的。秩序感是作為概念框架去進行選擇或合并以便將事件做出排序。即使這其實不能復制歷史,但是,通過對此事件的敘說或想象,其理想的秩序代表了一種渴望的目標和模式。巫師的故事便是有關一個以巫術為現實的社會秩序的故事。盡管可能存在這樣的事實,即,其超自然世界可能代表著與說話者所認知的現實世界相反的一面,①參見 The Reversible World: Symbolic Inversion in Art and Society. Barbara Babcock, Ed. (1978).但是,超自然的主題本身,只要是在說話人所認知的世界范圍之內,就不會使其成為對無序世界的描述故事。進一步來說,那些民俗學家稱為傳說(legend)的敘事,如鬼故事,也可以用有序和無序的概念來解釋,從而避免令人棘手的信仰問題。②參見 Linda Degh and Andrew Vazsonyi, "Legend and Belief", Folklore Genres, Dan Ben-Amos, Ed. (1976),pp. 93-124.依此,傳說是有關無序的故事,但表現為有序的敘事。從主題上看,這些故事不代表我們所認知的真實世界,但在表演中,它們顯得真實,或至少似乎是復制了說話人所認為的現實。傳說的意圖是將超自然的事物包容到現實中。
與此相反,任何意圖和目的的有關無序的敘事都是言語的創作,是在構建一個異樣現實的世界,一個說話人和聽眾都不了解也沒經歷過的世界。童話是有關無序的故事中的主要例證,這種故事都有各種魔器,而且主人公具有能打破我們的世界的自然法則的能力。但是,有序性故事和無序性故事之間的關系相對復雜。正如費南迪茲所提出的,③參見 James Fernandez, "The Exposition and Imposition of Order: Artistic Expression in Fang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Artist in African Societies, Warren L. D'Azevedo, Ed. (1973), pp. 194-220.神話和民間故事可以對社會和文化現實的秩序實施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將這種秩序的實施理解為是從宗教經歷向社會層面的經歷的關系轉移,是在為一種現實創建不同的理想模式,而這模式是說話人構想出來的原初的和無序的世界。同樣,從相反的角度看,對無序世界的構建也可以被闡釋為一種對理想現實的口頭言語創造,對不存在的事物狀態的渴望。
在這個口頭言語坐標內,還有必要區分一下兩種有序與無序的模式:橫組合模式和縱組合模式(借用語言學概念)。試圖構建橫組合秩序的努力涉及到原因、時間或空間概念的序列關系。縱組合的有序與無序則沒有這樣的關系,而只是對它們在自己文化中做認知的相同與相反事物的分類安排。例如,在上面提到的國王的故事中,其敘事順序本身有橫組合秩序模式,也有縱組合秩序模式,即,使用涉及到類似場景的與該事件和人物有關的俗語典故等。對于一個沒有背景知識的聽者來說,這樣的縱組合模式沒有什么意思,因此他會將此視為無意義的、無序的典范模式也因此被排斥忽略掉。
從語言現實自身來說,無序存在于口頭言語之中。例如,繞口令,如其名所示,就是試圖將一種語言置于語音的無序之中;而雙關語和謎語是在一種語言的形態學和語義學層面引入無序。
語言學意義上的無序形式對當前模式中的個人坐標有直接影響。繞口令和謎語主要是兒童使用,也主要是說給兒童的,為的是讓他們在語音、語法和語義層面掌握那種語言。有序感常常表現在兒童的敘事中,以有主題的重復方式出現。程式化的故事,即,同樣的情節以不同人物重復,主要出現在兒童故事中。基于我對貝寧的敘事傳統的研究,盡管還是處于印象階段,但我可以說,敘事的復雜性隨著敘事人和聽眾的成熟而增加。兒童敘事涉及到主題上和結構上的不斷重復,而成人敘事則轉向主題的變異,但仍保留結構上的重復。在業余的講故事人中,他們的重復主要是在橫組合方面。只有那些進入關注所有的詞語及其意思,并關注傳統事件的專業敘事人,才有能力構建出縱組合性的有序和無序,將某一特定事件與整個貝寧傳統聯系到一起。
然而,即使是專業講故事人,他對自己口頭言語創作性的徹底掌握只展示于對該表演恰當的承啟關系之內,而不超出這個范圍。每個社會都有一套適于表演的交際活動,每個故事或歌的復雜和簡單程度與表演場合和參與的人相互依賴。所以,敘事人和聽眾越是成熟,語言的使用就越綜合。成人與專門的講故事人可以利用兒童可懂的語音和語義層面的有序和無序,但是,反向的過程就是不可能的了。
總而言之,在文化的承啟關系中研究民俗可以揭示口頭言語表達的多樣性。這樣的研究所傳遞的思想是,識字能力本身體現了口頭言語創作的質的變化,也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作家所運用的語言特性,也許除了已經印在紙上的,至少一大半也同樣被口頭詩人和講故事人所使用,而且始終如此。僅就文學來說,暫且不論文化的其他方面,識字能力并沒有為口頭言語藝術帶來質的變化。自從古騰堡(Gutenberg)革命以來,已經有太多的垃圾被印刷出來。反之,承啟關系的研究已經并將進一步證明,口頭的表演并不妨礙復雜的口頭言語創作。依此,從文化和場景的承啟關系中研究民俗不僅能擴展研究的經驗領域,而且也能為解釋和探索社會中的口頭言語創造的多元性提供一個基礎。承啟關系論的研究基礎已經有了,一些方向也清楚了,但是,具體實際的研究還處于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