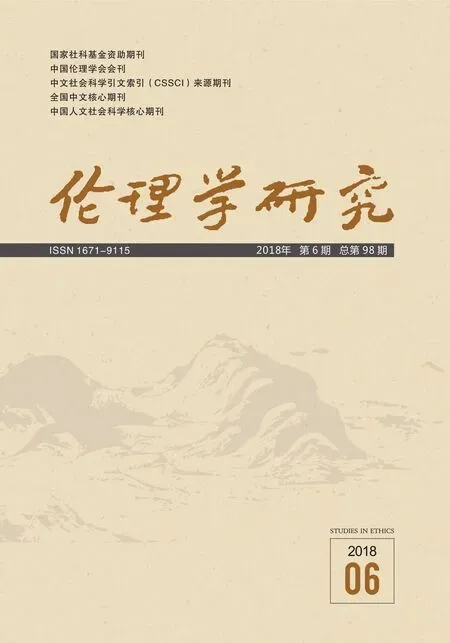疾病的道德歸因分析
孫雯波
史前文明中廣泛存在著把疾病視為一種具有強烈的社會、宗教和道德意義的過程和現象,人類對疾病的成因或歸因的探索一直不息。古代疾病觀大多認為疾病是外于人類本體的一種異己力量的作用而使人“得”病,或者認為是一種無限至上力量作用于人的一種方式或表現。疾病作為異己的神靈侵入以及靈魂喪失結果的觀念,可以在中西方舊石器時代的遺存中找到充分的證據。在中國歷史上,殷人信天帝,敬鬼神,有了疾病,認為是天帝降下的禍、祖先作祟,生病后以祭祀鬼神、祖先乞求禳解為主要治療手段。《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這在王充《論衡》中也有記載。即是鬼魅作祟生瘟疫,當驅鬼或祈祛神祛除。鬼神致病的觀念也普遍存在于古希臘早期社會里,《伊里亞特》中就有阿波羅神為懲罰希臘領袖阿伽門農二播撒瘟疫的記載。在美國早期的醫學人類學研究中,克雷門斯(F.Clements)在1930年代對所謂“原始民族”的病因觀念的研究,從總體上把“原始民族”的病因觀分為五大類:巫術作亂、靈魂迷失、違反禁忌、病物入身和鬼魂附體。當時不發達的醫學科學水平無法解釋疾病的病因,人們落后的認知水平也無法認識疾病與人體間的相互作用機理,東西方對疾病的神秘感甚至無助感最后都求助于宗教的解釋和歸因。文化哲學家丹瓦松(C.Dawson)曾說過:“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傳統的大河,他們流過各個時代,流過它們澆灌和哺育的變化著的歷史場景。”[1](P2)
一、天道之輪回:疾病因果報應論
古代文明中廣泛存在著把疾病視為社會的懲罰和道德上的過錯的觀念在中國歷史和社會中有著廣泛和長久的影響。除邪教外,凡具有正信的宗教群體,皆本著對世人勸善導善的愿念,虔誠地信奉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觀念。“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凈其意,是諸佛教”,善惡報應的觀念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在中國文化中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中國傳統的天命論思想基礎。六經之首的《周易》早就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警世名句。善惡報應的觀念源于佛教,在封建社會又為歷代的統治者所用,并與社會大眾的道德實踐相結合,被眾生所接受,形成中國民間普遍性的社會心理準則和倫理信仰,表達社會大眾向善抑惡的愿望,起到一定的扶世助化作用,成為中國古代儒家倫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補充。
在印度佛教理論中,人的行為被稱為“業”,“業”通常分為身、口、意三方面,故稱三業。從佛教倫理的眼光來看,三業的根源在于善、惡、無記三種倫理性質的動機,從三種倫理動機或道德意志引發、造作的行為稱之為善業、惡業和無記業。“心為法本,心尊心使,心之念惡,即行即施……心為法本,心尊心使,種信念善,即行即為,受其善報,如影隨形。”[2](P827)佛教理論認為,一切事物皆由因果法則支配,人的善惡動機與善業惡業有著緊密的聯系,眾生的思想行為決定了生命的再塑造,道德在生命轉化、自我塑造未來生命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正如佛學經典《無量壽經》所說:“天地之間,五道分明,恢廓窈冥,浩浩蕩蕩,善惡報應,禍福相承。”在宗教倫理意義上,它是一種鐵定的信仰的規則,決定著宗教生活中的道德選擇和道德評價,即決定著人們是作惡還是從善,也對人們的人生苦樂處境做出宗教倫理的解釋。如人們因疾病而陷入悲苦境地,在中國人的世俗觀念中往往將疾病與病者的善惡行為和品性相聯系,賦予原本單純的疾病以復雜的道德色彩和意味。如在清代,以鬼神司疫這一觀念為基礎,人們認為瘟疫的病源有二:鬼神和疫氣,而后者往往被歸于道德因素,即個人或集體的道德不修或有違天和而受到上天的懲罰,將“人事錯亂”視為瘟疫的原因。在不少論述中,患染瘟疫的個人也與道德因素密切相關,道德敗壞者常常會遭到瘟疫的報應,而品德高尚者則往往能夠在大疫之年幸免于難。依據因果法則,佛教對疾病的分類十分嚴密、細致、完全。如包括身心兩方面“因中實病”中的身病又分三“即四大五臟病相(包括四大增損所生病、五臟所生病)、鬼神所作病相(指怨鬼纏繞,令身心不安,或行瘟疫,或生瘡變)、業報所感病相。其中業報所感病相包括很多,如過去殺生,會引發肝臟眼睛毛病;過去偷盜,會引發肺部鼻子毛病;過去邪淫,會引發腎臟和耳朵毛病;過去妄語,引發脾臟和舌頭毛病;過去遮蓋佛的光明,今生皮膚又丑又黑;以惡眼視發菩提心的人,得無眼的報應等等①。
在社會生活中,道教義理有著多種多樣的表現形態,它圍繞宇宙本源、神與人的關系、形與神的關系、仙境與陰曹、善與惡、因果報應、神的靈驗等命題,在道功、道術、道儀等多方面論證道教的真理性。天道循環,善惡承負,道教也相信現實的因果報應,認為吉兇禍福乃是個人行為善惡的必然報應。老子直接將身體與人的德性相聯系,認為有道德修養的人,猶嬰兒般純真柔和,毒蟲不咬他,猛獸不抓他,惡鳥不搏他。《太上感應篇》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善者自興,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發之間,無有過。”“認為上有日月‘照察’,身中有心神與天‘音聲相聞’,有諸神疏記人的善惡,過無大小,天皆知之,到了一定的時候,天便校其善惡,予以賞罰,善者賜福增壽,惡者降福減壽,鬼魂打入地獄。”儒家思想濃厚、有著中國民間宗教的“圣經”之稱的《關帝覺世真經》中也倡導善惡因果報應:“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同時將其與疾病瘟疫災害相聯系:“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行諸惡事,官司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發不紊。”東漢哲學家王充《論衡》譴告篇第四十二里說:“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可見因果報應思想不獨在佛教傳入或是道教自生,它們與儒家思想結合已成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二、上帝的怒火:疾病天譴論
與疾病因果報應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在西方廣泛存在的疾病天譴論。古希臘早期社會典籍《伊里亞特》和《奧德賽》中說,疾病是以上天的懲罰、魔鬼的附體以及天災的面目出現的,阿波羅神為懲罰希臘領袖阿伽門農而在人間播撒瘟疫。疾病天譴觀與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思想及西方基督教、猶太教的原罪觀念有關。斯多葛學派從禁欲主義的角度,把情欲看作疾病的根源,肢體的無病在于凈化情欲。在《圣經·舊約》之《創世紀》中,人的始祖亞當和夏娃為上帝創造后被安排在伊甸園,他們可以隨意吃園中樹上的果子,只是不能吃智慧樹上的果子,但后來由于受到蛇的引誘,夏娃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并讓亞當也作了同樣的事,這就違背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上帝懲罰了蛇和人,并將人趕出了伊甸園②。這就是基督教和猶太教“原罪”的來源。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正統神學的奠基者奧勒利烏·奧古斯丁(AureliusAugustinus)對原罪進行了更加系統的論證,他說,人類始祖濫用了上帝所給予的信任,由從善走向了從惡,這種從惡的傾向不僅使得他們自己遭受了懲罰,還給他的后代帶來了世代遺傳的“原罪”[3]。在“原罪”思想下,基督教的塵世人生也就成為了一種罪感的人生:疾病、痛苦隨著原罪而來到人間。因為原罪,男人們汗流浹背地勞動,女人們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生育,到了收獲以后,人們還不得不經受疾病和死亡的苦痛。疼痛是對不忠和背叛的懲罰,現實世界中生活腐化、靈魂污染和作惡必受上天譴責和懲罰。基督教神學把物質看作精神靈性的墮落,疾病則是生命放浪不羈的罪惡結果,就這樣把疾病與罪惡(犯罪)緊緊捆綁在一起。人類在塵世的生活只是一個過渡期,是人類贖罪的過程,警示、告誡、拯救成為“神譴或天譴”理論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上帝恩賜的出現是為了拯救人們,使我們擺脫世俗及貪婪和罪惡,使我們有節制和公正地生活,等待幸福的希望和上帝的榮譽的出現(提多書2:11)。在《新約》的四個福音中隨處可見的都是耶穌基督為民去災治病的神跡,使人感到惡疾頑癥是人類背棄道德的苦果,而且整個治療過程則是信奉與傍依神靈,達到道德自新的過程。
隨著賦予疾病更多道德含義的基督教時代的來臨,疾病與“受難”之間漸漸形成了一種更緊密的聯系,身體與疾病意義的神學解釋變得日益復雜。“一方面,身體(肉體)根植于基督教的罪惡象征之中。人類身體的弱點和它最終腐爛以及人類不可避免的肉體有限性為原罪和自然墮落提供了一個顯見的隱喻(Trye,1954),另一方面,疾病可視作神意選擇的標志,通過神意選擇,正直的人們要受到痛苦考驗的凈化而變得完美,如約伯和拉撒路等圣經人物就表現了這一主題。于是就有了三種重要類型的病痛——麻風病、歇斯底里和癲癇病——傳統上這三種疾病既被視為人類罪惡產生的結果,又被視為神意選擇的標志。在所有這些‘神圣疾病’之中,在病痛的宗教定義語境中,麻風病尤其具有啟發性。”[4](P131)塵世的磨難被視為上帝的恩惠,比如麻風病人此世的痛苦會抵消掉來世的苦難,正如Brody所言:“這種病既是可惡的罪人患的病,又是上帝特殊恩典賜予的疾病”,雖然麻瘋病人被排斥在這個世界、這個有形教會的社會之外,但是他們的存在依然是對上帝的一個可靠證明,因為這是上帝憤怒和恩寵的一個表征。維也納教會的儀式書上說:“我的朋友,主高興讓你染上這種疾病,你蒙受著主的極大恩寵,因為他愿意因你在這個世界上的罪惡而懲罰你。”[5]拉撒路的寓言提供了視麻風病為神賜苦難的一種手段,通過忍耐,這種神賜的苦難最終會得到神的獎賞。古代基督教認為麻風病是天譴,是魔鬼侵入罪人的身心,也造成靈魂的污染。把麻風病與異教徒的歧視作連接,形成一套判斷人的文化論述,從而把病患打入文化的牢籠,并在現實中遭受歧視、排斥和迫害。
而瘟疫則更是天譴,在英國坎特伯雷教省,天主教大教堂主教于1348年9月28日的訓令對瘟疫的解釋是:“上帝對他的子民作下可怕的事,萬事萬物都要順從于其意旨的統治。那些人是他愛的,他責難的和他懲罰的;也就是說,他在他們的人世用各種手段懲罰后者粗鄙的行為,是為了不讓他們被永久地譴責。他經常讓瘟疫、悲慘的饑荒、沖突、戰爭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涌起,并且用它們來恐嚇、折磨人類,這樣就可以驅逐他們身上的罪孽。”[6]
蘇珊·桑塔格分析流行于西方的疾病天譴的觀念時說:“就前現代對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為,像任何一種極端的處境一樣,令人恐懼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壞品性統統都暴露出來了。然而,對流行病的常見的描述,側重于疾病對人格的毀滅性影響。史家們越是不受這種先入之問的左右,即疾病是對邪惡的懲罰,那他的描述就越發有能濃墨重彩于該流行病的擴散所昭示出來的那種道德腐敗……修昔底德談到公元前430年雅典爆發的鼠疫如何造成了混亂和無法無天(‘及時行樂的作風取代了榮譽感和得體的止’)……薄迦丘對一三四八年大鼠疫的描述——見《十日談》前于生產力和科技水平低下,歷史上人——所持的觀點不外乎是:佛羅倫薩的公民們行為不檢點。”[7](P39)如果說某些傳染病隱喻中的世俗觀念只是針對個體的審判,那么艾滋病則是在前現代語匯中對某個團體或全社會的“集體審判”。“艾滋病的隱喻是文化恐懼和焦慮中的膨脹和操縱中的‘古典瘟疫的版本’……人們感到艾滋病是無法避免的,全球流行的,并不是針對個體的懲罰,而是集體性的懲罰,是人類道德松弛和政治律令平庸造成的惡果。”[8]疾病天譴的觀念在艾滋病的社會反應達到登峰造級的水平,而且不僅表現對疾病的認識上,而且向更多的社會道德領域和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泛化,如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工業化國家“天譴論”流行,美國極右翼分子和教會極端保守勢力如綽號“惡魔”“保守主義復仇天使”的赫爾姆斯(即赫爾姆斯-伯頓法案的首要炮制者)和綽號“極右派小獵犬”的布坎南之流,他們不僅針對艾滋病等流行疾病,而且以反共、反對種族融和、反對男女平等和反同性愛論調名噪一時。
三、疾病的道德歸因:破除和反對闡釋
面對威脅人類生命和困擾人類身心健康的疾病,正確的歸因是疾病認識和治愈的前提。疾病是自然生理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社會現象。無論是“因果報應論”還是“天譴論”,東西方不約而同地把疾病視為一種具有強烈的社會、宗教和道德意義的過程和現象,身體的疾病由一套建立在以道德評判為基礎的基本結構之上的知識論所定義,疾病本身成為了一個符號性的判準,所有的身體表現都成為了必經其測量的一個客觀對象。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某種疾病可以被解釋為罪的咒詛或天譴,歸因為病患個體的德性、前世此生的行為經歷等,進而為病人貼上標簽,成為了一把衡量人的類別屬性的尺子,這尺子因背后的國民性理念而即刻升華成為一種道德的審判。同時與之相對應,醫學不再被看成是中性的,它所研究的問題,提出的方案本身都包含著價值因素,醫學價值觀也深深受到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這種歸因中明顯可以看出受到社會視角的影響和對自我價值的保護,體現出強烈的道德色彩,無論在歷史和現實中,疾病的道德歸因對社會文化和醫學科學發展的影響不可小覷。
亞里士多德曾提出的“校正正義”原則,即任何侵犯他人正當利益的暴力罪行,都應得到相宜的懲罰;任何被損害、破壞的人類交往正當關系或準則,都應得到相應的補救和恢復。面對社會道德危機,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賞罰機制猶顯重要,面對瘟疫疾病的肆虐和人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天譴和因果報應的觀念從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社會有效的道德約束和懲戒機制,正如亞當·斯密所說:“違反正義的行為必須在現世受到懲罰,并不僅僅是出于維持社會秩序的考慮,上帝和宗教讓我們指望這種罪行即使在來世也會得到報應。雖然人們沒有見過這種懲罰的先例,也不可能因此而不犯同樣的罪行,但是我們卻感到這種報應會如影相隨,直到死后。所以我們覺得不能沒有一個公正的上帝,他將為那些在世間飽受欺凌、無人為其主持公道的孤兒寡婦們復仇。因此,在任何一種宗教或世人所知的迷信中,都有一個地獄用來懲罰罪人,還有一個天堂用來報答善行。”[9](P82)這種機制引導人民按照宗教道德的教義規范生活,由此可顯現政治、道德文化因素在疾病特別是傳染病的防治和社會控制、在約束人們行為養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方面所發揮的正面積極作用。
疾病天譴和因果報應的觀念同時更是一種宿命性、毀滅性的道德力量,各種社會話語通過隱喻的方式把疾病的來源歸因于不良生活習慣、遺傳或性格,特別上升為個體或群體的德行考量,在原本單純的疾病之上賦加諸多價值意義,最終訴諸于上帝天譴和前世因果報應,這種抽象的歸因充滿道德偏見,它使病人這一稱呼嚴重污名化,從“受害者(Victim)”變成了“應得者(Deserve)”,由“不幸的人”變成“罪人”,一個道德上有過錯、有污點的人,即使他今生無錯,也肯定是前世沒做好事,這是一種或大快人心或令人絕望的道德懲戒。社會形成的疾病道德評判,很多時候是負面和恐怖的,它決定了社會對特定疾病和病人的道德和情感。對患上重疾的病人來說很容易產生恥辱感,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并進而轉換成一種罪惡感壓迫,由此引起的包括恐懼、害怕、焦慮、厭惡、懷疑、憐憫、過度保護等一系列常見的心理扭曲和社會反應,不僅使一些病患在懊悔、糾結、抱怨中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影響疾病的防治和預后,更有甚者會導致病患在心理絕望和社會偏見排斥中放逐自我或傷害他人。因為他者的生活方式的差異,即使并沒有妨礙自身權益,不尊重他人權利,將某種自居正派的社會文化與價值建構的知識偽裝為真理,端文化霸權之勢,行歧視排斥之實,以“天譴”“報應”詛咒他人在疾病中痛苦地死去,折射出我們社會中殘存的相當不健康的文化專制主義陰暗心態。人類歷史上,為保護自身健康,免于遭受病魔侵害,常常受宗教或迷信觀念的支配,將疾病視為因果報應或上天的懲罰,躲避、驅趕或關押乃至大批殘殺和消滅那些被認為患了傳染性疾病或瘟疫的個人、家庭、社群部落甚至整個人種,這樣的惡劣悲劇和慘痛教訓在歷史上曾不斷發生。而因果報應的詛咒甚至延伸到生前死后,這種冥冥中不確定何時來到的報應造成的精神折磨也絲毫不遜色于社會排斥和人身迫害。這種因病而生的偏見、排斥甚至迫害,直接踐踏了公民尊嚴的底線,侵害了病人的正當權利,傷及社會公正的終極價值,也最終影響社會和諧。
赫舍爾曾說過:世界原本沒有意義,而人通過各種話語賦予世界以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意義,這是一個使人的生活世界變得豐富多彩甚至具有一定神秘性的過程,也是使世界變得貧瘠、枯竭的過程。各種社會話語形成的疾病隱喻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反映和闡釋,它使疾病在日益復雜的社會空間里被附著上越來越多的社會文化、道德和政治意義,最終走向“因果報應”和“疾病天譴”宗教化的闡釋,正是一個“賦魅”的過程。這實質上是一種道德偏見。疾病并非隱喻,疾病本身是無辜的,福柯說:“疾病的‘實體’與病人的肉體之間的準確疊合,不過是一件歷史的、暫時的事實。”在西方的分類醫學那里:“疾病具有與生俱來、與社會空間無關的形式和時序。疾病有一種‘原始’性質,這既是其真實的性質,又是其最規矩的路線;它是孤立存在的,不受任何干擾,也沒有經過醫學的加工,它顯示了自身本質如植物葉脈的有序脈絡。但是,它所處的社會空間變得越復雜,它就變得越不自然。在文明出現之前,人們只有最簡單、最基本的疾病。農民和老百姓接近于基本的疾病分類表。”[10](P1)疾病隱喻帶來思考的認識,也帶來幻象、遮蔽,帶給被隱喻之物意想不到的陌生感。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光靠回避不行。它們必須被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11](P161)疾病通過隱喻等方式道德歸因過程的揭示,以及疾病因果報應和天譴的原罪分析,就是一個去蔽和“祛魅”的過程。凡是人尚且無力進行因果思維的地方,人們就會進行道德思考,對疾病的道德祛魅就是基于科學理性的觀點,反對道德在社會一切領域中的泛化和僭越,劃定社會生活領域中道德盤踞的疆界,反對疾病的道德意義闡釋。
殷海光先生在談及對文化的價值判斷時曾以醫學為例說明:“我們在把文化當作對象來看待之時不能對價值再做價值判斷,正猶之乎醫師在診斷病情時只能問某一病疾的實況怎樣,而絕不該問某病該不該患。問某病該不該患,那是倫理家的事。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尤其是,醫師在診斷病情時,不可有意無意預存對某種疾病的好惡之情。就一位倫理家的立場來說,也許患梅毒是一件可惡的事。但是,就一位醫師的立場來說,既不可喜好梅毒,又不可厭惡梅毒。論及文化也是一樣,論及者不可同時將自己對于作為論及的對象的價值戴上價值顏色的眼鏡來看。”破除和反對疾病通過隱喻等社會話語的闡釋和歸因,要平息想象,而不是要激發想象,撥開籠罩在疾病真相之上的蒙蔽,消解患者被“物化”乃至或被非人對待的狀況,澄明去蔽,回到福柯所說的疾病的“原始”性質,回到生命的本真。還疾病本來面目,破除病人的污名,將其視為身心陷入困頓需要救治和幫助的同類。不是以道德的名義、以健康的名義評判指摘他們的生活方式選擇,并在群體力量或者媒體權力的裹挾下形成社會道德偏見,制造恐怖氛圍歧視、排斥甚至迫害身心飽受病魔折磨的患者,而是更關注疾病的防治,關懷病患的身心,這對疾病防治和病患關懷以及社會文明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注 釋]
①大方廣總持經,梁皇寶懺,摩訶止觀輔行三十二卷.
②創世紀.第3章,第14-19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