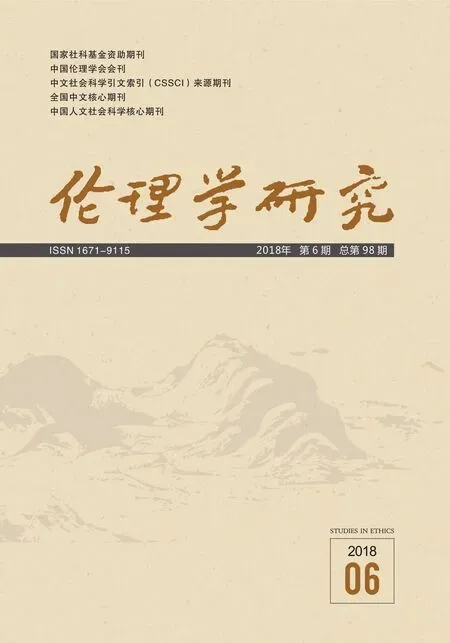居住需求倫理的本質與功能探論
陳叢蘭
一、居住需求是居住倫理的本始要素與基石
從生存的本體性層面來看,居住需求是人們身體棲息最為原初性和本根性的集中體現。“一切表象只有在時間與空間的舞臺上才能登臺亮相”[1](P38),沒有空間與時間,人和其他任何存在物都無從顯現,更妄論生存、生命的活動。而“住”則是對人的這種空間性的最本質表達,“是所有活動發生的地點,它們之間聯系以及共同的基礎”[2](P97),決定、限制與生產了人的生存需要、生活實踐和大多數的生命活動。“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等諺語即是對此的生動描述。如果把“住”落實到現象層面,居宅空間、社區空間到聚落空間和城市公共建筑空間,它們構成人類生存、生活和生命的棲身之所,人們在其中繁殖繁衍,容納與展開生活,在類的生活中發展與完善自己。
從生存的合目的性與意義維度上看,居住需求凸顯出人之生存的生命意義與倫理蘊含。與其他動物的生存活動不同,人的生命活動決定于其自然性與社會性、物質性與精神性、現實性與理想性的二重本質,其生命活動的獨特性在于人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3](P57),能把生命意識與生命存在區別開來,形成生命意識對生命存在的審視和反思。在人把生存活動作為自我意識審視和思考的對象的過程中,超越自然性而創造一個“屬人”的生活,一個人的生活世界。正如卡西爾指出的:“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就存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對人類生活的批判態度中。”[4](P10)因此,盡管在生存的本能層面,在生命的基本需求序列上,“食”的價值的確優先于其他所有的生存活動,為了維持生命,人可以露宿風餐、茹毛飲血,所謂“民以食為天”,沒有什么比“飲食”更基本、更重要的活動了。然而,如果僅僅從這一層面審視人的生命活動和人的生活世界,就像馬克思指出的:“如果我們的自由歷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的自由歷史和野豬的自由歷史又有什么區別呢?”[5](P5)人的生活又與其他動物的生存又有什么區別呢?因此,我們更多需要關注的是,人順應自然而又利用和超越自然后所創造的那個“屬人”生活和屬人世界。在“屬人”的世界中,“住”一方面總是比其他日常行為更緊密地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相連,涉及執政的合法性、制度的公正性等一系列問題,“人人擁有適當的住房”的“居住權”則構成人權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人類構筑的居宅、城市等日常居住空間,容納和生產人的日常生活行為,限制和規定包括飲食在內的其他所有日常生活行為,“風餐露宿”不再認為是自然而然的。“住”還是人們對人生狀態予以評價的根本標準,“住有所居”“安居樂業”是我們對于好生活的基本判斷,相反“居無定所”和“流離失所”都被視為人生最悲慘的境地,今天更是“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正是“住”使人更像人,通過居住,我們獲得自我本質,發展人性和提升了自我意識,最后成長為真正意義的人。
從存在的歷史意識維度看,居住需求是人建構生活理想和價值世界的本始要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既表現在生命時間的單向性,也體現為生存空間的有限性。所以,人努力追求的那種超越自然和自然局限的屬人生活,正是為了能使自己的生命具有超越時空的局限,即“不朽”。不同的文化系統中,人們實現不朽的機制大相徑庭。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借助對至上存在(Being)和天國的信仰加以實現。在中國的人本主義文化系統中,生命的超越由兩部分完成,一是肉體的不朽,這主要由生命自身的繁殖完成;另一個則是精神的不朽,這主要依靠個體德性與精神境界的攀越去實現。儒家將這種追求精神不朽的活動定格在日常灑掃應對進退的生活實踐中。盡管中西方追求生命不朽的文化機制不同,但在現象學層面卻達到一致,即都是以對象化的建筑空間為象征符號去言說、呈現和承續人類的這種希望與追求。西方連接人間與天國的神圣之所——教堂被重視,在中國,不朽就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帝王的宮殿,還是普通百姓的陋室,它們是中國人的“教堂”,承載了中國人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精神永恒不朽的信念。迄今沒有哪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對棲身之所投注如此深情的眷注并將其與安身立命之道緊密地聯系起來。幾千年來,人類正是通過自己的建筑活動與所創造的偉大建筑,表達人類的軟弱、寄托人類的希望和承載人類的存在意義。因此,這些建筑不僅僅是有尺度、有形態的物理學意義上的空間,更是人“據以度測他的安居、度測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逗留的尺規”[6](P94)。
綜上可見,相比其他的日常生活需求,無論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整體層面,還是從個體的存在意義層面,居住需求都具有更為豐富、豐滿和跨越時空的文化的、倫理的象征意蘊。人把生存活動作為自己的意識審視和思考的對象,不斷追問自己怎樣存在、為什么這樣存在、應當怎樣存在等,以找到理解我是什么、我將成為什么、我應當成為什么的基本根據,這構成“此在”的基本內容。哲學家海德格爾和詩人荷爾德林正是從人的此在出發來理解棲居,把“居”視為人的本質規定,進而把建筑看作是讓人類安居的詩的創造[6](P89)。因此,居住需求絕不僅僅是類似于人類其他日常需求的一般性需求,它在人們的需求體系中具有本始性、基礎性、根本性和普遍性要義,因而成為維系生存、活化生命、健全生活的“拱心石”。
二、居住需求的發展確證著生活倫理的內核與要義
人的“需要”理論上既表現為對需求對象的依賴,還表現為對需求對象的渴望,是激發主體活動的動力源泉[7](P49)。依此審視居住需求,它一方面體現為人們對居宅為核心的居住需求物的依賴,視其為生活的始基,通過“居”帶給人歸屬感、安全感、尊嚴感、自主性和價值感等情感滿足。另一方面,當居住資源缺乏時,人們必然在體內產生不平衡、焦慮感和無價值感等,為了消除這種感覺,就會把對居住物的渴望變成行為的動力機制。由于居住資源的缺乏會隨著外在條件的變化不斷變化,主體對于居住對象的渴望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馬斯洛的需求序列理論對此作了很好的分析,居住需求就內在于并彰顯著這一需求序列,在其動態的發展過程中確證著生活倫理的內核與要義。
首先,作為生存論意義上的居住需求構成以穩定的、適當尺度的居宅空間為核心的現實利益,是人們建構生活及其倫理的基礎和根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需要解決溫飽問題,以便能夠生存和維持身體健康,如果沒有適當的居宅及相應的衛生和保障等設施,就必然會導致主體的“明確的、客觀的嚴重傷害”,這種嚴重傷害不僅體現在身體健康、人身安全和精神的焦慮不安等,還會對人的生存和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使個體根本地喪失對美好愿景的追求能力。所以,滿足“住有所居”的需求應該被視為人的根本利益和生活的始基,這也是為什么聯合國在《人類住區溫哥華宣言》(1976年)中指出“擁有合適的住房及服務設施”是一項基本的人權。
其次,作為發展意義層面的居住需求構成以和諧、有序正義的居住環境為核心內容的現實利益,是塑造豐富人性和構筑美好生活的基礎。居住基本需要的滿足激發、創造了新的需要:需要再生產自己與生命,需要他人的支持且與他們保持融洽的關系,需要私有空間以培養自己的羞恥感;需要參與社會實踐獲得尊重與被尊重;需要在較高層次的學習中,形成評判性、解放性的理性意識,以評價自己所屬的文化的概念資源,支配自己的生活環境,以滿足馬斯洛關于自我實現的最高需求。在滿足這些需求的過程中,社會所提供的衛生、教育、通訊等居住滿足物具有絕對的道德力量,目前許多西方國家關于居住的福利主義和慈善團體對此所做的工作都證實了這種道德力量的存在。同時,這些滿足物所蘊含的人本而非物本、高雅而非卑俗、公正而非不公正等的倫理價值追求,在貞定人們的道德心靈、善化生活方面也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社會在保護現有的需要滿足水平的同時,應當盡一切可能的方式努力提高居住需要在這一階段的滿足水平。
最后,享樂意義的居住需求確證著人對生活美好的感受并形成幸福的生活品質。這主要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居住精神上的“樂居”,指居住主體精神超越物質環境的限制而達到的一種超然狀態,一種在陋巷而不改其樂的“樂居”境界。這可能是通過發展性居住需求的滿足后的結果,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必需的需要已經滿足之后的需要,是一種人類精神一定會達到的無所需要的需要”,在思維中達到自身并在自身中的寧靜狀態[8](P10-11)。另一個是在物層面的“豪居”,指一部分人所追求的遠遠超出普遍居住水平的居住狀態。但這些欲望滿足的前提在于不危害其他人的基本需求滿足、子孫后代和自然環境,因此需要他們必須具備一定的消費理性、社會責任和正義的美德。然而,在現代社會,由于異化擴展到全部生活,任何個人都無法擺脫這種異化[9](P196)。這使人的需要也嚴重異化,人們把對金錢、物質的追求視為至高無上的需要,對奢侈品的擁有成為衡量人的存在價值的唯一尺度,鋪天蓋地的廣告讓人們相信“豪居”才是好生活的標志,對物的依賴和消費的控制導致了當代的人住得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寬敞,各種服務設施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齊全、便利,但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感到糟糕、苦惱和焦慮。要想消除這種異化,按照列斐伏爾的觀點,社會主義國家就需要承擔應有的責任,“社會主義空間的生產,意味私有財產以及國家對空間之政治性支配的終結,這意指從支配到取用的轉變,以及使用優先于交換”[10](P55)。堅持優先發展諸如安居房、經濟適用房和民用房等基本需要滿足物質生產而非居住的奢侈享樂品生產,保障“房子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用來交換的”,以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參與社會生活、發展自身的機會。
要之,作為一個歷史的范疇,居住需求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都生動具體地反映了人們對于生活的基本需求與其根本利益所在,確證著生活的意義和人性的豐富程度。因此,對于居住需求,任何社會都不應當將其僅僅視作一個經濟問題,而應該充分關注和重視其所涉及的人性尊嚴、個體權利、生活意義和社會正義等重大倫理問題。同時,社會在對居住需要滿足的過程中,必將引起整個社會生產、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態等一系列的變革,從而推動著社會的發展進步,而社會進步也在更高水平上不斷完善居住需要的性質,從對物質利益的純粹追逐深入到對善、美等精神價值的追求境界。
三、居住需求構成民生倫理、執政倫理的價值基礎
“民生”即百姓的基本生計、生存,它以衣、食、住、教為核心內容。對于以居住為生活方式的人類來說,居住需求的滿足無疑是關鍵要素,為基本需要滿足的最優化目標。只有通過居住空間,人類才能為生命形態的身體提供一個相對安全的棲息之所,給自己的生命繁殖與種的繁衍提供便利的條件,因此,“這些需要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行為者才能有效地參與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實現任何有價值的目標”[11](P69-70)。滿足與否、在多大程度上被滿足都將根本地決定身體的健康,以及道德的培養、自我的建立等精神健康問題,繼而也就賦予社會應該使所有人的居住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滿足的義務與道德準則,使居住需求必然與執政倫理、社會倫理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對于執政者來說,首先必須把居住需求的滿足置于國家治理、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是民生之根本利益,也是執政的倫理價值基礎。所以,自古及今,百姓居住需求的滿足都是執政者和思想家致力思考解決的重要問題。按照哈耶克的國家防止貧困最低“安全網”的意義,居住需求的滿足具有絕對的意義,當人們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和居住貧困等表示憤怒的時候,背后的一個信念就是:居住是一個社會應當優先得到滿足的需求。因此,執政者必須把給人民提供足夠的居宅和其他的公共建筑、文化服務設施作為發展的首要目標,以確保人民最低水平的生存、健康需要和鋪展生活。只有這樣,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才能夠筑牢執政的價值基礎。
其次是在具體的實踐層面,為滿足人民的居住需求,執政者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生產和繁衍系統,以供應和分配人們關于居住需求的滿足物,即現實利益的生產、繁衍與分配等問題,這是保障民生與鞏固執政基礎之本。在生產階段,一方面執政者需要把功利與道義相結合,有效協調需求與市場、生產與環境等多方面的利益關系。另一方面,必須意識到,對于居住需求的滿足問題,如果僅僅依靠國家主義只會導致普遍的“貧居”,例如在國家家長式統治下,國家通過對需要的控制實行對社會的勞動階層的嚴格控制,為工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物質條件,以保證工人較低水平上的生理和文化再生產;但只遵循市場邏輯則會帶來居住的巨大貧富差距,以及潛藏著的社會矛盾和危機。正如柯布西耶指出的,現代人的棲身之處,是他的城市、街道、住宅和忍無可忍的公寓。因為現行城鎮和居住區的布局,是樓房越來越密集,逼仄的街道縱橫交錯,噪音喧囂……這樣的環境甚至阻礙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家庭的危機,直接就波及人性的危機、社會的危機和政治的危機[12](P237)。因此,在居住需要的生產過程中,執政者必須肩負起引導、規范和監督的職責,把可持續發展變成空間生產的根本倫理原則,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建設建基于此。
在居住需求品的分配階段,執政者所制定的公正分配制度無疑是最重要的。以居宅為例,居宅通過消費轉化成個人、家庭和社會的需要滿足。在每個人、家庭和社會階層之間分配居住空間,使他們能盡可能有效地參與自己的生活方式,把這些利益滿足轉化為個人的健康、家庭的和睦和社會的和諧等需求。在這一分配的過程中,無論是程序還是實質,公正的社會分配是根本的倫理原則,使人人有權利并且能夠獲得居住需要的滿足物。假如居住資源生產的總量和質量的提高是以滿足需要奢侈品的形式實現,或者不能分配給那些需要的人,有著舒適宜人的自然、社會環境的居住區總是被“高端人口”所占據,所謂“低端人口”將不得不忍受擁擠的居宅、污染的空氣和水源等,就是對后者權利的剝奪與損害,必然阻礙后者形成尊嚴、信心和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也將根本影響執政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危。所以,作為民生倫理的核心內容,居住需求的滿足關乎人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在現代社會中,這些都必須是在一個制度的環境中才能獲得,而社會制度的長期存在也有賴于此。
最后,執政者還需要保證有一套使人們居住生活正常進行所必需的倫理價值系統,這種倫理價值需要得到足夠大范圍內居民的認同,沒有這種普遍的認同,就難以形成生活在本質上的和諧,甚而使共同的生活難以為繼。在居住生活中,人們主要結成三組倫理關系:家庭、鄰里和路人。在傳統社會,基于血緣、地緣的居住格局,由家族主義和儒家文化等共同打造的生活空間總體呈現出一種整體性、同質性(homogeneous),這使得“居同倫”很容易被確立起來,“父子有親、夫婦有義、長幼有序”等家庭倫理規范,以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鄰里規范獲得相對普遍的認同,同時以“擬血緣化”的方式,保證居民與路人之間建立彼此認同的倫理關系[13]。但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曾經“被嚴格控制的、同質化的總體社會架構分化成諸如家宅、勞動、休閑、運動、旅游等的空間碎片”,這些結構清晰、功能明確的空間體有著自己的語言表述系統、專業人士的期許和社會的目標指向[14](P91)。與空間碎片化相應的是人們在這些不同空間中所遵循的倫理價值的異質化(heterogeneous),這種異質化導致整個社會的倫理結構的震蕩重組,造成人與自身、家庭、鄰里等倫理關系的矛盾沖突,原子化的居住方式變成當代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從根本上違背人的情感、尊重、認同和自我實現等精神需求。因此,執政者必須充分意識到這種現象對以往確定無疑的生存、生活意義的解構,對整個社會起到的離心作用,需要在尊重多元化選擇的基礎上,確立符合人們生活需求、具有主導意義和社會引領作用的倫理系統,因為認同總是通過國家、宗教和社會等提供給人們的價值得以形成,這正是從居住生活所審視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時代意義所在。
要言之,居住需求不僅是民生之本,又因其需求對象的基礎性本根性意義而與執政倫理有著最為內在的關聯,關乎人權、社會和諧和執政倫理建設等價值的實現。今天,習近平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而美好生活的核心內容就在于“居住的美好”。但不容忽視的是,當代中國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使居住問題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和長期關注解決的重大問題。正所謂“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健康中國、幸福中國的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均需要從對人民居住需求的滿足開始,因為對于身居大地又仰望星空的人類來說,需要擁有一片屬于自己的空間,在這一空間以及這個空間所賦予的全部生活內容中,去實現人性的豐富和個體與類的統一,而只有具有豐富人性和“共同善”等倫理意識的國民才是美好生活、中國夢的真正建設者與守護者。
四、居住需求凝聚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
居住需求既關乎民生倫理,還深契著執政、社會的倫理內涵,更聯通著使人之為人的形上精神追求。所以,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價值追求就滲透在居住需求發展的每個階段,它們在構成每個階段居住需求精神要義之時,也反映了居住需求在導引人們生活意義追求和實現的功能特征。
在基本需求滿足階段,對容納身體、保護生命的適度居住空間的需要是生存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住有所居”就成為這一階段人們追求的普遍的、基本的價值目標。作為以“居住”為生活方式的動物,在這個等級排列與和諧的宇宙中,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位置,而人只有依靠以住房表現出來、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等等的產品才能生存和生活[3](P161)。從最簡單的穴居、巢居、地面的土木建筑到今天的鋼筋水泥大廈,無論哪種形式,它們都是人生存的基本物質資料,如果“有居”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不僅健康受到了最基本的傷害,而且將會被排除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之外。人類對居住需求物所提供的遮蔽、保護等功能的追求,也被多亞爾稱為“中間的需要”,即實現人的發展這一更高價值的中介,決定了居住需求及滿足物的“實用性”特征。例如中國古代建筑實踐以“厚生”為根本的道德原則,“厚生”包含兩個層面,一為“便生”,“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棟下宇,足避風露;高臺廣廈,豈曰適形”(《 隋書·煬帝紀上》)。這里的“便生”既有方便生活之義,更有以現世生活為本、方便現世人的內涵。“厚生”還要求建筑實踐做到“阜財利用,繁殖黎元”,也就是以老百姓的生存繁衍與國家的寧和為目的,即“國泰民安”。當代社會更需要把對普通民居、安居房、經濟適用房等基本需求生產作為優先發展的目標,否則就是對人權的剝奪與傷害。基于居住需求對“有居”的價值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功利利益通常被作為道德的基礎,勤勞、謹慎、秩序、判斷等被視為最重要的品性,它們趨于增進具有這些性格的人的生活福利。
在居住需求的發展階段,基于規范、秩序與和睦等價值的“善居”是人們的核心需求。正如亞里士多德指出,城邦等居住共同體的長成出于人類居住生活的拓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15](P5-6)。在滿足居住需求的過程中,人類生產了自己,更生產了社會。所以,“住所(shelter)概念不只是與氣候和溫度有關,而且與社會為住所確定的用途有關……住所包含了做飯、工作和娛樂空間以及隱私的概念,還包括了更高層次上的文化概念,如溫暖、溫度、特定家庭成員的隔離以及諸如睡覺、做飯、洗衣、排泄等不同的功能”[11](P28)。夫婦、父子等家庭關系、鄰里、朋友等其他一系列社會關系漸次產生,相應產生的是如何協調個人與集體、公與私、人與我利益矛盾的需要,于是“夫義婦聽”“父慈子孝”“守望相助”的道德規范與關系的和諧成為居住生活追求的理想價值目標,即“善居”。對“善居”的追求凸顯出居住需求的“倫理性”特征。從傳統走到今天,日常的言行規范、建筑的空間格局等都已發生根本改變,然而,居住滿足物必須蘊含的人性、人本和人文的倫理內涵,日常生活中應該把他人的利益作為道德的基礎,個人的居住需求滿足必須符合其他人的需求滿足,關注社會與個人的相互協調,等等,仍然是基本的道德原則。而誠信、孝義、友善等仍然是增進倫理關系與社會和諧的最重要品性,這些都不會隨著歷史的變遷、社會形態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改變而發生改變,始終是實現“善居”的價值方式與核心倫理內容。
人之為人,其生存的價值絕不僅僅是對“有居”“安居”的基本利益滿足,以及一般意義的“善居”這一倫理性滿足,而是有更高的意義和追求,由此而進入居住需求的“審美化”追求向度,即人們對居住滿足物和居住生活所提出的美不美要求。按照盧卡奇的觀點,這是人追求自己的總體性之使然,因此,藝術的深層根基從來沒有脫離日常生活,藝術的“獨特的活動受益于其在日常生活層面所獲得的豐富性”[2](P95)。而人正是在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創造美和實現自己的總體性存在。為追求一種“美居”和“雅居”的生活形式,居住需求不再局限于實用性、功能性的層面,而是追求居住滿足物是否符合審美要求的問題,居住矛盾在很多時候也已顯示為人們對兩者的追求和愿望無法滿足之間的矛盾。居住滿足物的生產者則通過將美學滲透在產品的設計中,把美變成千家萬戶生活的一部分,以公共建筑、居住設施等美學形式為日常生活建構了一個審美化的環境,居住需求開始超越現實與私利,邁向對抽象原則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亦即海德格爾的“棲居”,“棲居的真正困境并不僅僅在于住房匱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戰爭和毀滅事件更古老。真正的棲居困境乃在于:終有一死的人總是重新去尋求棲居的本質,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16](P170)。本質上看,“棲居”即“樂居”,它意味著人的居住生活全過程,是一種“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自覺狀態。
結 語
綜上可見,人人都有對居住的需求,人人都有正當的居住需要得到滿足的道德權利。居住需要的豐富程度及其滿足程度反映著人性的豐富程度和社會的文明化程度,也是我們確定生活美好與否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始終只能生活在貧乏的居住空間這一狹窄的活動邊界,只能有限地生存和行動,只能過著匱乏的、碎片化的生活,被焦慮所困擾,這是與人們的美好生活追求相違背的。因此,我們的社會所擁有的所有資源,它的能源和活力,它的價值觀和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應該集中于對人和人得以發展的健康生活的建立上,現實的政治、制度設計和社會努力也應該將如何滿足經理性所思考確立的居住需要作為發展目標,并以此來判斷社會的正義、和諧度,以及生活美好與否的問題。畢竟,生活的美好從居住的美好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