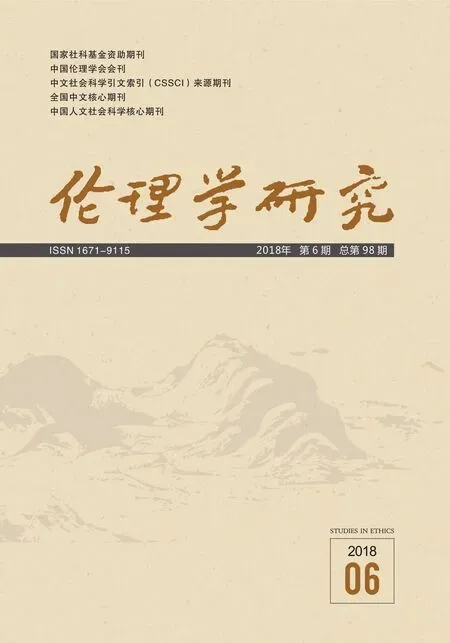先秦儒家道德自由思想的當代價值
譚培文
馬克思主義自由意識的道德自由思想,在中國民族文化中的最初基因是先秦儒家自由意識的道德自由。先秦的自由思想真正開拓者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為代表的儒家。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不僅遠遠超出了莊子的水平,甚至達到了古希臘遠未達到的先進水平。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無疑是馬克思主義自由意識道德自由中國化的民族文化基因,是社會主義自由核心價值觀的優秀傳統文化根源。
一、先秦儒家對道德自由的理解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先秦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種人倫文化,而人倫文化的邏輯起點即是自由意志的道德自由。既然承認中國先秦儒家文化是一種人倫文化,又說中國缺乏自由意志的道德自由概念,無疑是一種邏輯悖論。先秦儒家(以下簡稱“儒家”)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的核心命題是《論語·為政》中的“從心所欲不逾矩。”這里的“從心所欲”即儒家對自由意志自由含義的理解。按儒家的思想,“心”就是指的精神,而精神又包含了“思”與“欲”、“志”與“氣”、“神”與“行”等方面的關系。通過這些關系的厘定,闡明了自由是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
首先,通過“思”與“欲”的區別,闡述了“欲”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思想。“思”是思維的意思,“欲”為人的意欲。儒家“從心所欲”的“心”,并非物質體的心臟,而是指的人的精神。《荀子·解蔽》說:“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1](P225)。心是形體的支配者,更是精神與智慧的主宰。“心”作為精神既然包括思維與意志,那么,“心”就是作為認識的思維與作為“欲”的自由意志的統一。儒家的“從心所欲”的心,既然是一種精神,那么“欲”就是一種精神的意欲。欲望、意志才是自由的。
其次,通過“志”與“氣”的區分,闡述了是否具有“志”的自由意志是培養道德之氣之前提的思想。《孟子·公孫丑上》在談到如何養浩然之氣時,論述了志與氣的關系。孟子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這里“志”,就是自由意志;這里“氣”,就是由“志”統帥、支配的意氣,如喜、怒、哀、樂、勇、怯、羞恥等。如何才養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呢?孟子認為,“培養浩然之氣”的前提在于把仁義等道德自由意志內化于心,而不是像告子那樣只知道做一些外在的表面功夫。孟子說,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8]。浩然之氣是一種道德正氣。道德正氣不是心外的東西,而是仁義等道德自由意志的一個長期培育和內化于心的過程。由于告子把義等道德意志當作一種外在的東西,這就不懂浩然之氣的培育方法。按照告子的方法去培育浩然之氣,那就等于拔苗助長一樣。換言之,不斷地把道德的自由意志內化于心,才是培育浩然之氣的根本途徑。
再次,通過“神”與“行”的區分,闡述了意志自由就是出于德性原則的自己為自己立法的思想。心是精神的主宰,是發出命令而不是接受命令的。形可以隨心詘申,但精神“不可劫”而改變自己的自由意志。精神的作用就是自己禁止和支配自己的身體,自己放棄和制止錯誤的意見或命令,自己主張自己的行為,自己停止自己的意念。這種自己支配自己的行為、自己命令自己的意念,就是自由意志。
儒家思想家雖然不可能用現代的概念來表示意志自由,但是,他們用中國的民族語言揭示了現代自由意志概念的思想內涵。在孟子那里,這種自己為自己立法的德性原則,是人們出于善的本性本來就應該具備的。《孟子·公孫丑上》認為,人人皆有怵惕惻忍同情之心,“無惻忍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忍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P56)按孟子,心本身具有認識判斷是非的能力與自由。孟子把德行原則看作是善之本性具有的原則,人們對于仁、義、禮、智、信等這些德性原則的踐行,決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一個愿不愿為的問題。《孟子·梁惠王上》在談到人人都有不忍之心時,認為,做國君的只要愿意行王道,推恩以施仁政,就可以“保民而王”。他說:“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2](P137)能不能夠、愿不愿為,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能夠并且愿意,就等于說,你能夠,所以你應當。孟子不僅通過“為長者折枝”的比喻,說明了“施仁政”是“不為也”,非“不能”之緣故,從而揭示了作為道德行為自由選擇的“你能夠”與作為一種道德立場的“你應當”之間的聯系,而且認為“你能夠,因為你應當”之自由選擇與道德立場,都是出于人之本性本來就有的“不忍之心”的善的道德意志。孟子這種人性善的觀點,荀子并不贊同,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1](P267)但是,孟子與荀子從“心”出發論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道德行為都是出自道德自由意志的行為。孟子從人有不忍之心出發,認為,“為與不為”,取決于“你能夠”的意志自由選擇。荀子之所以把人的行為看作是“自禁、自使、自奪、自取、自行、自止”的行為,是因為“心容其擇”,即“心”有意志的選擇自由。張岱年說:荀子提出的“所謂‘心容其擇’,意謂心有抉擇的自由,也就是意志的自由。”[3](P236)
二、先秦儒家道德自由思想的基本內容
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自由思想內容十分豐富,大大地超越了同時代的古希臘。
1.明確地提出了自由與“矩”的必然限制相聯系的思想
“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矩”,原本是古代畫方形的用具,也就是現代的曲尺。《周髀算經·卷上》云:“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有規矩、法度之意,“不逾矩”就是不跨越“仁”的倫理規矩與法度的限制。《孟子·離婁上》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2](P115-116)。雖然孟子的“法先王”之“法”主要是指道德規范,它并不同于管子所講的“治世”法治之法,但孟子與管子都是針對“矩”的限制而言。限制相對于自由,就是一種必然。因為,作為與自由相關的必然,不是超越主體之外的純自然(如斯賓諾莎的“實體”,就是一種脫離精神的自然),而是作為外在自然規律、作為社會環境或主體認識能力與水平限制的必然。當然,孔子的“矩”,主要是指人倫道德規范作為必然的限制。但是,也正是由于這一主要指向,往往就掩蓋了儒家對必然限制的全面理解。事實上,儒家的對天人關系的理解、儒家法家學派關于法的限制的思想,就涉及到“矩”的必然限制的自然規律與社會環境等內容。比如,孟子用“拔苗助長”的比喻來說明如何養浩然之氣的路徑,實際上闡明了對于農作物的種植,必須尊重植物自然生長規律的思想。這就是說,先秦儒家所說的矩,就是指的必然的限制。既然這里的矩是指的必然的限制,那么,在孔子那里,自由就是一個必然限制相聯系的范疇。這就不僅大大地超越了同時代的古希臘,而且近代西方也不過只是接近或達到先秦儒家的思想水平。如孟德斯鳩關于自由不僅需要法的界限,“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的思想[5](P154),以及盧梭關于自由就意味著限制的思想等。可見,只有中國先秦儒家關于自由與限制思想,才是人類最初對自由思想探索的文化基因。
2.明確地揭示了自由的不同境界的思想
孔子把“從心所欲”與“不逾矩”相對立,實際上揭示了“從心所欲”自由理想境界與現實“矩”的限制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是,這里的“不逾矩”究竟如何理解?“不逾矩”既可以與“逾矩”相對而言,“不逾矩”也可以與符合“矩”的要求相對立。所以,這里實際蘊含了三種關系:自由與“不逾矩”的關系,自由與“逾矩”的關系,自由與符合“矩”的規范要求的關系。這三種關系展示了先秦儒家自由思想的不同境界。
在儒家看來,“欲”的意志是人的本性,但欲的自由意志,一是具有無限性,二是具有兩面性。如《荀子·正名》認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1](P259)由于欲的無限性,人人盡欲是不可能的,但欲之可節也。孟子雖然主張寡欲,但他論述了欲的兩面性,《孟子·告子》云:“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義者也。”[2](P198)在《論語·堯曰》,孔子也說:“欲仁而得仁,又焉貪?”[5](P192)這就是說,欲有生與義之層次高低、仁與貪之善惡的兩面性。在生與義的二難選擇之間,在仁與貪的善惡選擇面前,人的欲望意志應該舍生取義、欲仁而不貪求。
由于欲的兩面性,面對現實,究竟如何處理欲與仁的關系?《孔子·憲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5](P127)原憲問,一個人如果在現實中不再有欲望,是否可以稱之為仁呢?孔子說,那真是太難了。然而,即使欲之不行,是否達到仁的高度,我也說不清楚。可見,企圖在現實中消滅人的欲望意志,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欲不可去,那么,“欲”就是實然。但是。基于欲的兩面性,那就應當給“欲”一種“德”或法的規范限制。這就需要像“矩”一樣的尺度。按孔子“矩”的規范就是“仁”,但即使去欲,是否就達到了仁的規范的要求?“吾不知也”。這就是說,“從心所欲”的價值規范是符合“仁”的要求,而不是“不逾矩”。“不逾矩”僅僅只是一種現實中符合倫理底線的自由。可見,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的基本維度就是現實性。“不逾矩”是不跨越與在“矩”的規范要求之內之意,而逾矩就是“超過”“跨越”。“超過”“跨越”并非一定是壞事。因為,“超過”“跨越”往往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存在與“矩”之現實要求更高理想道德之“逾”,如《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5](P56-57)可見,“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超越了“仁”的要求達到了“圣”標準;二是有觸犯現實“矩”的規范的不道德之“逾”,即孔子認為的“過猶不及”的“過”。這就是說,“逾矩”包含了好壞的兩極,不具有規范意義。那么,面對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情勢,儒家何以只要求“不逾矩”就可以了,而不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來約束自己和影響別人呢?這與先秦儒家思想的立足于現實來研究自由意志有關。
“不逾矩”是與逾矩相對相成的兩面。而“從心所欲”而逾矩的二重性說明,“逾矩”并不一定是“善”的行為,自由作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意志自由,也非儒家理想中的自由。那么,什么樣的意志自由是儒家理想的自由?自由就意味著限制。因為人在任何條件下都必然有來自現實的自然、社會和精神環境的影響與限制,“從心所欲”的自由只有在“逾矩”(跨過、跨越)與“不逾矩”的相互矛盾中展開和發展,“從心所欲”的自由才是人類現實生活中的自由。這就是說,“從心所欲”的意志自由可以區分為四種類型,三種境界。第一種類型是“從心所欲”而“逾矩”,即跨越或觸犯“仁”的道德規范的為所欲為,這無疑不是真正的自由。第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認為,這是他“七十”才達到的自由。從儒家的思想體系來看,“仁”是儒家的核心范疇,“仁”也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矩”的倫理規范,“從心所欲”而符合(中)“矩”的規范要求,應是自由的第三種類型。第四,“從心所欲”而“逾矩”,超出“仁”的規范而達到“圣”的自由。從四種類型可以看出,第一種類型因為不是真正的自由,當然不算是自由的境界。其他三種類型表述了儒家自由思想的三種境界:由于儒家把欲看作人的不可消滅的本性,欲既然不可滅,人的自由首先要達到的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底線倫理境界。第二,高于“不逾矩”層次的是“中”,即不偏不倚、不過不及地符合仁的“矩”的規范要求,因此,“從心所欲”符合仁的規范,這是自由的中庸境界;而“從心所欲”達到“圣”的高度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三種境界中,“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實際上只是一種底線倫理的現實自由,而“從心所欲”符合“矩”(仁)的規范就是一種中庸的自由,而“從心所欲”超越“矩”(仁)的規范而達到“圣”,才是最高理想的自由。《孟子·盡心》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2](P255)“圣”就是能把善、信、美融為一體,發揚光大,從而成為“百事之師”、萬世師表的意思。在孟子看來,圣人因為是“百事之師”,除開堯舜禹湯等,近百年以來,離他最近的只有孔子。不過,“圣”雖然是最高的終極理想境界,但是,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圣人,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可見,孔子的愿望是符合“仁”的規范的君子。符合是事物相互一致、相符、相中的意思。《禮記·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6](P450)“中”是不偏不倚,不過不及,即符合之意。“中”既是一種標準,也是一種路徑。如《論語·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5](P54)這里的“中”就是中等標準的意思。“發而皆中節”,即喜怒哀樂表露出來而都符合法度禮儀規范,“中”即“符合”,也是一種踐行“禮節”的路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這就是說,先秦儒家自由的根本標準和路徑,是要符合“矩”的法度與仁的禮儀規范要求。
西方現代新自由主義者伯林提出的“兩種自由”概念,被推崇為自由思想研究的經典。在我國,也不乏學者將其捧為“圭臬”。這無疑值得商榷。伯林認為,自由可以區分為“免于……”限制的消極自由與“去做……”的積極自由等兩種自由。伯林將前一種自由說成是現代西方個人不被國家和其他個人干涉的消極自由,而把后一種自由看作是古代羅馬人、希臘人企圖成為主人,積極參與城邦、國家民主政治理想的積極自由。尤其是伯林在未涉及任何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第一手資料情況下,從古代羅馬人、希臘人那里,想像出古代中國人的自由也是一種積極自由。他說:積極自由“這種說法似乎同樣適用于猶太人、中國以及所有其他存在過的古代文明。”[7](P197)事實是,如果按伯林的自由劃分,先秦儒家自由思想的三種境界,不僅蘊含了消極自由,也包含了積極自由思想。先秦儒家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即包含了一種“免于……”“矩”的限制的消極自由思想。因為“不逾矩”,如果只按字面的理解,即是一種不跨越“矩”的限制的自由,如“非禮勿動”等。但是,作為倫理的自由,就不只是一種不跨越“矩”的外在限制的自由,而是將“矩”的規范內化和上升為一種自己命令自己的道德意志自由(這一點留到后面再說)。一當“矩”的規范內化為道德的自由意志,“從心所欲”就不會跨越“矩”的限制,而做到“免于……”“矩”的限制的消極自由。而“從心所欲”符合“仁”的規范,實際是說,在自由的中庸境界,應該“去做……”符合仁的規范的積極自由。可見,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的劃分與我國先秦儒家自由思想的三種境界的思想相比較,我國先秦儒家自由三種境界的思想,不僅蘊含了“兩種自由”概念劃分的思想,而且其對自由境界的理解本身,就明顯超越了停留于“兩種自由”概念理解的思想水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先秦儒家自由境界的理解缺乏伯林那樣的現代西方自由思想地平線上的事實材料,也不可能具有伯林所理解的兩種自由之政治含義。這不足為奇。遺憾的是,伯林關于兩種自由論述的真正地平線也只局限于西方現代的個人自由,他對中國先秦儒家的自由思想幾乎一無所知。他甚至在完全缺乏先秦儒家自由境界思想第一手資料證明的情況下,將中國古代先秦的自由思想簡單等同于古羅馬、希臘人的積極自由,這不能不說是其自由思想研究國際學術視野的“硬傷”。
3.認識到自由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
自由屬于哲學認識論范疇。從近代唯理論的斯賓諾莎到綜合近代唯理論與經驗論的康德,以及黑格爾等都是從哲學認識論來研究自由的[8]。同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自由,也是從認識論的視角來看自由。如恩格斯說:“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9](P456)認識論的自由,雖然在理論上首先涉及的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但是,它為現實的倫理道德、社會自由和對自然改造的自由,提供了世界觀、方法論根據。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自由思想,不能僅僅把其完全看作是倫理性的自由,而忽視其哲學認識論的學理基礎。倫理道德問題的學理基礎首先就是認識論,因為真、善、美始終是辯證統一的,只有真的東西,才是善的。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自由思想就是把自由看作一個認識的漸進發展過程。如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5](P9)孔子雖然是在“七十”才涉及到自由的境界,但是,他把這個境界看作是終其一生學習、探究認識的結果,即把“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的認識看作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漸進過程。孔子認為,學習是認識水平提高的第一階梯。《論語·衛靈公》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5](P152)思,即思考認識之意。離開學習去思考和認識,不可能有什么收獲,只有學習才有益于逐步提高自己的思考和認識水平。《論語·泰伯》曰:“立于禮。”《論語·季氏》曰:“不學禮,無以立”[5](P162)。這就是說,通過青年時代的學習,到了三十多歲時,就能夠按照外在的禮議規范來行動了。所謂“四十不惑”,更是從認識的發展過程來規定的。《論語·子罕》、《論語·憲問》皆認為:“知(智)者不惑”。這就是說,由于學習和掌握了各種知識,認識上的各種問題就有了自己的解決能力,不再糊涂、迷惑而不解,進而認識到自然運行的規律和判明眾說紛紜中的是非曲直、善惡美丑。直至七十才達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現實自由境界。可見,自由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不斷提升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從幾個階段來看,孔子不是隨意劃分的。每個階段自由上升的不同程度反映了他對自由與限制認識的不同水平。“學”是對自由與限制認識的初始階段,這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立于禮,何以不能算是自由的目的呢?當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時,顏回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5](P106)。“克己復禮為仁”就是使自己的言語行為符合周“禮”的規范,以實現合乎“仁”的目標。可見,“立于禮”只是對言語行為的外在規范,并未達到自由意志自己命令自己的內在水平。所以,這種自由無非是一種被限制的消極自由,并未達到“隨心所欲”的高度。因此,認識到為什么不能非禮勿動等,才是“隨心所欲”即從自發自由上升到自覺自由的必要條件。所以,“不惑”“知天命”“耳順”,都說的是認識由外在的“不惑”“知天命”的認識,到內在的“耳順”的遞進過程,而只有這樣,才能最后內化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盡管孔子畢其一生之追求,如此不斷地學習和認識,但他認為,自己最后到了七十,才達到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現實自由的底線倫理要求。也就是說,自由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歷史發展過程,即使我到了七十歲,還不能說我就達到了“從心所欲”符合“矩”的“仁”的規范要求的中庸自由境界與進入了“圣”的終極自由理想境界。
三、先秦儒家道德自由思想的當代啟示
先秦儒家自由思想既為馬克思主義自由思想中國化提供了民族文化土壤,也是社會主義自由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基因。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10]。這就是說,以自由意志道德自由為行為規范的自由是人民依法享有的人權。自由不是源于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按黑格爾《歷史哲學》,自我意識的意志自由最初啟蒙于東方世界,最終成熟于日耳曼世界。黑格爾否定東方文化的日耳曼民族文化自信,顯然是片面的。在中國先秦儒家等思想中,就存在比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等更為豐富的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自由思想優秀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堅持和踐行社會主義自由核心價值觀是堅持文化自信的核心內容。先秦儒家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為我國堅持文化自信,乃至堅持和踐行社會主義自由核心價值觀,提出了幾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1.探索“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文化內涵,明確社會主義自由與限制的辯證關系
如果“從心所欲”指的是自由,那么“不逾矩”表述的是自由的界限。真正的自由是從心所欲與不逾矩的相互統一。儒家把“從心所欲”看作是人生自由實現的一個關鍵詞,說明“從心所欲”并不是壞事,關鍵是要“不逾矩”,即加以限制。限制又有內在的倫理道德自我約束和外在的“矩”的法律強制。這就說明,自由總是與限制、必然相聯系。那種認為,自由就是沒有限制的自由,顯然是極其錯誤的。盧梭認為,自由就意味著限制。他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1](P8)自由與限制是對立統一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將失去前提。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每個經濟人都有了“從心所欲”的自主生產、自主經營、自由交換、自由貿易的自由,但是“從心所欲”不是不要“矩”的限制。這就要求,必須正確處理自由與限制的辯證關系。一是要正確處理“從心所欲”與道德、法律規范的關系。“從心所欲”不是任性,不是為所欲為,“從心所欲”就意味著“矩”的限制。這種限制,主要是道德與法律限制。“從心所欲”的自由如果只涉及個人自己私人生活領域,而不關涉他人,那主要是道德自由的自律。一旦自由涉及他人尤其是公共生活領域,那不僅要受道德自律的約束,更要受到法律他律限制。尤其是公共生活領域,公共生活賴以形成和進行的基本前提是秩序,因為你的自由一旦逾矩,就必然侵犯他人的自由,反之亦然。所以,公共生活領域“矩”的規范限制主要是法律。二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的實現是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既要社會環境等自由的外在可行條件的保障,但更為主要的根據是具備學養修為的可行自由內在主體素質。孔子終其一生都把個人的學養修為看作獲得自由的根據與條件。這是對的。“從心所欲”的關鍵是每個人對意欲的把握和控制,即自律。《禮記·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6](P450)慎獨就是一種自律方式。這就是說,對于道德與法律規范的遵循,最為重要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在有人監督的情況下要遵循道德與法的規范,在沒有人看到的時候也要一樣地遵循。儒家不僅論及自律,甚至還涉及到自律的具體內容,如《論語·季氏》有“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5](P160)三是正確處理“從心所欲”、敢干敢想、大膽創新與“不逾矩“的關系。“從心所欲”就是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大膽創新。但是,敢想、敢干、大膽創新,必須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不能違背良心,不能逾越“矩”的道德規范底線與法律規范的紅線。
2.重視“欲”的人性基礎,探索市場經濟“不逾矩”的自由實現路徑
先秦儒家“從心所欲”的“欲”是出自人性之意欲。由于欲是出自人性之欲,那么,欲的存在既是不可消滅的,也說明它的存在就有存在的合理性,孔子、孟子深刻地論述了“欲”的兩面性。但是,及至封建社會,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等人提出的所謂“明天理,滅人欲”的主張,這就可能導致對先秦儒家“欲”的思想理解片面化。事實上,封建的“滅人欲”,針對的是庶民,而統治階級則無不窮奢極欲。馬克思把欲望、需要看作是人類第一個歷史活動的動機。他說:人們要生存,必須能夠生活。“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2](P79)市場經濟是一種利益經濟。利益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內驅力。市場經濟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欲望、需要和潛能,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市場經濟是一柄雙面劍,市場經濟也帶來了道德危機與信仰危機等問題。問題是,市場經濟為什么會成為一柄雙面劍?由于我國對人性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噤若寒蟬、望而卻步,一直未能從人性的角度來挖掘這一問題,所以在道德研究中曾出現了否定市場經濟的思潮。事實上,市場經濟的兩面性產生的根源不在市場經濟的本身,而在于市場經濟經濟人的人性欲望激發的兩面性,即市場經濟在激發人們的正能量的同時,也激發了一些人企圖不勞而獲、一夜暴富、為非作歹、制假賣假、明搶暗盜、權利尋租、貪污腐敗等負能量。因此,必須重視市場經濟的人性基礎,根據人性“欲”的兩面性,探索“不逾矩”的自由規范的具體內容,才能從根本上探索出一條從道德與法治的角度防止道德危機、信仰危機的正確途徑。
“矩”是衡量欲望的尺度,既有“量”的規定,也有“度”的限制之意。“不逾矩”就是不跨越道德底線“量”與法律“度”的限制。但是,量與度并非絕對對立的兩極,“量”的積累一旦接近度的臨界點,就必然突破量的限制而達到“度”的質變,如“多行不義必自斃”。所以,相對法度而言,“不逾矩”就是指不得觸犯法的度的紅線。所以,“從心所欲不逾矩”關鍵是不得逾越這兩種“矩”的限制。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的實踐路徑,有十分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國在市場經濟的自由實踐中,通常注重的是榜樣模范的典型導向教育,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對于市場經濟每一經濟人的自由行為規范,還遠遠不夠。對于市場經濟的每個經濟人,要懂得什么是應該的,但更要懂得什么是不應該的,即必須懂得什么樣的自由才是不逾道德與法的規范的自由。“不逾矩”是一種底線倫理禁止性的規范約束。這就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須具體制定“矩”的道德與法的規范內容。比如,在道德規范上,根據“八榮八恥”中的“八恥”的內容具體制定出各行各業的禁止性倫理底線規范約束或負面清單;在法律方面,明確設定哪些是不得跨越法律禁止的紅線,哪些行為是法律禁止的行為,從而做到,法有禁止不可“逾”,法無授權不可為。
3.探索“從心所欲不逾矩”與仁的關系,明確自由意志道德自由的三種境界,處理好社會主義自由的現實與理想的關系
孔子為什么把“從心所欲不逾矩”作為自己畢生追求才達到的自由境界,而不是把符合“仁”的中庸自由和“圣”的終極理想自由作為現實要求。相對“從心所欲”的自由而言,遵守底線倫理的規范約束比符合“仁”“圣”的要求更具有現實意義。因為,“從心所欲”的自由是人人具有,且人人所企求的自由。對于每一個人的自由而言,“不逾矩”的現實的底線倫理約束,比符合“矩”的仁的規范與圣的理想目標,更為現實可行,而要求每個人的自由都達到符合“仁”的規范,那是比較難的事情。這就是說,對于自由,遵守“不逾矩”的底線倫理規范是最為切實的現實要求,而符合“仁”的中道“矩”的規范和“圣”的終極理想目標,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先秦儒家的自由意志道德自由思想對于如何踐行社會主義自由核心價值觀,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踐行自由的核心價值觀,首先要突出的應該是一種底線倫理規范約束,同時又必須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的價值追求。這是因為底線倫理約束的立足點是現實,而理想目標價值的指向是未來。理想價值的實現雖然是一種改變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條件都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12](P87)。這就是說,沒有現實的底線倫理要求,自由的理想價值就是一個缺乏前提、條件的可望不可及的“應當”。而沒有自由理想目標價值的追求,現實的底線倫理自由也就因為沒有“應當”的目標追求,而迷失方向和失去牽引力。換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現實的底線倫理自由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自由提供前提與條件,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價值自由的追求是現實的底線倫理自由的方向和航標。除此之外,在介于兩間之間,還應有中道“矩”的道德與法律標準。只有以中道標準為中介,才是打通底線倫理的自由與終極理想的自由之間聯系的橋梁,從而產生一種推進底線倫理自由的上升力和落實終極關懷的向心力,使終極關懷的理想自由不再漂浮于太空而立腳于現實的基礎。在我國,如果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必須實踐“不逾矩”的底線倫理規范,那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一種符合中道“矩”的規范標準的自由,而終極目標是實現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理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