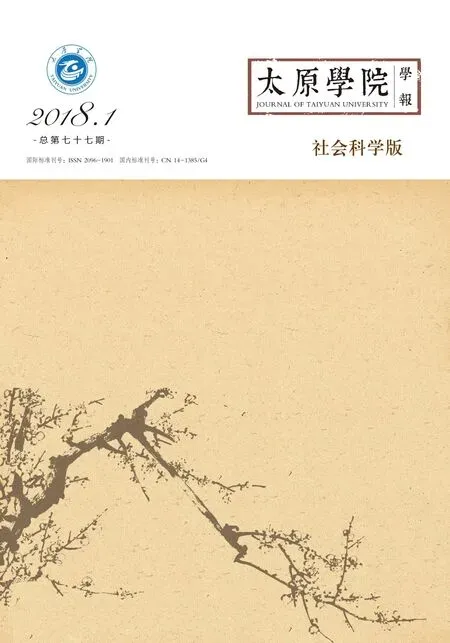韓少功小說中的宗教意識
郭
(西南大學(xué) 文學(xué)院,重慶 400715)
自古以來,文學(xué)和宗教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宗教意識對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來說,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由于宗教探討的是生死和解脫等生命的根本問題,因而宗教意識往往被作家們看成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不少作家終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種創(chuàng)作中的宗教精神。沈從文在創(chuàng)作時(shí)常有這樣的感覺:正如一個宗教信徒或一個思想家臨死前所感到的沉靜嚴(yán)肅[1]。史鐵生則顯得更虔誠:文學(xué)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體現(xiàn)[2]。宗教是一種信仰,而在作家那里,文學(xué)就是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宗教。
于作家而言,宗教意識是一種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更是一種創(chuàng)作的境界,大多數(shù)嚴(yán)肅的作家,其創(chuàng)作都或多或少地帶有一定的宗教意識,這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使命的體現(xiàn),突顯出作家對創(chuàng)作以及生命的敬畏。韓少功曾說:選擇文學(xué)實(shí)際上就是選擇一種精神方向,選擇一種生存的方式和態(tài)度[3]。韓少功對待文學(xué)的態(tài)度,無疑有著宗教般的虔誠,而且,韓少功在2001年功成名就之際,毅然選擇歸隱于湖南汨羅的八景鄉(xiāng),在某種程度上,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更大的宗教皈依。毋庸置疑,韓少功所創(chuàng)作的小說,必定也有著濃厚的宗教意識。
一、佛教意識
作家的經(jīng)歷和思想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著巨大的影響,韓少功在下鄉(xiāng)當(dāng)知青時(shí),便對佛學(xué)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形成了韓少功對佛學(xué)的態(tài)度。韓少功的鄰居,是一個姓朱的老知青,這個貧困潦倒的老知青一天做完苦活后,就在昏暗的燈光下研讀佛經(jīng)和創(chuàng)作詩歌,并和韓少功促膝長談,由此,使得韓少功從佛家思想里,獲得了審度自我的廣闊空間,嘗試著從宗教的高度,來理解世間的苦難和生命,而且,韓少功“向往的是佛的‘大我品格’,……駐足佛學(xué)的動機(jī)仍然是企圖找到一個思想的支撐點(diǎn)……許多人從佛學(xué)中看到了‘空’,韓少功則把目光轉(zhuǎn)向了對眾生的關(guān)注”[4],并把這種思想運(yùn)用到其小說創(chuàng)作中,刻畫出了許多具備佛家意識和精神的形象。很顯然,這便是韓少功的“佛學(xué)”,其中包含著極大生命智慧,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一種特殊的關(guān)于生命的哲學(xué)。
佛教講究輪回和報(bào)應(yīng),種多大因,就收獲多大果,有多大業(yè)即有多大報(bào)。長篇小說《馬橋詞典》是韓少功的代表作,里面有不少地方即體現(xiàn)出了佛教的生命輪回意識:在“醒”一節(jié)里,楚國的屈原幾乎沿著同樣的路線流落到曾經(jīng)被楚國驅(qū)殺的羅國境地,并于此自投汨羅江,卻得到了羅地百姓的諒解和祭奠,歷史在重演,只是已經(jīng)換了角色,同泊異鄉(xiāng)淪落,恩怨復(fù)何言?在“走鬼親”一節(jié)里,金福酒店一個才十三歲叫黑丹子的女子經(jīng)常無理由地救濟(jì)賭錢輸了的勝求,說勝求是她前世的兒子,而且從未去過馬橋的黑丹子竟然識得去馬橋的路,尤其到了前世的家以后竟然熟門熟路,知道各種家什的所在,并一眼就認(rèn)出了半躺在床上的前世的丈夫,被大家認(rèn)為是戴鐵香的轉(zhuǎn)世。在“萵瑋”一節(jié)里,墳?zāi)估锍赂┓镊俭t,意即不愿死者重返陽世延續(xù)厄運(yùn),讓他們臉面朝下,就是讓他們無法重見天日不能轉(zhuǎn)生。尤其“放轉(zhuǎn)生”一節(jié),馬橋鄉(xiāng)親對“放轉(zhuǎn)生”的解釋,更是極其明顯地體現(xiàn)出了佛教的生命輪回意識:殺豬宰牛等血腥事,被叫作“放轉(zhuǎn)生”,畜生也是一條命,前世作孽,現(xiàn)世遭罪,殺了它們是讓它們早點(diǎn)轉(zhuǎn)生,脫離苦難,乃一件大恩大德的善事。
佛教的生命輪回意識,其根本精神在于,讓我們勘破世間虛幻,除卻名利的執(zhí)障,凈化靈魂,超脫生死玄關(guān),破除對于肉體的執(zhí)著及焦慮,獲得解脫,以求得生命的真諦,達(dá)到一種真正自由的境界。在韓少功的小說里,這一佛教意識體現(xiàn)得很是明顯。長篇小說《馬橋詞典》里“貴生”一節(jié)可謂是對于生死超脫最為貼切的注腳。水水的兒子雄獅在三十年后被日本飛機(jī)于一九四二年丟下的炸彈炸死了,馬橋的鄉(xiāng)親安慰水水時(shí),用到了“貴生”這個詞:“貴生”是指男子十八歲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歲以前的生活,相關(guān)的則是“滿生”,指男子三十六歲和女子三十二歲以前的生活,活過了這一段就是活滿了,再往后就是“賤生”了,不值價(jià)了。用馬橋鄉(xiāng)親們的這個觀點(diǎn)來看,死得早一點(diǎn)好,死得早一點(diǎn)才貴。馬橋的鄉(xiāng)親們沒有什么知識,也說不出什么高深的哲學(xué)道理,但他們對于生命和生死的理解,卻完全帶有一種原始的生命意識:對艱難求生的悲戚,對超脫待死的寬容。這是一種樸素的生死觀,雖然帶有一定的無可奈何,但卻有一種超脫生死的博大胸襟在里面,也體現(xiàn)出了佛教的生命意識:雖關(guān)切生死,對待生的痛苦和蒙昧以及死的超升和輪回,時(shí)刻保持警醒,卻又淡漠生死,視生死無差別,能破除肉體的自我執(zhí)著,把死亡看成是滅度和圓寂,看成是生命的極致飛揚(yáng)的一種大歡喜,從而達(dá)到一種無我的精神境界。
佛教強(qiáng)調(diào)責(zé)任和奉獻(xiàn),探求生命的真諦在于超越和解脫,有著大悲精神,這種大悲是悲蕓蕓眾生,有一種度世的責(zé)任,在強(qiáng)調(diào)自度的同時(shí),也要度他,甚至寧可不自度,也得先度他,有一種拯救蒼生的強(qiáng)烈責(zé)任感在里面,此即是佛教的菩薩行觀念。佛家常有一種說法: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種說法其實(shí)體現(xiàn)出了佛家救世度人的宏大愿望以及為了救世度人而承受無量苦難的偉大人格,佛的下地獄,是為癡愚眾生承受苦難,這是佛家的生存法則。佛家的救世精神,是忍受世間無量諸苦,來作饒益眾生的事業(yè),佛家的釋迦牟尼出世以后,曾割肉喂鷹和投身飼虎,佛家的觀世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化身,佛家的堅(jiān)持食素而不殺生等等,都無一不體現(xiàn)出這種救世于苦難的偉大佛教精神。
這類形象,我們單在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中,便能找出不少:萬玉平時(shí)本是一個相公身子,膽小又受不得痛,但他總是一次次不由自主地卷到鄉(xiāng)親們夫妻的打架事件中,為女子打抱不平,于是他陸續(xù)付出了皮肉之苦的代價(jià),甚至付出了頭發(fā)和牙齒,但他卻依然挺身而出,把自己陷于挨打之中;鹽午因成分太大,被學(xué)校開除,三耳朵為了讓鹽午重返學(xué)校,用鐮刀劃自己的手腕,最終幫助鹽午重回學(xué)校,三耳朵很愿意為朋友兩肋插刀,他的兩只手臂上已布滿密密麻麻的刀痕,全是急朋友所難劃傷的,而且三耳朵有一個宏大的抱負(fù),他想在天子嶺上開銅礦,讓馬橋的鄉(xiāng)親們享福,以后都不作田了,不種苞谷棉花紅薯了,為此,三耳朵去賣血攢錢,最終還死在了這個遠(yuǎn)大的抱負(fù)上,三耳朵為籌錢開礦去打劫糧車,被部隊(duì)和民兵追捕,被活活炸死在異鄉(xiāng),死時(shí),身上還帶有一枚銅礦籌建委員會的公章。
佛教認(rèn)為世間乃苦集之場,但苦諦當(dāng)知而不當(dāng)斷,真正具有佛家智慧與勇氣者應(yīng)該知道人生無處不苦,但并不回避苦難,而是要在苦難的磨礪中救世度人:于諸痛苦,為作良醫(yī);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為作光明;于貧窮者,令得伏藏。[5]98-99無疑,韓少功小說中的萬玉以及三耳朵等形象,正是這種佛教精神的化身。
佛教中對生命的敬畏,壓制欲望,看破紅塵世事,蕓蕓眾生,以及報(bào)恩精神和眾生平等思想等等,都在韓少功的小說中有所體現(xiàn)。短篇小說《飛過藍(lán)天》中,那只名叫晶晶的鴿子,一路向南,就算歷經(jīng)一切艱難險(xiǎn)阻,飛過整個藍(lán)天,也要回到他的身邊。中篇小說《爸爸爸》中,雞頭寨“打冤”失敗,被迫“過山”,寨中一些鄉(xiāng)親不愿走,仲裁縫用一種叫雀芋的草熬汁,一戶戶送上門,鄉(xiāng)親們面向東方而坐,在一種極度的莊嚴(yán)神圣中殉道而死,極其悲壯。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中,馬疤子打醮崇尚清心寡欲和從善;九袋爺大年三十出門討飯,教育娃崽要知苦中苦等等,莫不隱含著各種佛教意識,尤其韓少功在“散發(fā)”一節(jié)里的這一段話,甚至堪稱其小說中佛教意識的宣言:生命結(jié)束了,也就是聚合成這個生命的各種元素分解和潰散了……我們凝視萬物紛紜生生不息的野地時(shí),我們觸摸到各種細(xì)微的聲音和各種稀薄的氣味,在黃昏時(shí)略略有些清涼和潮濕的金色氤氳里浮游,在某棵老楓樹下徘徊,我們知道這里寓含著生命,無數(shù)前人的生命——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另外,韓少功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了一些佛教文化意象,比如幽林和月夜,比如晨鐘和暮鼓,以及寺廟和香火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其小說佛教意識的體現(xiàn)。
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到韓少功的歸隱汨羅。佛家講究禪,“禪定是佛家三學(xué)之一……靜坐之外,山居也是一種方式,在喧囂嘈雜的現(xiàn)代都市里蝸居,并且忍受著高強(qiáng)度視聽刺激和生存競爭的作家們,往往于心靈中企盼著一塊可以避世的清凈福地”[5]125-127,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才是韓少功最大,而且體現(xiàn)得最為極致的佛教意識。
二、基督教意識
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我們很難發(fā)現(xiàn)韓少功和基督教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但細(xì)讀其小說,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實(shí)韓少功的小說中有不少地方都隱含著濃厚的基督教意識,在此,我不是想論證韓少功曾受過基督教多大的影響,而是想說明,韓少功并不是某種宗教的信徒,他的宗教意識,也并不是哪一種宗教意識,而是隱含著各種宗教的影響,是一種融合了多種宗教的哲學(xué)思想及觀念,其中有佛教意識,也有基督教意識。
長篇小說《馬橋詞典》里,志煌是個傻子,被鄉(xiāng)親們叫做煌寶,但從基督教那里來看,志煌卻是一個充滿博愛和寬恕精神的基督徒:一次,一個鄉(xiāng)親來到志煌的石場哭泣,說他死了舅舅卻沒錢下葬,求志煌賒他一塊墳碑,志煌卻說,賒什么,你拿去就是,便挑了一塊上好的青花石,鏨了塊碑送給他,還搭上一副繩子幫著抬下嶺;志煌一點(diǎn)兒都不在乎自家的東西,好像那些東西和他沒什么關(guān)系,當(dāng)年他同水水離婚的時(shí)候,水水娘家來搬他家的東西,幾乎搬光了,他也滿不在乎,看著大家搬,還給大家煮茶喝;遇到小偷來偷自家的竹筍,也不生氣,在小偷逃竄掉落溝里時(shí),他順手砍斷一根小樹,把小偷救了上來,并把竹筍送給了小偷。
在拯救和責(zé)任,以及犧牲等方面,基督教同佛教其實(shí)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佛家有‘舍我其誰’的選擇,基督以‘受難’的精神拯救人的罪惡”[6]134,但在佛家和基督教那里,都體現(xiàn)為一種偉大的救世精神,犧牲自己,來拯救世間的一切苦難。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宣揚(yáng)博愛思想,但基督教對現(xiàn)實(shí)也有著強(qiáng)烈的批判精神:“基督教有兩個世界,‘魔鬼的國’和‘上帝的國’,此岸的世界和彼岸的世界,基督教的價(jià)值建立在彼岸的世界,人要為進(jìn)入天國而活著,所以,基督教是批判世俗社會的宗教,是有超越精神的宗教”[6]19-20。
在韓少功的小說中,對現(xiàn)實(shí)的世俗社會的批判幾乎隨處可見,如《飛過藍(lán)天》在罪惡中對貪欲的批判,《馬橋詞典》在語言的反思中對世俗的批判,等等,無不鮮明地體現(xiàn)出基督教的批判意識。從某個角度來說,一個作家能夠保持著對現(xiàn)實(shí)世俗社會的強(qiáng)烈批評精神,正是一個作家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作家需得從大家共見的社會現(xiàn)象中,看見普通大眾不能輕易看見的東西,并對其進(jìn)行批判,這是一個作家的責(zé)任,更是一個作家的使命。當(dāng)然,批判并不是目的,由批判而引起的對于歷史的和現(xiàn)實(shí)的反思,并進(jìn)行行之有效的改善,才是其真正的目的,這正如基督教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在此岸,是為了達(dá)到彼岸,而批評,也正是為了反思和救贖。
于此,批評則有了其相關(guān)的指涉意,那便是基督教的原罪和贖罪意識。基督教是有原罪論的宗教,基督教認(rèn)為人類的祖先亞當(dāng)和夏娃因偷食禁果而觸犯了天條,是有罪的,后世須為其罪惡而贖罪,罪是先在的,無條件的,贖罪是通往蒙恩和獲救的唯一途徑,于是,便有了基督教的罪惡和救贖,并在救贖中完成復(fù)活和新生。
在短篇小說《飛過藍(lán)天》中的“麻雀”以及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中的“鹽早”和“復(fù)查”身上,便鮮明地體現(xiàn)出了基督教的這種罪惡感及贖罪意識:一個叫“麻雀”的下鄉(xiāng)知青,為了能夠順利回城,把自己飼養(yǎng)的心愛的鴿子“晶晶”作為賄賂品送給了招工師傅,使得“晶晶”孤獨(dú)地來到了遙遠(yuǎn)的北方,但“晶晶”卻非常念舊,歷盡千難萬險(xiǎn)憑著強(qiáng)大的意志力飛上了“回家”的路,而于此同時(shí),“麻雀”卻并沒有因此而成功回城,依舊滯留鄉(xiāng)下,于是他消極怠工,制造一切可以制造的事端,悲劇由此而來,有一天,“麻雀”在外出打獵的時(shí)候,無意中用氣槍打死了從遙遠(yuǎn)的北方飛回來找他的“晶晶”,當(dāng)他看見死于自己槍口下早已因飛越藍(lán)天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晶晶”的尸體時(shí),便開始了他的贖罪和自我救贖。鹽早因?yàn)楦赣H的關(guān)系,被認(rèn)定為漢奸,加上家里還有個“蠱婆”,以致有了一種深深的罪惡感,于是很少說話,被迫成了個啞巴,大家叫他干什么,他就默默地干什么,總是干著寨子里最臟最累的活兒,就算自己中了毒,腦袋腫得像個南瓜,也只是用塊布包著而已,從不抱怨。在基督教看來,鹽早承受苦難,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其實(shí)是他身上的“原罪”意識在作祟,他默默地做事,更多的是一種贖罪意識。復(fù)查因咒了羅伯一句“你這個翻腳板的”,第二天,羅伯就被瘋狗咬了,最終走上了歸途,復(fù)查違反了嘴煞,鄉(xiāng)親們和復(fù)查自己都認(rèn)為羅伯的死和這句咒語有關(guān),復(fù)查便很自責(zé),從此一蹶不振,使得復(fù)查此后幾十年都生活在一種永遠(yuǎn)無法消除的罪惡感中,甚至連贖罪的機(jī)會都沒有。
基督教有著豐富的內(nèi)涵,除了以上論及的幾個方面以外,在韓少功的小說中,依然隱藏著諸如布道和尋求等其他基督教意識,在此就不一一論及了。總之,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說,韓少功的小說,都隱含著濃厚的基督教意識。
三、巫楚文化意識
韓少功曾明確地表達(dá)過對于巫楚文化的態(tài)度:絢麗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那么浩蕩深廣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時(shí)候在什么地方中斷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鄉(xiāng)土是城市的過去,是民族歷史的博物館。鄉(xiāng)土中所凝結(jié)的傳統(tǒng)文化,更多地屬于不規(guī)范之列……其中大部分鮮見于經(jīng)典,不入正宗,更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潛伏在地殼之下,承托著地殼——我們的規(guī)范文化。在一定的時(shí)候,規(guī)范的東西總是絕處逢生,依靠對不規(guī)范的東西進(jìn)行批判地吸收,來獲得營養(yǎng),獲得更新再生的契機(jī)。不是地殼而是地下的巖漿,更值得作家們注意。[7]76-84于是,韓少功開始去尋找,開始去重新審視腳下的國土,回顧民族的昨天,并在湘西的崇山峻嶺里找到了還活著的楚文化。
可見,韓少功的創(chuàng)作對于巫楚文化是極其重視的,巫楚文化意識在韓少功的小說中,理應(yīng)占有極大的比重。
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融合進(jìn)巫楚文化,前可追溯到戰(zhàn)國時(shí)期的屈原,近可延續(xù)到湘西的沈從文,屈原被流放到楚地時(shí)所作的《離騷》《九歌》《招魂》等作品,大多取材于楚國民間的祭祀歌曲和流行于民間的巫歌,很多篇章更是模仿民間巫師招魂的口吻而作,可以說,屈原的作品中是帶有最原質(zhì)的巫楚文化特色的,而沈從文的作品,不管是散文還是小說,都帶有明顯的巫楚文化特色。
韓少功的小說創(chuàng)作,受屈原和沈從文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韓少功曾經(jīng)在汨羅江邊插隊(duì)落戶,住地離屈子祠僅二十來公里,韓少功曾去細(xì)察當(dāng)?shù)仫L(fēng)俗,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厝杂性S多方言能同楚辭掛上鉤,可見韓少功對屈原的《楚辭》頗有研究,而韓少功和沈從文同為湖南作家,所關(guān)注的都是湘西這塊特殊的地域,不論是其思維方式,還是作品中對于巫楚文化的態(tài)度及運(yùn)用,都有著極大的相似程度。何謂巫楚文化?巫楚文化又有著什么樣的特點(diǎn)?
張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說:巫楚文化是以江漢區(qū)域?yàn)橹行模谠甲诮毯臀仔g(shù)以及神話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一支由楚人創(chuàng)造的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化,其重要特征是崇神信巫和畏鬼[8]32。我國的巫文化,源遠(yuǎn)流長,古時(shí)的巫,說的是那些能“以舞降神”的女子,其最初意為通過歌舞來祈求神靈的保佑,從古至今的幾千余年間,上至宮廷,下至草野,從驅(qū)災(zāi)辟邪,到祭祀治病,巫術(shù)幾乎無所不能,只是后來以儒家思想為正宗,輔以佛教道教等思想,巫文化才流落到邊緣,開始在民間傳襲,變成了一種原始的遺風(fēng)。但即便如此,巫文化在某些偏僻之地,仍然居于主要地位,尤其是在韓少功所生活的湘楚一帶,更是如此,據(jù)《荊楚文化志》記載,“無論何族何寨,莫不信鬼神,重祭祀”,“楚俗尚巫”,等等。
巫術(shù)和宗教是分不開的,很多宗教活動及儀式都保留有巫術(shù)的影子,尤其是巫術(shù)中祭祀的影子,而且,巫楚文化其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區(qū)域文化”[9]101,在某些落后地方實(shí)際上是起著宗教的作用,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的宗教。
作為宗教形態(tài)的巫楚文化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致特征是:篤信鬼神的巫鬼氣息,自然和圖騰崇拜的尊天敬神思想,以及迷信傳說和時(shí)空混沌觀念,等等。
巫鬼氣息是巫楚文化中最為顯明的特征,通常經(jīng)由鬼神信仰以及相關(guān)的巫術(shù)和祭祀活動表現(xiàn)出來,伴隨著極其濃厚的神秘色彩。這個特征,在韓少功的小說中比比皆是,可以說基本貫穿了韓少功大部分的小說創(chuàng)作。
短篇小說《歸去來》中死去的姐姐變鳥,天天在叫,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短篇小說《鼻血》中的柴房鬧鬼;短篇小說《會夢一笑》中紅頭蜥蜴能受命復(fù)仇;中篇小說《女女女》中,不能受孕的婦女常常赤身裸體去山嶺上睡臥著承接南風(fēng),說是南風(fēng)可使婦女們受孕;修路遷墳時(shí),拖開祖墳,里面盡是蛇,尺把長一條,足足有半籮筐;地震前,成千上萬的老鼠竄出來,形成了鋪天蓋地的鼠河,等等。
中篇小說《爸爸爸》和長篇小說《馬橋詞典》則更是可以看著被巫楚文化中的巫鬼氣息重重包圍的小說,幾乎整篇都透露出一種陰邪無比的神秘氣息。中篇小說《爸爸爸》中,鄉(xiāng)鄰傳說丙崽的傻是因?yàn)楸棠锒嗄昵芭懒艘恢恢┲刖珜?dǎo)致;取下女子的一根頭發(fā),系在門前的一片樹葉上,當(dāng)微風(fēng)輕拂時(shí),口念咒語七十二遍就能把女子迷住的花咒;殺男子祭谷神;打冤前用高高的鍋臺架一口鐵鍋,把冤家的一具尸體切成一塊塊,和豬肉混成一鍋煮,然后用大竹扦戳肉吃的“吃槍頭肉”儀式。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中,殘忍至極的殺長子風(fēng)俗,把第一胎視為來歷不明的野種,用盡各種辦法處死,比如塞進(jìn)尿桶等等;兩扇新打的磨子同茂公家門口的一個石臼大戰(zhàn),發(fā)出咣當(dāng)咣當(dāng)?shù)木揄懀恢辛嗣陨街洌銜月罚辛巳』曛洌瑒t會神志不清,最終變成行尸走肉;長于墳?zāi)估锼勒呖谏嗵幍摹叭n瑋”,是很好的補(bǔ)藥,可以理氣補(bǔ)血和滋陰壯陽;走著走著突然不見了的“飄魂”;房英把弟弟魁元的棺木高高地豎起來,用幾塊石頭從旁撐住,為弟弟“企尸”鳴冤……
自然崇拜和圖騰崇拜等巫楚文化特征在韓少功的小說里也有體現(xiàn)。中篇小說《爸爸爸》中雞頭寨的鄉(xiāng)親們對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無比崇拜,經(jīng)常進(jìn)行著最為原始的祭祀行為,把祠堂一個向上彎彎翹起的尖尖的檐角看成一只傷痕累累的老鳳,指引著雞頭寨鄉(xiāng)親們的“打冤”以及失敗后悲壯的“過山”,這里,“鳳”即是一種圖騰,具有很明顯的符號學(xué)特征,具有其豐富的象征意義,而雞頭寨鄉(xiāng)親聽命于“鳳”的指引,則表現(xiàn)出巫楚文化中強(qiáng)烈的圖騰崇拜特征。長篇小說《馬橋詞典》的“楓鬼”詞條中,羅伯家后坡上那兩棵巨大的楓樹,似乎也是馬橋的象征,多年前一場山火,坡上的樹全都死了,唯有這兩棵楓樹安然無恙,甚至不損一片樹葉,被稱為“楓鬼”,具有靈魂,一遇大風(fēng)雨則暗長數(shù)尺,收縮自如,馬鳴畫過楓樹后,右臂紅腫劇痛三日,砍掉楓樹做成排椅后,坐過的鄉(xiāng)親都患上瘙癢癥,服用任何藥物均不見效,是為“楓鬼”報(bào)復(fù)砍伐的兇手;在“馬疤子”詞條中,有一片竹子,大旱那年,田里顆粒無收,而這一大片竹子卻開出白色的花,并結(jié)出籽,煮成飯后清香撲鼻,附近的鄉(xiāng)親以此度過了饑荒,而竹子開花以后則全部死掉了。
當(dāng)然,韓少功小說中的巫楚文化意識,肯定遠(yuǎn)遠(yuǎn)不止巫鬼氣息和自然圖騰崇拜,必定包含著其他內(nèi)容,比如巫楚文化中的時(shí)空混沌以及豐富的想象和浪漫的激越等等,但不管從哪個方面來說,都體現(xiàn)出了巫楚文化的固有特征,帶有一種極其明顯的原始宗教的意味。
除去佛教和基督教以及巫楚文化意識以外,韓少功小說中同時(shí)也隱含著其他的宗教意識,如道教的“逍遙”思想,以及伊斯蘭教的“兩世并重”[10]100意識等等,這里就不一一討論了。
四、宗教意識在韓少功小說中的作用
宗教意識對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宗教是精神,是信仰,關(guān)注的是生命和靈魂等深層次的東西,這和文學(xué)一樣,甚至可以說,宗教和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是最為親密的,博大的宗教精神往往會成為文學(xué)的至高境界。夏志清曾說: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shí)由于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rèn)識。[11]322夏志清的說法雖有失偏頗,中國現(xiàn)代許多作家作品其實(shí)都是有著相當(dāng)濃厚的宗教意識的,但我們?nèi)阅軓钠湔f法中見出宗教對于文學(xué)的作用。
一個優(yōu)秀的小說,理應(yīng)表達(dá)出對于天地和生命的敬畏,并在剝離其文字以后,呈現(xiàn)和傳達(dá)出一種源于小說,而又高于小說的東西——關(guān)于生命的思想和觀念,小說的敘述對象可以是“小”的,但其中所蘊(yùn)含的思想和內(nèi)涵,一定得“大”,須得暗示和影射出一種完全超越作家自我的可以遍及一切的生命內(nèi)涵,而這種生命內(nèi)涵,就是小說的宗教意識,而具有宗教意識的小說,才是有深度的小說,這樣的小說,溝通天地萬物,連接塵世和上蒼,有著極其深刻的生命體驗(yàn),能夠揭示出生命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
那么,宗教意識對于文學(xué)作品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我以為,宗教意識在增強(qiáng)文學(xué)作品的神秘傾向等淺層次方面,以及提升文學(xué)作品的主題,使文學(xué)作品具有深邃的思想等深層次方面,均有著巨大的作用。而在作家韓少功身上,這幾點(diǎn)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
韓少功的小說有著非常強(qiáng)烈的神秘傾向,這幾乎已達(dá)成一個共識,而且韓少功小說中的這種神秘傾向,主要就來自于其小說中的宗教意識,尤其是巫楚文化中的巫鬼氣息,這在上文已有所論及,在此就不再贅述了。我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韓少功小說中的這種神秘傾向,其實(shí)質(zhì)是想經(jīng)由神秘而抵達(dá)莊嚴(yán),一種宗教的莊嚴(yán),從而讓其小說上升到一種思想的高度。
沒有思想的文學(xué)是貧血的。一個文學(xué)作品中有了思想,尤其是有了深度的思想,則更能顯示出其價(jià)值的含量,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們很難想象,假如抽掉了魯迅作品中的思想,將會是怎樣一種狀況?如果說一個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是外衣,內(nèi)容是身體的話,那么思想則是其靈魂,少了思想,就像少了靈魂,是活不長久的。
什么樣的東西才是神秘的?未知的,先驗(yàn)的東西,就是神秘的,就像自然界中的鬼神。中國的作家是很喜歡寫鬼神的,這可以在無數(shù)個作家身上得到證實(shí),作家們正是想通過鬼神的刻畫,來使作品達(dá)到一種“通神”的狀態(tài)。相對于困苦的世間來說,神靈是高高在上的,是一種超然的存在,他們可以以俯視的眼光和超然的態(tài)度,來看待世間的一切,從而更客觀,也更深刻。另外,作家們生活在現(xiàn)時(shí)現(xiàn)世,由于各種各樣復(fù)雜的原因,他們有很多話,是想說,而又不能說的,此時(shí),就必須借助于神靈,很多東西一旦披上了“神靈”的外衣,就變得方便多了,可以真實(shí)地表達(dá)自己的看法,而不用擔(dān)心一些無法左右的因素,可以“暢所欲言”了,因而,鬼神在作家那里,變得倍受青睞。
什么東西才是“通神”的呢?顯然是那些異質(zhì)的東西,比如精神病患者,智障者,有特異功能的巫師和蠱婆,以及一些奇異的事件,等等,在作家的眼中,這是溝通世間和神界的橋梁,是能夠代言其思想的特殊存在。因此,在無數(shù)的作家作品中,便不斷地出現(xiàn)此類形象和事件,甚至都成了一種值得探討的文學(xué)現(xiàn)象。
韓少功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小說中就多次出現(xiàn)這類靈異的形象和事件,顯然,韓少功小說中的這些靈異形象和事件,肯定不只是為了增強(qiáng)小說的神秘感那么簡單,作家是想通過他們來完成“通神”的效果,用以提升作品的主題,完成作品從世俗到神以及宗教的轉(zhuǎn)變,最終到達(dá)一種思想的深度。
韓少功是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蘊(yùn)藏著思想的光芒,從小說到散文,從《馬橋詞典》到《暗示》,思想因素越來越強(qiáng),而韓少功也在這種極強(qiáng)的思想中,走向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深處。韓少功在接受王堯采訪時(shí)曾說:“我曾經(jīng)以為,感覺是接近文學(xué)的,思想是接近理論的。一個作家應(yīng)該以感覺為本,防止自己越位并盡可能遠(yuǎn)離思想。但是……我們很多作家在唾棄思想以后,是感覺更豐富了,還是感覺更貧乏了?是感覺更鮮活了,還是感覺更麻木了?”[12]237而韓少功小說中思想深度的形成,自然和其小說中的宗教意識有著莫大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可以說,正是韓少功小說中的宗教意識,成就了其小說的思想深度,甚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宗教意識就是其思想本身。
總而言之,韓少功的小說中,既有佛教意識,也有基督教意識,以及巫楚文化等其他的宗教意識,這些宗教意識融合在一起,對韓少功的小說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僅豐富了其小說內(nèi)容,更提升了其小說主題,使其小說完成了從世俗到宗教的蛻變和超越,形成了一種有思想深度的小說。
參考文獻(xiàn):
[1]沈從文.談文學(xué)的生命投資[G]//沈從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459.
[2]史鐵生.病隙碎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197.
[3]韓少功.我為什么還要寫作[G]//韓少功研究資料.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51.
[4]何言宏,楊霞.堅(jiān)持與抵抗:韓少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3.
[5]譚桂林.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佛學(xué)[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6]王本朝.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基督教文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7]韓少功.文學(xué)的“根”[M].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
[8]張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龔敏律.韓少功的尋根小說與巫楚文化[J].中國文學(xué)研究,2005(2):101.
[10]馬麗蓉.20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與伊斯蘭文學(xué)[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1]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5.
[12]韓少功,王堯.韓少功王堯?qū)υ掍沎M].蘇州:蘇州大學(xué)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