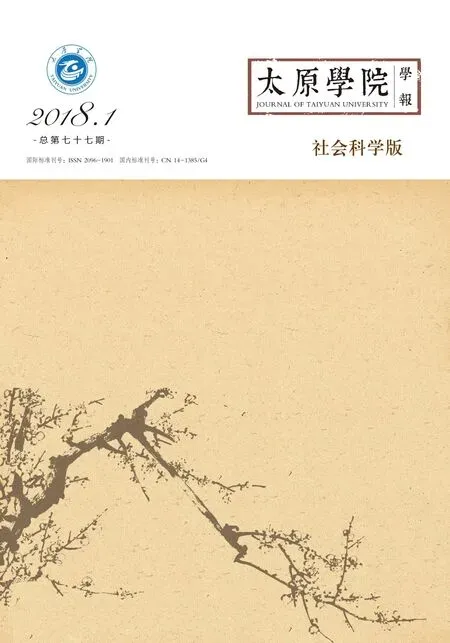孫奕“老而詩工”的文學觀念
張
(太原師范學院 文學院,山西 榆次 030600)
陳寅恪先生曾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2鄧廣銘先生在《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文章中也提到“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2]宋代文化達到高度的繁榮,筆記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蘊含的內容也較為豐富,社會生活、風俗人情、文學思想等等皆有涉及。“老而詩工”的文學觀念即是孫奕在其《履齋示兒編》卷十“老而詩工”中提出來的:
客有曰:“詩人之工于詩,初不必以少壯老成較優劣。”余曰:“殆不然也。醉翁在夷陵后詩,涪翁到黔南后詩,比興益明,用事益精,短章雅而偉,大篇豪而古,如少陵到夔州后詩,昌黎在潮陽后詩,愈見光焰也。不然,少游何以謂《元和圣德詩》為韓文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一、“老而詩工”的文學觀念
孫奕生活在南宋孝宗、光宗、寧宗時期,作品主要有學術筆記《履齋示兒編》(又稱《示兒編》),共計23卷,包括總說、經說、文說、詩說、正誤、雜記、字說7大部分,本書富含文學思想(主要集中在經說、文說、詩說這3部分)。孫奕于書中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在其他文學思想方面,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創作論側重“作文法”和煉字;語言主要涉及俗語和用字;發展論重視句法和文意的繼承。“老而詩工”是孫奕《履齋示兒編》中唯一直接提出的文學觀念,立論較為新穎和客觀。
《說文解字》關于“老”和“工”的解釋分別為:“老,考也。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須變白也。”“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與巫同意。”作為修飾語的“工”,多含巧妙、精巧、嚴整的意蘊。就引文來看,孫奕所提及的“老”并不是古人所說的“七十曰老”,主要是指詩人詩歌創作的中晚期或晚期,與創作的早期相對(多指詩人30歲之前)。而“工”作為修飾語主要是指詩歌的寫作手法成熟,風格明確且影響力顯著。詩人在早期的不斷探索、借鑒學習前人的基礎上,中晚期詩歌寫作技法逐漸成熟、詩歌整體風格得以確立,從而使得詩歌更為內斂、自然,更易為世人所接受。所以筆者將孫奕“老而詩工”的文學觀念解釋為:詩人在創作的中晚期,詩歌較早期技法更為成熟、風格更為明確、影響力更為顯著。孫奕在引文中列舉了歐陽修、黃庭堅、杜甫、韓愈四位大家作為例證。
歐陽修(1007-1072)一生的活動大體可以分為5個階段,與其詩歌創作階段大致相應。筆者將其分為兩個時期來分析,被貶夷陵之前(1023-1036)與被貶夷陵之后(1036-1072)。夷陵之前,因宋初文壇受西昆體的影響,其詩歌風格較為接近西昆體,期間也開始了新的嘗試和探索,學習唐人的詩歌,尤其是韋應物和韓愈,注重從詩歌的記敘性出發,同時盡量規避西昆體的艷麗雕琢和晚唐體的瑣碎。這一時期的探索主要體現在記游寫景的作品中,如《秋郊曉行》《被牒行縣因書所見呈僚友》等作品。從中可以看出其對清淡風格的追求。這一時期的歐陽修尚處于學習和探索的階段,作品的影響力有限,詩歌風格也尚未成熟。30歲時被貶成為夷陵縣令,政治生活發生改變,其文學創作也隨之變化。所謂“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隨園詩話》)歐陽修夷陵之后的詩歌創作皆源于在夷陵時期的生活。貶謫夷陵期間他寄情于山水,詩歌創作大體可分為贈答、詠物、記游三種。元代方回《瀛奎律髓》卷 4選錄了歐陽修在夷陵所寫的《夷陵歲暮書事呈元珍表臣》《寄梅圣俞》《戲答元珍》三首詩,評曰:“讀歐公詩,當以三法觀:五言律初學晚唐,與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為散誕;七言律力變‘昆體’,不肯一毫涉組織,自成一家,高于劉、白多矣;如五、七言古體則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類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在寄情于山水、自然的同時,在詩歌中融入理性思考,逐漸趨向“宋詩主理”,《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黃溪夜泊》等詩足見其心態的平靜與坦然。同時在歌行、律詩中融入了古文章法,并最終使得“以古文章為詩”走向成熟。1045年被貶滁州之后,確立了其平易疏暢的詩風。《題滁州醉翁亭》《滄浪亭》皆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作品。晚年退居潁州時,生活歸于平淡,將平易疏暢的詩風與自然情趣相結合。歐陽修被貶夷陵之后較之夷陵之前的詩歌,印證了“老而詩工”文學觀念。
莫礪鋒先生在其《論黃庭堅詩歌創作的三個階段》文章中,將黃庭堅的詩歌創作分為三個階段:22歲至41歲(1066-1085)是早期創作階段,莫礪鋒先生認為其獨特的黃庭堅體就形成于這一時期,正如陳巖肖所說“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3]182早期的詩歌,在用典、對仗、形象、語言、聲調等方面刻意求奇,但稍欠穩妥。41至49歲(1085-1093)這8年是其詩歌創作的第二階段,黃庭堅所創作的400余首詩歌中,酬唱類的達到一半以上,在早期求奇的基礎上,繼續追求詩藝進步,重視詩歌的押韻,同時多以成語典故入詩,符合宋代詩歌“以學問入詩”的特點。紀昀評黃庭堅名作《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云: “點化甚妙,筆有化工,可為詠物用事之法。”可見這一時期的黃庭堅仍然在求奇求新的道路上探索。51歲至去世(1095-1105),是其詩歌創作的第三階段,黃庭堅52歲被貶至黔南,學界對于黃庭堅貶謫巴蜀時期詩詞的評價,歷來甚高。《苔溪漁隱叢話》有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大卜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己。”“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埃,故能吐出世間語。”貶謫期間的詩詞,對仗工整、形式多樣;用典貼切,山谷詩詞講究“無一字無來處”,大量使用典故,是其詩詞特色,在巴蜀時期自然也不例外;修辭豐富,意象生動,比喻、擬人、指代、摹狀、曲指、夸飾、暗合、雙關、倒反,皆有應用;諧謔調侃也是其貶謫巴蜀時期作品的重要特點。同時,黃庭堅晚期詩歌的最大特點是趨向平淡質樸,例如《書摩崖碑后》《跋子瞻和陶詩》等詩皆是回歸自然的代表,真正做到了其所追求的“不煩繩削而自合”。詩歌較早期的刻意求奇更為穩妥、內斂。
動蕩的時代,坎坷的遭遇成就了一位心系國家安危和民生疾苦的詩人杜甫。困守長安時期(746-755),杜甫十載長安,歷盡辛酸,留下了《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名篇,陷賊與為官時期(756-759)寫下了《春望》《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別”等篇。杜甫55歲漂泊至夔州,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是他一生的總結和凝縮。此間,杜甫沒有忘記創作,他寫了四百多首詩歌。創作的詩歌較之前而言,藝術水準達到了新的高度。這一階段,杜甫游覽古建筑,留下了《白帝》《八陣圖》等名篇;思考民生問題,寫下了《負薪行》《詠懷古跡五首》等名篇;總結人生經歷以及歷史教訓時,寫下了《秋興八首》《八哀詩》等篇。而關于軍政大事則有《諸將五首》等篇。題材豐富,表現手法多樣,從而使得杜甫的夔州詩歌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
韓愈的詩歌創作主要分為四個階段,18歲至29歲(785-796)期間,韓愈多為模仿漢魏詩歌。例如胡應麟評《青青水中蒲》三首曰:“退之《清清水中蒲》三首,頗有不安六朝意。然如張王樂府,似是而非。取兩漢五言短古熟讀自見。”[4]2330歲至36歲(797-803)期間,韓愈因為沉淪下僚,詩歌風格逐漸由古樸轉向奇崛。期間的酬唱類如《遠游聯句》《答孟郊》等;抒懷類如《山石》《利劍》等;紀事類如《苦寒》《落齒》等都敢于突破傳統,詩歌更顯自由和靈活。朱彝尊評價《利劍》詩曾云“語調俱奇險,亦近風謠。”[4]18437歲至47歲(804-814)期間,韓愈崇尚雄奇怪異之美,韓愈奇崛瑰麗的詩風逐漸成熟。羅宗強先生所說的:“韓愈的詩,常常表現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表現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的震蕩和變化,表現一種怒張的力。大自然在他眼里,全都是蒙上了一層奇光異彩,彌漫一層神秘莫測的氛圍。”[5]恰當地概括了此時期韓愈詩歌的特色。《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是這一時期奇崛詩風的典型代表作,瞿佑云: “昌黎《陸渾山火》詩,造語新奇,初讀殆不可曉。及觀韓氏《全解》,謂此始言火勢之盛,次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克相濟之說也。”[4]698但過于追求險怪、奇特,卻忽略了詩歌應有的“妥帖”和“平淡”。48歲至57歲(815-824)是其詩歌創作的最后階段,52歲的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此期韓愈詩文創作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揚棄險怪,趨向平易。清劉熙載《藝概》卷一《文概》云:“昌黎文兩種,皆于《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余’,‘心醇而氣和,是也。”[6]韓愈貶潮時間雖不長,創作數量雖不多,但他此期所表現出的棄險趨易的創作傾向,卻對他晚年的詩文創作影響較大。晚年的作品中酬唱類、記游詠物類、抒懷類等都體現了平淡與自然。例如朱彝尊評《過始興江口感懷》一詩云:“道得真切,煉得簡妙。”[4]1123評《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一詩云:“景絕妙,寫得亦絕妙。”[4]1258詩風較之前更為內斂。
此外,屈原38歲作《離騷》,50歲以后寫了《九章》的大部分作品;曹操51歲作《苦寒行》,52歲作《步出夏門行》;曹植30歲作《野田黃雀行》,32歲作《贈白馬王彪》;陶淵明42歲作《歸園田居》,51歲作《雜詩十二首》,53歲作《飲酒》二十首;謝靈運39歲作《登池上樓》;王維51歲居輞川時,寫了大量的山水詩,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其中就包括我們熟悉的《山居秋暝》《山中》等;孟浩然32歲以后開始大量創作詩歌;白居易詩歌影響力較大的《長恨歌》《琵琶行》,分別作于35歲和45歲;柳宗元30歲后人生兩次的重大貶謫,注定此生和長安無緣,永州、柳州兩地是他長期生活的地方,也是《江雪》《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等作品誕生的地方;高適34歲作《燕歌行》;劉禹錫54歲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李商隱42歲作《夜雨寄北》,46歲作《錦瑟》;王安石38歲作《明妃曲》,54歲寫下《泊船瓜洲》;蘇軾36歲作《飲湖上初晴后雨》,43歲被貶黃州之后,詩風也逐漸趨于平淡。47歲作《題西林壁》,48歲作《惠崇春江晚景》,57歲被貶惠州,58歲作《荔枝嘆》,貶惠州之后,詩文多了些瀟灑曠達。趙翼批沈德潛《宋金元三家詩選·蘇東坡詩選》下卷所說的“遷謫中無侘傺不平之氣,汗漫九垓,是何等胸次,擺落一切”;[7]168楊萬里52歲作《插秧歌》,62歲作《初入淮河》;陸游42歲作《游山西村》,47歲作《劍門道中遇微雨》,52歲作《關山月》,61歲作《書憤》,62歲作《臨安春雨初霽》,68歲作《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85歲作《示兒》。以上所舉皆是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頗具影響力的詩人及其較為出名的作品,能夠體現各自詩歌的風格特點,且皆是詩人經過不斷的探索和學習之后,成就了這些名作。這些詩歌的寫作年份大多處于詩人創作的中晚期或晚期。
筆者所列舉的這些詩人及其作品也印證了孫奕“老而詩工”的文學觀念的客觀真實性。同時,引文中用來例證的這幾位詩人,醉翁之于夷陵,涪翁之于黔南少陵之于夔州,昌黎之于潮陽,皆處于詩人政治上不得志時期,和歐陽修提出的“詩窮而后工”的“窮”有異曲同工之妙。“老而后工”一定程度承接了“窮而后工”的觀念,但“老”相對“窮”的內涵更為豐富。
二、“詩窮而后工”及其與“老而詩工”之比較
在中國文學批評中一直存在“詩能窮人”“詩能達人”的爭論,也存在“窮而后工”“達而后工”的爭論。以“窮”“達”論詩,開始于中唐,皆有存在的合理性與真實性,但大多數人還是樂于接受“窮而后工”“詩能窮人”的說法,誠然,這是歷史的事實,同時也受司馬遷、韓愈、白居易、歐陽修、蘇軾等大家的詩歌影響。唐代白居易于《李白墓》詩中提出“詩人薄命”(“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8]363到宋代蘇軾于《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韻答之》詩中提出“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9]159從此,詩人和“窮”開始結緣。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的發展進程中,“發憤著書”“不平則鳴”“窮而后工”的發展存在一定的承接關系。相較“發憤著書”而言,韓愈“不平則鳴”超越了個體的悲憤,而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則超越了韓愈簡單的比喻和舉例。《孟子·盡心上》指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里的“窮”特指不得志,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
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于此,歐陽修提出了“詩窮而后工”的觀念,在《梅圣俞墓志銘序》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圣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許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忿,可謂君子者也。……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10]歐陽修所說的“窮”也同樣指不得志,然而大多數的不得志,都伴隨著物質層面的窮困潦倒,他們其實是不矛盾的。在政治上不得志,所以“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自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于此,“詩窮而后工”與“詩可以怨”自然、直接地聯系在一起。
孟子指出“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11]353-354;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敬通雅好辭說, 而坎坷盛世, 顯志自序, 亦蚌病成珠矣”;[12]419鐘嶸《詩品序》“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塞客衣單 ,孀閨淚盡。”韓愈“不平則鳴”、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皆是“詩可以怨”的延續,大多抒發詩人仕途不得志、歷經坎坷時的情懷。而這些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活,正是詩人創作的“財富”。
仔細斟酌“老而詩工”和“詩窮而后工”這兩種文學觀念,“詩工”是一種實踐的結果,而“窮”和“老”更多是一種性質上的差異。童慶炳先生認為: 詩人之窮,在一定意義上,正是詩人之富 ,正是在窮中, 詩人蓄積了最為深刻、飽滿、獨特的情感, 正是這種帶著眼淚的情感, 以一種強大的力量把詩人推上了創作之路。[13]30而“老”亦是“詩人之富”,孫奕所謂的“老”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創作時期劃分亦或是年齡的老少,詩人經歷豐富,見識淵博,心態回歸平和,自然內容詳實,筆法老練,進而達到“詩工”的效果。
“老而詩工”的影響因素中包含詩人政治生活的不得志,但“老”更多是一種客觀的狀態,而“窮”則可能存在詩人人生的各個階段,歷時或短或長。“老”和“窮”是詩人不同人生階段的狀態,而這兩種狀態在不同的詩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現。
孫奕自然也知曉關于詩人“窮”“達”的相關爭論,其實,所謂爭論,只是論者所著重的角度不同、例證不同,他們都是客觀存在的文學觀念。孫奕沒有溺于這些爭論,而是客觀地提出了“老而詩工”文學觀念。“老而詩工”雖只是孫奕文學思想的一小部分,但其獨創性值得我們細細品味,為我們思考“詩能窮人”“詩能達人”,“窮而后工”“達而后工”這些爭論,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參考文獻:
[1]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M].成都:巴蜀書社,1997:2.
[2]鄧廣銘.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J].社會科學戰線,1986(2):138.
[3]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M].北京: 中華書局,2003.
[6]吳文治.韓愈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7]曾棗莊,舒大剛.三蘇全書[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8]白居易.白居易集:卷17[M].北京:中華書局,1979.
[9]蘇軾.蘇軾詩集:卷4[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0]曾棗莊,劉琳.全宋文:18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93-94.
[11]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13[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3]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M].北京: 中華書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