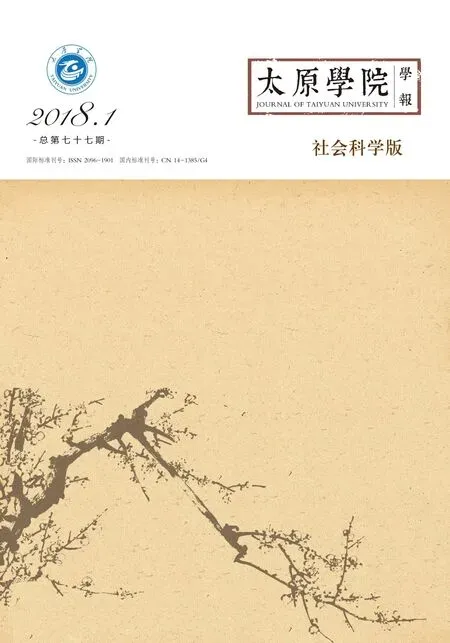論錢穆的文化類型學
呂
(青島市社會科學院 文化研究所,山東 青島 266071)
錢穆門人陳啟云在《錢穆師與思想文化史學》一文中說:“思想、文化、歷史三方面,包括了錢先生生平著作的大部分。可以說‘史學’是先生學問的基礎,‘文化’是其宏觀視野,‘思想’是其核心關注。”[1]51。這段話對錢穆一生的治學,進行了準確的概括。錢穆一生的治學,可以分為三大部類,文化研究是三大部類之一,且終生不輟。自早年抗戰時期撰述的《中國文化史導論》,至臨終前最后一篇遺稿《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錢穆無不殷殷關切中國文化的命運。這種命運肇始于晚近以來中西方文化的沖突與碰撞,文化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民族存亡攸關的核心命題。錢穆尚言:“在我的看法,今天的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并不僅是一個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問題,而已是一個整個世界人類的文化問題。一切問題都從文化問題產生,也都該從文化問題來求解決。”[2]1
錢穆曾經明確申明他研究文化問題的初衷:“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3]34然而文化研究與比較,要得出客觀公允的結論,不受主觀喜好之左右,優在何處,劣在何處,要有科學的論斷。故而錢穆有意建立一門“文化學”,將文化分為不同的階層、類型和要素等,以使中西比較有的放矢,不落窠臼。他對“文化學”的重要性和科學性頗有自信,斷言此門學問必將成為學術思想中一重要科目。
一、文化的三階層
“文化學是研究人生總體意義的一種學問。……是就人類生活之具有傳統性、綜合性的整一全體,而研究其內在意義與價值的一種學問。”[2]6然而,要以人類生活這一“整一全體”作為一門學問的研究對象,還需要進一步的分剖,劃分出不同的階段和層次,以使得這一“整一全體”更加清晰地呈現。
錢穆將人類生活劃分為三個階層:第一個階層是物質的、自然的或經濟的人生,主要是人與物的關系,此階層的人生,面對的是物質世界,如衣食住行等。人生首先是一自然人生,不能脫離物質的支持。此一“物質人生”,是人類生活最先必經的一個階段,其人生目的僅在于“存在”,即只求用外在的物質來保全自己生命的存在與延續,可以稱之為是“小我人生”。
第二階層是社會的、政治的或集團的人生,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面對的是人的世界,如家庭組織、國家禮制、民族分類等,凡屬于群體關系的,即屬于此一層次。此一“社會人生”,其目的是“安樂”,即在超越了物質人生之后,在各得保全自我生命之上,要求相互間的安樂,來過一種集體的人生,也可稱之為“大群人生”。
第三階層是精神的或心靈的人生,主要是心與心之間的關系,面對的是心靈世界,屬于觀念的、理性的、趣味的范疇,如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等。此一“精神人生”,其目的是“崇高”,即在超越了前兩個階層的人生之后,把握人類內心更深更大的共同要求,使得你我之心、古今之心,心心相印,相互融成一片,也可稱之為“歷史人生”。
錢穆認為文化的演進,正是此三階層的逐步提高,從第一階層到第二階層,乃至完成于第三階層。前者是后者的基礎,但后者同時必然包涵、容攝著前者,即“崇高”必然包涵著“安樂”,“安樂”也必然包涵著“存在”。僅就第一階層而言,因為面對的是物質世界,人要攝取物質為我所用,來維持生命的存在,必然就存在向外獲取的特性,故而此一階層的“斗爭性”就特別的突出。就第二階層而言,因為轉向了人類的圈子之內,面對的是人的世界,則斗爭性必然沖淡,而特別強調“組織性”。就第三階層而言,人類文化面對的是內心世界,是內外一體、物我交融的境界,則“融和性”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按照錢穆的意思,文化的演進,正在于人生目的的逐步提高,從低到高,層層遞進,以待三個階層的全部完成,才是最健康的。如果某種文化的某一階層缺失或腫大,都會有畸形或病態之虞。譬如近代西方文化,則第一階層特別腫大,強調向外的索取與斗爭,便阻塞了向更高階層的發展;印度文化則直接從第一階層越至第三階層,缺失了第二階層,屬于文化早熟的變異形態。
二、文化的兩類型
錢穆做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有一個十分獨到的地方,就是從文化起源的地理背景,來分析文化性格的不同。而且這種方法一直貫穿著他的文化類研究,可以稱之為“文化地理學”或“歷史地理學”。錢穆在《文化學大義》中提出:“大抵人類文化,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之不同,尤要的如氣候物產等之相異,而影響及其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響到此后種種文化精神之大趨向。”[2]24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亦有相似論述:“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4]2依此而論,世界人類文化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即: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展于草原高寒地帶,農耕文化發展于溫帶平原河流灌溉之區,商業文化則發展于海濱及近海各島嶼。
按照各類型文化之性格,錢穆又將它們歸為兩類,農耕文化為一類,游牧與商業文化為一類。他這樣歸類的理由如下:農耕文化是自給自足的,人們安土重遷,百畝之地于生存已是足夠,人們生老病死于斯,故而是安定、保守的;游牧和商業文化需要向外獲取:牧民逐水草而遷徙,商人外出交換以補給自身的不足,故而是流動、進取的。農耕文化自給自足,安分守己,故而是和平的;游牧和商業文化不斷遇到陌生的環境,需要不斷克服外在的困難,故而是斗爭的。農耕文化靠的是天地人的相互配合,才能有好的收成,人順應天地,故而是天人合一的;游牧和商業文化需要憑借舟馬,征服外界,故而是天人對立的。
農耕文化是“安足性”的內傾型文化,游牧商業文化是“富強性”的外傾型文化。兩者各有優缺點,前者“足而不富,安而不強”,后者“富而不足,強而不安”。錢穆評價道:“在理論上,外傾型的觀念,比較欠圓滿,但在實踐上,憑其戰斗向前精神,易于取得臨時的勝利,而終極則不免要失敗。內傾型的文化,就理論講,其觀念似較圓滿,但在實踐上,和平而陷于軟弱,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遠景雖美,抵不住當前的橫風暴雨。于是人類文化,遂在此兩類型偏勝偏短處,累累地發生了無窮的悲劇。”[2]30
如果按照錢穆的分析來對照中國歷史的話,可以看到,晚近以來,中國文化所受西方文化之沖擊,也正是此兩種文化類型的沖撞。中國文化雖在理論上較圓滿,但終一時敵不過西方文化的進取精神,要守守不住,要定定不下。但是,西方外傾型的文化,也早已暴露出其弱點,矛盾重重,乃至有無法克服、難于自圓之虞。從文化類型學上來分析的話,其原因乃在于:其一,外傾型文化要向外征服其依存者,此依存者被征服,最終此文化將失去其所依存之處;其二,征服再征服,至于無可征服之時,其最后之成功,無異于最后之失敗;其三,內外雖然對立,但內外界限并不明確,人本身也是自然之一部分,不可能與自然徹底對立,要征服自然,必要連帶征服人本身;其四,最終,并不能獲得一個實際的外在世界,從而落入空疏抽象。
因著中西文化各自的精神特質,人類文化的圖景,還需要兩者相互調和補充,故而,錢穆便生出了對于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必然會大有作為的信心,甚至曾明確宣稱:“因于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我以為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趨,恐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5]363
三、文化的七要素
文化的兩類型,畢竟還是一種比較概括粗簡的劃分,如若再進一步,來領略文化的繁復變異之諸多相貌的話,還需要進一步細分。錢穆將人類生活諸多形態劃分為七大類,稱之為文化七要素,并認為:“古今中外各地區、各民族一切文化內容,將逃不出這七個要素之配合。我常好把人類文化譬喻作七巧板。雖則板片只有七塊,那七塊板片各各不同,經過各種拼湊配搭,卻可形成諸種的異態。”[2]31-32文化七要素即:經濟、科學、政治、藝術、文學、宗教和道德。
經濟包括衣食住行種種物質生活,相當于文化第一階層。經濟雖然是人類文化的基石,但是它在整個的文化體系中,卻是消極的價值大于積極的價值。沒有經濟基礎,固然影響甚大;但是經濟水準愈高,它對于整個文化體系所能貢獻的意義與價值,并不見得愈高,甚至可能因為經濟的獨大,而滯礙其他文化要素的發展,造成整個文化體系底層的臃腫。
科學就其實際應用方面來說,如電燈、飛機的發明,都還屬于物質經濟生活的范疇;就其精神來說,科學屬于人類的理智,而理智僅是人類心靈功能之一種,人類的全部心靈決不能用理智一項來包括。科學真理是自然真理,但還不是人生真理,最多算是人生真理的一部分。科學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種,自然科學主要淵源于數學與幾何學,其研究方法是推概性的,由一推概到一切;但是到了氣象學與地質學,則需要多一些具體的事實;生物學研究的對象是生命,就更加不同,需要更多的具體事實。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則又在生命上加了心靈,從經濟學到政治學,再到歷史文化學,推概的方法愈見不適用,而應該使用綜括的研究方法。“若把人類知識排列成一條線,數學、幾何在一極端,歷史、文化學在另一極端,那一端是推概性的,這一端則是綜括性的。中間各科,或則推概可多于綜括,或則綜括宜多于推概。生物學則在此兩極端之中點上。”[2]38近代西方雖則自然科學突飛猛進,但是他們將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文科學,這便是一大問題,近代西方文化的諸多缺陷,往往由此問題而引發。
政治包括人群組合之種種法律、制度、習慣、風俗等,其內容約相當于文化第二階層。“人類從經濟人生出發,前面分張著兩條大路。一條是科學,一條是政治。……面對著物世界,故需科學;面對人世界,故需政治。一邊創造出自然科學;另一邊創造出人文科學。”[2]40即,從政治開始,便是進入到了人文科學的領域。西方政治形態,歷史上有:希臘的“市府政治”或曰“民權政治”,根本精神在個人之自由平等,少數服從多數;羅馬的“帝國政治”或曰“皇權政治”,根本精神在權力之征服與組織;猶太-基督教的“神權政治”,根本精神是宗教領導政治。此三種政治,只有神權政治,是要把政治提升到文化的第三階層,另外兩個,因為個人的現實意向,很容易被物質經濟所決定,從而滑向文化第一階層。但是,神權政治因為是用出世的精神來指導現世的事務,所以總有隔閡,無法溝通。故而,現代西方政治是政教分離的。但政教分離的政治意識,沒有更高的理論領導,依然是卑之無高論,不免有遷就第一階層的下傾趨勢。但是中國政治,其政治理想是上傾的,其領導中心在道德,不在宗教。道德的終極歸向,乃是為著多數人。人類文化,正該是由道德領導政治,再由政治來支配經濟。即文化的第三階層領導第二階層,第二階層再領導第一階層。故而,西方政治是下傾的,有墜入第一階層的隱患;中國政治是上傾的,乃是要提升到第三階層去。
藝術、文學、宗教與道德,此四種要素,不像科學和政治,已經沒有了人與物或人與人的對立;到了此一境界,只有渾然一體的“心靈”,古今之心,你我之心,彼此交融,凝成一體,此時才是真正的人生,屬于文化的第三階層。藝術是把人生投射到“物質世界”,即把自我的生命和心靈,投入到自然界中,而與之融為一體,既在自然界中發現自我,又在自然界中忘卻自我。文學是把人生投射到“人的世界”,在他人中發現自我,同時自我又消融在他人之中。藝術是忘我于物,偏重在趣味;文學是忘我于人,偏重在情感。宗教是藝術和文學的變相,是人到了無可奈何之時,才將人生投射到“天”或“上帝”,自我和天融為一體,忘我于天,這是人類在情感的極端狀態下,如恐懼、痛苦、無助、絕望等,心性中的根本需求。道德是純粹內在的、無需外求的心靈境界。藝術、文學、宗教,總還要有求于一個外在的對象,道德則“盡其在我”,不向外求。比如,父求慈,不求子之必孝;子求孝,不求父之必慈。這正是所謂“求仁得仁”之意。道德的發揮,不過是將一顆真性情的心流露出來而已,這個真性情雖然也秉自于天,但既然天已經賦予我了,便是在我之內。故而中國文化強調此真性情乃是人類內在所發,是一種內傾性的道德文化。西方文化則是外傾性的宗教文化,認為人類的真性情,必然來自于超越于人類之外的上帝,不在人類自身。
錢穆認為,每一種文化,必然具備上述七要素。只不過在各種文化中,七要素之間的搭配、比重、地位等各不相同,遂導致各文化之性格與價值趨向的不同。比如中國文化偏重政治、道德、文學、藝術等,是典型的內傾型文化;西方文化偏重在經濟、科學、宗教等,是典型的外傾型文化;印度文化則偏重在宗教、藝術、文學等。西方文化既偏重向外征服的科學,又偏重向外臣服的宗教,是其文化精神難以克服的一種內在矛盾;印度則脫離現實,距離物質人生太遠了,一種早熟的變異形態;中國文化則隔離科學太遠,也有一種虛弱之癥。
四、中西文化之比較
錢穆曾做過一個譬喻,把文化比做一棵樹,第一階層的經濟,第二階層的政治和科學,好比土壤、陽光、水份和肥料;第三階層的文學、藝術是花果;宗教與道德則是樹的內在生機。各階層第次進展,各方面相互協調,才是一棵健康的樹,某一方面的缺失或臃大,都將導致文化的不健康。
近代西方文化有三大淵源,即希臘、希伯來和羅馬。希臘文化是一個畸形發展的文化,它是從第一階層直接上升到第三階層(即從個人人生到宇宙萬物),再從第三階層直接落到第一階層(即從宇宙萬物到個人人生),而忽略了第二階層的大群人生(即政治)。他們的科學、文學、藝術造詣都很高,但是政治沒有安排好,始終沒有構成一個國家。這就譬如腰部虛空,以致影響到全身健康。希伯來民族顛沛流離,根本無暇顧及政治這一層面,而將個人人生脫離苦難的希望,投入到了宗教上,連文學藝術都沒有。大群人生的關懷少,缺少政治層面,也是腰部虛空。羅馬在第二階層的政治上成就大,但羅馬文化卻停滯在了腰部,沒能進入到第三階層,得了腰部腫大的侏儒癥。雖然中世紀政教合一,但宗教是外傾的、出世的,政治是內傾的、入世的,由宗教來控制政治,也是一種毛病。后來的文藝復興,正是要復興個人的現世人生;宗教改革,也正是要政教分離;再加上近代新科學的興起,西方文化也是處在混亂的狀態。所有這些,根源乃在于西方文化是三種不健全的文化拼湊而成的。
中國文化相對于西方文化而言,不是各種文化的拼湊,而是從一個源頭上發展而來的,每一階層的發展都比較正常。“中國文化,就上述文化三階層言,實在能就第一階層透過第二階層而進達到第三階層;還從第三階層向下領導控制第一、第二階層,符合于文化演進之正常軌道。”[2]63正因為中國文化的體系搭配與演進比較合理穩健,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危機,多自外來——以前是游牧文化,現在是商業文化。如果說中國文化自身有什么問題的話,則有一些虛弱。雖然中國文化屢次受到外來文化的侵擾,但都沒能動搖中國文化的根本,推不倒中國文化的體系,反倒是漸漸被中國文化所消融、同化掉了。
錢穆認為,農業是人類最基本、最主要和最正常的生業,故而農業文化這種內傾型的文化,也是最基本、最主要和最正常的文化。中國是一個大型農業區,氣候較寒冷,生產較艱辛,文化果實也就結的最堅實飽滿。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至少經歷了兩千年的長期演進,才漸臻成熟;到了秦漢時代,全部文化體系的大方案、大圖樣和大間架已經確立。故而中國文化堅實的內生力,可以抵抗歷次外來文化的沖擊,如匈奴來犯、五胡亂華、佛教傳入、安史之亂、遼金元內侵等。這些外來文化,不能根本動搖中國文化體系的大方案、大圖樣和大間架,事后經過一番提煉、調整和充實,便被中華文化的大體系所吸納和融化。
近代西方文化是在希臘、希伯來和羅馬三系文化的基礎上,加上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與勃興。自然科學使得物質生活發生了突變,第一階層過度膨脹,無形中形成了第一階層引導、支配其他階層的趨向。借助自然科學所帶來的物質經濟的強大,再加上其文化外傾型的性格,近代西方文化在不斷地向外擴張,對其他文化形成了壓迫之勢。但是按照文化七要素理論,科學僅僅是七要素之一,它在全部文化中,也主要是屬于文化的第一階層。我們不能因為這一階層的強大所帶來的暫時的便利,便否定其他階層、其他要素和其他文化的搭配樣式。
近代西方文化之所以有領導世界的力量,就在于這一階段自然科學的發達。但是,近代西方文化卻過于偏重了自然科學,而忽略了人文科學,導致文化的第一階層過于膨大,而第二和第三階層萎靡不振,其他文化要素難以發展伸張。所以,西方文化的科學愈發達,愈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許多不良影響。當今能夠與西方文化相抗衡、相補充的,唯有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德性一元”的宇宙論,《中庸》說:“盡己之性,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就是說,人與自然萬物,都秉持著天地之性。那么,自然科學其實也就是一種盡物之性的學問,這和盡人之性的學問,并不隔閡、沖突。故而,中國文化中的德性之學,是可以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相互融通的。
錢穆特別提醒到,在此人類文化大變動、大融合的時期,各國文化將何所歸往,是特別值得重視的問題。今天的中國,對于文化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完整明晰的認識,沒有一個總體方案的話,舊的隨便拆,新的隨便蓋,也不過是徒費體力罷了。這里并不是要抱殘守缺,而是要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大體系、大框架,為今后文化的發展,穩住根基,守住自信,找到出路。
參考文獻:
[1]韓復智.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卷一)[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
[2]錢穆.文化學大義[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3]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 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錢穆.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