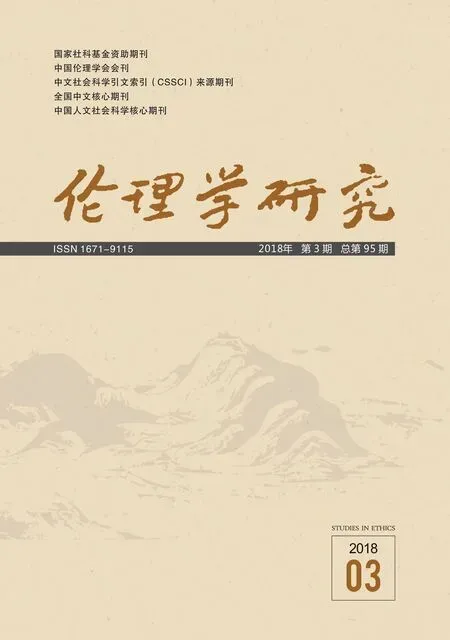古希臘目的論誠信體系初探
李婧琳,王淑芹
將對誠信的理解置于對自然、本性的認識之中,是古希臘誠信思想最主要的特征。最早神話自然中關于誠信的最樸素和簡單釋義,為整個古希臘誠信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調。古希臘神話中“匹斯提斯”(Pistis)女神形象就是當時人們對信服、信任、誠實、可靠等美好品質希冀的集中表達。這種理解,隨著自然進一步被自然哲學家發現,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處通過哲學思辨的洗禮與希臘城邦制度中的具體實踐,形成了古希臘最具特色的自然目的論誠信體系,影響深遠。
一、自然目的圖景中的美德論誠信
對古希臘人而言,諸神的故事蘊含著他們對自然與人性的理解,神話世界與城邦生活相互映射。從泰勒斯開始的早期自然哲人,以理性方式代替神話的迷蒙,思考世界的本原。這一思路,為亞里士多德尋找人與所處世界之間的協調統一性,進而形成自然目的式的倫理、政治理論框架提供了入口。
追尋自然哲人,亞里士多德放棄了從神話、宗教等超越性的神秘維度,解釋萬物流變、人事更迭的嘗試,把主導事物的依據放回到世界本身之內,將事物的自然本性作為討論人、物的基礎。人的自然傾向是追求幸福,手段則是運用理性做出思慮和選擇。在認識自己的天賦、秉性或職司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運用理性,以中道為標準,培養自己的性情,做出合宜的行為。
誠信在自然目的式美德論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剝離了“Pistis”之上的神話信仰含義后,亞里士多德聚焦于“一種誠實品質的鍛造和誠信行為的展示”層面上的誠信。相應地,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他詳細討論了“誠實”和“友愛”這對與誠信密切相關的品質。誠實是關于個體誠信具體倫理涵義的界定和澄清,而誠信作為友愛的前提,則是共同體得以形成和維護的關鍵。
亞里士多德認為,誠實或真誠作為一種具體的倫理德性,是自夸與自貶的中道。要理解一個誠實和真誠的人需要去對比理解他是如何對待自己聲譽的,要在言辭和行為上觀察他的真或假。《倫理學》中簡短的討論,貌似簡單,然而正如意大利學者凱文(Flannery Kevin)指出的,要真正理解這兩個概念其實相當困難,必須要聯系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相關討論。具體行文中,亞里士多德使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術語,他將一個真誠的人稱為“”,字面意思是“一個自身”(each him-self)。這一術語需要結合到《形而上學》第五卷29節中圍繞“說謊”()所展開的討論一并澄清。亞里士多德認為,說謊的人熱衷于錯誤的表述。當他說謊時,就把虛假注入自身當中,遮蔽了自身的本性和自然,從而成為了“假人”[1](P116)。這就讓他與“真”(無遮蔽)出現了分離,不能成為“一個自身”,即真實的自己。真正的是其所是,即具有德性,而不會吹噓或隱藏,否則就不能說其是真實的存在。由此看出,亞里士多德認為,作為具體德性或美德的真誠或誠實是“真”(最高目的)本身的體現。從本體論意義上而言,真和善是同一的,都是讓世界維持自身的那個最高的理想原則和目的體現。
具體來看,實踐智慧“中道”意義上的誠實指向一種“真”的狀態。這種狀態是作為人這種存在,自己將自己的本性最充分地表達和成全出來,例如,一顆橡樹種子成長為一顆高大的橡樹,而不是柳樹,這就是一種真,一種自然本性的施展。這一狀態類比于人,就意味著人在理智的指導下,恰當地行事,讓最能代表人的品格最為充分地實現。簡言之,“真”既是誠實的邏輯起點也是最終的歸旨。對于秉承自然目的學說的亞里士多德,讓誠實成為誠實的東西并非是允諾和誠信行為帶來的利益和好處,而是人之為人的本性和自然的充分施展。
將近代契約論語境下的誠信與亞里士多德的誠信對比考察,可以發現古代美德論誠信觀的獨特之處。首先,美德論誠信觀并不是首要地“指守約或涉及公正與不公正那些事務上的誠實”,而更多地是關于一種人際交往和交談方式上的誠實,更重要的是,這種誠實是一種美德或德性“真實地體現和展示”;其次,近代契約論主義主要建立在利害或利益交易的基礎上,因而在政治國家建立和商業活動中被反復強調,例如對這類“誠實”(信用)的破壞是會受到律法處罰的。而古代美德論誠信觀則強調“一個自身”,與個體的本性、自然和品格緊密聯系。因此,它是一種自由的品質,不涉及任何利益,完全是建立在一種良好的自然傾向基礎上的品格。
與誠實密切聯系的概念是友愛,誠實或誠信既是友愛的前提,也是友愛的結果。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強調,“人是城邦的動物”。人之充分實現或真的狀態,并不能單憑離群索居的孤獨個體所能獨自實現。人離不開城邦,而在城邦中,“友愛”是個體間相互粘合,粘合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愛與被愛之間保持有信任、誠信的關系。
亞里士多德將城邦中公民的關系視為建立于愛與共同關涉之上的共同體。他認為,理想的城邦并不能太大,公民間都需要彼此熟識,人們的善意能以中道的形式付諸于實踐,在持續性的人際交往中形成共同的道德,這種善意就是一種“誠”的外化。真正的“善的友愛”中的“誠”是主動的,給予德性上相似的人以友愛,以“誠”對對方,也是在實現自身的本性,即至善。現代實用主義的誠信、友愛關系中更多的是相信對方可以為自己帶來“好處”,或是快樂或是其他,不具備善意的屬性。而古希臘時期“善的友愛”關系中的誠信,則是蘊含著正義,以相互尊重為基礎,利他為原則的親密性,這種親密性就是時刻心存對熟悉“他人”的“誠”和主動利他實踐行為的“信”的結合。套用滕尼斯的觀點而言,這是一種熟人社會建立社會誠信的方式。熟識和友愛構筑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這種信任的前提又是個人自我誠實、善好品質的養成。
綜上所述,在亞里士多德自然目的基礎上的美德論誠信觀中,人的自然本性中具有誠實的潛能,同時也具有實現誠實這種德性的能力。自欺、自夸、欺騙、狡詐都是這種品質缺失時的表現,是對自然本性的遮蔽,將虛假注入自身,讓“真”缺失。這種缺失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虛榮。無論怎樣,它們都不合乎自然本性的舒展,是一種違反本性的、不合乎理性的選擇,從而導致不幸。人只有通過理智智慧體貼自然本性中合乎理性的成分,運用好作為實踐智慧的“思慮”和“選擇”,讓每一次的行為都符合誠信、符合中道,不斷地將誠信的潛能現實化,最終使誠信作為一種品質被固定下來。包括誠信在內的各種德性的實現,即是達及至善,獲得幸福的關鍵,也是獲得友愛、融入城邦生活、擔負公民義務的開始。具有卓越品質的真誠之人,通過相互友愛和親近構成的政治共同體,不僅是亞里士多德倫理、政治理論所希望澄清的,同時也是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政治制度所渴望保護的。
二、目的論誠信觀的制度化
古希臘的誠信系統并非只是一種思辨的哲學體系,還包括與之相應的具體誠信保護性措施和制度建設。這種思辨與實踐統一的誠信系統,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將人的幸福與城邦正義進行有機結合,維護城邦的核心價值。簡單來說,誓言、修辭和民主評議制度三項比較具有典型性。
1.誓言制度
相較于古羅馬具有嚴格的成文法典,古希臘的法典更類似于習俗的集合體。這與其原始的神話信仰架構不可分割,荷馬史詩神話中對神祗的祈禱和獻祭具有十分嚴肅的神圣性。女神斯提克斯(Styx)在神話中,主掌誓言之河,所有神的誓言都被其約束。古希臘自然目的與人之本性具有同一的觀念,人對神之行為的模仿和遵從,也是在去除靈魂的遮蔽,因而公民的誓言制度對城邦的穩定,猶如神祗的誓言對奧林匹斯山穩固的縮影。古希臘神話中“Pistis”不僅是人類內心渴望和追求的圖騰性、象征性映射,同時也成了管理、監督和教化人們誠實、守信的宗教規范的一部分。源自于對“Pistis”女神的敬畏和內心對誠信、正義篤信,從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時代阿提卡地區開始,關于公民權質疑的宣誓、民主議事會以誓言等發誓都是實實在在的制度或必需的程序。
古希臘有一種類似于賭博的裁判制度——“證據性誓言”。當爭端發生的時候,雙方分別對神袛發誓,自己所爭取的或是勝利的獎品或是所獲得的財物的確是自己應得且是屬于自己的。這一制度來自于《荷馬史詩》中赫爾墨斯(Hermes)向眾神發誓自己沒有偷阿波羅的牛,此宣誓是其用來證明牛的所有權的證據。這一“立誓”的程序:由原告發起,被告同意,但賭注最終歸國家。在篤信神祗的古希臘人看來,向神宣誓,要求足夠的內在品德,是在遵循神的行跡,公民依照神的模式進行實踐,正是善的高級樣態,因此受到古希臘人的尊崇。
另一種誓言被稱為“莊重誓言”,則是更為正式的誠信制度,存在于司法程序中,最初辯訴雙方被要求向神袛拉達曼提斯(Rhadamanthys)發誓,不敢發誓的一方被判輸,敢于發誓的一方被判贏。這同樣依據的是古希臘人在神袛背景下對內心美德的自控。當誓言與修辭學結合時,卻也有被濫用的可能,但是,任何不誠實的誓言、偽證意味著自我放逐和不可饒恕,自此人格將被懷疑。然而缺乏約束機制的偽誓,依舊開始流行,最終這樣的誓言流于形式,并隨著古羅馬時代的到來而徹底改變。
古希臘人注重內在美德的實現,但并不妨礙以形式和程序保證誠信行為的制度存在。人的美德與城邦美德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完全相同,但同樣遵守“自然”等級次序,符合潛在轉化為現實的自然目的,城邦的誠信制度是人的誠信美德的直接延伸。在梭倫(Solon)執政期間,在經濟方面有著較豐富的規定,例如對市場誠信行為的監督,就要遵守十分嚴格的程序,運用抽簽選舉的方式進行。在當時的阿提卡地區,司法審判是需要執行陪審和審判的人員進行宣誓以彰顯誠實,獲得公民信任。這樣的宣誓被稱為“”,這是梭倫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在古希臘后期被廣泛采用。誓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還與另一項制度密切相關,即修辭制度。
2.修辭制度
古希臘的修辭不僅是七藝之一,還是城邦中一項重要的制度。這是因其與政治、法律的緊密聯系相關。修辭是通過公共演講討論政治問題,注重的是辭語的效果,即說服力,用以力證事情是“真”。“希臘人成功地管理他們的城邦不僅是因為他們特別注重個人誠信,也因其為整個政治體系——工作合作的綱領、政治責任的法律機制,以及其中最為重要的修辭,這些要素一同讓人們如其所是的行為。”[2](P4-5)古希臘在政治上的“真”是一種外向顯現的誠信,這與中國古代更重內省式的修辭是兩條路徑。修辭即運用三段論規則在邏輯推斷基礎上進行的公共演說或民主決策,是政治學討論的范疇,“一種能在任何一個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3](P24),“Pistis”的另外一個重要維度:通過系統的、邏輯的論證方式,說服某人和確證某事,在交互關系中獲得他者的信任。古希臘政治家的修辭學和智者詭辯術不同,以過往行為品質為基礎,在修辭教育的幫助下,執政官可以在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構下,改良制度、推行政策、決策公共事件。
由于對修辭的注重,促使古希臘人對口頭證據的重視要甚于書面證據。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其喜劇《黃蜂》一幕中對狗的審判,就是對古希臘人對口頭證據注重的戲劇性還原。因為口頭證據具有抗辯性,更能彰顯出當事人的誠實樣態,以取信于審判者。梭倫立法時由于修辭學鼎盛,采用了許多詩歌的樣式。雅典的政治誠信中常常可以見到通過演講對修辭制度的運用,當公民們為商討某項城邦要事而舉行大會之前,多由祭司用水灑成一個圓圈,將所有的參與者圍在其中,以表示凈化、圣潔之意,然后向諸神祈禱之后,再行開會;演說臺亦被視為神圣之處,演說者登臺時要頭戴花冠,以示其言論權利為神所保障和祝福,并在演說前先作禱告;城邦對官員的選擇,也以虔誠、真誠、守信、敬神為首要標準。精彩的演說和優美的修辭體現在具體的選拔之中,選拔需要審查的既是公民的可信程度,這種審查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與當代的信用制度有相似的因素,但制度的基礎并不相同,這時的信用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是建構在一定地域基礎上的禮俗關系。
修辭制度,不僅僅是一種誠信表現形式,更是一種被古希臘習慣法所確立下來的制度,這種制度也可以看作是城邦的靈魂,通過不斷的政治實踐,逐漸積淀為城邦的品質。
3.民主評議制度
信任,是古代雅典政治生活得以維系的關鍵要素之一,這種信任與其全體公民參與的民主制息息相關,建構在同一種信仰基礎上血緣和地緣的友誼,正對應著亞里士多德關于誠信與友愛的思想。“陶片放逐法”又被稱為貝殼放逐法(),根據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記載,現今西方學者大致推斷是始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克里斯提尼對民主制的維護,最初目的是為了保證民主制不受僭主的破壞,對懷有野心企圖篡奪人民權力的政客進行放逐。
陶片放逐法并不是司法審判,而是單方面的行政行為,沒有抗辯,被放逐人是否真正具有某些僭越民主制的事實并不能真地展現在公民大會上。那么是否放逐的決定就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同時以投票人誠實的內在美德進行投票。“這種善的圣靈,也不固定在他的位置上,而是居住在它的崇拜者們的良心里”[4](P67)。哪些人是值得信賴的朋友,哪些是不能依仗的敵人這恰恰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始點。“陶片放逐法”的運用,正是希臘人的誠信制度思想最深層的體現。
相對于處理不誠信僭主破壞民主制度的陶片放逐法(行政投票),對那些直接損害人民利益和危害城邦安全的欺騙行為,古希臘公民則趨向于以更清晰明確的司法審判程序進行,更徹底地對不誠信行為進行矯正和警示,因此,確立了欺騙人民罪。無論是不采用修辭和演講抗辯的“陶片放逐法”還是運行抗辯的欺騙人民罪,或是不信神的信仰審判都是經過公民大會的表決。
如果一個誠信系統完全建立在投票者的主觀情感判斷上,那么這個制度的隨意性和可被操控的風險就會增加。亞里士多德自然目的誠信美德的彰顯,需要理性思辨精神的學習,并且通過不斷實踐才能真正實現。因此,正如亞里士多德對政體區分的擔心,多數人的統治如果能一直保持在誠信內,則制度正義;如果多數人的統治違背了誠信美德,介入主觀感受,在政治投機者的煽動下,極其可能發生因“多數人不誠實”引發的暴政。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Aristeides)便是在公民對其功績和信用“不了解”的情況下,被投票放逐的,在被放逐兩年以后,阿里斯提德又被雅典召回,重新授予將軍一職抵御波斯入侵,蘇格拉底的審判也與此類似。這都是不忠誠于本心,隨意投票,而又缺乏客觀限制規則的惡果。
古希臘的誠信,并非近代規范論誠信觀指引下的規范性原則或規則。相較于西方近代誠信思想訴諸于個體的理性或人性,古希臘時期的理性精神是以思想和制度互促的方式,幫助人把握、趨近于某些極致或永恒。在自然目的中,理性是靈魂的一個部分,與非理性相對應,理性把握知識(普遍本質)對應著真,稱為理論理性;理性把握美德對應著善,稱為實踐理性。這種語境下的誠信思想與誠信制度仿若善的一體兩面,相互依存,一方牽動著另一方。誠信并不是欲望的驅動,也不是善良意志對人理性普遍立法的遵守,而是通過實踐理性的無數次選擇,最終在現實中確定下來成為人的品質,擴展到城邦中便以制度形式顯現出來,又回饋到公民的品質塑造中,使其不斷地接近恰如其分。
[1]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苗力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2]Steven Johnstone.A History of Trust in Ancient Greec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3]亞里士多德.修辭學[M].羅念生,譯.上海:三聯出版社,1991.
[4]費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