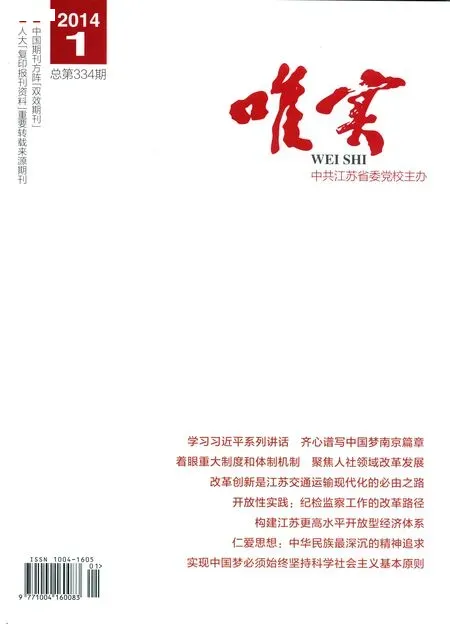張之洞與中越邊境和南海勘界
謝世誠
晚清時期,兩廣總督張之洞處理中越邊境和南海勘界,維護了國家領土和領海主權,體現了高度的智慧和深遠的謀略。
一、張之洞與中越邊境勘界
清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挑起了中法戰爭。然而,他們遇到了強悍的對手:海內外中國人民堅決抗爭,兩廣總督張之洞、云貴總督岑毓英這兩個能吏和劉銘傳、馮子材、劉永福等將領指揮清軍將法軍打得落花流水,先后取得鎮南關、臨洮等大捷,迫使法國重新走上議和談判桌。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中法兩國在巴黎簽訂《巴黎議定書》,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簽訂《越南條款》,結果則令中外大跌眼鏡:清廷勝后妥協,法國基本達到了戰爭的目的,真所謂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所攫取的利益最重要的一條則是越南“獨立”——正式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并進一步將其勢力向中國西南邊境逼近。
越南與中國廣東、廣西、云南三省交界。兩國長期存在傳統的宗藩關系。而當越南成了法國殖民地、保護國后,與中國的傳統關系戛然終止,《越南條款》第三款即規定:自條約畫押后六個月內兩國派員勘界。光緒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清政府派內閣學士周德潤、總理衙門大臣鄧承修為欽差大臣分別前往云南、兩廣會同當地督撫辦理中越劃界事宜。
張之洞深知此次勘界關乎中國版圖,更關乎他所管轄的兩廣地區的安全,故十分重視,全力配合。八月二十四日,鄧、周到達廣州,張之洞即與之籌商一切,一方面介紹邊疆情況,一方面提供物資、人員,包括翻譯、地圖等,他得知法國勘界人員多為武職,意在“考察形勢,審探路徑,用意正深”,因而也選定一批熟悉邊界情形的武職員弁先行介入。
張之洞認為,勘界重點應是收回原屬中國的土地,所以應寸土不讓,能爭必爭。廣西、越南邊界,集中在諒山及以北地區的歸屬,并涉及通商問題。清廷下令停戰時,張之洞即主張暫緩從諒山撤軍,以加強在談判中的地位,未果;后又建議在諒山和鎮南關之間建立“歐脫”之地即緩沖區,也未成。鎮南關南距諒山四十里。此時,他認為應盡量將通商地點南壓:鎮南關南下,距文淵十里,文淵至驅驢墟二十里,再十里至諒山,中間僅隔一河。張之洞提出桂越分界設關最好設在驅驢,不成,再議文淵,以此為限,決不能在鎮南。鄧承修與張之洞觀點一致,談判中提出諒山以東至保樂州、以東至海寧府(芒街)應劃給中國。法方當然不肯,雙方僵持不下,清廷害怕與法國決裂,在英國等撮弄下,最后形成如今這條桂越邊界。
張之洞真正能掌控的地區實際在廣東,所以粵越邊界是他關注的重點。
廣東欽州(今屬廣西)與越南邊界,江平、白龍尾等處歸屬雙方爭論激烈。張之洞多次上奏,提出要收回這些土地,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所上《欽越邊界亟應改正折》提出,廣西上思、下思、思陵三州沿邊以外有崎嶇荒僻地數百里,東為廣東欽州,西為越南諒山、廣安,南濱大海,有快子籠、亞溇灣、九頭山、青梅頭諸島嶼,北界北侖、扶隆、愛(上竹頭下覃)等隘,十萬大山盤亙其中,其他總名古森峒,亦稱三不要地,“按照條約,亟應改正,自宜畫歸華界,上游緊接廣西三峒思陵土州之地,下游直出新安州海口,東包青梅頭、海寧府芒街,接連竹山、江平、白龍尾一帶,以正封域”。要求電飭勘界大臣鄧承修與法方力爭,“庶邊氓不至終淪異域,而于設防固圉實大有裨益”。并赍送地圖。(《欽越邊界亟應改正折》,光緒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全集》第1冊,第372頁)光緒十二年九月七日他又上《辨認欽州老界繪圖列證請旨飭辦折》,根據檔案、遺址等提出十條證據,說明欽州一帶屬于中國,如:“第六證,古森港海口為中國界。古森河,今名古森港,在州西南,距東興十余里。……第九證,江平、黃竹為中國界。江平、黃竹在州西南,距思勒十里,距防城三十余里,去州城約一日程。明崇禎間系潘土目將田土私賣與越民為業,并無官文書案據(見峒長后裔黃輔文等公稟)。江平為欽州安良社地,今猶名安良街(見明萬歷三十八年峒長分單,街門刻字現存)。”又:“第十證,海面快子籠、青梅頭以南至九頭山附近諸島皆為中國界。諸島皆在州西南,為大洋中、越相接之處,所居皆系華人,并無越官、越兵駐扎。查九頭山即狗頭山,同治九年十二月前兩廣總督瑞麟因欽州洋面鄰接亞婆、狗頭山等處向為洋盜窩聚之所,除派兵剿辦外,照會越南國王派兵會剿,旋接該國王呈覆:‘下國廣安海分原無亞婆、狗頭山等名號,現派工部署參知阮文邃等管帶師船往廣安省之白藤江按截等候等語。是白藤江口以外海中諸島并非越境所轄,其為華界無疑(見同治十年正月十一日越南國王呈覆原文,現存兩廣督署有案)。”
關于白龍尾,張之洞又找出嘉慶十六年三月施行的巡海新例規定,每年兩班,上班正月初十日、下班十一月初十日,龍門協與該屬一都司、兩守備在白龍尾自行會哨,責成欽州稽查稟報,“此現行定例,載在每年題咨洋巡冊及道光十二年刊本廉州府志卷十四”。他特別強調,白龍尾處在中國內海,此條例“并于內外洋面下列有白龍尾名目,注云‘內外洋界祗就中國所管洋面分之,非內華外夷之謂也等語。特詳陳以備辯論”(《兩廣總督張之洞電》,光緒十三年正月十四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法戰爭》第七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104頁)。
這些證據有力支撐了談判,終使法方于光緒十三年同意將爭議的白龍尾、江平、黃竹等處一律劃歸中國。張之洞即于同年十二月巡視粵海各口時親至白龍尾地方登岸查閱該島形勢,隨后升改欽州政區,在白龍島設兵駐守,由龍門協添派水師加強巡緝洋面。
二、張之洞與南海劃界
欽州劃界涉及南海若干島嶼的歸屬。
廣闊無垠、富饒美麗的南海,自古以來就是中華兒女活動的舞臺,包括南沙、西沙、東沙、中沙在內的南海諸島,是中國人最先發現、開發,早已載入中國的版圖,有史可征,鐵證如山。清代對南海的管轄更加重視。
胡瑞書、楊士錦的《萬州志》(道光八年修)卷三《山川略》記載道:“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然俱在外海,海舟觸沙立碎,入塘無出理。”而光緒年間鐘元棣、邢定倫所撰《崖州志》卷十二的《海防志一·海防,環海水道》稱崖州:“分界洲北七十里,至柑蔗洲,水深一丈,沙底,東北風可泊。柑蔗洲北六里,至大洲灣,內外皆可過船。洲頭灣口,水深四丈,西南風可泊船五六只。洲尾白沙灣,水深二丈,可泊船數只。洲東接大洲洋,有千里石塘,萬里長沙,為瓊洋最險之處。”endprint
修于道光二十一年的《瓊州府志》特別強調瓊州是“海外之要區,西南之屏障”。銅鼓嶺在文昌縣清瀾港東北,東北最險處亦名銅鼓角。“嶺北有大灣,遇西南風可泊十余船。南有小灣,可泊船四五只。距嶺百余里為七洲外洋,北接硇州,東通夷洋。嶺外水深無底,亂石如麻,皆有漩渦急流,舟經此者多沉溺,行大海中但望見銅鼓角輒不可救”。“文昌縣七洲之下有泉出焉,其味甘洌謂之淡泉。航海者于此取水采薪”。“大洲灣東三十里有前后坡,東接大洋,名大洲洋,中有前后觀嶺、雙篷嶺、雞冠嶺,皆屹立大海,不能泊船”。該書卷十八還詳細記述南海潮流狀況:“每月初一、三十日、初二、三、四、五、六日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二十一日,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至七洲洋及外羅洋。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至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退流東。二十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洲洋及外羅。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凡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鳥(島)聲見如白鳥(島)尾帶箭。此系正針足近外羅對開。灘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如望見,船身抵下,若見石頭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二十三、三十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二十六忌。”
對南海航路的認知更進一步深化。《瓊州府志》稱:“沙線礁石……瓊南沙礁俱有,西路多沙線,東路多暗礁,萬州文昌外洋為最險。”約編于17世紀末的《東南洋針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稱:“用單坤針十二更取七洲山,洋名七洲洋。《瓊州志》在文昌縣東一百里海中,有山連起七峰,內有泉甘洌可食。舶過,用牲粥祭海厲,不則為祟,舟過此極險。稍貪東,便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七洲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趾東京,用單申針五更見黎母山……又七洲洋,用坤未針三更,取銅鼓山,《廣東通志》曰在文昌東南,銅鼓海極深陷,用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又從赤坎山,用單未針十五更,取昆侖山,屹然海中,山高而方,山盤廣遠。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侖,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顏斯綜所作《南洋蠡測》(1842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帙)則稱:“南洋之間,有萬里石塘,俗名萬里長沙,向無人居。塘之南為外大洋,塘之東為閩洋。夷船由外大洋向東,望見臺灣山,轉而北,入粵洋,歷老萬山。由澳門入虎門,皆以此塘分華夷中外之界……塘之北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雖小船亦不樂走。塘之西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十余年前英利據此島名之曰星忌剌坡……此島由外洋至粵十余日,由七洲洋至粵僅七八日。”
中國人在南海的活動更加頻繁。吳宜燮主編的《龍溪縣志》(1762年刻本)卷十七《人物·孝友傳》中記載道:余士前,字庸然,父(據《漳州府志》記載其父名錫彰)在西洋貿易,娶婦生三子。父卒,士前攜三弟歸故里時,在萬里長沙遇險,士前兄弟與同舟十七人漂流到一海島,靠雨水活了18天才遇商船獲救,“士前先扶擁三弟過船,己獨后,槎(在海島用破木所扎)忽解,眾撤長繩使挽之,再墜乃得升”。
此外,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指南正法》、《海國聞見錄》等書都記載了中國人在南海諸島生產和生活的情況。
清政府對南海及其諸島的主權意識更強。金光祖的康熙《廣東省志》卷十三《山川·萬州》中稱:“長沙海、石塘海,俱在(萬州)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郝玉麟在雍正《廣東通志》卷四《瓊州府·形勝》記載:“長沙海石塘海,俱在城東海外洋,古志云萬州有長沙海石塘海,然俱在海外……瓊以海為界,地饒食貨,黎峒介峙,郡邑環之……萬州三曲水環泮宮,六連山障、州治千里長沙,萬里石塘,煙波隱見。”《瓊州府志》卷三《輿地志·疆域》稱:“古志云:南則占城,西則真臘交趾,東則千里長沙萬里石塘,北接雷州府徐聞縣。”雖說中國與越南兩國關系特殊,但清政府對疆界從不忽視。也如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月三十日(1833年1月20日)道光帝所說:“惟華夷洋面雖連而疆域攸分。”(《宣宗實錄》卷二三○)
光緒初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張德彝皆記載西沙群島是中國的領土:“(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辛亥晴,水平風順。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左近巴拉塞小島,中國屬島也。荒僻無人,產人(海)參、珊瑚,均不佳。”(張德彝:《隨使英俄記》,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284頁,第841頁)
“(光緒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午刻,共行八百三十一里。船主云在赤道北十七度半(倫敦之東百一十度四十九分),計當在瓊州府南百余里,船人名之‘齋納西,猶言中國海也。海多飛魚,約長尺計,躍而上騰,至丈許乃下。左近帕拉蘇島,出海參,亦產珊瑚而不甚佳,中國屬島也。系荒島,無居民……廿七日午正,行北緯道十六度十一分,經度值巴黎東一百八度二十三分,計行二百二十六買爾(合中國六百七十八里)。舟歷七星洋,有無數小島值瓊州東南,名巴拿塞爾。船主伯魯蘭云:‘島無居民,惟土石相雜而已,向為盜舟出沒之所。”
清政府維護主權的措施更加得力。為維護海域主權,清政府采取了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抓手之一是巡海,每年對海疆的巡視抓得極緊,從未中斷。如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二十九日(1756年11月21日),兩廣總督楊應琚奏,廣東每年分兩班巡南海,上班二月出洋,六月撤師,下班六月出洋,十月撤師。帶隊的為總兵、參將等高級武職,參巡的兵員既包括熟悉南海海況的老兵,也酌帶尚未諳習者,使生熟相間,以使全營水兵得到訓練,務令熟悉風云氣色、掌握港嶼情形。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44年9月17日),兩廣總督耆英等議復御史江鴻升奏水師巡哨章程,對廣東洋面分中、東、西三路。每年分為上下兩班,三月、九月間皆由中路虎門起巡。東路之南澳與西路之瓊州營,分定以六月間往中路三面會哨。南澳鎮兼轄閩粵洋面,除于六月、九兩月會巡之外,每月還分兩班輪巡,與閩省左營會哨。黃任、郭賡武所編《泉州府志》(1870年本)卷五十六《國朝武跡》中記載康熙、雍正年間的吳陞,同安人,積功擢廣東副將,調瓊州,自瓊崖,歷銅鼓,經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視,后晉浙江提督。雍正三年,加太子少保。endprint
《瓊州府志》卷十八《海防》記載所巡區域:共分海口營、崖州營、儋州營。海口營分管洋面東自樂會縣博鰲港起,西自臨高縣迸馬角止,共巡洋面一千一百余里。崖州營分管洋面東自萬州東澳港起,西至昌化縣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羅占城夷洋,西接儋州營洋界,東接海口營洋界。儋州營分巡洋面南自昌化縣四更沙起,北至臨高迸馬角止,共巡海道五百余里。鐘元棣、邢定倫編《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一,海防·環海水道》記載:崖州營水師營分管洋面東自萬州東澳港起,西至昌化縣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羅占城夷洋,西接儋州營洋界,東接海口營洋界。李翰章主持編著的《廣東輿地圖說》(1889年刻本)稱:“粵省地勢,東西袤長,南北稍狹,然前襟大海,其中島嶼多屬險要,故水師每歲例有巡洋,東自南澳之東南南澎島,西迄防城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頭山……皆粵境也。今之海界以瓊南為斷,其外即為七洲洋,粵之巡師自此還矣。”
以上材料多次提及七洲洋,絕非偶然,這是由于七洲列島位于海南省文昌外海,是海南最東部的海島,該海域是中國重要漁場。七洲列島——西沙永興島航線是海南島與西沙群島及南海諸島之間的主要補給線,對維護西沙群島乃至南海的安全穩定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清代對此如此重視,正是總結歷代經驗的結果。
南海周邊各國不僅對中國擁有的南海主權毫無異議,更對清廷十分“恭順”,乾隆二年閏九月,陳五勝租用張清趕繒船從臺灣運米回廈門,將米換麥,前往呂宋,冒稱遭風漂此,將船、貨盜賣。呂宋官方發現后,將押船的陳同等人拘拿、通緝,于乾隆四年九月派人將判決書和賣船的銀一百元赍送閩浙總督郝玉。乾隆帝接報十分高興,贊揚“該國王輸誠報效甚屬可嘉”,傳旨嘉獎(《高宗實錄》卷一○一)。
蘇祿國(位于現在的菲律賓蘇祿群島)國王乾隆時期甚至數次要求將該國歸并入中國版圖。如乾隆十九年二月,他派在進入該國的福建人楊大成即武舉楊廷魁(在中國國內犯事出逃)為副使來中國入貢,且“愿以地土丁戶編入天朝圖籍”。二月十八日(1754年3月11日)乾隆帝發諭旨認為:“我朝統御中外,荒夷向化,該國王土地人民久在薄海臣服之內。該國王懇請來年專使赍送圖籍之處,應毋庸議。”(《高宗實錄》卷四五七)蘇祿國國王不甘心,很快又遣官進貢方物,請入附版圖。乾隆帝于十一月三日(1754年12月16日)頒旨,再次婉言謝絕(《高宗實錄》卷四五六)。
與清廷、南海關系密切的越南,對清廷的“恭順”,表現為在南海積極配合清廷的活動。
如中越雙方協同救護海上遇險人員。康熙八年廣東都司劉世虎等駕舟巡海遇風,飄至越境,廣南國王差趙文柄等送劉世虎等歸粵。乾隆三年,越南漁民鄧興等捕魚時遇颶風于五月四日漂入文昌縣清瀾港口;令奉等運谷船五月十三日被風漂至崖州保平港。經地方官報告,兩廣總督鄂彌達先后批示布政使發給口糧、撫恤,資遣回國。乾隆十年四月十七日(1745年5月18日),兩廣總督那蘇圖奏報,越南黎文請等七人在乾隆八年駕藤步單桅船一只往廣義采玳瑁,被風漂至崖州望樓港,已經支給口糧,加意撫恤,現發遣回國。道光十一年九月南澳鎮總兵在洋巡緝時發現夷船一只,馳往查探,該船人士稱系越南行階陳文忠、高有翼奉本國王命,駕船護送福建省故員李振青眷屬及難民來閩。道光帝接奏大為贊賞。
這種配合特別表現為越方按清廷指令協助圍捕中越海盜。
如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746年11月12日),廣東巡撫準泰奏報:江坪一帶洋面有海盜搶劫商船。自己一面加強防緝,一面會檄越南國王嚴飭查捕。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一日(1790年8月20日),廣東遂溪縣船民陳朝球船只遭劫,越南巡洋屯將范光章剿殺盜匪,奪回原船。乾隆帝為此于十月二十一日諭令軍機大臣轉知越南國王阮光平:“安南與粵東洋面毗連,遇有盜船逃竄國王境內沿海一帶,務須飭令鎮目屯將等一體嚴緝查拿。若拒捕即當剿殺,不可以中國之人略從觀望,以期綏靖海洋。國王承受恩榮更無既極,將此諭令知之。”(《高宗實錄》卷一三六)
根據大量的歷史證據,張之洞等人在談判中據理力爭,迫使法方放棄諸多無理要求,光緒十三年五月六日(1887年6月26日)簽訂的《續議界務專條》規定:“廣東界務,現經兩國勘界大臣勘定邊界之外,芒街以東及東北一帶,所有商論未定之處均歸中國管轄。至于海中各島,照兩國勘界大臣所畫紅線向南接畫,此線正過茶古社東邊山頭,即以該線為界(茶古社漢文名萬注,在芒街以南竹山西南),該線以東,海中各島歸中國,該線以西,海中九頭山(越名格多)及各小島歸越南。若有中國人民犯法逃往九頭等山,按照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和約第十七款,由法國地方官訪查嚴拿交出。”(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13頁)按此條款,中越海界緊靠越南,北部灣絕大部分、中沙、西沙、東沙皆屬中國,與越南無涉。
很快,張之洞即在邊防一線修筑工事,創設廣安水軍,布置海口設防,并親自巡視瓊州、北海、汕頭各海口,察看沿海形勢,特別派洋務局官員會同洋務學堂師生按現代測繪方法測繪詳細的粵海地圖。
三、余言
張之洞并不因爭得近海島嶼而沾沾自喜,他有更深的憂慮——防范將來越方謀占南海的遠海島嶼。
界約將簽訂前夕,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1887年4月17日),張之洞更致電總理衙門稱:“海界只可指明近岸有島洋面,與島外大洋無涉。緣大海廣闊,向非越南所能有。若明以歸越,渾言某處以南或西,則法將廣占洋面,梗多害巨,宜加限制,約明與劃分近岸有洲島處,其大海仍舊,免致影射多占。” (《兩廣總督張之洞等電》,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全集》第7冊,第5229頁)
從中可以看到,張之洞對維護南海主權有著何等深謀遠慮!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員)
責任編輯: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