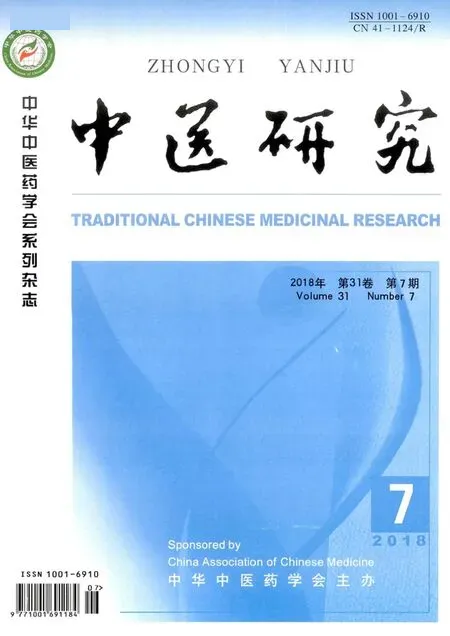李妍怡教授治療郁病臨床經驗
任宏霞,王 濤,達德玲
(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
李妍怡主任醫師為甘肅省名中醫,國家級老中醫藥專家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博士研究生導師,從事中西醫結合內科臨床、教學、科研工作 30 余年,學驗俱豐,臨床尤擅神經系統疾病的中西醫結合診療。筆者有幸隨師侍診,受益匪淺。現將李主任治療郁病經驗介紹如下。
1 郁 病
郁病又稱郁證,《中醫百病名源流·郁》曰:“郁之為言, 抑郁也。抑郁,閉塞不通之謂也。”并指出郁作為病名至少有2種基本含義,即“五氣之郁”和“七情之郁”。是以心情抑郁、情緒不寧、胸部滿悶、胸脅脹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異物梗塞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證[1]。中醫學郁病的概念比較廣泛,包括抑郁癥、神經衰弱、焦慮癥、癔病、強迫癥等精神類疾病。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家庭、事業等社會問題日益增多,人們所產生的社會心理問題越來越多,郁病的發病率逐年升高[2]。某省最新的流行病學研究報告發現:精神障礙總的現患率(最近1個月)為19.48%。各類精神障礙現患率由高到低依次為心境障礙(5.93%)、物質使用障礙(5.62%)、焦慮障礙(5.50%)、精神病性障礙(1.28%)[3]。世界衛生組織預計到2020年,郁病將可能成為繼冠心病后的世界第二大疾病負擔源[4],精神障礙和自殺傾向將持續增加[5]。本病復發率高,治愈率低,嚴重降低患者生活質量,給患者帶來巨大痛苦。西醫學在該病的治療上大多采用常規抗抑郁、抗焦慮藥物,如單胺氧化酶抑制劑、三環類抗抑郁藥、四環類抗抑郁藥、五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及其他類抗抑郁藥物,重者可加入增效劑并配合心理疏導、經顱磁刺激、電休克治療;但抗抑郁藥物治療周期長、價格較昂貴,毒副作用、成癮性大,極大地影響了臨床療效。
中醫學對郁病有系統的認識,早在《黃帝內經》就有五氣之郁的記載,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云:“五運之氣,亦復歲乎?……郁極乃發,待時而作也。”以及“郁之甚者治之奈何?……木郁達之,火郁發之,土郁奪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指出了五郁乃五運失常,引起五臟氣機不暢,郁滯不能疏泄,從而機體受病而引發各種相應病證。漢代醫家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亦認識到郁病,雖未出現郁證病名,卻以“百合病”“臟躁”和“梅核氣”等病癥之名提及,并記載了其癥狀及證候之特點,如《金匱要略·百合孤惑陰陽毒》曰:“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三因篇》記載:“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臟腑郁發,外形于肢體,為內所因。”《雜病源流犀燭》曰:“諸郁,臟器病也,其原本于思慮過深,更兼臟氣弱,故六郁之病生焉。”說明氣機郁滯,臟氣衰弱是本病發生的內在原因。元代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六郁》云:“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佛郁,諸病生焉。故人生諸病,多生于郁。”強調了郁在疾病發生中的作用,認為該病的病因為“氣、濕、熱、痰、血、食”首倡“六郁”之說,并創制了越鞠丸、六郁湯等方劑。直到明代,虞摶在《黃帝內經》五氣之郁及朱丹溪六郁之說的認識基礎上總結并發揮,才在《醫學正傳·郁證》中首次提出“郁證”名稱。明清時代的醫家漸漸發現七情、六淫、飲食等相關內外因素皆可導致郁病的發生。清代葉天士對郁病的治療手段多樣,遣藥靈活,并加以心理治療。此后,許多醫者將郁證作為對以情志不舒為主要臨床表現的疾病的特指,而使其與西醫郁證的關系更為密切。中醫學認為:郁病的病機是情志所傷、肝氣郁結,導致肝失疏泄,脾失健運,心失所養,臟腑陰陽氣血失調,病位主要在肝,但可涉及心、脾、腎,病理性質在起病初期多以邪實為主,日久多為虛證或虛實夾雜。近年來,諸多醫家在中醫內科辨治郁證的基礎上,結合個人臨床經驗,從臟腑及痰濕、瘀血等方面進行辨證論治。李文雄[6]認為,郁病治療首先應調和五臟,從五臟相關進行辨證論治;王自立[7]認為,難治性郁證當從痰論治,在臨床中以黃連溫膽湯化裁治療;馬捷等[8]通過近10年資料分析,認為無論七情所傷,還是五臟失和,其最終致郁的核心病因是“瘀”,提出在辨證論治過程中,應多思“瘀”之因。中醫學認為:郁病治療當以理氣開郁、調暢氣機為原則。吳勉華[1]主編的《中醫內科學》將郁病分為:肝氣郁結證、氣郁化火證、痰氣郁結證、心神失養證、心脾兩虛證、心腎陰虛證。
2 導師經驗
導師認為:“五臟六腑皆令人郁”,郁病的發生與情志、環境、自身因素有關,而情志不暢為根本原因。《靈樞·本病論》曰:“人憂愁思慮即傷心。”《素問·靈蘭秘典論篇》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心藏神主神明,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既是一切生理活動、心理活動的主宰,又包括意識、思維、情感等生命活動外在的體現。人的精神意識和思維活動雖分屬五臟,但由心所主,心神正常,臟腑功能強健,身體健康。而神的產生,離不開血氣的充養,血是神志活動的基本物質基礎之一,《靈樞·營衛生會》記載:“血者,神氣也。”指出郁病的發生與心神失養、氣血不和有密切關系。心主血,血化神養神,心神方可敏而不惑。若心神失養,心情抑郁,氣機阻滯,血液的生成運行受阻,則發為郁病,治療當以養心安神、調和氣血為主,而非單一的活血、養血。臨證予佛手養心湯加減以養心安神、調和氣血,藥物組成:當歸 30 g,川芎20 g,丹參15 g,茯神10 g,遠志15 g,夜交藤30 g,太子參10 g,玄參 10 g,麥冬10 g,柴胡15 g,香附10 g, 甘草5 g,生地黃10 g,大棗10 g ,浮小麥30 g。方中以當歸、川芎、丹參調和氣血,補養氣血,兼以行血、活血、涼血,使氣血得補而不滯、不燥;以浮小麥甘涼并濟,益陰除煩,與茯神、夜交藤、遠志相伍以治心神失養、神志不寧;柴胡、香附行氣解郁;以太子參、玄參、麥冬滋陰清熱;生地黃清熱養血,養陰生津;甘草、大棗為甘溫質潤之品能補養心氣,益氣和中,可鼓舞氣血生長。諸藥相伍,共奏養心安神、調和氣血之效,故以“佛手養心湯”為名。
3 病案舉例
患者,女,46歲,2017年10月4日初診。主訴:情緒低落,頭暈伴失眠1年,加重2個月。刻下癥見:神志清,精神差,情緒低落,少言,不愿與人溝通,頭暈,善太息,飲食可,眠差,入睡困難,易早醒,二便調,舌暗紅,苔薄黃,脈弦。現病史:患者家屬及患者訴1年前因與他人發生爭執,生氣后出現情緒低落,頭暈伴失眠,當時未予以重視,休息后未見緩解,此后癥狀時輕時重。為緩解癥狀,遂于當地醫院(具體不詳)住院,查頭顱CT、核磁均未見明顯異常,診斷為抑郁癥,經治療(具體治療方案不詳)后好轉出院。2個月前上述癥狀加重,少言,不愿與人溝通,眠差,夜間難以入睡,睡后易醒,現為進一步明確診治,今來本院就診,門診以“抑郁狀態”收治入院。查體:神經系統檢查未見陽性體征。抑郁焦慮量表提示:中度抑郁、無焦慮。心電圖:竇性心律,大致正常心電圖。復查頭顱CT、核磁均未見明顯異常。西醫診斷:抑郁狀態。中醫診斷:郁病,證屬氣血不調,心神失養。治宜養心安神、調和氣血。方用佛手養心湯加減化裁,處方:當歸 30 g,川芎20 g,丹參15 g,茯神10 g,遠志15 g,夜交藤 30 g,太子參10 g,玄參 10 g,麥冬10 g,柴胡15 g,香附10 g,甘草5 g,生地黃10 g,大棗10 g,浮小麥30 g。6 劑,1 劑/d,水煎,早、晚 2 次分服。同時予以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四川海思科制藥有限公司生產, 批號H20153014,10片×2板),0.5片/次,2次/d(早、中),并囑患者放松心態,多與人交流。2017年10月12日,二診。患者訴情緒低落、頭暈癥狀較前減輕,睡眠較前改善,仍易早醒,近日出現鼻塞、不通氣,流涕等癥狀。追問病史,既往有鼻竇炎病史,近日因受涼出現鼻塞、流涕等癥狀。故導師在上方基礎上加辛夷10 g、蒼耳子10 g、白芷10 g,繼用7劑。2017 年 11月 22日,三診。患者訴上述癥狀明顯減輕,鼻塞、流涕消失,效不更方,守方繼進。15 d后,諸癥明顯好轉,偶有情緒低落,余無特殊不適。復查抑郁焦慮量表提示:無抑郁,無焦慮。囑患者繼續口服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半年,待癥狀完全消失后逐漸減量停藥,日常生活中應放松心態,多參與社交。
按 本例患者從癥狀、病史及相關檢查診斷為郁病,結合舌、脈象,辨證屬氣血不調、心神失養,以佛手養心湯加減調和氣血、養心安神。該方由古方佛手散合天王補心丹化裁而來,方中李妍怡主任醫師重用當歸、川芎,岷當歸為甘肅道地藥材,甘、溫,歸心、肝經,補血活血,為補血之圣藥;川芎辛、溫,歸肝、心包經,既能活血化瘀,又能行氣通滯,為血中氣藥。兩藥相伍,補而不滯,調和氣血。國醫大師張學文提出“郁病”屬于腦病的范疇[9],故在遣方用藥中導師取丹參、川芎“上行頭目”之功,為引經藥,入心腦,心腦同治。茯神、夜交藤、遠志相伍增養心安神之效。太子參、玄參、麥冬滋養心陰,此為天王補心丹的組成藥物,導師在此處取其安神養心之功,只取其法而不用其方。柴胡、香附針對本病的病因入手,行氣解郁。導師在臨證中發現,情緒低落日久,易耗傷陰血,擾亂心神,故常加甘麥大棗湯。甘麥大棗湯出自《金匱要略·臟躁》:“婦人臟燥,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該方主要用于治療臟陰不足,虛熱躁擾所致的臟躁病,臨床常用本方治療神經精神疾患,如神經衰弱、癔病、更年期綜合征、精神分裂等;還可用于治療小兒盜汗、夜啼、厭食等兒科疾病[10]。導師在臨床疾病的診療中堅持中西醫結合,對于病程長,病情重者,常配合西藥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抗抑郁治療,成人:1片,2次/d(囑其早、中服用)。老年人:早晨服1片即可。囑其按時服藥,定期復診,在醫師指導下減量。
4 小 結
李妍怡教授在充分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郁病氣血不調、心神失養的常見臨床表現及其治法。指出郁病之所以形成氣血不調、心神失養證,其原因在于患者長期情志不遂,勞逸過度、先天遺傳稟賦不足等所致。本病虛實夾雜,在臨床診治中要因人而異,辨證論治。在用藥時靈活掌握補虛泄實的進退,補血而不忘行氣,常獲良效。同時又注重患者的自我康復、心理疏導調節,此亦為其治療該病之特色。導師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發現:很多患者在早期并不把“情志不暢”作為病態表現而尋求醫療幫助,導致郁病的診療中存在的治愈率低,治療周期長,易復發等問題。希望我們每一個人能重視自己的心理問題,積極、早期尋求醫療幫助,以提高健康指數。
5 參考文獻
[1]吳勉華.中醫內科學[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351.
[2]黃潔云.抑郁癥的發病機制與治療進展[J].中國療養醫學,2013,22(3):233-235.
[3]張敬懸,盧傳華,唐濟生,等.山東省18歲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0,24(3):161.
[4]周學東,陳興寶.抑郁癥經濟負擔研究進展[J].上海醫藥,2006,27(12):539-541.
[5]HAN Y,KHODR CE,SAPRU MK,et al.A micro RNA embedded AVV alpha-synuclein genesilencing vect or for dopaminerginceurons[J].Brain Res,2011,1386(1):15-24.
[6]李文雄,林偉鵬.五臟致郁論[J].河南中醫,2015,35(10):2312-2314.
[7]蘆少敏,王煜.王自立主任醫師妙用溫膽湯治驗4則[J].新中醫,2012,44(8):231-232.
[8]馬捷,李峰,毛萌,等.從瘀論治抑郁癥的研究與思考[J].國醫論壇,2012,27(6):15.
[9]鄭永亮.國醫大師張學文辨治郁病腎虛血瘀證經驗探析[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9):4023-4025.
[10]范永升.金匱要略[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