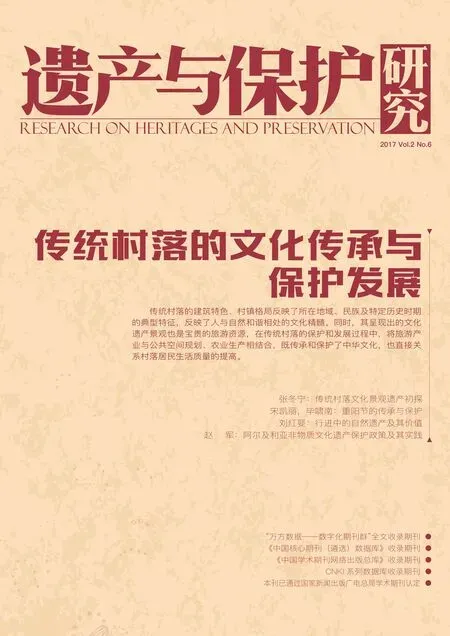考古技術在中俄首次聯合搜尋二戰時期蘇軍遺骸中的應用與前景
王 赫
(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2015年5月12日,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中俄雙方開展首次送蘇軍烈士“回家”的活動。“中俄首次聯合搜尋在中國境內犧牲的蘇軍烈士遺骸活動”的啟動儀式在牡丹江市穆棱縣下城子鎮舉行。這是中俄雙方首次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在中國境內對日作戰犧牲的、蘇軍烈士遺骸進行的搜尋行動。
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考古隊應俄方邀請,參與了本次搜尋工作。在本次搜尋工作中,搜尋隊伍成員包括來自俄方的6名檔案學、地質勘探、醫療鑒定方面的專家和11名勘探隊員,以及我校歷史文化旅游學院的9名師生。在本次搜尋活動中,考古學調查與發掘技術的運用,為搜尋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本文將對比兩國考古學技術的差異,為田野考古學技術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一點思路。
1 歷史背景與搜尋經過
1945年8月8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代表蘇聯政府正式約見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宣布從即日起,蘇聯正式對日宣戰,次日凌晨,蘇聯駐遠東部隊在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統帥下,跨過邊境線,向中國東北挺進,對盤踞東北14年之久的日本關東軍發起全面打擊,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直接促成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人類性的災難正式進入了歷史。牡丹江地區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地,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火的洗禮[1]。
蘇軍的意圖是用約58萬蘇聯紅軍從東、西、北3個方向,向中國東北縱深實施向心突擊,奪取沈陽、長春、哈爾濱、吉林等,意圖切斷關東軍與關內日軍及在朝鮮日軍的聯系。牡丹江市位于牡丹江下游,周圍黃金原煤等戰略資源富足,這里是日本關東軍駐扎的核心區域。為抵抗蘇聯紅軍的進攻,同時向東保護哈爾濱這一重要戰略防御樞紐,日本關東軍在這里集結,這一地區便成為了蘇聯紅軍進入中國東北腹地的第一道關卡。
1945年8月9日上午,蘇聯遠東第一方面軍第五集團軍跨過國境,向綏芬河發起進攻。揭開了牡丹江戰役的序幕。牡丹江戰役共包括4場戰斗,分別為綏芬河戰斗、樺木車站戰斗、挺進牡丹江和血戰東寧。戰斗異常慘烈,雙方損失慘重。火燒山位于黑龍江穆棱縣柳毛村,這是日軍為抵抗東線蘇軍設置的第二道防線。由于蘇軍的猛烈攻勢,日軍節節退敗,通信全部中斷,位于穆棱縣的關東軍因沒有接收到日本天皇投降的詔書,與蘇軍垂死抵抗。1945年8月19日,蘇聯遠東第一方面軍第五集團軍190步兵師與日關東軍124師在此展開激烈戰斗,共413名蘇軍將士陣亡于此[2]。
2012年8月,柳毛村農民劉光臨偶然在火燒山上發現一塊腿骨并進而發現4具完整遺骸。經中俄雙方學者鑒定,該4具人骨均為在火燒山戰斗中犧牲的烈士,這次發現引起了俄方學者的高度重視。
2015年5—6月中俄聯合搜尋隊在火燒山區域,通過區域系統調查方法確定墓葬位置,并運用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手段,對烈士遺骸進行提取、保存、運輸,出色完成了這一跨國合作項目。這也為今后雙方在考古學研究上的更深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 考古調查發掘方法在搜尋中的應用
在本次中俄聯合搜尋活動的搜尋隊中,俄方隊員包括檔案學、地質勘探學、醫療鑒定、野外搜尋、考古學等方面的專家,共計17人,而中方隊員主要來自黑龍江大學考古隊。在此次搜尋工作中,考古學技術的應用顯得尤為重要。由于中俄雙方的考古學在方法上存在著差異,因此使用的方式也略有不同。
2.1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
在搜尋的準備階段,俄方提供了1:10萬的地圖,是1906年繪制的。地圖中記錄了在這片土地上埋葬的第一方面軍第五集團軍190步兵師112團、58團和158團的軍官和士兵。少尉以上的單獨埋葬,少尉以下的集中埋葬。這些官兵被埋葬在32 m2的范圍內,加上年代久遠等客觀原因,搜尋的難度非常大。
搜尋隊員希望選擇一種短時間內可以對大面積區域進行搜查的方式,區域系統調查這一簡單高效的理論成為了搜尋隊員的首選。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最早起源于西方,起初目的是服務于聚落考古,并研究古代社會的系統性的抽樣調查方法。
20世紀50年代,部分西方考古學者認為僅通過類型學方式研究考古學遺存,無法反映古代社會,認為考古學應該是通過遺存研究古代社會規律,掌握人類生活的一門學科,進而促成了新考古學的誕生,區域系統調查方法應運而生。1984年,張光直先生在北京進行講座,聚落考古的模式開始進入國內考古學者的視線;1989年,嚴文明先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的考察》一文中提出聚落考古學的重要性。1990年后以北京大學為首,國內開始進行聚落考古學研究,區域系統調查方法也正式被引入中國。
區域系統調查方法在中俄聯合搜尋活動中的使用,極大地縮小了搜尋難度。通過這一具體的理論方法,搜尋隊員可以在更短的時間里搜尋更大空間,在疑似地點進行標記,之后運用探鏟確定遺跡范圍。
2.2 考古鉆探方法
考古鉆探是考古學的重要調查手段之一,是為了初步確定埋藏于地下的遺跡范圍的一種手段。主要使用探鏟向地下打孔,通過帶上來的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判斷遺存的埋藏情況。
探鏟(圖1),又稱為洛陽鏟,相傳洛陽鏟最早出現于清朝的河南洛陽地區,是盜墓賊通常使用的工具之一。20世紀20年代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衛聚賢先生親眼目睹了盜墓者使用洛陽鏟的情況,受到啟發,最早將其運用于安陽殷墟、偃師商城等古代遺址的發掘當中,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20世紀50年代,洛陽鏟經過了我國考古學者的改進后,廣泛地使用于我國的考古工作當中。
經過我國考古學者的努力,洛陽鏟的種類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多,鏟頭被分為土鏟、破磚鏟、泥沙鏟頭和筒子鏟4大類。土鏟即普通鏟頭,主要使用于大多數土壤情況下,是考古探查最常使用的工具;破磚鏟,這種鏟頭適用于土鏟因碰到較硬石塊而無法進行探測的情況;泥沙鏟,這類鏟頭適用于土質松軟的沙土地,泥沙鏟的鏟頭是在土鏟鏟頭兩側增加護翼,以解決其他鏟頭無法將沙土帶上地表的問題(圖2);筒子鏟,這是一種新興的鏟頭,適用于普通鏟頭無法帶出如水一般的泥沙而設計的。

圖1 探鏟

圖2 包曙光老師向俄羅斯學者展示探鏟使用方式
使用洛陽鏟時,身體站直,兩腿叉開,雙手握桿,置于胸前,鏟頭著地,位于二足尖間,用力向下垂直打探。開口到底,不斷將探鏟頭旋轉,四面交替下打,保持孔的圓柱形。否則探不下去,拔不上來,將探鏟卡在孔中。打的探孔要正直,正是不彎,直是不歪。打垂直孔也并不十分容易。測驗探孔的正直彎曲,可以拿電筒之類,借助光線,垂直從孔口往下照,光線射到孔底,則探孔是直的;如果光線射到孔壁下不去了,則探孔是彎的,必須修整工具后再打。打彎的探孔在拔鏟時是很費勁的,雙手拔桿時也可以將肩頭頂靠接桿借力上拔[3]。
結合區域系統調查方法,搜尋隊員在疑似區域進行拉網式打探,每10 m打一個探孔,根據土質土色對于疑似埋葬區域進行細致探查并做標記。最初,俄方搜尋隊員對于洛陽鏟的精確度存疑,仍采取打探溝的方式進行搜尋,費時費力。經過幾天的共同工作和實踐的檢驗,我們使用的洛陽鏟的準確度還是比較高的,俄方搜尋隊員也開始接受這種簡單高效的方法,并主動要求學習。這是聯合搜尋活動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兩國考古學技術交流的一個重大突破。
2.3 中俄雙方的考古學調查發掘方法對比
在遺骸埋葬地點的發掘過程中,搜尋隊員首先通過打探的方式確定墓葬位置,之后俄方隊員對墓葬區域布下1 m×1 m的方格,根據揭露情況進行擴方,同時按照發掘深度,將一定深度作為一個人為地層,進行記錄。這種發掘方式與國際上采用的考古學方法相同。
中國考古學方法分為兩種體系:舊石器發掘方式與法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的發掘方法相同,采用國際通用的發掘方法;新石器及之后的發掘方式大多數采用5 m×5 m探方進行發掘,部分大遺址采用10 m×10 m探方進行發掘。發掘方式遵循地層學的方法,按照地層進行揭露。
筆者在2016年對俄羅斯考古遺址的實地考察發現,俄羅斯的田野考古發掘遵循國際通用的考古學方法。首先,根據一定深度劃分人為地層的方式方便記錄,由于俄羅斯緯度較高,地層的土質土色較難區分,利用這種方式有利于在不易區分地層的情況下出土遺物遺跡的記錄,也方便之后的修正。其次,采用1 m×1 m的小規格探方更加便捷,對于已經確定了位置的遺跡,發掘可以減少很多無用做功。最后,保留遺物下方埋藏介質的方式,可以更直觀地看到遺物出土的位置關系,利于發現其內在規律。
相比較我國的考古學技術,從調查、發掘到整理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完整的程序。各類遺跡的發掘方式,包括不同時期的發掘方式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并隨著科技的發展,各種高科技產品已廣泛應用于考古發掘工作中,如無人機航拍,全站儀、RTK精準測量,CAD繪圖,3D建模等,中國的考古學技術越來越規范化、科學化、先進化,我們的考古學已經邁向了世界一流水平。但是一個學科的發展不能僅僅停滯于自己的小圈子當中,需要有國際大視野,與其他文化進行比較,相互學習,尋求共同提高。中俄兩國的考古學技術手段各自存在優缺點,只有相互取長補短才能尋求考古學更高層次的發展。2.4 考古學調查發掘技術在搜尋工作中的重要性
在本次聯合搜尋活動中,考古學技術手段成為搜尋工作的強大助臂。實踐證明,考古學發掘方法已不僅僅局限于考古這個小框架當中,而是有了廣闊的使用空間。首先區域系統調查與考古探測相結合,短時間內對大面積區域進行調查,真實地還原該區域的地層情況。這對于搜尋工作是至關重要的。一般的搜尋工作由于時間、人力資源有限,無法對大面積的區域進行短期高效的調查,區域系統調查與考古探測的加入,完美地解決了這一難題,為搜尋工作節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其次,考古發掘方法的引入,為本次搜尋提供了強大的后期保障。一般來說,與本次搜尋性質類似的活動中,會出現因沒有科學完整的體系,且由于工作人員不細致而破壞遺物的情況。作為考古挖掘則此情形絕不允許發生,由于考古工作的性質決定,考古發掘工作對于人骨的提取、保存、運輸等有一系列完整的流程,這正是搜尋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3 聯合搜尋工作成果
搜尋成果如圖3所示,在為期一個月的搜尋工作中,中俄聯合搜尋隊走遍了火燒山及其周圍32 m2的所有區域。共發現了5具有確切名字的蘇軍烈士遺骸。另外還發現了至少3具蘇軍無名烈士的殘骸,僅發現幾段肢骨而無頭骨。除此之外,還搜尋到蘇軍使用的鋼盔、彈片、槍架、子彈、衣物殘片和勺子等近50件遺物。這些遺物與烈士遺骸一并移交給穆棱市外事辦和民政局。

圖3 搜尋到人骨與部分遺物
4 總結
本次聯合考古搜尋活動,共歷時1個月,順利地完成了既定任務,讓長眠于此的蘇軍烈士回家。同時兩國學者相互交流,令我們看到了考古學調查與發掘技術發展的廣闊前景。
俄羅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陶米恒說:“這具有里程碑意義,怎么形容都不過分。”正如所言,在這次聯合搜尋活動當中,考古學技術手段大放異彩,為考古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時代在進步,一門學科也應該順應時代而發展,不應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當中,而這次活動正好為考古學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考古學技術的發展,同樣也會帶動其他學科的進步,考古學從今以后不再是遙不可及的,而是可以實實在在為民眾服務的。
其次,這次活動促進了兩國考古學者的密切交流,學科在交流中發展,兩國學者取長補短,相互借鑒,這對于考古學這一學科的發展時至關重要。經過這次合作,中俄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2016年我校考古隊應俄方邀請,赴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對伊萬諾夫卡河口墓地遺址進行共同發掘,進行更深入地交流。正如俄羅斯學者杰尼斯.沃爾科夫所言:“俄國人用左眼看阿穆爾河,中國人用右眼看黑龍江,現在可以自豪地說,我們可睜開雙眼共同開拓這片考古研究圣地,過去的一小步如今已經成為一大步,愿我們的合作如奔騰流逝的黑龍江水,滾滾向前,不斷開拓進取,勇攀高峰”。
最后,合作與交流是這個時代的主題,相信通過這次合作,中俄雙方已經敞開了合作的大門,未來兩國的考古學事業一定會在合作中更加輝煌。
[1]孫曉,陳志斌.東方的落日:蘇聯緊急出兵中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125.
[2]蘇亮.血戰牡丹江:日本軍國主義的“滑鐵盧”[J].安徽文學月刊,2008(9):251-253.
[3]洪昀,王輝.洛陽鏟在取土場勘探中的應用[J].工程與建設, 2014 (3):32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