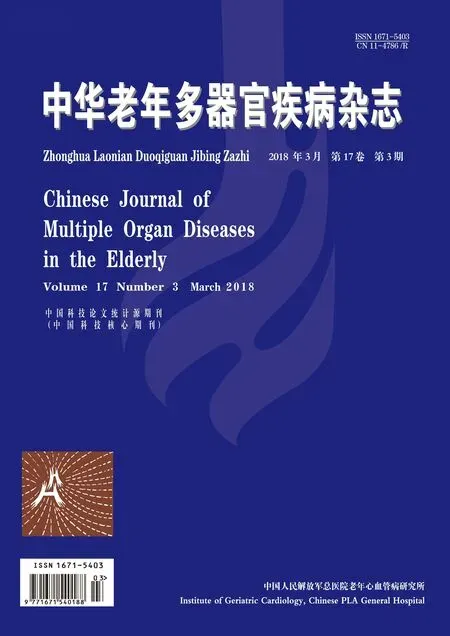夜間哮喘發病機制及特殊治療的研究進展
金琳羚,張希龍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南京 210029)
夜間哮喘是發病率較高的一種哮喘類型,約占哮喘總患者的2/3[1]。夜間哮喘的急性發作可導致患者睡眠質量下降,表現為入睡困難及睡眠時間縮短,其中多達一半的患者可出現白天困倦并影響生活質量[2]。此外,夜間哮喘的急性發作使哮喘癥狀更難控制,不僅增加了藥物的使用量,也增加了哮喘的死亡率[3]。由此可見,夜間哮喘是一種潛在的、可致命性的哮喘類型,需要提高對其認識并尋求相應的治療方案。
1 夜間哮喘的發生機制
與正常人相比,哮喘患者的夜間呼氣流速峰值較白天明顯下降。夜間哮喘患者在夜間清醒時和睡眠時的下氣道阻力均會增加,且夜間睡眠時下氣道阻力增加更明顯。人體睡眠階段的多種因素均可以引起夜間肺呼氣流速下降、下氣道阻力增加,從而導致哮喘發作[4]。現將可能導致夜間哮喘發生的機制總結如下。
1.1 氣道副交感神經活性的改變
睡眠是一種在哺乳動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休息狀態。正常人體的肺功能在睡眠階段有所下降,主要表現為肺容量降低、功能殘氣量降低、血氧含量降低及呼吸道阻力增加等。位于脊髓左側核中的迷走神經節前神經元(airway-related vagal preganglionic neurons,AVPNs)以及迷走神經背側運動核中的神經元在睡眠時調節氣道副交感神經活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5]。AVPNs與氣管支氣管神經節的節后神經元共同支配調節氣道平滑肌、黏液腺和血管的相關活性,促覺醒系統中藍斑核和副藍斑核神經元釋放的去甲腎上腺素能介質可抑制AVPNs的活性,同時這些促覺醒中心又能被下丘腦催眠神經元抑制[6]。夜間睡覺時腎上腺素能神經緊張性減退使AVPNs抑制作用解除、氣道副交感神經活性增強,促進呼吸道黏膜腺體分泌、支氣管血流及下呼吸道阻力增加[5]。
1.2 氣道反應性的增加及氣道平滑肌的收縮
睡眠時肺容量的下降可導致氣道阻力的增加。正常人在深吸氣或嘆息動作停止時氣道反應性迅速增加,然而在乙酰膽堿激發前的深吸氣動作可降低支氣管的收縮,使用氣道平滑肌的肌動蛋白-肌球蛋白偶聯理論可以解釋上述現象。這一理論認為肺充氣過程是一種機械性的拉伸,會傳遞到肌球蛋白的末端使其與肌動蛋白纖維分離,從而破壞肌動蛋白-肌球蛋白偶聯降低氣道平滑肌的收縮力。睡眠時偶爾出現的深吸氣和嘆息動作,能增加肌動蛋白-肌球蛋白的結合,收縮支氣管,從而導致夜間哮喘的發生[7]。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哮喘患者體內還存在氣道平滑肌的遷移,這種遷移能促使細胞增生、增加氣道平滑肌群數量、加速氣道重構,最終導致哮喘的發生[8]。在哮喘患者中氣道的慢性炎癥可引起周圍支氣管壁增厚,這種增厚不僅能降低氣道平滑肌的順應性還能進一步增加支氣管的收縮力[9]。
1.3 晝夜節律的變化及生物鐘基因的影響
夜間哮喘的加重及哮喘患者清晨死亡率的增加可能與機體本身的晝夜節律變化有關[10]。人體中一些神經激素水平呈晝夜節律變化,其中血漿皮質醇濃度在清晨醒來時達峰值,凌晨降至谷值。腎上腺素水平也呈現24 h周期性變化,在下午達到峰值,凌晨降到谷值。哮喘患者因受睡眠的不利因素影響,在睡眠過程中會出現呼氣流速峰值的急劇減弱和氣道阻力的增加。非腎上腺素能、非膽堿能神經系統的晝夜節律改變也可導致夜間氣道功能的改變。夜間哮喘患者氣道白細胞、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的計數水平在清晨較下午較高,這與夜間呼氣氣流的下降有關[11]。
在下丘腦視交叉上核和外周器官中生物鐘基因表現活躍,這些基因在特定轉錄因子的作用下由復雜的轉錄-翻譯反饋回路組成,能調節多達10%的細胞轉錄因子的表達[12]。雖然嚙齒類動物模型中能觀察到夜間哮喘與生物鐘基因功能的關系,但吸入性糖皮質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或β2-腎上腺素受體(beta 2-adrenergic receptor,β2-AR)激動劑易對人類的生物鐘基因產生影響。一項針對人支氣管上皮細胞生物鐘基因mRNA表達的在體、離體研究表明[13],ICS或β2-AR激動劑能誘導人體Per1 mRNA的表達,這也是一種重要的生物鐘基因。此外,Sundar等[14]亦發現,多種免疫炎性細胞對分子生物鐘具有調控作用。這項發現不僅提示免疫炎性細胞可作為預測哮喘炎癥程度的生物標志物,也為夜間哮喘的有效治療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1.4 睡眠相關的外源性因素影響
冷空氣的吸入、過敏原的接觸、毒物或微生物菌群的聚集[15]、仰臥位及睡眠狀態等均能引起夜間哮喘的發生,但去除這些外源性因素并不能完全緩解夜間哮喘的癥狀。例如,夜間冷空氣的吸入及體溫的降低被認為可引發夜間哮喘,然而即使將溫度和濕度保持在白天水平,夜間呼氣流量依然會出現下降;床上用品中的過敏原能誘發夜間哮喘,但避免接觸這些過敏原并不能緩解患者夜間支氣管的收縮[16]。
1.5 β2-AR的多態性
吸入性β2-AR激動劑是治療哮喘急性發作的重要方法。人類β2-AR基因的遺傳多態性,尤其是16、27位基因型的改變可導致受體功能的不同。β2-AR由于基因突變可導致16位精氨酸(arginine,Arg)替換為甘氨酸(glycine,Gly),27位谷氨酰胺(glutamine,Gln)替換為谷氨酸(glutamic,Glu)。多項研究調查了β2-AR多態性與夜間哮喘的關系。一項針對中國國民的研究顯示[17],β2-AR的16位點的多態性與夜間哮喘的發生密切相關。在定位誘變和重組表達研究中發現,β2-AR的16位點上的突變(Arg突變為Gly)能增強激動劑所促發的受體下調,由此推測Gly16可能與夜間哮喘的β2-AR下調有關,是夜間哮喘的重要遺傳因素。
1.6 共患疾病的影響
1.6.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 哮喘患者常伴有嚴重的打鼾及白天嗜睡現象,在排除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及年齡等相關因素后,重度哮喘的人群中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的患病率高于中度哮喘人群[18]。多種機制可以解釋哮喘與OSAHS之間的相關性[19]。(1)OSAHS患者睡眠時氣道相對狹窄使得氣道阻力及胸腔負壓,增加并刺激迷走神經張力升高導致夜間哮喘的發作;(2)OSAHS患者睡眠時發生的呼吸暫停可刺激喉及聲門處的神經受體,引起強烈的支氣管收縮導致哮喘發作;(3)OSAHS患者睡眠時常伴隨低氧血癥,可通過刺激頸動脈體反射性誘發支氣管收縮,導致哮喘發作。OSAHS還能引起對全身和上氣道炎癥都有影響的促炎狀態產生,這種促炎狀態可促進哮喘發生[20]。具有促炎特性的瘦素在OSAHS中會升高,能增加過敏原誘導的支氣管收縮,而針對OSAHS的持續正壓通氣(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治療可降低體內的瘦素和其他促炎因子的水平[21]。
1.6.2 胃食管反流 胃食管反流(gastroesophageal reflux,GER),尤其是夜行性GER,與多種呼吸系統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22]。Mastronarde等[23]對2600例哮喘未控制的成年人進行食道pH值監測,發現40%的受檢查者同時患有GER。GER能引發夜間哮喘的機制與神經原性炎癥及微吸入有關[24]。非胃酸(如膽汁)反流可能在哮喘的發生中也起到一定作用,但這一現象及相關機制尚缺乏試驗研究[25]。
2 夜間哮喘的特殊治療——時間療法
生理節律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生物系統的影響引出了時間療法的概念[26]。根據疾病本身特點并結合相應的藥理學知識調整給藥時間、劑量及方式,確保能在夜間達到最大效果的治療方案,即為夜間哮喘的時間療法[27]。這種根據人體晝夜節律變化規律而制定的特殊治療方法,能大大提高藥物的有效性及患者的依從性[28]。ICS是治療哮喘的基石,鑒于一些ICS制劑在肺內能較長時間滯留,睡前用藥成為控制夜間哮喘的理想用藥時間。研究證實,1次/d(下午)與2次/d吸入ICS相比,療效相當、應用方便,夜間可達到最大效果,且對腎上腺抑制無明顯差異[29]。同理,睡前使用緩釋型β2-AR激動劑可改善清晨支氣管的收縮。日本研發了一種經皮給藥的β2-AR激動劑,這種制劑在睡前使用能有效改善夜間哮喘癥狀[30]。哮喘臨床研究中心的一組數據顯示,低劑量的氨茶堿較孟魯司特納及安慰劑能更有效地控制夜間哮喘癥狀及減少清晨肺功能下降,且因其價格便宜,可作為控制夜間哮喘癥狀的理想選擇[31]。Ranjan等[32]在上述時間療法的基礎上設計出一種滲透控制脈沖釋放膠囊,可在一個預定的釋放期后短時間內持續釋放一定量的藥物,延長了藥物的作用時間,提高了藥物利用率,在預防特定時間哮喘的發作及相關過敏性鼻炎的治療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夜間睡眠階段是人體呼吸系統功能下降的時期,易導致夜間哮喘的急性發作。進一步探求夜間哮喘的發病機制,在治療上根據哮喘的夜間變化規律,調整相應的給藥時間、劑量及方式具有重要臨床價值。目前對生物鐘基因及晝夜節律機制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今后可進一步探討這些生物鐘基因及其產物是如何調控夜間哮喘特定分子通路的,以及探尋晝夜節律失調在其他共患疾病中的作用,通過尋找恢復和防止晝夜節律紊亂的方法進一步控制夜間哮喘的發作。
[1] Raherison C, Abouelfath A, Le Gros V,etal. Underdiagnosis of nocturnal symptoms in asthma in general practice[J]. J Asthma, 2006, 43(3): 199-202. DOI: 10.1080/02770900600566744.
[2] Sanz de Burgoa V, Rejas J, Ojeda P,etal. Self-perceived sleep quality and quantity in adults with asthma: findings from the Coste Asma Study[J]. J Investig Allergol Clin Immunol, 2016, 26(4): 256-262. DOI: 10.18176/jiaci.0044.
[3] Braido F, Baiardini I, Ghiglione V,etal. Sleep disturbances and asthma control: a real life study[J]. Asian Pac J Allergy Immunol, 2009, 27(1): 27-33.
[4] Bjermer L. The role of small airway disease in asthma[J]. Curr Opin Pulm Med, 2014, 20(1): 23-30. DOI: 10.1097/MCP.0000000000000018.
[5] Haxhiu MA, Kc P, Balan KV,etal. Modeling of sleep-induced changes in airway function: implication for nocturnal worsening of bronchial asthma[J]. Adv Exp Med Biol, 2008, 605: 469-474. DOI: 10.1007/978-0-387-73693-8_82.
[6] Saper CB, Chou TC, Scammell TE. The sleep switch: hypo-thalamic control of sleep and wakefulness[J]. Trends Neurosci, 2001, 24(12): 726-731.
[7] Morrison JF, Pearson SB, Dean HG.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in nocturnal asthma[J]. Br Med J (Clin Res Ed), 1988, 296(6634): 1427-1429.
[8] Salter B, Pray C, Radford K,etal. Regulation of human airway smooth muscle cell migration and relevance to asthma[J]. Respir Res, 2017, 18(1): 156. DOI: 10.1186/s12931-017-0640-8.
[9] Fredberg JJ. Frozen objects: small airways, big breaths, and asthma[J].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0, 106(4): 615-624. DOI: 10.1067/mai.2000.109429.
[10] Sundar IK, Yao H, Sellix MT,etal. Circadian clock-coupled lung cellular and molecular functions in chronic airway diseases[J]. 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 2015, 53(3): 285-290. DOI: 10.1165/rcmb.2014-0476TR.
[11] Zhang XY, Simpson JL, Powell H,etal. Full blood count para-meters for the detection of asthma inflammatory phenotypes[J]. Clin Exp Allergy, 2014, 44(9): 1137-1145. DOI: 10.1111/cea.12345.
[12] Durrington HJ, Farrow SN, Loudon AS,etal. The circadian clock and asthma[J]. Thorax, 2014, 69(1): 90-92. DOI: 10.1136/thoraxjnl-2013-203482.
[13] Vasalou C, Herzog ED, Henson MA. Multicellular model for intercellular synchronization in circadian neural networks[J]. Biophys J, 2011, 101(1): 12-20. DOI: 10.1016/j.bpj.2011.04.051.
[14] Sundar IK, Yao H, Sellix MT,etal. Circadian molecular clock in lung pathophysiology[J]. 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15, 309(10): L1056-L1075. DOI: 10.1152/ajplung. 00152.2015.
[15] Noval Rivas M, Crother TR, Arditi M. The microbiome in asthma[J]. Curr Opin Pediatr, 2016, 28(6): 764-771. DOI: 10.1016/j.jaci.2014.11.011.
[16] Woodcock A, Forster L, Matthews E,etal. Control of exposure to mite allergen and allergen-impermeable bed covers for adults with asthma[J]. N Engl J Med, 2003, 349(3): 225-236. DOI: 10.1056/NEJMoa023175.
[17] Yin K, Zhang X, Qiu Y. Association between beta 2-adrenergic receptor genetic polymorphisms and nocturnal asthmatic patients of Chinese Han nationality[J]. Respiration, 2006, 73(4): 464-467. DOI: 10.1159/000089819.
[18] Julien JY, Martin JG, Ernst P,etal. Prevalence of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in severeversusmoderate asthma[J].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09, 124(2): 371-376. DOI: 10.1016/j.jaci. 2009.05.016.
[19] 陳佳娣, 張希龍, 孫培莉. 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與哮喘[J]. 中華老年多器官疾病雜志, 2017, 16(4): 304-307. DOI: 10.11915/j.issn.1671-5403.2017.04.071.
Chen JD, Zhang XL, Sun PL.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 and asthma[J]. Chin J Mult Organ Dis Elderly, 2017, 16(4): 304-307. DOI: 10.11915/j.issn.1671-5403.2017.04.071.
[20] Ryan S, Taylor C, McNicholas WT. Predictors of elevated nuclear factor-kappa B-dependent genes in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6, 174(7): 824-830. DOI: 10.1164/rccm.200601-066OC.
[21] Wong CK, Cheung PF, Lam CW. Leptin-mediated cytokine release and migration of eosinophils: implications for immunopathophysiology of allergic inflammation[J]. Eur J Immunol, 2007, 37(8): 2337-2348. DOI: 10.1002/eji.200636866.
[22] Emilsson ?I, Benediktsdóttir B,lafsson,etal. Definition of nocturnal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for studies on respiratory diseases[J]. Scand J Gastroenterol, 2016, 51(5): 524-530. DOI: 10.3109/00365521.
[23]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Asthma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Mastronarde JG, Anthonisen NR,etal. Efficacy of esomeprazole for treatment of poorly controlled asthma[J]. N Engl J Med, 2009, 360(15): 1487-1499. DOI: 10.1056/NEJMoa0806290.
[24] Solidoro P, Patrucco F, Fagoonee S,etal. Asthma and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a multidisciplinary point of view[J]. Minerva Med, 2017, 108(4): 350-356. DOI: 10.23736/S0026-4806.17.05181-3.
[25] Asano K, Suzuki H. Silent acid reflux and asthma control[J]. N Engl J Med, 2009, 360(15): 1551-1553. DOI: 10.1056/NEJMe0900117.
[26] Tran TH, Lee BJ. On-off pulsed oral drug-delivery systems: a possible tool for drug delivery in chronotherapy[J]. Ther Deliv, 2011, 2(9): 1199-1214.
[27] Burioka N. Chronotherapy of bronchial asthma[J]. Nihon Rinsho, 2013, 71(12): 2146-2152.
[28] Nainwal N. Chronotherapeutics — a chronopharmaceutical approach to drug delivery i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J]. J Control Release, 2012, 163(3): 353-360. DOI: 10.1016/j.jconrel.2012.09.012.
[29] Thorsson L, K?llén A.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assessment of the systemic activity of budesonide when given once or twice dailyviaTurbubaler[J]. Eur J Clin Pharmacol, 2000, 56(3): 207-210.
[30] Burioka N, Fukuoka Y, Koyanagi S,etal. Asthma: chrono-pharmacotherapy and the molecular clock[J]. Adv Drug Deliv Rev, 2010, 62(9-10): 946-955. DOI: 10.1016/j.addr.2010.03.012.
[31] 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Asthma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s. Clinical trial of low-dose theophylline and montelukast in patients with poorly controlled asthma[J].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7, 175(3): 235-242. DOI: 10.1164/rccm.200603-416OC.
[32] Ranjan P, Nayak UY, Reddy MS,etal. Osmotically controlled pulsatile release capsule of montelukast sodium for chronotherapy: statistical optimization,invitroandinvivoevaluation[J]. Drug Deliv, 2014, 21(7): 509-518. DOI: 10.3109/10717544.2013.853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