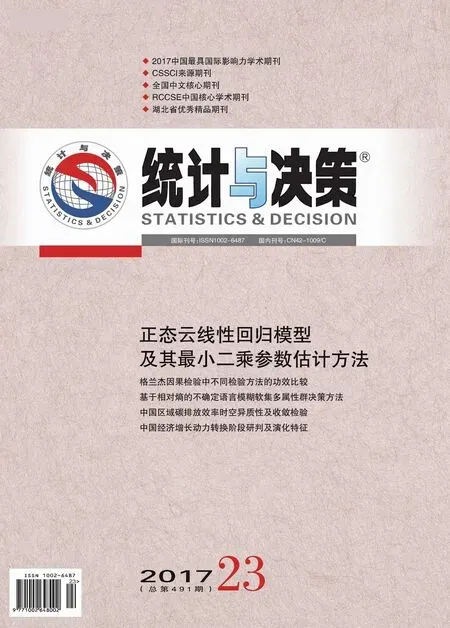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統計檢驗
董志華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金融學院,武漢 430073)
0 引言
人力資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Schultz(1961)[1]提出,他認為人力資本是體現在人身上的資本,是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能和綜合能力,是勞動者素質的體現。人力資本作為主要的生產要素,是技術創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源泉,其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作用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國經濟在過去三十多年間高速增長,人力資本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動力[2]。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階段,經濟增速整體放緩,增長方式從傳統的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人力資本將是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動力。所以,在當前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背景下,準確測算人力資本存量,研究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國內的學者對人力資本推動我國的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和機制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其焦點問題是如何測算人力資本。由于使用的測算方法不同,相應的結論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常見的測算人力資本存量的方法主要有特征法、成本法、勞動收入法和J-F終身收入法。
特征法,即采用受教育年限或其他教育相關指標如識字率作為衡量人力資本存量的方法[3]。但僅使用受教育年限等指標來刻畫人力資本的方法忽視了工作經驗、健康以及生命周期等影響人力資本的重要因素,并不能準確衡量人力資本的真實水平。成本法采用永續盤存的思路,將人力資本分為有形與無形人力資本[4]。但學者們對投資具體包含的項目和折舊率等問題上看法不一,且這一方法對數據要求較高,以我國為例,需要用到90年前的統計數據來進行相關計算。所以,成本法并不太適宜在我國使用。勞動收入法將沒有工作經驗的勞動者(簡單工人)的工資作為衡量人力資本的基本單位,全社會勞動收入總和除以簡單工人工資的結果就是全社會人力資本總量。由于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簡單工人工資受多方面因素影響,所以使用該方法測算的人力資本結果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缺乏可比性。
終身收入法最早由 Jorgenson 和 Fraumeni(1989)[5]提出,也稱J-F終身收入法。其基本思路是假定個體能像物質資本一樣在市場上交易,其價格即為該個體預期未來終身勞動收入的貼現值。相較于勞動收入法,該方法使用終身收入而不是當前收入來度量人力資本,能更準確合理地反映出教育、健康等長期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另一方面,J-F終身收入法已被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所采用,使用該方法對我國人力資本進行測算,有利于進行人力資本的跨國比較[6]。但由于需要龐大而多樣的數據、估計工作量大和參數選擇復雜等原因,使用該方法對我國的人力資本進行全面測算的工作一直鮮有人嘗試。直到2009年,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的“中國人力資本的測量及人力資本指標體系的構建”項目開始著手使用J-F終身收入法系統測算我國人力資本,并將結果發布在年度報告中,該報告提供了國家和省級層面的人力資本估算結果,這對定量把握我國人力資本總體狀況,深入探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了極大的支持。
本文旨在利用《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報告2016》(下稱《報告》)中最新的中國人力資本指數數據(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報告2016》,http://humancapital.cufe.edu.cn/rlzbzsxm/zgrlzbzsxm2016.ht?ml.),基于擴展的索洛模型,探討人力資本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的影響
1 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分析
1.1 中國人力資本指數簡介
《報告》中計算的中國人力資本指數采用修正后的J-F終生收入法,其核心思想是以個人預期生命期的終生收入的現值來衡量其人力資本。通過生存率、升學率和就業率來估計預期未來收入。在估算未來的收入時,該方法考慮到了勞動收入增長率和折現率,并假設二者是不變的。采用倒推的方式,利用退休年齡60歲人口的終生收入計算59歲人口的終生收入,再計算58歲,以此類推,一直計算到0歲。對于因在校而沒有參加工作的學生人群,計算的是其畢業后的預期終生收入。《報告》既估算了1985—2014年間我國國家和省級層面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均人力資本存量、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以及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存量,也分別考察了包括城鎮和農村以及不同性別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其中,人力資本總量涵蓋了女性0~55歲人口,男性0~60歲人口;勞動力人力資本涵蓋了16歲及以上,不包括學生的非退休人口。
1.2 中國人力資本指數比較分析
為了比較不同測算方法,分別選取各類方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測算結果。J-F終身收入法選取《報告》中的全國勞動力人力資本總量;勞動收入法選取梁潤等(2015)[7]的測算結果;成本法選取焦斌龍等(2010)[8]測算結果;特征法選取最常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數據來源于《報告》。GDP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1985年為不變價計算。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各類測算方法的理論基礎存在較大區別,所以得到的結果在數值上并無太大的可比性,本文關注的只是各類測算方法結果的相對變化趨勢以及其同GDP變化趨勢的比較特征。

圖1 人力資本存量對數圖

圖2 人力資本存量對數差分圖
為便于觀察,圖1給出了按四種方法測算的我國人力資本存量結果的對數值時間序列圖。可以看到,按J-F終身收入法計算的中國人力資本指數的變化趨勢,與按成本法和勞動收入法計算的結果較為一致,它們與GDP對數的變化趨勢也基本相似。按教育年限特征法測算的人力資本變化趨勢較GDP變動則顯得相對平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在1994年前后發生較大的波動,這與其他的數據表現出較大的差異,相關的研究將其解釋為1994年前后我國經濟結構性的變化[9]。由于本文討論的重點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所以有必要考察人力資本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關系。圖2給出了按各類方法測算的人力資本存量結果的對數差分值。為便于比較,對GDP對數差分和中國人力資本報告數據的對數差分做了適當的平移處理。可以發現,與GDP增長曲線相比,按照梁潤(2015)[7]、焦斌龍等(2010)[8]和教育年限測算的人力資本的增長率曲線相對平穩,按照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6)計算的人力資本的增長曲線波動較大,雖然其與GDP增長率變動趨勢不完全一致,但通過簡單圖形分析可以推測按J-F終身法測算的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
2 模型構建和數據來源
2.1 模型構建
為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從最簡單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D生產函數)出發:

其中A為綜合技術水平,Y、K、L分別表示總產出、物質資本存量與勞動力數量,α、β分別為物質資本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投資、知識累積影響著物質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形成,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在生產模型中,對勞動投入的測算不宜簡單地使用勞動力的數量,而是應該使用能夠體現勞動力生產效率差異的人力資本。因此,出現了一類具有C-D生產函數形式的有效勞動模型:

其中H表示人力資本存量,β表示人力資本產出彈性。而Mankiw等(1992)[10]提出的擴展的索洛模型則將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勞動力一樣視作投入要素。具體表現形式為包含三要素的生產函數模型:

其中,α、β、γ分別表示物質資本K、勞動力L和人力資本H的產出彈性。如前文所述,在實證研究中,人力資本經常用不含總量因素的平均教育年限表示。為便于比較,在使用中國人力資本指數時,應剔除勞動力總量因素。所以,本文使用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來分析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體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Ait表示i省在t時的技術水平,Yit表示i省在t時的總產出,用各省GDP衡量。Kit、Lit、hit分別表示i省在t時的物質資本存量、勞動力數量和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α、β、γ為相對應的產出彈性,εit為隨機誤差項。取對數的目的在于避免宏觀經濟變量中常見的異方差問題。
2.2 數據來源
各省GDP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1985年為不變價計算。物質資本存量按照張軍等(2004)[11]所使用的永續盤存的方法,利用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構建物質資本存量時間序列,以1985年為基期,折舊率取10%。勞動力人口數、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數據來源于《報告》,勞動力定義為16歲及以上,不包括學生的非退休人口數量。另外,作為比較,除了使用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在估計式(4)時,本文還報告了當使用勞動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資本時的估計結果,平均教育年限數據來源于《報告》。
3 實證分析
本文首先比較傳統生產函數模型(1)與有效勞動生產函數模型(2)的估計結果。表1中(a)列和(b)列是使用混合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b)列中的人力資本比(a)列中的勞動力具有更高的產出彈性;當使用人力資本作為有效勞動投入時,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有所下降。這與Li等(2014)[12]的結論是一致的。另外,比較Adjusted R-Squared值可以發現人力資本比勞動力對經濟增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其次,本文對面板模型進行了F-檢驗和H-檢驗,結果顯示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比混合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更為合理,(c)列和(d)列報告了個體固定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仍高于勞動力。另外,(d)列中各個要素的估計系數表現出了生產函數的不變報酬性質。然后,本文對(4)進行了估計,分別使用《報告》中的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指標。在使用混合面板模型時,(e)列中lnh的估計系數略高于(f)列中lne的估計系數,但在個體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中,(g)列中lnh的估計系數小于(h)列中lne的估計系數,在使用不同的方法衡量人力資本時,特征法的平均教育年限比收入法的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具有更高的產出彈性。但這并不表示教育年限比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好的解釋能力。按照中國人力資本指數的計算過程,教育年限是指數核算的重要考量因素。實際上,人力資本指數包含了除教育之外更多的因素,如健康、工作經驗等。本文認為,由于測算的理論基礎不同,按不同方法衡量的人力資本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只是在實證分析中存在估計系數上的差異。這里的比較分析說明,教育水平作為人力資本的主要表征形式,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表1 估計結果
另外,本文發現在(e)列和(g)列中,勞動力數量的產出彈性都略高于人力資本產出彈性,說明在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勞動力人口數量帶來的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重要源動力。一些研究認為,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13]。為驗證這一觀點,本文分2000年之前和之后分別對式(4)進行估計,結果報告在表2中。可以發現,在使用教育年限作為衡量人力資本指標時,2000年之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且相對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占主導地位;在2000年之后,教育對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這與我們通常認為的教育對經濟影響力正逐步增強的觀點不符。然而,在使用中國人力資本指數中的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進行估計時,卻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果。結果顯示,2000年之前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為負且不顯著,但是物質資本與勞動力數量的估計系數顯著,說明在過去三十年間,前半階段中國經濟主要靠大量的物質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數量快速增加在驅動;在2000年之后,勞動力的估計系數不顯著,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后半階段,中國經濟主要靠人力資本驅動。模型中的人力資本剔除了總量的因素,所以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并非簡單的勞動力人口數量增加。

表2 2000年前后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程度比較
李海錚(2013)[9]基于中國人力資本指數的研究表明,我國人力資本的區域差異明顯,發達地區的人力資本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且差距呈進一步擴大趨勢,人力資本的地區差異會導致區域經濟增長的差異。本文對31個省(市、自治區)按東、中、西三個區域分別估計了式(4)。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由于中部與西部的估計結果近似,表3中只報告了東部與中西部的估計結果。可以發現,東部地區的人均人力資本產出彈性明顯高于西部地區;在東部地區,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明顯高于勞動力數量,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質”而非“量”,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量”而非“質”來體現。本文還分2000年前后對東部和中西部分別對式(4)進行估計,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2000年前后的時間差異、東部與中西部的區域差異與表2和表3所顯示的結論一致。

表3 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區域比較
4 結論
基于《中國人力資本指數報告2016》,本文比較了根據特征法、成本法、勞動收入法和按照《報告》中J-F終身收入法測算的中國人力資本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人力資本指數反映出的人力資本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并未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但相對于較為平穩的教育年限增長率,人力資本指數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可能更具解釋力。利用《報告》中的人力資本指數數據,實證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1)相較于勞動力人口數量,包含“質”和“量”雙重因素的人力資本具有更高的產出彈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顯著;(2)在使用中國人力資本指數中的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衡量人力資本的“質”時,與勞動力人口數量相比,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別并不明顯。但分時段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三十年間的前半段,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量”來體現,“質”的效應則不顯著,但在后半段,人力資本“質”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明顯,這與我國在目前經濟轉型階段提出的由要素驅動轉移到創新驅動的基本策略是一致的;(3)從地區差異來看,人力資本的“質”在東部地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比“量”更為顯著,在中西部地區卻正好相反。相對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變得越來越重要,由人力資本差距導致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問題日益顯著。
[1]Schultz T.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
[2]Fleisher,et al.Human Capital,Economic Growth,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92(2).
[3]楊曉智.金融發展、人力資本的耦合機制與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5(1).
[4]Kendrick W,Lethem Y,Rowley E.The Formation and Stocks of Total Capital[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6.
[5]Jorgenson W,Fraumeni M.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U.S.Econom?ic Growth[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0(94).
[6]李海崢,李波,裘越芳等.中國人力資本的度量:方法、結果及應用[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4,1(5).
[7]梁潤,余靜文,馮時.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測算[J].南方經濟,2015,33(7).
[8]焦斌龍,焦志明.中國人力資本存量估算:1978—2007[J].經濟學家,2010,(9).
[9]李海崢,賈娜,張曉蓓等.中國人力資本的區域分布及發展動態[J].經濟研究,2013,(7).
[10]Mankiw N G,Romer D,Weil D 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Nber Working Papers,1990,107(2).
[11]張軍,吳桂英,張吉鵬.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經濟研究,2004,(10).
[12]Li H,Liu Q,Li B,et al.Human Capital Estimates in China:New Panel Data 1985—2010[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30).
[13]尹銀,周俊山.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