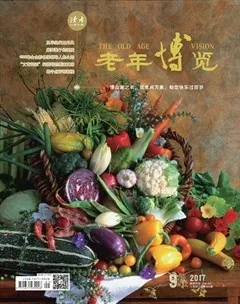看水在石上滲開
這些年我畫畫或寫書法,原本是為了用這種形式把心中想說的話說出來,但是在筆接觸到紙的那一剎那,卻有另一種感動蕩漾開來。
我發現自己更多的時間在專注于看水滴在硯石上滲開的過程。我常用的硯有兩方,都很普通,但它們都有石頭原本的粗樸。當水滴在硯上的時候,石頭的紋理和質感都發生了變化,仿佛回憶起了它們未被雕琢成硯以前在溪河邊與水廝磨的歲月。
水在石上滲開的速度很慢,層次也很復雜,使一塊枯槁了的石塊仿佛又滋潤復活了。中國筆墨使我著迷,正在于其工具本身似乎就有洪荒初辟時的混沌大氣,從石頭與水開始了宇宙的創造,也開始了人的創造。
墨是一種難懂的東西。我們一般以為墨是一塊凝固的黑色的固體。但其實墨是松煙,一種極細微的、塵芥似的粉末,被聚合了,膠著在一起。那植物焚燒以后聚合的焦枯的黑色,是曾經活過的樹木一生的呼喊吧?因此,這些年我但凡得到一塊好墨,就特別珍惜。那被水潤濕后在石上廝磨而起的墨的煙痕,與水和石的紋理一起流動,如煙云變幻,早在“水墨畫”之前已有了水墨的交融。“水墨”二字習用太久,人們已經不太記得“水墨”二字說的就是“水”和“墨”,而不是山水或花卉。
物質最本質的存在常常遠比形式更重要。繪畫從形式繁復的經營造作沉淀到“筆墨”的抽象領悟是一層境界,從“筆墨”的抽象領悟再沉淀到只是“水墨”的存在與不存在,更有著不可言喻的喜悅。
墨因為時代的不靜而特別難以領悟。替代的墨汁、黑色顏料都不再是聚合樹之灰煙的“墨”,墨也逐漸再無與水的激情糾纏,只剩下死滯的黑色。
紙是載體。中國書畫用的材料從絹帛、礬紙一變而為生紙,大約是在宋元之際。紙是許多植物的纖維緊緊糾纏在一起營造的一片空間。在埔里看工人抄紙,以竹制篩篾抄起紙漿,纖維和纖維擁抱在一起,還可見到一種立體的組織。壓平曬干之后,我們對它的組織個性就遺忘了。但是,每當水墨在紙上滲暈開來的時候,紙仿佛又蘇醒了,記起自己曾經是風光雨露中的一種植物,如今雖已破碎成纖維,仍能一分一分地在水中復活。
中國書畫令我不安,也是因為筆墨紙硯中俱蘊含著生命,它們在水中一一蘇醒,呈現出它們的歡喜、悲哀、傷痛與感謝。
中國書畫,到最后只是“水墨”二字而已,所以也可以不學書畫,只靜看屋頂上雨漬的“屋漏痕”。然而桌上有筆墨紙硯,心可以異常端正,因為面對著大千世界中的樹之死、石之死,而又心中有愿,愿在水的滋潤、淚的漫漶下有樹之生、石之生。所以書畫是悲情,也是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