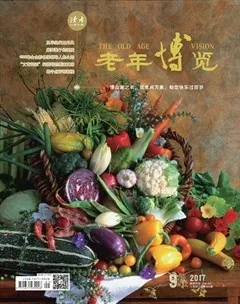蘇雪林的“信癖”
古人云,人無癖不可交。衣食住行皆可成癖。近讀蘇雪林長達50年間的四百萬言日記,發現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是“信”,我姑妄稱其有“信癖”。事一成癖,趣隨之生矣。
蘇雪林年過花甲后,日記中常有“還信債”或“一天光陰又在寫信中度過”或“今日為寫信最多之日”的記錄。94歲時則曰:“余現別無所樂,唯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報章,乃稍稍開心耳。”(1991年8月24日)
蘇雪林一生節儉,用她自己的話說“近乎嗇”。但由于她愛寫信,郵資成為她生活中一筆不小的開支。日記有載:“于今每個月郵費及信封、信紙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郵票可用數月,今則半月耳。”(1959年1月17日)為節省郵資,信封她常用商家塞在信箱內的廣告自己糊制,信紙則由隨手抓來的各樣替代品充當,甚至包括餐廳的餐巾紙。80歲時,她偶見舊物中一疊老得發皺的信紙,“熨了一下。此信紙乃余20年前自法國攜歸,或20余年前臺北所購,早已微黃而皺,幸熨后尚可用”。
20世紀50年代末臺灣郵資下調,她十分高興:“我可以寫薄信紙四張,而不用航空信箋,殊方便也。”好景不長,后臺灣郵政當局宣布作廢了一批郵票,她牢騷不已,說“這是坑民”。20世紀70年代臺灣郵政當局又出新花招:凡在郵局定做寄信用的規范化橡皮章者,鈐此印八折收費。她專定一枚,云:“定做此物以來,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貪,發出三四封信皆加此章,則回信不致冷落。”她是求信若渴,想廣種多收罷了。
寄臺外郵資昂貴。某次她讓女傭到郵局掛號寄兩本書到九龍,一過秤要250元,她嫌貴,讓女傭改為平郵。到了20世紀80年代,臺灣航空信箋從9元漲到10元,她盤算著還是寄航信劃算。可是一旦超重便會被退回,還要罰款,她嘆道:“以后不便寫信矣。”蘇雪林寫信如作文,往往下筆千言。她喜用薄紙,正反面都寫,仍稍不留心便會因超重被退回。鑒于此,她專備了一個小秤,信封口前先過秤,如果超了,去掉一頁便是。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是1991年臺灣郵資大漲,她很是不滿,以實際行動“抵抗”:“郵資增資后,即少寫一二封,乃市民之消極抵抗也。信少,郵局收入也少,則增郵資實為失策,或不久的將來又將減資,則我輩勝利矣。”(1991年8月1日)還有更有趣的是,20世紀50年代她由法赴臺,船泊西貢一天:“余聽說西貢寫信到巴黎航空亦僅需十五方,竟欲占占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寫信,計寫五封……下午寫完去寄,問管信件之船員,則由巴黎寫航信到西貢為十五方,而由西貢寫航信到巴黎則需五十五方。”(1952年6月25日)遺憾的是此日記無下文,不知信她最后寄了否。
為省郵資,蘇雪林常請從海外回臺的朋友帶信。“因明日公宴陳通伯(陳西瀅)先生,余將利用渠飛歐機會托其攜帶信件,故今日將學生作文束之高閣,大寫其信……共十三封,直寫到晚上11時始睡。”(1952年11月2日)20世紀60年代她一度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書,該校各人來信一律存在圖書館。圖書館距其住地較遠,她為了能及時讀到朋友們的來信,不得不每日奔波到圖書館取信,雖然直喊劃不來,但仍照跑不誤。她寄的信數量多、質量高(長),而所得回報極不平衡。在日記中她歷數友人不夠朋友:“叔華來信,余立復一航箋,寫得密密麻麻,比她來信的字多五六倍。”她常抱怨謝冰瑩寫信像寫條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她發誓要“以牙還牙”,寫短簡,可一揮筆又剎不住了,非千言不罷休。
蘇雪林寫信的熱情,筆者深有體會。1996年的半年內,她共致我7封信,用的都是超薄型大白紙,密密麻麻,正反面均寫,有一封字密到與落款重疊,看都看不清楚。最長的一封長達3000字,而那時她已百歲。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距她50年日記終結的1996年10月19日只有11天。那時她的字已歪扭重疊、筆畫不全,幾不成形。這或許可稱是她的“絕筆”了。
蘇雪林晚年耳朵失聰,不能接電話,與人面對面交流也只能靠筆談。特別是與她共同生活的姐姐淑孟過世后,她一人獨居,終日面壁無語,更賴寫信排悶遣愁取樂自娛了。
蘇雪林一生究竟寫了多少信,且看“今日為余燒信日”一篇記載:“昨日燒信紙未盡,又到后院燒之。下午睡起,看報二份畢,續燒廢紙。三四年來積信上千封,連一些被白蟻蝕之物皆付一炬,足足燒到晚餐的時候。”(1974年11月2日)筆者又從蘇淑年《雪林師與我》中獲悉,僅她收藏的蘇雪林的信就有300多封。與蘇雪林有書信往來者很多,包括胡適、曾虛白、蔣夢麟、王雪艇、張道藩、謝冰瑩、潘玉良、凌叔華等等;晚年她與大陸友人的通信也多,包括冰心、錢鐘書、蕭乾、袁昌英、舒乙等等。蘇雪林自言,友人的信她是每信必復;而友人復她者,“唯半數耳”。由此我估計她一生寫的信,諒有一二萬封之多,或可獲當代文人寫信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