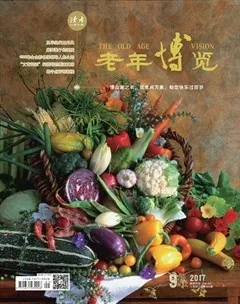啟功的幽默詩詞
啟功先生在他66歲那年曾自撰“墓志銘”,概括自己的一生。全文共72字,每句3字,合轍押韻,風趣幽默,在樸實無華中引人深思:
中學生,副教授。
博不精,專不透。
名雖揚,實不夠。
高不成,低不就。
癱趨左,派曾右。
面微圓,皮欠厚。
妻已亡,并無后。
喪猶新,病照舊。
六十六,非不壽。
八寶山,漸相湊。
計平生,謚曰陋。
身與名,一齊臭。
寫此銘的三年前,啟功先生的妻子章寶琛病逝。其時,年過花甲的啟功先生也多病纏身,不時住院治療。在醫院的病床上,他用病歷紙寫下了《沁園春·致病魔》:

舊病重來,依樣葫蘆,地覆天翻。怪非觀珍寶,眼球震顫;未逢國色,魂魄拘攣。鄭重要求:“病魔閣下,可否虛衷聽一言?親愛的,你何時與我,永斷牽纏?”
多蒙好友相憐,勸努力精心治一番。只南行半里,首都醫院,縱無特效,姑且周旋。奇事驚人,大夫高叫:“現有磷酸組織胺。別害怕,雖藥稱劇毒,管保平安”。
住院期間,因骨質增生,須做頸椎牽引術。在理療室里,啟功又寫下了一首《西江月》:

七節頸椎生刺,六斤鐵餅拴牢。長繩牽系兩三條,頭上數根活套。
雖不輕松愉快,略同鍛煉晨操。《洗冤錄》里每篇瞧,不見這般上吊。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啟功先生聲譽日隆,擁有十幾個社會兼職和一大堆閃光的頭銜。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找不著北,老先生對此卻有清醒的認識。他說自己就是個普通的讀書人,并不高人一籌,因此他拒絕“大師”“巨匠”“泰斗”等稱謂。據說當時央視《東方之子》欄目組多次要求采訪,他都婉拒了,稱自己“頂多算是‘東方之孫’,不夠條件”。為此,他還寫下一首自嘲的《沁園春》:
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閑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
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解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煩煩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收拾起,一孤堆拉雜,敬待摧燒。
1989年,啟功先生心臟病再次突發入院搶救,病勢十分兇險。數天后醒來,見到病床周圍的親友同事和學生,問自己怎么了,醫護人員介紹了搶救經過,他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各種管線。閉目休息片刻后,老先生慢慢口占長句曰:
填寫診單報病危,
小車直向病房推,
鼻腔氧氣徐徐送,
脈管糖漿滴滴垂。
心測功能粘小餅,
胃增消化灌稀糜,
遙聞低語還陽了,
游戲人間又一回。
啟功先生對生死一向看得很淡,因曾多次到了“鬼門關”卻去而復返,遂自謂與鬼有緣。有一年去四川,他特地去豐都鬼城參觀游覽,還寫了一首五言詩:
昔有見鬼者,
自言不畏葸。
向他擺事實,
給他講道理。
你是明日我,
我是昨日你。
鬼心大悅服,
彼此皆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