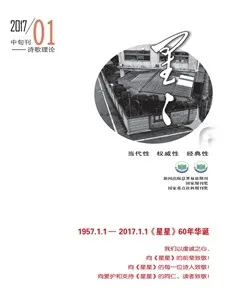詩如何思?
2017-12-29 00:00:00李曉靜
星星·詩歌理論
2017年1期
法國詩人保羅·瓦雷里曾說,人們在閱讀現(xiàn)代作品時經(jīng)常會感到困惑,不知該關(guān)注創(chuàng)作本身呢,還是該關(guān)注創(chuàng)作的審美效果。在我看來,產(chǎn)生這種困惑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現(xiàn)代詩在探索現(xiàn)代世界的復(fù)雜情形時,并沒有為我們展示一個完美的結(jié)論,而是如德國畫家保羅·克利所說,現(xiàn)代詩歌想把詩歌的思維過程也放進一首詩的最終審美形態(tài)。
風荷的詩,將古典詩歌了無痕跡地化用,讀來別有一番江南水鄉(xiāng)的婉約清雅,耐人尋味。《說詩》用獨白型的語調(diào)娓娓道來。詩的開頭“你一眼就瞥見了/我的小”,為我們構(gòu)建了一個溝通對話的場景,我的詩歌激起的浪花在“你”面前只是小兒女的情狀。要學李清照的大境界,既能譜寫“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的豪氣,也能“尋尋覓覓”勾勒“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多情與哀愁。詩歌不僅要在收尾處畫龍點睛,雋永有韻外之致,還要表達我的情感與哀思,喜我之喜,憂我所憂。然而詩人的筆鋒一轉(zhuǎn),境界遂深。是的,詩還可以是鳥飛翔的弧度,是九省通衢的四通八達,是愛的起伏,或是牙齒的陣痛,具體或者抽象,都是波濤式起伏無定而又連綿不斷的。從對我“斷流的章節(jié)”的“小”的反思,至最后詩的境界的飛躍,詩人為我們展示了她思維聚合的過程。
熊魁的《當時光把生命快遞給我》,意義深遠,是詩人對生與死這個人類永遠無法回避的宏大命題的思考。他將生與死的過程建構(gòu)為時光把生命快遞的過程,抽象變?yōu)榫唧w,產(chǎn)生了一個很新鮮的情景移位。……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