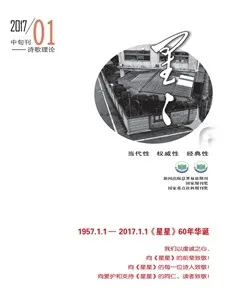身體隱喻,以及詩學的縮地法
2017-12-29 00:00:00蔣藍
星星·詩歌理論
2017年1期
畢竟是兩代人,老夫與李清荷不熟。隔著一個遙遠的“代”,2014年里,偶爾回眸,我像是看見清荷在河對岸點草成林,撒豆成兵,她是十萬朵桃花的王——女王,她用了100首詩來點染桃花的淺粉、血與脂膩。這似乎是一種來自于天命的針刺放血療法,她用一些近于極端的詩學修辭,把桃花演繹成了一種絢麗、打開、彌散的女性文化,有些寫法已經進入身體政治域界。我在《極端植物筆記》里描述過桃的桃樹、桃葉、桃花、桃實的四位一體的悖論,這讓我想到一個古代隱喻,說一個煉劍師為了鍛造出一把千古名刃,不惜把生命鍛打進去,精神成為劍芒,成為鞘中長嘯龍吟的精氣神。清荷互訓桃花,喻象如何回到喻體?就像博爾赫斯所言“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中”,這分明是一個回環接龍魔術,但是,草本如何成為木本?但,她似乎做到了。
《布景者》當中抽空了桃花,清荷顯然移走了她的道具,匆忙間僅僅有些花瓣散落在字里行間,既像出于無心,又像是某種刻意安排。這樣,無香味的花瓣構成了清荷階段性的詩歌生命蹤跡,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色如故。色即是空,但空,未必就是色。在著意與放棄的過程中,桃花之王與詩歌女子移形換位,就像一朵迎風怒放的桃花,它吐出的夢境因為風的緣故,又為自己加冕了一層逆光的絲絳。我隱約感覺到,不從這個入口進入《布景者》,就找不到北,甚至容易成為“桃花瘴”的中蠱者。
《布景者》分為四輯,由于她沒有標注寫作時間,我的推測是:詩集是“倒編”而成的——從現在開始,逆時推向過去。……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