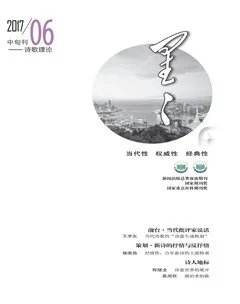從知性中構筑詩歌造型及精神疆域
2017-12-29 00:00:00盧輝
星星·詩歌理論
2017年6期
“整個下午,我坐在水泥叢林中/每一口清茶,都有蘭香回歸血脈/每一次沖泡,都能看見/白馬彎弓的身影”。當詩人曾章團把成年時期那陽剛的毅力與萌春年華那陰柔的微力結合在一起時,他詩歌所持有的語言“造型能力”立刻把非本質的東西——時間,給取消了。也正是在時間“被取消”的一剎那間,他詩歌的“恒定值”顯露出來。
在福建詩壇,曾章團的詩一向以知性、硬朗、靈性、開闊見長。這次,我從他新近出版的《鏡像懸浮》拜讀了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近幾年的詩歌作品,我驚奇地發現他的詩歌在無限世界中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機體化的,都有著一種無限之力,有著穿透過那外在的、限定著的“物象”中去。尤其是他對“茶”有著特別的靈性與銳度,他對茶的語言“造型能力”有著許多過人之處。在他看來,茶是他心目中“全一”的本體,一個普遍的、絕對的、終極的精神“外化”。因而,他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把他心目中“全一”本體的不透明性和沉重性轉化為透明的、輕靈的永恒:
在閩南的紅壤地里
一株小小的植物
注定要長出鋸齒狀的
英雄主義,對抗繚繞云霧
注定要在涼青、萎凋、揉捻
和發酵中,剝下鐵的銹色
讓鐵的靈魂擲地有聲
——《安溪鐵觀音》
很顯然,曾章團詩意化的“茶”儼然是一個理想的精神國度,它與現實有著超驗的距離,就是因為他的茶是以最高的本體——神性、大全為根據地,最終“生成”為一個生命的范疇。在他所垂青的茶園里,一株小小植物的“英雄主義”和“鐵的靈魂”被詩人整合得擲地有聲:“今夜,所有的茶樹/都選擇隱姓埋名/紛紛放下成長的刀劍/用發酵忍住悲傷/在皸裂的掌心下/漾出觀音的慈懷”。……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