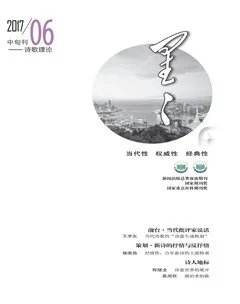這就是人生
2017-12-29 00:00:00蘭田
星星·詩歌理論
2017年6期
我第一次看到“人生”這兩個字的時候,還是在少年時期。或許是青春期必然要有的傷春悲秋,那時候寫東西、說話,總愛拿“這就是人生”一類的話說事,儼然一副智者的模樣,好像自己經歷了多少事情一樣。但不知從何時起,“人生”這兩個字再不敢妄談,當初動不動就為人生皺眉惆悵的樣子只覺得可笑。“這就是人生”,再不是強說的感慨,而是經歷了一些事情后的真情實感。每個人都是這樣,詩人自然也不例外。
徐書遐是一個不忘故鄉的人。小時候母親的別針方法使得針總也丟不了,可是詩人作為那根“針”,卻在成長的歲月里離開了家鄉。在詩中,作者把自己比作那根夢中的針,“帶著自身的沉”丟在了一個床底和地面之間的位置,兩邊都夠不到,“朋友們同樣望不到”。離開了家鄉,就是離開了家鄉的人,家人,朋友,我們熟悉了多少年的一切的一切。有些人走著走著,就丟了家鄉。所幸詩人是一個丟不了的人。她的身上仍然有“故鄉打上的針孔”,中間穿著一根叫做故鄉的線。詩人筆下的“針”實際上是很多在外生活的人的人生寫照。他們因為工作等其他原因離開了最熟悉的地方和人,可是在心里,那根叫做故鄉的線一直在自己的針孔中默默穿著,未曾斷過。
李之平的《萬物同喜》則給我們講述了人到中年后對于婚姻的體悟。一個人的人生必然要經歷婚姻。有人說婚姻是墳墓,但詩人卻在婚姻不可避免的“拌嘴和責怨”中漸漸學會了和愛人平靜相處,發現了婚姻生活也可以享受平靜的快樂。……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