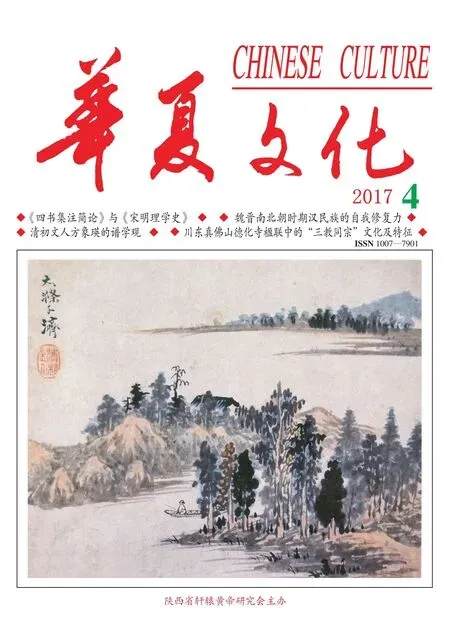儒家倫理的價值和意義
□任鵬程
儒家倫理的價值和意義
□任鵬程

儒家倫理的核心內容是人性論。人性論是做人的起點和基礎。所以,儒家哲學的精髓其實是人生哲學,或者說,儒學是一門做人的學問。
先秦時期,孔子指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意思是,天生之性差異甚微,后天的習染則會導致不同。孟子首倡性善論,以為人生而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存之即人,擴而充之便為仁義禮智。舍之即獸,寡欲和求放心以補救之。荀子則提出性惡論反對孟子,以為人性不美,故極力勸學,倡導教化使人們走向性善。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于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5頁)。自此,孟、荀兩人開啟了傳統儒家道德哲學的兩條不同進路,即涵養和學習。
漢代儒者都試圖調和孟荀兩人的人性論。漢儒董仲舒認為,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人性就質地而言,是可以為善的,但要實現性善則須有待外在的禮義道德教化,這就是“性待漸于教訓而后能為善”(《春秋繁露·實性》)。繼之,揚雄倡導人性善惡相混說,其言曰:“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修身》),意在號召人們通過后天的學習努力改造人性。隋唐時期,道教、佛教吸引了眾多的崇奉者。韓愈發明“道統說”,認為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義道德,而這正是釋、老二教所缺乏的。他主張克制情欲,改善人性。李翱作為韓愈的追隨者,卻認為人性本是善的,而情則是惡的。性與情兩者是互相依存的,性是情的基礎,因此,要恢復人類本來的善性,就必須做到去情,即“復性”。簡言之,隋唐儒者面臨多元文化的侵襲依然對性善之說懷有信心。
宋明時期,儒家人性論發展到極致,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他完善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思想,用“理”之本體與流行的兩個層面,較好地解釋了性善與性惡兩者所發生的緣由。同時,他倡導為學之道,變化氣質,改善人性。與理學家所不同,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家們打出“本體即工夫”的旗幟,認為成人之道沒有詳細具體的方法或步驟,且開啟了所謂發明本心、致良知的道德涵養路向。道問學與尊德性便成為理學、心學兩家涵養路數的標識。宋明時期,理學逐步成為古代社會官方哲學,理論活力和道德功能相對減弱,最后淪為鉗制人們思想的工具,以致明末清初出現了批判和鞭撻理學的思潮。
因此,儒學從來沒有逸出我們平常生活之外,它尤其注重日常倫理和社會生活秩序的建構,可以說,儒學本質上是一門生活的學問。不論古代儒者們提出何種人性說,他們普遍對人性持有向善的信念,這種內在的德性具備自然性、自發性,只是由于人類的主觀刻意而泯滅。所以,儒者們都號召通過工夫修持達到人性圓滿。更為重要的是,崇善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價值信念和生活準則,深深印入華夏民族的記憶之中,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情境,這也就是儒家所說的“百姓日用即是道”。
但與儒家哲學所不同的是,西方學者普遍把對知識的追求看成人類的本質。亞里士多德以為“求知是人的本性”,“惟有人憑技術和推理生活”(亞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譯:《形而上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也就是說,人類之所以與禽獸不同,在等級上高于禽獸,在于我們具有推論的能力。推理則意味著人類能控制自己的行為,表達自己的心聲。所以,做人在西方學者們看來就是在現實生活中彰顯或表達自己!在這種突顯理性光輝、張揚個人價值的理念支撐倡導之下,西方社會形成了對抗性的、競爭性的現代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由此進入了現代性社會。

反觀儒家倫理,相對來說則忽視人類的欲求、表達。無論是孟子的寡欲、董仲舒的王道教化,韓愈和李翱的克制情欲,或是朱熹的孜孜為學克服氣質流弊,或是王陽明的致良知等等,都是以期實現人性至善的努力,并不提倡人們對一己之私的追逐。顯然,儒家倫理似乎對人類的個人追求和個體主見有某種抑制作用。
今天處于市場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期,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于要求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能夠做出判斷和選擇,最大限度地、合法地獲取個人利益。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隨著中國社會逐步向現代化道路的推進,各國之間文化交流也日益頻繁,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文化思潮紛紛涌入中國,大行其道,并逐漸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其結果是,理性精神逐步成為中國人社會生活的信條和做事的普遍法則,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導和統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際交往、社會運行,等等,由此我們便看到社會逐步走向制度化、規范化、體系化。似乎有一種聲音,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徹底拋棄舊有文化,因為傳統便是保守的代表,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社會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和排斥。
但是,我們也應該十分清醒地看到,現代社會對理性和自主性的過度關注,倡導理性化的公共秩序的構建,密切關注個體切身實際利益,諸如,律法條文和科目日趨復雜完善,雖然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為人們追求自我和自身價值的實現提供了路徑和前提。但是類似法規、契約、制度等長期性的、外在性的、形式化的規范制度力量持續侵入人類的心靈和約束人們生活,由此導致了人們自身固有的德性資源相對被削弱和忽視,由此引發了許多法律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例如,社會人情味缺失、精神世界荒蕪、價值觀念扭曲、行為舉止墮落、信仰匱乏缺失、拜金主義猖獗,等等。
那么,儒家倫理能夠為之做些什么呢?
儒家哲學向來以人類的日常生活為學問研究的聚焦點。儒家倫理思想自誕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人類自身所固有的道德資源,以做人為宗旨的儒學一直對人性持有一種美好的愿景,主張人性有一種最終會走向善的趨勢。從先秦到宋明,儒者們皆是如此。儒家的這種道德理念引發出一系列道德涵養工夫,它們路數形態雖不同,但都致力喚醒人類的道德自覺和自然的倫理感情,雖然以儒家倫理為代表的做人操守和價值信念并不具有類似法律那樣的強制性、義務性、規范性的特點,但是,這種傳承已久的崇善傳統和民族習慣必然會為心靈凈化、社會和諧與健康群體的形成提供豐富的理論資源。因此,我們必須正本清源,改變本末倒置的局面,使道德主體自身所固有的德性資源成為人們生活的依據,同時采取必要的制度約束,兩者互相配合,以此規避和矯正現代理性化思潮昌盛所帶來的風險和不足!這便是儒家倫理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山東省濟南市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郵編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