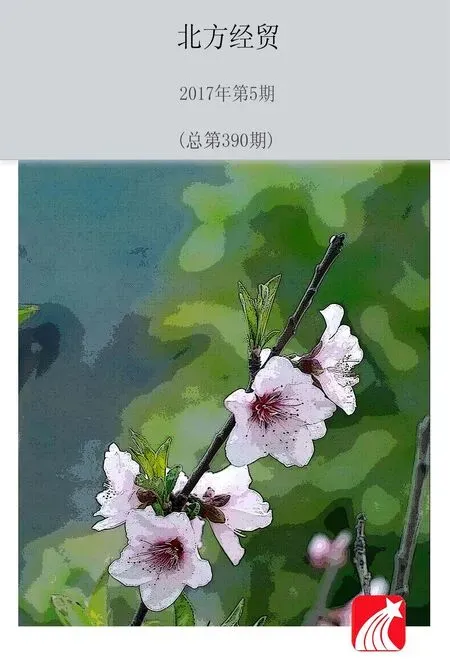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法理分析和路徑
朱鶴群,童 茜
(巢湖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巢湖238000)
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法理分析和路徑
朱鶴群,童 茜
(巢湖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安徽巢湖238000)
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問題,無論是法理層面,還是實踐層面尚有許多的問題亟待研究和探討。雖然,憲法、法律法規和政策性制度等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做了一些基本規定,但由于實體性和程序性的制度保障缺失,制約了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行使和功能的發揮,因此,必須構建起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規范有序的參與機制、暢達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和良好的社會機制。
環境保護參與權;民間環保組織;參與機制
從風險社會形成誘因看,環境風險是當代風險社會形成的重要誘因之一,環境風險的形成雖然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無形推手有很大的牽連,與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環境責任欠缺有關,但最為關鍵的是公眾參與權缺失,特別是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缺失。在憲法層面,公民參與權則更多地體現為一項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而在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層面,公民環保參與權與環境知情權、環境監督權并列構成程序性環境權,為實體性的公民良好環境享有權或“環境權”的實現提供程序保障。在實踐層面,民間環保NGO作為環保公益組織代表公眾行使環境保護參與權,則是公民環保參與權最為集中的實踐體現;然而,在我國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實踐方面,仍然面臨著諸多理論和現實問題,諸如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權利基礎、法律制度安排、參與路徑以及政策性保障等,都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規范和構建。筆者在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應然性、實然性分析的基礎上,探討構建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制度路徑。
一、民間環保組織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應然性分析
(一)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應然性———權利視角
“主權在民”思想——“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早在18世紀,啟蒙思想家就對其做了系統的理論闡述,特別是政府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盧梭認為,國家權力來源于平等的人,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契約,每個個人把自己的全部自然權利讓渡給社會,即主權性的集體“公意”。在高度發達的市民社會,市民個人只服從“公意”——社會意志,而不服從任何其他個人或權威。主權就是意味著執行公意,人民主權是由公意行使的權力,法律是公意的體現,政府是人民的代表。[1]費希特則進一步指出,全體人民表達共同意志的方式,則是通過將他們那部分管理公眾事務的權力轉交給他們選舉出來的政府——法治共同體來代表公眾完成,[2]政府必須對全體人民負責,運用法律和正義管理國家。在憲法具體實施中,只有行政權力才可能成為“反叛者”。[3]由此可知,在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上,政府是基于人民的委托,運用行政權力,代表人民行使公共管理職能。
然而,在對政府或法治共同體的權力生成邏輯的精辟論述的同時,也涉及了如何限制公權力或保障公民的權利問題。人民將自己的某些權利委托出去而形成公權力,掌握并行使公權力的政府或政府授權的機構或公務人員,往往會陷入洛克所言的公權力異化的悖論,即“公權私用、公權作惡,使政治權力反轉成為侵害個人權利的利器。”[4]在一個順應公意且治理良好的國家中,公意才能夠增進所有人的福祉,只有在違逆公意且治理不善的國家,才可能存在“特殊利益會扼殺或凌駕于共同利益之上”。[5]也就是說,本質上異化的公權力來源于公眾的權利,卻變成了凌駕于社會之上并支配公眾的權力。[6]為了限制公權力和防止異化的公權力的“惡”,避免其對公民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侵害,現存國家,幾乎無一例外的,除在憲法中規定公民權利保障條款外,在立法技術上,通過創設公民參與權,使之成為一種對公權力的制衡力量,從而制約和監督公權力的不當行使。各種權利的創設活動,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為解決和應對各種生存和發展問題而產生的,因而,權利表征為一種制度和文化現象,伴隨著法和國家一同出現,每種權利的內容及其保障形式,都是基于一定社會現實利益的沖突的回應。也就是說,權利的背后總是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公益”或“私益”。
在環保領域,由于環境損害的累積性和損害因素的復雜性以及“政府失靈”的顯著性特點,因此,環境保護不能完全依賴運動式的政府作為,而是需要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并通過立法,建立一種公眾參與的長效機制,確保公眾參與的有效落實,從而監督政府的環境責任履行和相關企業的違法排污行為。[7]民間環保NGO作為公民社會的組織部分,在環保領域作用的發揮,主要體現在:一方面,憑借其專業優勢,在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為政府的環境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決策咨詢;另一方面,相較于“環境私益”,在“環境公益”的保護上,公民個人更缺乏積極性,更多地體現為“搭便車”現象,從而陷入“公地悲劇”的窘境。民間環保NGO作為環保公益性的社會組織,其環保參與權的正當性同樣來源于人民權力或權利的正當性,正如哈貝馬斯所言,人民主權原則是通過確保公民的公共自主性的溝通權和參與權,并且被公民享有的公共自主性的溝通權和參與權所體現,由此,法律基于其作為同等保護私人自主性和公共自主性的工具而獲得正當性。民間環保NGO通過組織社會強力來倒逼或強制政府和排污企業履行環保責任,因此,其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正當性源于公民參與權,而不是基于政府的授權。
(二)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應然性——法律政策制度視角
1.我國現行立法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規定
作為我國根本法的《憲法》,對公民參與權的憲法性昭示,集中體現在其第二條的規定,在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同時,賦予人民依法對國家事務管理的參與權。該條之規定被闡釋為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憲法性權利淵源,不僅從根本法的高度賦予并確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而且也為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正當性的獲得提供了憲法性依據。在環境保護立法層面,2015年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第5條明確將環保公眾參與作為環境保護的基本原則之一予以規定,并在該法第五章——“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詳細地規定了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權利和義務。為保障公民實體環境權的有效實現,新《環境保護法》除第14條和第27條明確規定了公眾的建言權以及意見須得到充分考慮外,該法第53條還明確規定了三種“程序性環境權”,即環境信息知情權、環境保護參與權、環境保護監督權。特別是在公眾環境知情權的保障上,新《環境保護法》第54條、第55條和第56條明確規定了相關主體,特別是各級政府環保部門和重點排污單位的有關環境信息公開義務,并且對具體環境行政行為以及相關項目環評的信息公開做了強制性規定。在公眾實體環境權的救濟方面,新《環境保護法》第57條和第58條,除環境監督權外,還明確規定公眾的檢舉權和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此外,其他單行環保立法,也同樣明確規定了公眾參與權。尤其體現在2016年修訂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第5條、第21條規定的環境影響評價的公眾參與權。為徹底改變相關建設項目環評的“被參與”現象,進一步有效實施新《環境影響評價法》,環保部于2016年4月發布了《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征求意見稿)》。該《征求意見稿》對涉及建設項目環評的公眾參與權的行使范圍、參與對象、公眾參與權的行使原則、公眾參與的途徑、征求公眾意見載體以及公眾意見得到考慮權等問題都詳細地加以規定。總之,現行立法對公眾參與權的規定,在為我國民間環保NGO監督環境行政機關及其行政人員是否依法行政、單位和個人是否有損害環境的行為提供切實的立法保障的同時,也體現出環保預防為主的首要原則。
2.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規定
1986年12月,聯大第41/128號決議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序言規定,在“承認發展是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全面進程”的同時,通過“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已達到在對發展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礎上,“不斷改善或增進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的福祉。”該《宣言》第1條進一步規定,“發展權”作為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而具有廣泛性,即參與主體的廣泛性——“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和參與領域的廣泛性——“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以此“在發展中,充分實現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該《宣言》第2條第1款規定,“人”既是發展權的主體,同時也是發展權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該《宣言》第8條第2款規定,將各國鼓勵和保障公眾參與權界定為“發展和充分實現人權的重要因素”;1966年12月聯大第2200A(XXI)號決議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第25條(甲)規定,每個公民都應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權利和機會。雖然我國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該《公約》,但是鑒于實際國情的考慮,以及該《公約》與國內法還存在諸多的沖突等問題,導致全國人大至今還沒有批準該《公約》。但是,自2004年我國“人權”入憲以來,特別是在2012年我國政府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中,“環境權利”再次作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到我國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體系,并作為保護目標。由此可見,這些國際公約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規定,也亟待我國國內法能夠作出回應性的規定。
二、民間環保組織環境保護參與權的實然性分析
(一)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保障機制缺失
1.從實體性的法律規范看,缺失公民環境權規定
實體性環境權是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基礎和保障。公民環境權作為一種新興權利,正如有學者所言:“任何一項權利的主張與訴求,都始終是基于主體對于自身的現實生活的真實需要,其實質是對自身現實與未來的利益的考量。”[8]也就是說,公民環境權的基礎,是基于“環境風險”而引發的公民對“環境擔憂”的一種安全利益需求的考量。雖然,從憲法層面,公民環境權是作為《憲法》中“人權”的子權利而存在;而在單行環境法規層面,公民環境權卻作為一項公民的義務,尤其體現在新《環境保護法》第6條之規定,有學者認為該條暗示了“公民環境權”的內容,[10]但是,并沒有明確賦予公民的“環境權”,不能以此作為民間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實體法依據。
2.從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看,缺失參與環境執法監督、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權利
縱觀我國現行的環境立法,關于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之規定,存在著過于籠統、過于抽象的弊端,尤其缺乏參與權行使的具體程序之規定。雖然,2016年修訂的《環境影響評價法》,比此前的《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對于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的原則性規定有了長足進步,但在程序的規定方面仍然欠缺,缺乏可操作性。如公眾參與的具體方式、組織者及其權利義務、聽證會或論證會的程序、公眾評論期限等。對負有環境監督職責的環境行政人員的違法行為,新《環境保護法》第67條第1款規定了“上級政府或環保主管部門對下級政府或環保部門的監督”以及對環境行政人員的違法行為可以提出處分建議、第68條規定了對負有環保監督職責的行政人員,有關違法許可、包庇、違法查封等八種行政行為給予行政處分以及第69條“環境刑事責任”之規定。在環保實踐中,盡管許多地方出臺并實施了環保公眾參與的法規、規章,但是,從云南、杭州等地因項目審批、排污監管等政府的環保不作為而引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中,不難看出這些地方性的環保公眾參與法規發揮的作用有限,公眾參與明顯不足。由此可見,在“上級對下級的監督”和“行政機關之間的相互監督”的模式下,必然導致經核實的單位和個人的環境違法行為也只能由環境行政機關依法處理,相關行政機關是否處理、處理是否得當而公眾卻并不知曉,而民間環保NGO作為環保公益組織,基于環境公益,對與自己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環境違法行為,沒有提起司法審查和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的權利。
(二)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行使路徑不暢、范圍受限
根據《憲法》第41條和新《環境保護法》第5條、第6條之規定,我國環保NGO行使環境保護監督的方式,即對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的“檢舉、控告”。由此可見,在參與階段上,仍然以事后監督為主,屬于典型的末端參與,缺失事前參與、事中參與的規定。對于事前參與或“源頭參與”的原則性規定,主要集中在對建設項目環評方面,例如,2016年修訂的《環境影響評價法》第5條規定的建設環評的公眾參與權,即在對可能存在環境風險或直接涉及公眾環境權益的專項規劃項目的審批時,政府部門有責任或義務在該項規劃審批前,通過聽證會等形式,征求公眾對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的意見。可以說,這一公眾參與的“前置程序”設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眾環保參與權的行使,但是仍然存在著公眾參與的范圍過窄,只限于“專項規劃和建設項目”。而對于規劃環評或政策實施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則無權參與,導致許多地方政策造成了大規模的環境破壞,究其原因在于,現行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著權力過度集中的弊端,集中體現為將行使環境影響審查權的主體與行使項目審批權的主體,都賦予環保部門集中統一行使,而在地方政府的經濟項目的開發決策行為中,環保部門卻常常處于被動、尷尬的地位,由此導致由環保部門主要承擔的公眾參與,并不能有效介入地方政府經濟開發的各個環節,導致公眾在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幾乎處于無權參與或“被參與”的法律地位。[11]近年來,由于項目審批、排污監管以及垃圾焚燒廠的選址等事項而引發的環境群體性事件,則是公眾參與不足的明顯佐證,就其根源在于公眾參與的具體條件、具體方式、具體程序缺失明確且可操作性的法律規定,公眾一旦遇到具體的環境問題或者某種環境擔憂時,不知道如何參與。[12]因此,正是由于公眾“源頭參與”的機會缺失,從而導致作為公眾的代表人——民間環保NGO,同樣缺失環境保護的“源頭參與”機會,特別是不能參與環境發展的重大決策以及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重大戰略的制定過程的參與。
(三)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先決條件缺失
環境信息公開或披露機制既是公民環境知情權的有效保障,又是公民環境保護參與權行使的先決條件。因而,良好的環境信息公開或披露機制,則要求政府和相關排污單位等義務主體,對其披露的信息必須做到并確保其公開信息具有及時性、有效性、全面性和便于公眾理解性以及公開載體的權威性。
首先,在政府信息披露模式上,2008年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了兩種信息公開模式——“政府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就“政府主動公開”而言,一方面,該《條例》第10條明確規定,縣級以上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必須主動、重點公開的信息,主要包括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和區域規劃等政策信息、重大建設項目的批準和實施情況信息以及環境保護、公共衛生等監督檢查信息。另一方面,該《條例》對信息公開規定了諸多的限制或規定了許多不利于信息公開的內容,諸如:該《條例》第4條第2款第4項要求的“對擬公開的政府信息進行保密審查”;第6條禁止公民或單位發布所謂“影響或者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虛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第7條規定發布信息應與有關行政機關進行溝通、確認,保證發布的政府信息“準確一致”,并禁止發布未得到“國家有關機關批準的”信息;第8條禁止發布“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信息;甚至該《條例》第14條更是把可發布信息的范圍無限縮小,因為它規定,行政機關在公開政府信息前,不但要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還要遵守“其他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而這個“其他”的范圍難以限定和預知。并且該條第4款規定“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且不說國家秘密肯定不屬于發布范圍,因為前款搬出的《保密法》肯定已經包含了這個內容,就“涉及”二字來說,太過模糊,范圍不清楚。因此,這部《信息公開條例》對根本解決長期形成的信息屏蔽來說,作用甚微。如果政府與污染企業構成利益聯盟,或者政府過于擔心公開污染信息的社會穩定后果,信息屏蔽就是必然的。2016年7月,因“中法核循環項目”選址,而引發的江蘇連云港群體性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佐證。
其次,在環境信息披露的行政主體上,無論是新《環境保護法》,還是《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以及《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都將環保部門規定為環境信息公開的責任主體,且級別僅限于國務院和省、市、縣級政府的環保部門。這種單一行政責任主體且僅限于縣級以上環保部門的規定,制約了環境信息公開的程度,導致鄉、鎮一級的環境監管真空,致使部分污染企業向鄉、鎮等偏僻的農村轉移,而鄉、鎮周邊的環境信息狀況,公眾卻無法獲悉。另外,環境信息公開的責任主體僅限于縣級以上環保部門的規定,從而忽視政府其他部門就其掌握的環境信息進行公開義務,制約了環境信息的來源。在現行的環境監管框架中,環保部門,特別是地方環保部門“名義”上受國家環保部和地方政府的“雙重”領導,而實際上環保部門官員的任免、環保行政人員的工資福利等待遇,卻完全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基于“招商引資”和“財政拓源”的雙重壓力,往往對既是環保執法對象又是財政收入來源的污染大戶施予地方保護。如2013年修訂的《合肥市優化投資環境條例》第29條規定:“對同一市場主體的檢查一年不得超過一次,上下級部門對同一市場主體不得重復檢查。法律、法規或者規章另有規定的除外。”[13]這樣就在地方政府和排污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貓鼠共生”狀態,企業排污信息屬于保密材料,政府的環保機構就成為排污企業的“保密局”,導致“依申請公開”也變為不可能。
最后,在企業環境信息強制公開方面,現行環境立法對相關企業強制公開的環境信息,界定得過于籠統和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法律層面,新《環境保護法》則籠統表述為“環境質量狀況和環境污染事故”,《清潔生產促進法》則將企業強制公開的環境信息表述為“與清潔生產相關的信息”等。在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層面,《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僅將“超標準、超總量排污的企業”界定為負有強制公開其環境信息之義務,同樣,2010年11月實施的《安徽省環境保護條例》則將“使用有毒、有害原料進行生產或者在生產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質的企業”列為環境信息公開和審核的范圍。然而,在實踐中,即使屬于強制公開環境信息的企業,往往都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排污信息,更談不上,那些“非超標或者合法排污”的企業“自愿公開”環境信息,由此導致,日益嚴重的累積性環境損害問題。
三、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路徑選擇
(一)構建規范有序的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法律法規
雖然我國憲法抽象地規定了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有關法律法規以及地方性法規如《安徽省環境保護條例》第14條,對環保NGO參與環境行政決策中的某些環境行政程序,如聽證、建議等有一些專門性的規定,黨和政府的政策文件和工作規劃中也有對民間環保NGO參與環保的指導性意見,這些法律法規和政策性規定確實為我國民間環保NGO參與地方環保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但是,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的原則與規則、權利與義務、范圍與程度、渠道與路徑、內容與形式、步驟與方法、保障與救濟、責任與承擔等規范性的體系化制度構建還是個空白,而且既沒有實體性的制度安排,更沒有程序性的制度設計,要使得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達到有序、規范、效率和質量的目標,參與環境保護的實體性和程序性制度構建是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二)構建暢達充分的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信息披露機制和制度
當前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的信息披露,無論是渠道的通暢度,還是內容的充分性都存在某種程度的缺陷和不足,阻礙了民間環保NGO獲取相關信息的速度和效率,導致民間環保NGO與參與對象、參與相對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對參與的能力、效率、成本和效果產生了直接影響,完整充分的信息披露是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因此,依據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從地方法規和政策層面加快建立暢達充分、主動有效的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門信息披露機制和制度系統已經刻不容緩。
(三)構建真實有效的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評估機制和制度
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的效果和質量如何,誰來評價或判準,目前還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從環境保護的實踐看,評價機制多半偏重于上級主管部門的評價,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缺乏有效的權利制約機制和評判機制。環境保護的成效如何,如果由地方公眾或環保NGO參與的評估和判準,那將產生兩個方面的積極效應:一是促使環境保護工作進行價值轉型,由注重對上負責向注重工作的實效性、可持續性和向公眾負責的價值轉變;二是促使地方公眾或環保NGO更加積極和有效地參與地方環境保護,發揮參與的主動性和創新性,提升公眾的環保意識和環保NGO社會公信力。
(四)構建良好的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社會機制
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除需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之外,客觀上營造良好的社會機制對于環保NGO參與環保的作用和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構建良好的民間環保NGO參與環境保護社會機制包括:一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民主和開放環境;二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行政權力運行的約束和陽光機制;三是確立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價值理念;四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不同層次的外部組織架構、參與通道和非政府的社會動員體系;五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行政、司法救濟機制;六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協調、協商和協議機制;七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環境沖突預警和多元環境沖突化解機制;八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利益表達、利益選擇、利益評價、利益平衡和利益保障的多元調整機制;九是構建有利于保障環保NGO環保參與權的非制度性和制度性參與的資源整合機制。
從應然性的角度分析,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有眾多權利支撐,但從實然性的角度分析,我國現行立法對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保障不力,主要表現在實體性和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缺失、監督渠道和路徑不暢和參與范圍窄、信息公開制度不夠健全、組織自身的獨立性弱、主動性不強、公信力較低,因此,必須構建起保障民間環保NGO環境保護參與權的規范有序的參與機制、暢達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和良好的社會機制。
[1]單培培.論盧梭的公意思想[D].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2014:22.
[2]梁志學.費希特《自然法權基礎》評述[J].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2):82-91.
[3] 朱未易.地方法治建設中公民參與的法理分析與制度進路[J].南京社會科學,2010(10):106-114.
[4]周少來.人性、政治與制度:應然政治邏輯及其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67.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71.
[6]周光輝.論公共權力的合法性[M].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2007:11-12.
[7] 曹明德.環境保護的根基[N].學習時報,2007-06-18(5). [8] 王慧娟.政府公共服務外包的法理分析與制度選擇[J].行政與法,2012(10):25-29.
[9]姚建宗,方 芳.新興權利研究的幾個問題[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50-59.
[10]周訓芳.蔡守秋環境權理論研究述評[C].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年會論集,2003:809-816.
[11]汪 勁.中國環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41.
[12]潘 岳.環境保護與公眾參與[J].綠葉,2004(4):17.
[13]合 肥 市 人 大 網 .[EB/OL].http://renda.hefei.gov. cn/8541/8542/201306/t20130614_1791152.htm l. [2014/11/24].
[責任編輯:金永紅]
Legal Analysis and Approach of System Construction on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NGO’s Rights of Particip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Zhu He-qun,Tong 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oHu University,Chaohu Anhui238000 China)
On the pro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NGO’s Rights of particip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s,there remain lots of problems which are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at both legal level and practical level.Although some basic provisions have been stipulated in the Constitution,laws,regulations and policies,these provisions haven’t been guaranteed substantively and procedurally from the view of system.It restricted the exercise of Environmental NGO’s Rights of particip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ts 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therefore,wemust build an orderly participation mechanism,accessible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and a good social mechanism to guarante the Environmental NGO’s Rights of particip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nvironmental NGOs;participationmechanism
DF529
A
1005-913X(2017)05-0033-05
2017-03-10
2017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項目(SK2017A0480)
朱鶴群(1968-),男,安徽巢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經濟法、環境法;童 茜,女(1980-),安徽巢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