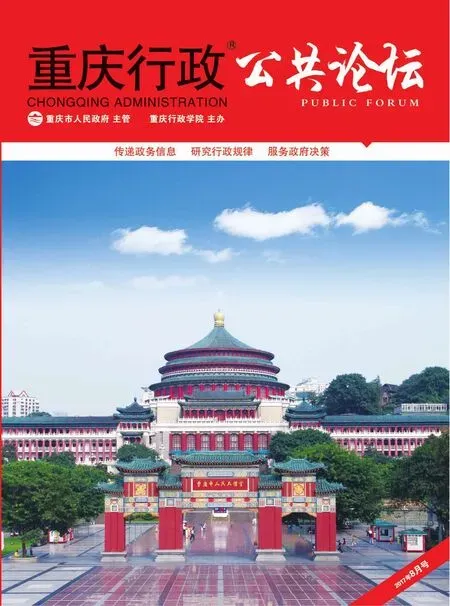“運動式”行政問責的困境及其反思
□李忠漢
☆行政與法☆
“運動式”行政問責的困境及其反思
□李忠漢
行政問責是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發達形態,也是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關鍵環節。目前,中國式行政問責仍徘徊于運動式階段。作為對公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機制,行政問責要真正發揮其應有的功效,必須實現從運動式問責向制度化問責的根本轉變。本文在對當前中國行政問責實踐所面臨的困境進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超越運動式問責的革命思維,強化對政府權力結構的制約與平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轉變“自上而下”的單項式的行政模式,完善異體監督,形成監督合力等措施,以期為中國行政問責走出困境提供一個分析視角。
一、行政問責是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發達形態
在政府治理形態上,民主制對君主制的置換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的必然結果。在君主制下,主權系于君王,甚至是絕對的,凌駕于法律至上。而民主制的一個基本理念是“人民主權”,人民是一切權力的所有者。從邏輯上講,“人民主權”是在國家權力的終極歸屬上,即“誰來做主”的問題上的給予的正當性的回答。但這只是民主政府從理念層面落定為實踐形態的第一步,具有價值上的優先性。與“誰來做主”相承接的是“如何做主”的問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民親歷國務的集體決策,會因“法不責眾”而釀成無責任政治的惡果;而在間接民主的委托代理的法理模式中,人民既給政府授予決策權力,同時也轉嫁了行使這種權力的責任負擔,進而建立可操控的問責和監督體制。這是現代社會尋求大國善治普遍采取的有效途徑。雖然直接民主更切近民主的理想型態,但無法應對大國善治的難題;而代議制采取了看起來不怎么“純粹”的間接民主形式,但這與其說是民主的倒退,不如說是民主的改進:“主人”與“主事”的分離,權責一并轉讓。作為“主人”的人民,不僅給政治精英授予“主事”的權力,而且向政治精英轉嫁了“主事”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反過來成為人民評價政府作為的重要依據。這樣輿論監督、社會監督、法律監督,連同質詢、罷免、彈劾等問責形式一起,就像是一柄達摩克利之劍,始終高懸在政府的頭頂。[1]如果政府及其官員在政府活動中有違法、失職、瀆職、濫權、失責之舉,就可以依法啟動問責機制。
行政問責不僅是民主政治運行的必然邏輯,還是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的根本要求。前者體現的是責任政府和行政問責的政治性,后者體現的是其憲法性和法律性。[2]它強調權責一致、權責對等;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侵權要賠償,這是現代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從法治的角度看,有權利就有相應的義務,有權力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政府及其官員既是行使權力的主體,更是應然的責任主體,在政府權力的運作過程中,必須始終處于被問責狀態。依據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政府及其行使公共權力是基于公民間締約而產生的,其目的是履行契約精神,保護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基本權利。這一“契約”在現代國家形態下,就是作為一國根本大法的憲法和民議機構制定的法律。
從中國政府實踐來看,政府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法治政府、服務政府、廉潔政府和高效政府。這樣的政府首先是責任政府,其基本屬性是憲法性和法律性。這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報告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該報告明確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憲法是保證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權威。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全面貫徹憲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建立健全全社會忠于、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制度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可見,我國社會主義憲法與責任政府和行政問責具有一致性和相容性。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行政問責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的發達形態。
二、中國式行政問責的困境
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危機”,既考量中國人民的智慧,也給中國公共管理帶來了制度創新的契機,最突出的表現是中國行政問責制的啟動。“非典危機”之后,席卷全國的“問責風暴”一浪高過一浪,時至今日,已經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從十年后的今天來看,行政問責制作為中國行政體制的完善和創新,也是中國政府在特定背景下自覺開展的一項自上而下的“健身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必須直面的困境。所謂中國式行政問責的困境是指行政問責制在公共行政領域和公共行政環境中,出現的一些事與愿違的現象,并且這些現象在理論解釋上好像又陷入了悖論之中。筆者認為,當前中國式行政問責必須直面的困境主要有一下幾個方面:
(一)缺失頂層設計
“非典危機”好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使全國人民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盡管以單純的死亡人數來比較事態的嚴重性,各類頻發的安全事故,包括生態安全、食品安全、生產安全尤其是礦難的安全事故,也許更為嚴重。然而,在人民群眾生命、健康、財產和正常生活遭受嚴重威脅的時刻,仍有些官員無視政府的重重禁令,玩忽職守,失職、瀆職、失察、失責行為頻頻發生。在“非典危機”的倒逼機制下,啟動了“問責風暴”。“忽如一夜春風來”,從中央到地方行政問責制一夜之間全面鋪開。這種運動式的問責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其一,高壓的問責態勢專注于瞞報、漏報“非典”疫情和處置不力的官員,并采取撤職、引咎辭職等高官問責方式。其二,理論上準備不足,缺乏可操作性。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行政問責基本上呈現虛設狀態。雖然也有追究領導人責任的情況,但比較零散,更沒有制度化。并且,在傳統的“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人們普遍對追究官員的責任,也就是常說的“民告官”不以為然。故當時對我們來說,行政問責是一種“新制”。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探索中才剛剛起步,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況。行政問責制作為一種追究和實現政府責任的監督機制,其效力的真正發揮,除了得力于高層開展行政問責的堅定決心和問責的高壓態勢外,最為關鍵的是要有一套規范性的問責程序,這包括政府責任失范行為的發現、對責任的法律性和行政性解釋與認定和判斷以及相關責任的追究等。此外,還缺乏明確的可量化的責任標準,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模糊性和原則性的規定。可見,行政問責制在啟動之時,缺乏頂層設計的整體明確性和可操作性,這在以后的行政問責實踐中仍然有一貫的表現。
(二)選擇性問責
目前來看,中國的行政問責實踐還處于一種運動式階段。這種運動式的問責模式不可避免的結果除了上述的草率啟動和理論準備不足之外,還有的就是問責領域的不平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選擇性問責”。首先,這種選擇性表現在所問之“責”類型的不平衡上。“問責制的‘責’包括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法律化的政治責任仍屬于政治責任的范疇,與嚴格的法律責任有著重要的區別。在行政問責上既要追究法律責任,又要追究法律化的政治責任。然而,由于我國在政治責任的制度化、規范化方面還存在著較大的缺陷。因此,在問責實踐中,重在追究因違法、違規、違章、違紀行為直接導致人民生命財產或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損失而引起的法律責任;而對因政策、決策失誤或失職、瀆職、濫權導致人民生命財產或國家利益、公共利益重大損失而引起的法律化的政治責任責‘輕描淡寫’”。[3]其次,由于缺乏一套制度化、規范化的問責標準和程序,在問責的具體實施過程中也表現出很大的選擇性和隨意性。比如在責任的界定上,由于缺失明確的、可操作性的問責標準,所以,在行政過錯行為的主客觀原因的分析以及相關責任的認定上就有很大的選擇性和隨意性,難免是非理由和人情因素充斥其中;甚至一些權力部門借助選擇性問責來施展官場權術,達到排斥異己、爭權逐利的政治目的。最后,選擇性問責還表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順應問責潮流,迎合媒體和大眾的心理,撈取不正當的政績,而推行的一些“問責秀”和“假問責”等現象。
(三)問責文本泛濫與法治精神流失
行政問責是法律規制公權力的整體機制(包括權、利、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法治精神的體現和保障。自2003年以來,問責風暴持續發力,正在演變為一種嚴厲的常態程序。有學者將之解讀為問責制向“制度化、法律化”發展的一個積極信號。但與之相悖的是,雖然這種“疾風驟雨式的問責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收到了整肅社會流弊、震懾行政違法、恢復社會秩序的效果。但是,這種運動式的問責從一開始就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為代價的”。[4]導致法治精神流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前文所述的問責的選擇性、隨意性以及責任設定比較模糊,既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也沒有可操作的標準,是否問責常常取決于領導人的意志。此外,在問責過程中出現的“問責秀”、“假問責”等負面效應,不僅削弱了問責的力度,而且也使公眾產生了質疑。這既導致了法治精神的流失,也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然而,與法治精神的流失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各地各部門制定的問責文本“泛濫成災”,比如,普遍的做法是層層簽定責任狀,層層分解責任,切實做到責任具體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這樣各級政府的任務壓下來,就責無旁貸地落到鄉鎮干部的頭上。據報道有的鄉鎮干部一年要簽幾十個責任狀。其實,這樣的責任狀更多的是一種文字游戲,是“壓力型體制”的產物。法治精神的流失于問責文本的泛濫,這二者相映成趣,令人不解。
(四)官員心理的迷茫和不作為
行政問責制始于2003年的“非典危機”,就其啟動的時機來看,正值于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之中。轉型中的社會既是機遇期,也是眾多社會問題和矛盾的突發期。一方面,社會轉型的壓力使中國公共行政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比如,行政領域交互性和復雜性的增強增加了決策的難度;互聯網及新興媒體管理、醫療衛生監管、環境污染防治等新興領域不斷涌現,使現有的行政監管盲區不斷擴大等。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失范行為的增加;另一方面,在社會轉型中,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引領作用,政府官員必須積極作為,甚至要敢于闖“紅燈”、闖“禁區”和觸“底線”。然而,在高壓的問責態勢和責任制的重壓之下,許多官員感到“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失去了銳意改革創新的勇氣。于是,甘于選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太平官和庸官。這種看似“謹慎”和“低調”的從政哲學,實則折射出諸多官員的迷茫和不作為。
三、中國式行政問責困境之反思
自2003年“非典危機”發力以來,中國的行政問責形成了具有震懾力的“風暴效應”。但從上述困境來看,它仍然徘徊于運動式問責階段,缺乏制度追究的恒久動力。如果沒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體制和機制,無論“問責風暴”多么猛烈,也不過是短期行為。因此,問責困境的有效化解,有賴于問責制度的完善。
首先,要超越運動式問責的革命思維。目前中國的行政問責仍然停留在運動式階段,這種運動式問責的主要特征是開展間歇式的問責風暴,將問責簡單等同于領導引咎辭職、上級對下級的整頓和事后的懲罰舉措等。這是對行政問責較膚淺的理解,還沒有觸及問責制的根本之義,是一種典型的革命思維方式在行政問責中的應用。這種運動式的問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強化官員責任意識,減少決策失誤和失范行為的發生以及震懾行政違法等作用,但絕非行政問責的常態化。一旦風歇雨住,容易死灰復燃,甚至變本加厲。因此,超越革命思維,尋求常態化的治理方式,這是中國行政問責從運動式、非常態化走向制度化、常態化的前提和基本思路,只有把思路搞清楚了,理順了,改革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超越革命思維要有“后手”,所謂后手就是制度和法律。一般來講,行政問責制是通過鎖定行政失范行為來依法追求相關行為主體的責任的,而行政失范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規范行使政府權力甚至濫用政府權力導致的。因此,行政問責實際上是對公共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制度安排。前已述及,權、利、責是制度(法律)制約和監督公權力的整體機制。在這個整體機制中,如果缺少“責”的制約,手握公權力的人就有可能運用手中的“權”去追逐“私利”而不是“公利”。而行政問責作為一種事后的監約機制,其有效性的發揮依賴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權力結構本身的制約與平衡,權力內部結構的制約和平衡是確保權力的規范性和有效性的基礎。如果缺少權力結構的制約與平衡,僅僅憑借事后的問責來實現對政府權力的制約與監督是不太現實的。并且,此種情況下的問責往往是乏力的。當然,本文所說的權力結構的制約與平衡不是西方政體意義上的“三權分立”,而是在行政權力內部的分工與制約,在政府管理系統內部,將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分離,并在運行的過程中進行制約與協調的管理體制。比如,行政三分制就是一種典型的行政“分權”。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所指出的,“強化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二是改變“自上而下”的單項式的行政運作模式。行政問責是對政府公共管理進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及其官員要回應民眾的需求,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因為“只有當受治者同治者的關系遵循國家服務于公民而不是公民服務于國家,政府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原則時,才有民主制度存在”。[5]因此,只有轉變自上而下的單項式的行政模式,形成多元參與的雙向行式政模式,才能改變行政問責中異體監督,尤其是公民監督和媒體監督相對薄弱的狀況。三是讓權力在陽關下運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的,要“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完善黨務、政務和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推進決策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也是行政問責制真正發揮實效的根本之策。再者,行政問責必須納入法治化和程序化的軌道。從法的一般意義上講,程序是任何一項健全制度必備的要素,正是程序決定了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通過程序保障在責任面前人人平等,相關責任人都要依法追究其責任,杜絕在問責過程中出現的“替罪羊”、“丟車保帥”的現象。程序性問責都是依據法律的,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完善的問責法律。問責主要依據還是一些規范性的文件,這些文件雖然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但只能算是內部紀律規范。并且,對問責的標準、方式和程序均缺乏全面的、系統的規定。因此,當務之急是制定一部完整的問責法規,包括問責事由、問責主體、問責范圍、問責形式、問責程序等。同時,也要考慮到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際情況,對于在行政體制改革中敢于闖“紅線”、觸“禁區”的官員要給予特殊考慮,在某種程度上實行“免責”機制。這樣才能形成正向激勵,發揮官員的改革創新精神和在社會轉型中的引領作用。
最后,完善異體監督。官員的責任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主要有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目前在實踐中主要鎖定的是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前者的追究主體是行政法治監督機關和司法機關,后者是人民代表機關。我國對行政官員的問責常常止于黨紀處分和行政處分,也就是說,目前的問責更多地是內部的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也叫同體監督;而外部的人大、政協、媒體、民意等異體監督十分薄弱。因此,在更好地發揮同體監督作用的同時,應完善異體監督,把二者綜合起來才能形成強大的問責“合力”。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我國的權力機關,責無旁貸地應成為最重要的異體問責機關。在人大的監督上可以進行大膽改革和創新,雖然不易于完全移植西方大多數法治發達國家實行的議會對官員的彈劾、罷免以及提出不信任案等做法,但可以進行有益的借鑒,強化和完善人大和常委會對政府官員的質詢、決策審議和對失職、瀆職官員的罷免、撤職制度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特別是加強各級人大和常委會對政府及其官員質詢的常態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尤為重要,它能夠大大強化現行問責的震懾力。[6]此外,對于政協、媒體、民意等異體監督也要給予充分的重視。在實踐中可以進行有益的探索,比如在政協機關內部設置專門機構實施監督和問責。充分重視媒體和民情輿論在行政問責中的線索作用,在保證其客觀、公正、理性的同時,要開辟更多的參與渠道,比如通過建立反映社情民意的網站,強化對行政失范行為的監督等。再者,政府及其官員作為一種“公共人”,也要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遵守職業操守,嚴格自律,樹立良好形象;道德責任理所當然應納入到問責范圍內。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在完善中國行政問責制上將實現質的飛躍。
總之,走出當前行政問責的困境,必須實現運動式問責向制度化問責的根本轉變。只有如此,才能有效發揮行政問責對公權力進行制約和監督的恒久動力,其承載的憲政民主和法治政府理念才能落到實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行政問責作為國家治理能力中自我“糾錯”和“”修復”功能的重要體現,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要環節。因此,完善行政問責制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1]張鳳陽等.政治哲學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65.
[2]蔣勁松.責任政府新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4.
[3]姜明安.“問責風暴”深層次思考:政治責任是否應當法定化[J].人民論壇,2008(21):34-35.
[4]王仰文.中國式問責悖論的政治學解釋[J].求實,2014(3):54-56.
[5]喬·薩托利.民主新論[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38.
[6]姜明安.“問責風暴”深層次思考:政治責任是否應當法定化[J].人民論壇,2008(21):34-35.
作者: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