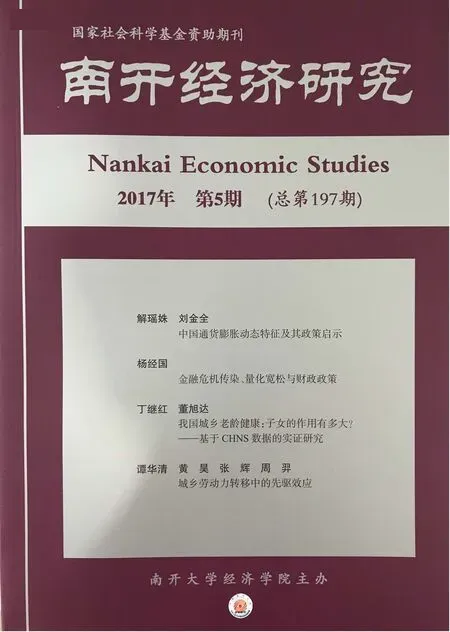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
譚華清 黃 昊 張 輝 周 羿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
譚華清 黃 昊 張 輝 周 羿?
本文使用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庫 2008年農村住戶調查(CHIP2008)數據,將最早外出時間在 1984年到 1992年之間的農民工定義為早期農民工,基于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信息不完全,我們分析了他們在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實證結果表明,早期農民工越多的地區,當地的農民外出的概率也越高,即城鄉勞動力轉移中存在先驅效應。考慮到信息傳播的質量,我們根據早期農民工的平均教育以及當地其他農民的平均教育進行分組回歸,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地區,先驅效應越強。本文還發現,先驅越多的地區,當地外出的農民工的行業集聚特征越明顯。作為穩健性檢驗,早期農民工定義的調整以及將1978年以前因外生因素外出的農村勞動力作為早期農民工的替代變量的分析都沒有改變文章的結果。
信息不完全;先驅;城鄉勞動力轉移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村成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一員,其轉移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對近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Brandt和Zhu,2010)。城鄉勞動力轉移的另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來自某一個地區的農民會在同一個行業內集聚,比如溫州的鞋業與打火機、著名的湖南婁底新化的復印行業等。根據馮軍旗(2010)的估計,目前從事復印打印行業的新化人大概有20萬人,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新化現象”。“新化現象”不是個例,城鄉勞動力轉移過程出現了大大小小類似的“新化現象”。比如深圳的出租車司機中超過 50%,“的哥”來自湖南省攸縣(陽智波,2013),還有甘肅以家政出名的“禮賢妹”等。既然不是個例,那么這些現象背后肯定有共同的特點。馮軍旗(2010)在描述湖南新化打印業的時候指出,剛開始只有本縣少數人從事該行業,在他們的帶動和影響下,當地越來越多的人離開農村并從事該行業。因此,這些早期農民工就像先驅一樣,為后來的農民工領路,帶領更多的同鄉外出,并且帶動他們從事和自己相似的行業。
先驅的出現對于中國城鄉勞動轉移極為重要。首先,在 1984年以前,嚴格的戶籍制度讓農村勞動力自由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務工或經商幾乎不可能,所以城市對于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而言是個未知的世界。其次,即使他們容許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由于教育程度很低(樣本中1992年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是7.2年左右),他們通過招聘廣告、報紙、電視等媒體獲得招聘信息的渠道有限,甚至很多農民工普通話都說的不好,幾乎不可能通過正式勞動力市場來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①中國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林毅夫,2012;張勛和徐建國,2016)。相對來說,東部地區發展要快于中西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勞動力要外出務工通常會選擇東部沿海地區。。
這樣,先驅的出現對于農民外出就業的作用顯得非常重要。早期農民工扮演著多重角色:(1)信使,向當地其他農民傳遞城市信息,這些信息包括勞動力市場信息和城市生活信息等;(2)社會資本,先驅的出現隨即成為當地其他農民外出就業的社會資本,成為農民工社會網絡的一部分。這些先驅通常會在老鄉外出就業提供直接的幫助,比如介紹工作、提供食宿等,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農民外出的成本。這兩種角色都會促進當地其他農民外出就業。但是先驅所帶來的社會網絡的效應和之前的討論農民工社會網絡的文獻(比如,Zhao(2003))沒有什么區別,所以本文試圖強調信使這個角色在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作用。
通常人們做出選擇之前需要了解兩個層面的信息:(1)知道有這個選擇,我們稱之為“打開眼界”;(2)然后把該選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盡量轉換為風險,我們稱之為“形成預期”②風險和不確定性是不同的。風險是知道成功或失敗的概率,而不確定性是連成功的概率是多少都不知道(Knight,1921)。。農民外出就業同樣如此,信息不完全和不確定性是阻礙農民外出就業的重要因素之一(Bryan 等,2014)。農民首先要知道存在去城市就業的這個選項,其次要了解去城市勞動力市場就業的風險與不確定性,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選擇外出打工和在家務農之間做出一個理性的抉擇。先驅這個信使的特殊性在于,他們是第一批農民工。對于那些對城市一無所知的農民而言,他們同時傳遞了兩個層面的信息:城市就業是除了務農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即“打開眼界”;城市就業是可行的,即預期的收益是可觀的。由于大量招納農民工的城市民營經濟的崛起也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所以農村絕大多數農民對城市勞動力市場是一無所知的,他們不知道還有外出就業這種選擇,而先驅的出現則告訴了他們這種選擇的存在。這也是先驅與后來文獻所提到的農民工的社會網絡所提供信息的不同。我們把這種帶動其他農民離開農村進城務工或者經商的特有作用稱為先驅效應。先驅效應的作用應具體體現為兩個方面:(1)帶動其他農民離開農村進城務工或者經商;(2)帶動其他農民從事和他們自己相似的行業。由于數據的信息有限,我們目前還不能直接考察先驅效應的第二個方面,但是作為替代,我們知道所有當前外出的農民工所在行業,據此,可以計算行業集中度指數,文中選擇了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作為農民工行業集中度的度量。
本文使用CHIP2008年農村住戶調查數據實證分析了先驅早期外出務工農民的數量對于當地農民外出就業的影響。估計的效應包括了先驅效應的兩個方面,因此算是一個加總的效應。隨后,我們還考察了早期農民工數量與農民工行業集中度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先驅數量越多的地區,當地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高。即早期農民工數量越多,先驅效應越強。在考察先驅與農民工行業集中度的分析中,我們發現,早期農民工比例越多的地區農民工行業集中度越明顯。這和現實經濟中觀察到的“新化”現象是一致的。
最后,我們做了穩健性檢驗。首先我們調整了早期農民工的定義。接著,我們著重處理了內生性問題。考慮到 1978年以前,戶口制度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離開當地農村大部分是由于國家命令,比如響應國家號召參與重大基礎設施的修建(Liu,2008),因此 1978年以前外出的農民可以看成是因為外生因素外出的。文章用這一部分外出的農民作為早期農民工的替代變量,回歸表明,先驅效應仍然顯著成立。
二、文獻綜述
本文研究的主題首先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文獻相關。以往的文獻全面地討論了眾多因素對于農民流向城市的影響。Lall等(2006)的綜述總結了影響農民流向城市的主要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城鄉收入差距;農民的個人特征,比如性別、年齡、教育、婚姻狀況等;家庭特征,比如家庭規模、擁有的土地面積、家庭財富等;還有社區特征,比如所在地區是否遠離城市、是否通電話等。此外,信息的影響很久以來也是研究城鄉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方面。信息對于城鄉勞動力轉移是重要的,城市信息的不完全是導致農民返回農村的重要因素(Allen,1979;Da Vanzo 和Morrison,1981)。同時,信息的成本對于不同的農民是不一樣的。Maier(1985)和 Stalker(1994)都指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信息成本越低,因為他們更有可能知道如何獲取高質量的信息。而這些研究并沒有關注第一批農民工的作用。也有很多研究中國經驗的文獻(趙耀輝,1997;Zhao,1999a;Zhao,1999b;Liu,2008)。這些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大。同樣的,這些文獻都沒有討論早期農民工在城鄉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本文研究最相關的是討論社會網絡與城鄉勞動力轉移的關系的文獻。如何區別本文所提出的先驅效應和社會網絡的作用是本文的關鍵。社會網絡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作用顯而易見(Banerjee,1983;Massey,1987;Carrington 等,1996;Munshi,2003)。社會網絡的作用體現在很多方面:(1)降低遷徙成本。通過向親朋好友借貸降低遷徙本身的貨幣成本(比如交通費和房租費用等)(Carrington等,1996),降低融入新環境所需的心理成本(Massey,1987);(2)增加找到工作的機會,例如有研究表明勞動力可以借助社會網絡比較容易獲得就業信息(Schwartz,1973),而且還能夠獲得更好的就業信息從而獲得更高的工資(Kono,2006)。對于中國經驗,也有很多文獻討論了社會網絡對于外出就業的影響(Meng,2000;Zhao,2003)。他們發現社會網絡的確在農民外出就業的過程中起了促進作用。后續的文獻從社會網絡的不同維度深入討論社會網絡對農民非農就業或者外出就業的影響。比如胡金華等(2010)利用福建的訪談數據分析了社會網絡的規模、實際強度、名義強度、行業異質性等特征對農民外出就業的影響;陸益龍(2011)分析了農民不同類型的關系網絡對于農民非農就業的影響;而劉璐寧(2013)進一步區分了社會網絡對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作用。先驅本身會成為社會網絡的一部分,但是他們是社會網絡形成的種子,作為種子本身,他們和網絡是不同的。網絡是點和線的連接,在改革開放初期,先驅在城市里至多是零星的點。研究社會網絡的文獻,不管他們是從什么維度討論,都是假設社會網絡是給定的,然后用不同的指標衡量這些社會網絡。本文與這些文獻的不同在于,我們研究社會網絡形成之前的那些零星的點的作用。圖1和圖2比較形象地對比了先驅和社會網絡的作用。
很顯然,先驅和社會網絡傳遞的信息是不同的。研究社會網絡的文獻都有一個潛在假設,農民已經知道有外出就業這個選擇,而事實上,這一假設和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的國情是不符合的。在放開城鄉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之前,公有制經濟構成了城市經濟的絕大部分,接納農民工的民營經濟的興起也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情,因此,對于絕大多數農民而言,城市并不是他們的勞動力市場。對于一個未知的世界,風險是巨大的而且通常是被高估的,需要一個人捅破這層窗戶紙。這些人就是先驅,在魯迅的作品里有另一個名字——第一個吃螃蟹的人①魯迅,《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為了區分社會網絡和先驅的作用,我們做了兩種處理:(1)直接在回歸中加入反映社會網絡的變量;(2)刪除依靠社會網絡找到工作的樣本。這些處理都沒有改變我們的結論:先驅效應仍然顯著存在。

圖1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先驅的作用

圖2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社會網絡的作用
所以本文的貢獻在于,將城鄉勞動力轉移看成一個動態的充滿摩擦的過程,基于此,提出了與社會網絡效應不同的先驅效應。之前討論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文獻較少涉及這一點。
三、理論假說與實證策略
(一)理論假說
從理論上講,給定城鄉工資差異,控制了農戶的其他特征,越了解城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的農戶就越有可能外出就業①衡量一個村莊早期農民工數量我們采用了兩個指標:一個是絕對數量;一個是相對數量,即比例。在基本回歸中我們報告的是絕對數量,在第四部分我們報告了早期農民工比例的回歸結果。。因此,我們可以預計,早期農民工越多的地區,其他農民外出的概率越大,即有假說1。
假說1:其他條件不變,早期農民工越多的村莊,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大。
接著,我們考察先驅效應的第二個層面,即先驅越多的地區,農民工就業的行業集中度越高。于是有假說2。
假說2:其他條件不變,早期農民工越多的地區,農民工就業的行業集中度越明顯。
考慮到早期農民工自身的差異,主要體現為信息種子的質量差異。我們用教育程度衡量早期農民工能力的差異。作為信息的最初接受者與傳遞者,能力越強的早期農民工,所吸收的信息越多,傳遞信息的時候錯誤越少。他們對當地農民的影響應該越大。于是,我們提出假說3.1。
假說 3.1:其他條件不變,村莊內早期農民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則先驅效應越大。
不僅信息的傳遞者有能力的差異,信息的接受方,也就是當地其他農民也有能力上的差異。這里還是用教育代理信息接受與傳遞能力。那么,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區,當地的農民吸收與傳播信息的效果越好,于是,我們提出假說3.2。
假說3.2:其他條件不變,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村莊,先驅效應越大。
(二)實證策略
我們主要關心早期農民工的出現對于其他人的外出決策是否有影響。很顯然,本文采用標準的 logistics 回歸模型是合適的。本文還考慮了農民可能面臨三種就業選擇的情況:外出就業,留在農村當農民,留在農村非農就業。對于這種情況,我們使用標準的multinomial logit(Mlogit)模型分析。
考慮到早期農民工的出現可能與村莊的特征有關,包括村莊的富裕程度、當地村民的平均風險偏好程度、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間等。我們會控制這些變量,以減少潛在的遺漏變量。此外,我們會采用穩健性檢驗來處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
四、數據與變量定義
(一)數據介紹
本文使用了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庫(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簡稱 CHIP)2008年的農村調查部分。該數據庫被廣泛用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等問題的研究。農村樣本數據包含三個部分:(1)農民個人信息,包括農民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就業經歷等;(2)家戶信息,這主要包括家戶的規模和家戶的資產消費情況;(3)村莊(社區)信息,社區特征包括所在地區是否靠近城市、勞動力就業結構以及是否是貧困地區以及村級管理的信息等。沿著主流文獻的方法,本文也只關注那些完整地報告了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和就業情況等信息的16歲到64歲的農村居民,并且還刪除了那些全職學生、退休的以及有殘疾或者重大疾病的農村居民。最后本文的樣本量達到了20809個,這些樣本分布在東、中、西9個省市中的82個縣285個行政村之中①東部省份有江蘇、浙江、廣東;中部省份有河北、安徽、河南和湖北;西部省份有四川和重慶。。
(二)變量描述
我們的關鍵變量是早期農民工。由于 CHIP2008年的數據問了農民第一次外出務工的年份,我們可以根據最早出去務工的時間先后順序定義早期農民工。具體來說,我們把最早在1992年及以前務工的農民定義為早期農民工。圖3表明1992年以前農民工的數量并不多,而這符合我們關于先驅的理解。

圖3 第一次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CHIP2008)
此外,遵循主流文獻(Zhao,2003;Liu,2008)的定義,我們把 2008年外出就業或者經商三個月以上的定義為外出就業者(即農民工),沒有外出就業的為農村就業者。農村就業者分為:(1)農民;(2)當地非農就業。我們把留在當地從事非農工作的勞動力稱為當地非農就業者。考慮到生活在離縣城比較近的農村的居民,可能通過在縣城里的交往獲得城市里的信息,所以我們增加離縣城的距離(time to country)作為控制變量①根據Myers等(2012)的研究,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比如電視和網絡,除了通過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獲取信息,人們對于類似于外生的媒體的使用越來越多,不過二者并不是完全可替代的。我們試圖控制這種非社會網絡的渠道,但是 CHIPS2008并沒有類似的數據。我們控制了村莊的通電時間段以及到達縣城的距離也是一種嘗試。考慮到農村互聯網發展相對滯后(高小衛,2007),農民工對于互聯網的使用相對較少。。表1概括了我們回歸中使用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

表1 變量的定義與統計描述
表 2描述了早期農民工相關的特征。我們把 1992年有外出就業能力的所有樣本放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子樣本(即在1992年年齡達到16歲的樣本),據此考察早期農民工的特征。

表2 早期農民工的描述性統計
從表 2可以看出,早期農民工在第一次外出就業的時候比非早期農民工外出就業的要年輕,而且更多的是男性,風險偏好更大,但是兩類人的教育程度沒有明顯差異。
五、實證分析
先驅效應包括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帶動農民外出,第二個層面是外出的農民更多地集聚在同一行業。相應的,實證部分也包括兩部分,首先考察先驅的出現對于外出的促進作用,然后再考察他們對于外出農民工的行業集聚作用。
(一)先驅效應與農民外出
表3分別報告了logit、multinomial logit(Mlogit)和OLS的估計結果。所有回歸的標準誤都聚集(cluster)在縣級層面。Mlogit回歸是考慮了農民有三種就業選擇的情況,即選擇留在農村當農民、外出就業或者留在農村非農就業。從表3可以看出,早期農民工越多的村莊,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大①考慮到早期農民工自身也會受到其他早期農民工的影響,這里的當地農民包括了早期農民工自身,即使不把早期農民工算作當地農民,回歸結果也基本不變。。
總體來說,關于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與以往研究城鄉勞動力轉移的文獻基本一致。外出就業的農民更多的是單身的年輕男性。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高。對于家戶特征來說,財富的影響是不明顯的,家庭規模越大外出的可能性越大①家庭規模在問卷中包括了父母、岳父母等,一定程度上和這些老年人生活在一起會幫助照顧孩子從而有利于年輕的勞動力外出。。如果考慮農民具有三種就業選擇:當地務農、外出就業和當地非農就業,則土地面積大傾向于降低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如果認為農民只有兩種選擇的話,則土地規模
大傾向于增加農民外出的概率。而事實上,將農民看成是具有三種就業選擇的時候,土地規模大對于外出就業是阻礙作用,這和 Zhao(1999a)的發現是一致的①這是因為,從表3可以看出,土地規模對于農民當地非農就業的阻礙作用要大于外出就業的阻礙作用,所以認為農民只有是否外出兩種選擇的話,外出就業將會與當地非農就業相比,于是出現正向的結果。。對于村莊特征的話,鄉鎮企業越發達則當地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低。平均風險偏好越高,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間越早,當地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大,但是都不顯著。和Zhao(2003)的發現一致,農民工的社會網絡越強,當地農村勞動力外出的概率越大。

表3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
(二)先驅效應與行業的集聚
雖然受數據所限,我們不能知道早期農民工最早外出時的行業,不過我們知道現在農民工所處的行業。作為替代選擇,我們考察了一個縣早期農民工比例和現在農民工的行業集中度之間的關系。本文選擇 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作為行業集中度的度量②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的基本原理,每個行業的人數除以總外出人數,然后求平方和。在計算指數的時候,我們刪除了現在(2008年)還是農民工的早期農民工。。表 4報告了回歸結果。由于回歸是在縣級層面,所以控制變量是縣級層面的特征③村莊層面的早期農民工數量很少,計算出來的 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誤差較大,所以這里我們用縣級層面的數據。。我們選擇了鄉鎮企業就業比例(Share of TVE)、農業就業比例(labor share agricul-ture)、工業就業比例(labor share industry)、平均風險態度以及縣的人口數作為控制變量。整個回歸分為三列,第一列不加任何其他控制變量,第二列加入所有縣級層面的其他控制變量,在第二列的基礎上再加上省級虛擬變量構成第三列。不管如何設定,回歸系數都比較穩定,而且這三列的回歸結果都表明,當地早期農民工比例越高,行業集中度越高。這和我們觀察到的“新化現象”是一致的。從估計量上,如果早期農民工比例提高1%,,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提高0.148%,左右。

表4 先驅與農民工的行業集聚
(三)先驅效應的影響因素:早期農民工的平均教育程度
Stalker(1994)發現教育程度會影響信息的獲取。教育越高的勞動者獲取的信息越多,質量越高,而且教育程度越高的勞動者更容易在城市勞動力市場表現更好。因此,如果當地的早期農民工群體自身的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們所獲得的信息水平越高,或者他們在城市勞動力市場表現更好,則他們對當地農民的影響應該越大。根據村莊內早期農民工的平均教育的均值把樣本分成兩組:高教育組和低教育組①用村莊內早期農民工平均教育的中位數分組所得結果仍沒有變化。。表5報告了相關回歸結果。表 5表明,和低教育組的回歸(1)、(2)相比,高教育組的估計系數更大而且更加顯著。可見,高教育組的先驅效應要比低教育組要大而且更加顯著②表2已經說明,早期農民工的教育并沒有顯著高于同時代其他農村勞動力,所以他們并不是教育程度高的。這說明,先驅效應并不是來自于因為他們教育高而使得他們在當地就有一定聲望,進而容易被其他農民視為榜樣。。相比于平均教育程度較低的組別,平均教育程度越高的早期農民對于當地其他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要高一倍以上。

表5 先驅效應與早期農民工的平均教育程度
(四)先驅效應的影響因素:流出地的平均教育程度
類似的,我們把樣本根據當地其他農民的平均教育程度的高低進行分組回歸。表6提供了回歸結果。我們看到了和表5類似的結果。和低教育的當地其他農民相比,對于高教育的當地農民而言,先驅效應更大而且更加顯著。這支持了假說 3.2。從接受方來看,如果當地其他農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高,那么他們能夠更好地消化和吸收早期農民工所帶來的信息。根據平均教育程度的分組回歸表明,對于平均教育程度越高的村莊,先驅效應比教育程度較低的村莊要大70%,。

表6 先驅效應與當地(村)其他農民的平均教育程度
總體來說,關注教育與先驅效應的關系其實是在考慮信息傳播的質量問題。從表5和表 6的實證結果來看,高教育地區的先驅效應要明顯大于低教育地區。原因可能在于教育越高信息傳播的質量越高,因此提高當地教育對于促進信息的傳播也有重要意義;也可能是高教育的先驅在城市勞動力市場表現更好,對其他農民的激勵更大。
六、穩健性檢驗
(一)調整早期農民工的定義
本文提出兩個新的關于早期農民工的定義:(1)最早外出務工或者經商的年份在1978年至 1992年之間的農民;(2)將早期農民工數量變量換成早期農民工比例。早期農民工比例定義為,村莊內早期農民工數量除以從未外出的農民的數量。在這里,我們只考察了不同定義早期農民工對于當地其他農村居民外出就業的影響。為了節省空間,我們只在表7中報告少數變量的回歸結果。和表3的一致,表7也告訴我們,對于早期農民工數量越多的地區,當地的農民外出就業的概率越高,而選擇當地非農就業的概率越低。
雖然我們在回歸中加入了社區層面的控制變量,但是內生性的問題仍然可能存在。考慮到因為 1978年外出的農民工在村莊層面非常少,所以我們選擇 1978年以前縣級層面外出的農村勞動力作為村莊層面早期農民工數量的替代變量(early migrant 1978)。在1978年以前,戶口制度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離開當地農村大部分是由于國家命令,比如響應國家號召參與重大基礎設施的修建(Liu,2008)。因此1978年以前外出的人可以看成是外生因素。表8可以看出,早期農民工越多的地區,當地農民外出的概率越大。

表7 早期農民工對于當地農民就業選擇的影響:其他定義

表8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外生因素外出的早期農民工
(二)信息效應還是網絡效應?
早期農民工對于后續農民外出的影響的作用機制并不單一:既有信息的作用也有網絡的作用。由于社會網絡對于外出就業的作用已經較多的討論,我們重點強調信息的作用。雖然在之前的回歸中,我們加入了反映農民工社會網絡(network)這個變量,但是并不能完全分離出信息效應和網絡效應①社會網絡也有信息作用,但是社會網絡的信息作用和先驅帶來的信息作用是不一樣的。在先驅出現之前,農民可能對于去城市務工是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有這個選擇,先驅就扮演著刺破信息面紗的作用。。先驅效應對于那些依靠親朋好友找到工作的農民工而言,既有信息效應也有網絡效應,而對那些找工作依靠自己的農民工而言,先驅效應更多的是信息效應。而這種信息效應是先驅效應最特殊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刪除那些找工作是依靠親戚朋友或者熟人的農民工樣本,然后進行回歸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檢驗信息效應的大小。回歸結果報告在表9中。從表9可以看出,先驅效應仍然顯著存在,而且和基本回歸(表 3)相比,估計系數和顯著性基本沒有差別,因此我們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表9 城鄉勞動力轉移中的先驅效應:信息的作用
(三)先驅效應的動態特征
回歸中,我們已經控制了大量的可能影響早期農民工數量的社區層面變量,比如當地農戶的平均風險偏好、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間、村莊的富裕程度等等,而且用 1978年以前因外生因素外出的農民作為早期農民工替代變量的結果仍然支持我們之前的發現。接下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潛在的遺漏變量問題可能并不重要。
根據農民最早外出的年份,我們可以知道每一年都有多少第一次外出務工的農民。我們從 1993年開始為每一年都構造了一個是否是當年第一次外出打工的虛擬變量,然后用該虛擬變量對村內早期農民工的數量進行回歸②控制了每個人的性別、年齡、年齡的平方以及教育程度、村莊富裕程度,而家庭規模、家庭財富等變量都是度量了在2007年的水平,不應該控制在回歸中。。把每一次的回歸系數和95%,的置信區間保留下來,根據與1992年間隔的年份數畫出圖4,比如1993年則間隔為 1,1994年則間隔為 2,依此類推。我們發現回歸系數在第一年(1993年)達到最大,之后逐步下降,到第8年(2001年)開始就不顯著了。這說明,先驅對于外出的直接效應在第8年以前是顯著的①受先驅影響的農民進一步影響其他農民,這種效應稱之為先驅的間接效應。。從圖4可以看出,早期農民工對外出就業帶來的正向且顯著的直接效應是隨時間遞減的,這說明了先驅效應至少不是來自不隨時間變化的其他變量。如果存在某種不隨時間變化的遺漏變量使得當地早期農民工數量越多的同時也會使得當地農民外出的概率越大,比如當地的農民天然的喜歡冒險(回歸中已經控制了),那么我們將不會看到,先驅的直接效應是逐年遞減的。因此,這類的遺漏變量或者內生性問題并不嚴重。

圖4 先驅效應的動態特征(1993—2002年)
七、結 論
本文關注了最早一批離開農村去城市務工或者經商的農民工對于城鄉勞動力轉移的先驅效應。借助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 2008年農村部分(CHIP2008)數據,我們考察了一個地區先驅的數量與當地農民就業選擇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先驅越多的地區,當地的農民更愿意外出務工。我們把這種效應稱之為先驅效應。考慮到信息傳播的質量,我們首先根據當地早期農民工的平均教育程度進行分組回歸,然后根據當地所有農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進行分組回歸,不管是從信息的傳播者角度(早期農民工),還是從信息的接受者(當地其他農民),我們都發現,高教育的地區先驅效應要明顯高于低教育地區。因此,提高農村的教育對于促進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在考察先驅與農民工行業集中度的分析中,我們發現,早期農民工比例越多的地區農民工行業集中度越明顯。從估計量上,如果早期農民工比例提高 1%,,行業集中度(Herfindahl-Hirschman)指數提高 0.148%,左右。最后,我們做了穩健性檢驗。首先我們調整了早期農民工的定義,這種定義的調整并沒有改變我們的結論。接著,文章著重處理了內生性問題。考慮到1978年以前戶口制度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離開當地農村大部分是由于國家命令,比如響應國家號召參與重大基礎設施的修建(Liu,2008),因此1978年以前外出的農民可以看成是因為外生因素外出的。文章用這一部分外出的農民作為早期農民工的替代變量,回歸結果表明,先驅效應仍然顯著成立。
先驅的意義在很多方面都有體現,本文借助較為穩健的實證分析方法從勞動力轉移的角度討論先驅的作用。可以歸納兩點政策含義,首先,在信息摩擦比較大的經濟環境下,從來沒有外出就業的農民會因為高估外出就業的不確定性而不敢外出。有了先驅之后,通過減少信息摩擦,降低外出就業的不確定性等機制促進老家的農民外出。因此,在類似的領域或者環境下,政府可以通過補貼等方式鼓勵先驅的出現從而帶動其他經濟個體的跟進投入,這會有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們也看到了,農村平均教育程度越高,則先驅效應也越大,即當地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通過增強先驅效應的方式促進農民外出。但是如何理解這一結論所暗含的政策含義還需要結合當地經濟條件。隨著《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的發布,我國的城鎮化導向有所調整,中小城市和城鎮的發展成為重點。對于城鎮化潛力很薄弱的地區比如中西部農村地區或者貧困山區,鼓勵農民外出流向附近的中小城市應該是政策著力點。對于這種情況,提高當地教育水平是有助農民外出的。而對于具有城鎮化潛力的小城鎮地區或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則可能需要留住人而不是鼓勵他們外出。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留住當地勞動力的同時采取政策鼓勵周邊農民流入,這些政策包括在社會保險方面的優惠以及落戶方面的優惠等等。因此,具體政策的制定也需要因地制宜。
[1]馮軍旗. 新化復印產業的生命史[J]. 中國市場,2010(13):5-8.
[2]高小衛. 中國城鄉數字鴻溝問題研究[D]. 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7.
[3]胡金華,陳麗華,應瑞瑤. 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社會網絡的視角[J]. 農業技術經濟,2010(8):73-79.
[4]林毅夫. 中國經濟專題 [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劉璐寧. 社會網絡視角下農村勞動力非農轉移的代際比較[J]. 農村經濟,2013(4):74-78.
[6]陸益龍. 關系網絡與農戶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基于 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實證分析[J].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1):45-55.
[7]陽智波. 深圳市“攸縣的哥”的身份建構研究[D].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
[8]張 勛,徐建國. 中國資本回報率的驅動因素[J]. 經濟學季刊,2016(3):1081-1112.
[9]趙耀輝. 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為基礎的研究[J]. 經濟研究,1997(2):37-42.
[10]Allen J. Information and Subsequent Migration:Further Analysis and Additional Evidence [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79,45(4):1274-84.
[11]Banerjee B. Social Network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Empirical Evidence on Chain Migration in India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1983,17(2):185-96.
[12]Brandt L.,Zhu X.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R]. IZA Discussion Papers No. 4764,2010.
[13]Bryan G.,Chowdhury S.,Mobarak A. M. Underinvestment in a Profitable Technology:The Case of Seasonal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J]. Econometrica,2014,82(5):1671-748.
[14]Carrington W. J.,Detragiache E.,Vishwanath T. Migration with Endogenous Moving Cos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6,86(4):909-30.
[15]DaVanzo J. S.,Morrison P. A. Return and Other Sequences of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Demography,1981,18(1):85-101.
[16]Knight F. H. 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 [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21.
[17]Kono H. Employment with Connections:Negative Network Effec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81(1):244-58.
[18]Lall S. V.,Selod H.,Shalizi Z.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Survey of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915,2006.
[19]Liu Z.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19(3):521-35.
[20]Maier G. Cumulative Causation and Selectivity in Labour Market Oriented Migration Caused by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Regional Studies,1985,19(3):231-41.
[21]Massey D. S.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6):1372-403.
[22]Meng X.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3]Myers S. A.,Zhu C.,Leskovec J. Information Diffus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 in Networks [J].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2012:33-41.
[24]Munshi K. Networks in the Modern Economy: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 S. Labor Marke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2):549-99.
[25]Schwartz A.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Mi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5):1153-69.
[26]Stalker P. The Work of Strangers: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M]. 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1994.
[27]Zhao Y. Labor Migration and Earnings Differences:The Case of Rural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9,47(4):767-82.
[28]Zhao Y. Leaving the Countryside: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2):281-86.
[29]Zhao Y.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The Case of China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03,21(4):500-11.
JEL Classification:J61 O15 R23
The Pioneer Effect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Tan Huaqing1,2,Huang Hao3,Zhang Hui4and Zhou Yi5
(1.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 Harvest Fund Management Co.,Ltd,Beijing 100005,China;3.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Hangzhou 310018,China;4.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5. Center of Social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CHIP2008),we analyze the pioneer effe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We define those who tried his first migrating experience during 1984 to1992 as the early-migrant which is viewed as pioneer during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process. We find there indeed exists pioneer effect:The more early-migrant a village has,the more likely the rural labor become a migran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we have grouped the sample based on the average education of the early migrant or the rural labor in a village. We find that the pioneer effect will be stronger for village with more education. We also find that in the rural area with more pioneer,its migrants tend to be more clustered in some industry. Finally our results are robust when we modify our definition of early-migrant and use rural labor who exogenously left the rural area before 1978 to be a migrant as an alternative of rural early migrant.
Incomplete Information;Pioneer;Rural-urban Migration

10.14116/j.nkes.2017.05.008
? 譚華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郵編:100871)、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郵編:100005),E-mail:htan023@163.com;黃 昊,浙江財經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郵編:310018),E-mail:ehome01@163.com;張 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郵編:100871),E-mail:nk94zhang@pku.edu.cn;周 羿,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郵編:100871),E-mail:yizhou@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