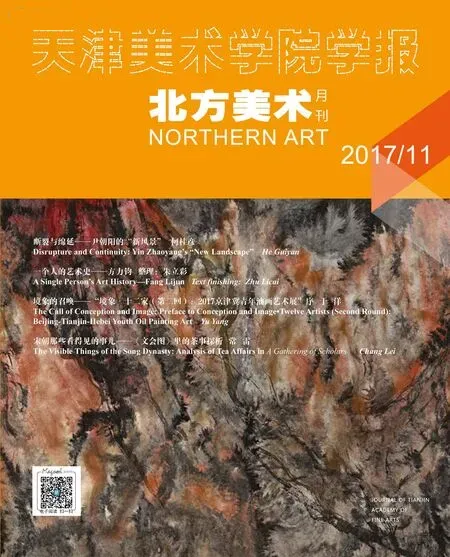斷裂與綿延
——尹朝陽的“新風景”
何桂彥/He Guiyan
2007年,以一批新風景,尹朝陽加速了畫風的轉變。如果熟悉尹朝陽早期作品的風格,那么,這次轉向多少會讓人感到意外,甚至有些突兀。而且,就藝術家個人創作的發展路徑來看,也是一次斷裂。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什么原因讓尹朝陽中斷了自己的風格?什么原因讓他選擇了風景?風景之于他,是否有特殊的意義?
解讀這批新風景,個人認為,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切入。第一個層面會涉及山水畫與風景的衍化與區別。這種關聯不僅涉及繪畫的傳統與審美趣味,而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圍繞風景與社會學敘事所形成的特點也有關聯。第二個層面是將新風景與藝術家個人創作軌跡的推進與斷裂予以結合。第三個層面則涉及中國當代藝術的藝術史情景,及其內部在近年發生的變化,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當代藝術如何面對傳統,如何從傳統中尋求滋養,積極地轉化,并賦予作品以文化身份。不同的切入的角度,自然會有不同的闡釋。而這三個層面的話題也會形成一種交織的、對話性的藝術史上下文。換言之,尹朝陽如何思考自己的創作,如何推進個人的創作軌跡,如何考量傳統與當代的關系,均離不開這個藝術史的上下文語境。
首先是山水畫與風景的關聯,及其背后隱含的創作傳統問題。從魏晉時期山水的出現,經歷隋唐,到北宋,中國山水畫在視覺再現上業已發展到巔峰。北宋以降,山水畫在藝術本體、創作方法論上均有質的變化,逐漸納入“士”階層的文化表述中。南宋以來,經歷元明清,山水畫在藝術本體方面不僅建構了一個自律的系統,而且,在審美、鑒賞、批評等領域形成了完善的體系。和西方繪畫至文藝復興以來形成的傳統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的山水畫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品格,集體無意識地支配著人們的美學趣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國家發起了對“中國畫的改造”,其實質是讓過去的山水畫為新的政權、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服務。20世紀50年代末期,尤其是進入60年代,一批“新山水”涌現出來,其內容大多是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與新農村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或者就是“毛澤東的詩意山水”。這種藝術創作觀念與形成的慣性思維,一直延續到“文革”后期。事實上,在中國的藝術發展脈絡中,山水與風景的區別,不僅僅體現在稱謂、題材、媒介上,更重要的是觀照自然的不同態度,以及繪畫承載的人文訴求有質的差異。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當代藝術的崛起,山水與風景是涇渭分明。不過,即便當代繪畫中出現了諸多的潮流、風格,但如果簡略地回顧,仍會發現,一個重要的藝術現象是圍繞“風景”展開的。譬如20世紀80年代初的“鄉土風景”、“新潮”時期出現的作為文化現代性訴求的風景、90年代以來的后工業時代的風景,以及2000年以來出現的“社會主義經驗的風景”。由于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一直受社會學敘事的支配,故此,我將這種創作現象稱為“社會風景”,亦即是說,沒有純粹的風景,只有不同時空與文化語境中的風景。所謂的“風景”也只是一種表象,一種通道,社會學的敘事則隱藏在表象之下,支配著“風景”的發展。

尹朝陽 窠石人物 布面油畫 80×100cm 2017年
表面看,尹朝陽的新風景與傳統山水畫并沒有太多關聯。其實不然。在《晴巒秋寺》(之一)(2013)、《層崖古樹》(2013)等作品中,畫面的視覺觀照與內部結構,全然不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傳統,也不是印象派的視覺經驗,畫面的內部機構反而更接近于清初的“四王”,或者說黃公望。尹朝陽對風景的表達,在意的是“胸中的丘壑”,而不是在三維透視的視覺機制中對自然的再現。即便是用油畫表達,其作品中隱含的觀看機制也更接近于卷軸畫。由此,傳統的山水與他的新風景會有一種聯系,在互文性中形成張力。在這批新風景中,我們仍多少可以看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山水傳統的某種聯系,只不過,這種聯系是隱形的、內化的。它們不是基于意識形態,更不是源于圖像化的表達,相反來源于畫面的宏大敘事,來源于作品彌散出的那種似曾相識的浪漫主義氣息。與此同時,當代繪畫中的風景創作,則為他的轉向提供了另一個上下文關系。因為,眾多藝術家的“風景”會形成一個參照系,為“風景”在當代藝術語境下的蛻變與發展,共同營造一種意義生效的新語境。

尹朝陽 空山夕照 紙本水墨 39.5×100.8cm 2017年

尹朝陽 寒林圖 布面油畫 250×950cm 2017年
第二個層面是藝術家個人創作脈絡的斷裂與藝術思想的轉變。作為70后中國當代繪畫領域的代表性藝術家之一,尹朝陽的繪畫以其強烈的主觀表現風格、濃郁的悲劇意識、無法回避的傷害感,使其在藝術界令人矚目。在《青春遠去》《失樂園》等系列作品中,藝術家揭示了青春話語背后個人所承受的異化與折磨,憤懣與傷害。這批作品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是藝術家對內心世界的一次剖析,也是對個人生存境遇的一次次拷問。與90年代初“新生代”對“近距離”現實的再現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尹朝陽的繪畫與現實是格格不入的,是批判性的,其視覺語言則充斥著“暴力”。《神話》《烏托邦》系列標識著藝術家的藝術思想又向前做了推進。此時,自我的青春體驗讓位于個人視覺記憶的挖掘,身體的傷害與精神的磨礪讓位于對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話語的反思。這一階段,對于尹朝陽來說,不再是對個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與拷問,而是希望將個人的成長融入整個70后所身處的時代語境,去言說70后一代的視覺經驗是如何被建構的,文化理想是怎樣被塑造的。然而,所謂的政治神話已經坍塌,空洞的理想主義走向了虛無,集體的話語狂歡則被殘酷的現實撕裂成碎片。對于往昔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時代,對于個人的生命歷程所面對的時代境遇,尹朝陽既有緬懷,也有感傷;既有敬意,也有質疑。但總體的基調是充滿悲劇意識的、荒誕的、解構的。
然而,尹朝陽并沒有在先前的創作路徑上繼續推進,而是在2007年轉向了新風景。面對急劇的轉向,在一些人看來,多少有些“不合時宜”。很自然,大家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尹朝陽已經很難超越此前的風格,于是,只有被動的轉變;有的認為,這是一種“大踏步的后退”,更準確的理解是“以退為進”;有的看法是,尹朝陽自身在傳統方面原本就有深厚的積累,轉變也在情理之中;有的則認為,向傳統的回歸,多少是一種策略,其中不乏商業上的考慮。當然,尹朝陽自己給出的解釋,是與自己的年齡有關。“不惑之年”猶如一個分水嶺。隨著年齡的增長,藝術家告別了青春期的焦慮與不安,更愿意以平和的態度面對生活,看待社會,也更愿意在新的領域嘗試,在風景中探尋新的可能。
每一種看法或許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不過,我更愿意將轉變理解為藝術家對那些既定的、成功的當代繪畫創作模式的厭倦與拒絕。首先是對庸俗社會學對繪畫的侵蝕保持警惕。“新潮美術”時期,中國當代藝術界曾圍繞“大靈魂”與“純化語言”掀起過一場大討論。在這場社會學敘事與“語言自律”的博弈與對抗中,“大靈魂”最后大獲全勝。90年代初,隨著“政治波普”與“玩世現實主義”的崛起,社會學敘事與“圖像化”的結合,使其主宰了當代藝術的意義生效方式。再后來,到了90年代末期就是庸俗社會學與犬儒主義的泛濫。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尹朝陽有意識地遠離社會學敘事,對庸俗社會學則十分反感。即便《烏托邦》系列、《廣場》系列仍充斥著政治性的話語,隱藏著社會學的視角,但它們與當時流行的“波普化”的表述大相徑庭,也跳出了后殖民話語設下的陷阱。其次,是對圖像式繪畫的抵制。2000年以來,圖像化、符號化成為當代繪畫的重災區。盡管《輻射》系列之中也有明確的圖像,但就藝術家的創作方法而言,本質是反圖像的。當然,不管是前期的風格,還是2007年以來的新風景,尹朝陽都極其重視藝術語言的表達。但是,和90年代后期以來的觀念性繪畫所不同的是,其作品中的語言只是一種修辭,藝術家并不會將語言的觀念化作為作品意義的主體。很顯然,尹朝陽的內心渴望轉變,他需要一次斷裂。斷裂的意義就在于遠離庸俗社會學,遠離圖像,對語言的觀念化保持清醒的認識,更內在的自覺,也在于與上一代藝術家的對話中反觀自身,以我為主,步步為營,將繪畫看作是一個人的戰爭。斷裂也意味著蛻變,藝術家希望擺脫既有的參照,打破創作思維慣性帶來的束縛,另辟蹊徑,形成個人化的語法與鮮明的風格。
從當代藝術的外部文化情景與藝術史價值尺度所發生的變化而言,新風景必然會涉及第三個層面的話題,即當代藝術如何向傳統回歸。2009年前后,當代繪畫界曾興起一股向傳統回歸的浪潮。但多少有些戲劇性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藝術在發展之初,其中的重要一脈,卻肇始于對傳統的批判。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當代藝術的轉型之下,重提傳統仍具有重要意義。無論是從整個20世紀的文化歷程,文化現代性的建設,還是從國家在新世紀的文化戰略的發展訴求等角度考慮,“回歸傳統”都有歷史的必然性。事實上,如果從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以及藝術史的書寫如何形成自己的價值尺度等方面考慮,激活傳統,使其在當下生成新的價值,更是迫在眉睫。這實質也意味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西方現代或后現代藝術的形式、語言為先決條件的當代藝術(或者說現代藝術),90年代那種反諷政治,以犬儒主義、媚俗為訴求的當代藝術,在今天已經喪失了自身賴以依存的文化語境和前衛性。換言之,當代藝術需要清理文脈,建立新的藝術史書寫模式。從這個角度講,“傳統”完全有可能為當代藝術提供豐富的文化與思想資源。

尹朝陽 一了 布面油畫 40×30cm 2017年

尹朝陽 布面油畫 47.5×61cm 2017年
早在“回歸傳統”的浪潮之前,尹朝陽已投入到新風景的創作中。在他看來,倘若今天的當代繪畫僅僅憑借簡單的幾個傳統圖像、符號,模仿宋元以來中國山水畫的某些圖式,就表明向傳統回歸,既俗套,也膚淺。就新風景的創作來說,對傳統的回歸,實質意味著在風景與山水畫之間能有一種內在的關聯。那么,如何才能領悟到山水畫的精妙,理解傳統的綿延,及其對繪畫的滋養呢?尹朝陽的一個基本方法是“讀畫”。在過去的十年間,尹朝陽參觀了許多重要的博物館,看了很多的古畫。比較起來,他更推崇北宋與晚明的山水。尹朝陽沒有系統地學習過國畫,而是版畫出身,所以,他不是從臨摹入手走近古人的世界。讀古畫,不僅要專注于畫面的筆法、墨法、布局、結構等與藝術本體相關的要素,更著重的是風格的變化與延伸,以及畫面彌散出的氣息。在藝術家看來,傳統繪畫的嬗變與其魅力,就源于氣息的感染。古人曾說,“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這種氣息首先發端于外部的自然之景,就像太行之于荊浩,鵲山之于趙孟頫,黃山之于黃賓虹。“師造化”的目的,在于在自然之景的催化下,藝術家會產生審美的移情。不僅如此,藝術家還可以進入一個更高的審美與哲學之境。所謂的“林泉之致”“澄懷味象”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難發現,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風景傳統比較起來,在中國的山水畫中,主體與客體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彼此交織的。為了走進自然,領悟山水之道,體會古人所說的“游心”與“暢神”,尹朝陽近年來遍訪名山大川。甚至,在一年之內,分別在春夏秋冬四季去過嵩山。

尹朝陽 飛雪巖 布面油畫 130×200cm 2017 年
對于尹朝陽來說,“師古人”,卻不拘泥于古人;“師造化”,卻不為自然之景所牽制。那些大師的作品,燦若星辰,以點成線,就像美術史中的坐標,彼此形成了參照。在這個參照系中,尹朝陽不僅需要學習,感受繪畫在中古時期的風度與格調,更需要反觀,進行自我的比照與審視,從而堅定自己的繪畫方向。不過,傳統對于尹朝陽而言,既遠猶近,既熟悉也陌生。倘若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考慮,傳統應是“四位一體”的,它體現在物理形態的器物層面,體現在實踐與交往的身體層面,體現在倫理與規范的制度層面,體現在審美與氣質的精神層面。故此,除了新風景的創作,尹朝陽平常還收藏佛像、建筑石刻和一些古代的器物。他癡迷于此,樂在其中。由于迷戀明清時的園林,他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工作與居住環境,一點一滴,力圖讓生活與繪畫融為一體。“潤物細無聲”,他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在不經意之間能感受到傳統散發出來的氣息。
如果從新風景的審美氣質上講,尹朝陽的作品與“北派”的山水似乎有一種共通性,講究造勢,強調鋪陳,畫面恢宏遼闊,氣勢撼人。因為,除了極少數的“小品”外,我們很難尋覓到“南宗”所追求的寧靜與清疏、蕭條與淡泊。尹朝陽的家鄉位于河南,離嵩山很近,很顯然,審美氣質的形成,與藝術家出生在中原有關,也與他的性格與視覺記憶有關。即便說與“北派”的山水氣質有一些共同點,但在畫面的空間與視覺結構的處理上,尹朝陽與傳統的山水創作卻完全不同。北宋的郭若虛在《林泉高致》中曾指出,好的山水作品應具有可觀、可行、可居、可游的特點。亦即是說,觀眾是可以進入畫面的,作品的各個細節都能統轄在一個空間結構中。然而,在尹朝陽的作品面前,觀眾猶如一個“他者”,無法進入畫面。一方面,藝術家并不追求對真實的自然進行再現,因此,他壓縮了畫面的視覺空間;另一方面,在處理自然的風景時,他的重點仍在于尋找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力圖賦予畫面一種內在的視覺結構。就這一點而言,尹朝陽明顯受到了塞尚的影響。一旦壓縮了畫面的視覺空間,觀眾就很難進入畫面,換言之,可行、可居、可游的特點全無。同時,作品的描繪功能也就自然會削弱,藝術家的情緒表達卻能更好地顯現。由于藝術家鐘情于“高遠”,所以,畫面更容易產生氣勢。在《空山夕照》《映山紅》《山陽秋高》等作品中,觀眾能感受到的是一種強烈的視覺沖擊,畫面的氣勢與優美無關,在視覺心理與審美趣味上,反而更接近于崇高。

尹朝陽 天門谷 布面油畫 160×200cm 2017 年
這種崇高感又是如何產生的呢?誠如前文所言,新風景之所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新山水”會形成一種潛在的互文性,就在于畫面中彌散出的浪漫主義意味。而浪漫主義與象征手法的結合,則會讓畫面具有不同的心理隱射,使其在慷慨中蘊藏著悲壯,豪邁中充斥著悲憫。這種審美心理的形成,或許是源于集體無意識的文化心理的傳承,或者發端于藝術家對個人視覺記憶的挖掘。同時,這種崇高感還來自于藝術家對自然對山水的禮贊與敬畏。在尹朝陽的筆下,觀眾不時會發現一些禪院、寺廟、塔林,如華山上的廟宇,位于恒山懸崖之上的懸空寺。它們并不太醒目,但不可或缺。作為一種意義的索引,它們的出現也并非偶然。看得出,藝術家對它們的著力描繪,或許是受到了古人精神上的感召,或者是來源于內心被喚起的宗教感。當然,繪畫語言也是生成這種崇高感的一個重要來源。如果說在早期的作品中,我們在藝術家的筆下還能看到培根、弗洛伊德、里希特的影子,那么,在新風景中,藝術家更多的是在東方化的視覺意象與西方抽象表現的語匯之間,尋求轉換與嫁接的可能。在那些率意、主觀的涂抹,抑或說是宣泄性的筆觸之中,在顏色的層層積壓,畫刀的刮擦之下,以及因偶然性而形成的斑駁肌理,共同使畫面顯得絢麗而奇幻,蒼涼而凝重。實際上,尹朝陽一直是一個主動與語言“較勁”的藝術家,也正因為如此,才使其能在新風景的創作中,在風格的蛻變與綿延之中,找到自我,走向純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