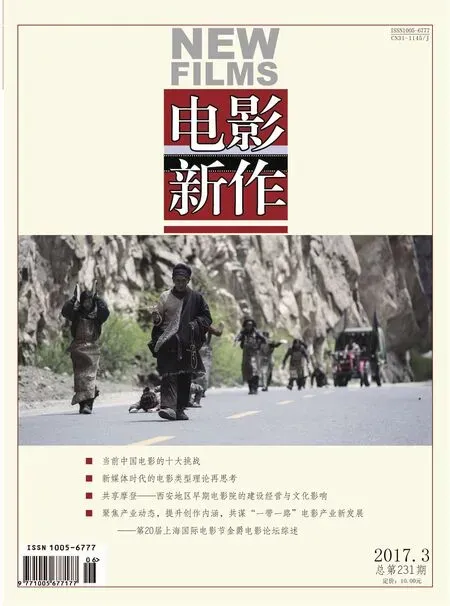傳統(tǒng)倫理、愛國情感與主旋律創(chuàng)作:成龍電影的價值轉(zhuǎn)向與重構(gòu)
翟莉瀅
傳統(tǒng)倫理、愛國情感與主旋律創(chuàng)作:成龍電影的價值轉(zhuǎn)向與重構(gòu)
翟莉瀅
從成龍自出道以來的創(chuàng)作歷程來看,影片中所蘊含的主題思想和價值內(nèi)涵發(fā)生了兩次較大的轉(zhuǎn)變。第一次轉(zhuǎn)變是從注重對傳統(tǒng)倫理表達轉(zhuǎn)向?qū)闼貝蹏楦惺惆l(fā),第二次則是近期向主旋律價值觀的闡釋與輸出努力轉(zhuǎn)變。文章通過對成龍的影片中的情感表達、精神母題與價值取向進行梳理與探詢,以管窺香港電影與內(nèi)地從離岸到融合的過程中,在倫理體驗、身份塑造、國族認同等多立面上發(fā)生的變幻與發(fā)展。
功夫喜劇 國族認同 主流價值觀
成龍的電影作品一直是華語電影圈內(nèi)的熱點與“爆款”,他在影片中頗具個人特征的表演風格、簡潔明快的動作剪輯與主題思想,使他早年在圈內(nèi)獲得了“大哥”這一尊稱。事實上,之所以成龍被稱作“大哥”,是因為在他的角色往往在片中傳遞古道熱腸、懲惡揚善、俠肝義膽的傳統(tǒng)倫理價值觀以及易于被觀眾接受的樸素愛國情感,從而令這些個性鮮明的角色被人所尊敬。不過,從成龍自出道以來的創(chuàng)作歷程來看,雖然他的電影中的功夫元素與喜劇特征一直以來是最大的票房賣點,但其所蘊含的主題思想和價值內(nèi)涵卻發(fā)生了兩次較大的轉(zhuǎn)變。從他早年在香港的出道之作、蜚聲國際后的大制作以及后來在內(nèi)地與香港合拍框架下的一系列新作中,能夠管窺并梳理出成龍影片價值轉(zhuǎn)向的主線與內(nèi)涵重塑的系譜。如今,香港回歸已然20周年,通過對成龍的影片中的情感表達、精神母題與價值取向進行梳理、探詢與研究,有利于我們管窺香港電影與內(nèi)地從“離岸”到融合的過程中,在倫理體驗、身份塑造、國族認同等多立面上發(fā)生的變幻與發(fā)展。本文以成龍新作《功夫瑜伽》及其他近期的作品為切入點,逆向溯源,試圖將這一轉(zhuǎn)變與重塑的脈絡在成龍自出道以來作品中貫穿。
2017年春節(jié)檔上映的《功夫瑜伽》,一共取得了17億的票房成績。從該片的市場表現(xiàn)上來看,作為春節(jié)檔期的開畫之作,上映之初中規(guī)中矩,后期依靠超高上座率逆襲《西游·伏妖篇》,成為登頂春節(jié)檔票房榜首的影片。這意味著,影片依靠環(huán)游世界、嬉笑打鬧、考古尋寶等觀眾所熟知的“成龍元素”,驗證了成龍的創(chuàng)作習慣在當下市場仍然旺盛的生命力和接受度。該片由唐季禮導演,成龍領銜主演。《功夫瑜伽》中,成龍飾演的考古學教授杰克致力于文物的發(fā)掘與保護。他與一名自稱埃什米塔教授的印度女子一起去找尋“摩揭陀國”失落的寶藏,因為這既能解開千年前印度遣唐將軍失蹤的謎團,而且聚焦“一帶一路”經(jīng)濟帶。于是杰克團隊一同踏上了尋寶之路,在經(jīng)歷磨難后,終于發(fā)現(xiàn)了古代“摩揭陀國”的寶藏。然而,真正等待著他們的并非取之不盡的黃金,而是大量保存完好的宗教、醫(yī)學等古代文獻。最后,連影片極力塑造的反派角色蘭德爾也與主人公們冰釋前嫌、共護文化瑰寶,將古代中印友好的佳話加以傳承。
可以看出,從內(nèi)容和題材上來看,近年來的成龍電影正在不斷向主旋律靠攏。包括《功夫瑜伽》在內(nèi),最近的《鐵道飛虎》《天將雄師》《十二生肖》《辛亥革命》等影片皆是如此,其主人公要么保家國以御外侮,要么懲盜竊以正視聽,甚至滑動至與一般的主旋律影片并軌的敘事模式來復述“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例如說,在《鐵道飛虎》里,由成龍扮演的抗日游擊隊隊長馬原帶領著幾名鐵路工人,白天在棗莊火車站工作,晚上化身為游擊隊與日軍周旋,阻擊日寇。《天將雄師》中,成龍則飾演被人陷害后發(fā)配到雁門關修城的西域大都護霍安,與保護羅馬帝國小王子的護衛(wèi)盧魁斯結(jié)為好友,以對抗野心勃勃的大王子提比斯所率領十萬壓境大軍,最后霍安在各民族的幫助下戰(zhàn)勝了提比斯。《十二生肖》則順應了中國追回海外國寶的政策與法律要求,成龍在影片里飾演了一名國際大盜,在與一批文物販子奪寶的過程中,他的愛國之心逐漸被喚醒,最終冒著生命危險為祖國追回文物。另外,由成龍聯(lián)合導演的《辛亥革命》,則將視線投向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民族面臨著重大歷史變革的時刻,他在片中扮演了英勇善戰(zhàn)的革命前輩黃興。
成龍電影不論是哪位導演執(zhí)導,也無論什么題材,成龍主演的標簽就已足以確立這部影片的商業(yè)賣點與風格基礎,使觀眾獲得確定的觀影預期。雖然成龍在電影創(chuàng)制中常常肩負導演、主演、編劇、監(jiān)制、武術(shù)指導等多個職務,但就“成龍電影”最為顯著的呈現(xiàn)特征及其精神內(nèi)核來看,就是它們貫徹了“功夫喜劇”的動作表演風格,以及承載了一定的價值倫理和意識形態(tài)等等。因此,本文所謂的“成龍電影”,主要是將由成龍主演的影片作為考察對象。不過,成龍電影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在當代華語乃至世界影壇仍然保持較高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創(chuàng)作早期形成的“功夫喜劇”所具有的鮮明表演動作風格。
“功夫喜劇”是傳統(tǒng)武俠電影和喜劇電影結(jié)合的特有類型,發(fā)軔于20世紀70年代后半期的香港影壇。20世紀70年末期,成龍、袁和平、洪金寶等人,經(jīng)過大膽地嘗試,將武術(shù)、雜技等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使“功夫喜劇”成為那一時期最受觀眾喜愛的電影類型①。在賈磊磊看來,他的“喜劇+動作”的諧趣武打片作品在中國武俠電影中獨樹一幟,是傳統(tǒng)武俠動作電影與現(xiàn)代喜劇電影相互結(jié)合的成功典范②。陳墨認為:“功夫喜劇將李小龍式的真打硬斗還原成妙趣橫生、令人眼花繚亂的雜耍功夫,將李小龍式的英雄傳奇還原成世俗故事;將充滿意識形態(tài)的教訓和道德宣傳的武俠電影還原成純粹的娛樂形式;將喜劇表演引入傳統(tǒng)的功夫電影之中,讓劇中人物有了更多的藝術(shù)表演的余地。”③
70年代末,“功夫喜劇”成為成龍電影乃至香港電影最顯著標簽之一。其特點是借助道具將武打動作夸張化,通過詼諧滑稽的動作設計來弱化殊死決斗時的緊張感,并以此突顯主人公輕松幽默的人物個性。憑借這一具有程式化、類型化的創(chuàng)作套路,成龍奠定了“成氏喜劇”的風格與基調(diào)。不過,這時他的影片通過以功夫喜劇挾帶傳統(tǒng)倫理的創(chuàng)作思路獲得成功,并沒有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承載功能。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些影片是對傳統(tǒng)武俠片中的兄弟情義、幫派恩仇、殺富濟貧等精神思想的繼承。比如《蛇形刁手》《醉拳》,宣揚的就是扶危濟困、欺強不凌弱等傳統(tǒng)價值觀。在《蛇形刁手》中,成龍飾演的簡福只不過是一介在武館中打雜的伙計,當他目睹隱姓埋名的蛇形門長老白長天被市井無賴欺負時,卻路見不平、出手相助。又如,他在《醉拳》里飾演的黃飛鴻,雖然是一個惹是生非、嬉皮笑臉的青年,后來折服于蘇乞兒的武藝拜其為師,最后救家族于危難時刻,成長為一位見義勇為的青年。從精神承載、倫理宣揚的功能性乃至敘事模式上來說,它們與歷史上大部分功夫片、武俠片是一致的。不過,在“功夫喜劇”的包裝之下,成龍的英雄形象塑造往往帶有更接近市井小民的性格特征,他們偶爾偷奸耍滑、妙語連珠,從而使影片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更加豐滿,亦更接近觀眾日常生活的體驗與經(jīng)驗。因之,這種“接地氣”的故事與角色處理方法,使這些影片所挾帶的傳統(tǒng)“俠義”觀念與觀眾之間在傳播接受的過程中更為順暢。另外,不管是《笑拳怪招》的復仇故事,還是《師弟出馬》的懲奸除叛,都是這一時期成龍在“功夫喜劇”與傳統(tǒng)倫理價值相結(jié)合的代表之作。
經(jīng)過成龍等人的努力,“功夫喜劇”已然成為動作片與喜劇片相互交叉滲透的亞類型之一。此后,成龍開始嘗試在“功夫喜劇”的外衣下,包裹不同的精神內(nèi)核。從《蛇形刁手》《醉拳》等奠定他影壇地位的代表作來看,它們遵循的依舊是在傳統(tǒng)武俠片所“規(guī)定”的價值框架下的拔刀相助、懲罰奸佞、除暴安良等元素壘砌,而有所區(qū)別的正是在于成龍利用“功夫喜劇”的外殼賦予了它們與傳統(tǒng)武俠片截然不同的呈現(xiàn)形態(tài)。萬眾矚目的“功夫喜劇”已然被研究者反復吟味,而成龍電影中扁平、質(zhì)素的價值宣教與倫理灌輸功能及內(nèi)容卻往往遭到忽視。雖然“功夫喜劇”是成龍電影獲得商業(yè)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管是何種電影類型也會有審美驚奇、審美接受與審美疲勞的不同時期。所以,恰恰是成龍電影中飽滿而富有支撐力的價值內(nèi)涵才是其長久不衰的保障。
但是,成龍電影中承載的價值內(nèi)涵與意識形態(tài)并非是穩(wěn)定的,在成龍在香港影壇正式出道的四十余年間至少經(jīng)歷了兩次較大的轉(zhuǎn)變。與前述《蛇形刁手》《醉拳》等更為靠近傳統(tǒng)倫理的影片有所不同,在80年代的《龍少爺》《A計劃》與此后的《A計劃續(xù)集》等一系列影片中,成龍開始在影片中注意表達更為宏大的樸素愛國情感,這成為他創(chuàng)作生涯中在影片思想主題的第一次轉(zhuǎn)向。也就是說,影片的思想內(nèi)核從以往的傳統(tǒng)倫理表達向愛國情感逐漸轉(zhuǎn)移。《龍少爺》是成龍第一次執(zhí)導影片,背景設定在清朝覆亡之時,講述了偷運國寶并與洋人交換利益的大內(nèi)總管被代表正義的成龍一伙所鏟除,從而確保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的故事。《A計劃》系列則講述成龍飾演的馬如龍與港英政府在廢除水警問題上產(chǎn)生爭執(zhí),最后他與他的朋友們糾彈邪惡、打擊貪腐,保護了香港的安寧,壓制了貪婪的外國人。如果說,《龍少爺》依然部分在懲奸除惡的傳統(tǒng)倫理框架下進行表達,那么《A計劃》則對他的樸素愛國情感的呈現(xiàn)已然相當明顯。例如,在《A計劃》中,有一段長達4分鐘的他怒斥港英政府高級官員的場景,并且把英國人與海盜互相勾結(jié)的惡行斥為“卑鄙無恥”。
需要注意,之所以將這一愛國情感稱之為“樸素”,是因為它一旦與香港的本土主義嫁接就在視野與思想上表現(xiàn)出了狹隘與局限。將時代背景設置于20世紀初年香港的《A計劃》,提供了愛國情感與本土情結(jié)相互對沖的博弈場。例如,片中英國高級官員同意馬如龍重建水警隊時,馬如龍立刻表現(xiàn)出了合作與媾和的態(tài)度。又如在《A計劃續(xù)集》里,革命黨人要求馬如龍加入革命團體,“一起挽救中華民族”。馬如龍的回答卻是否定的,因為他要“保障香港的每一個人都安居樂業(yè)”。這說明,此時成龍電影的樸素愛國情感表達,依然被限制在香港本土情結(jié)的范圍內(nèi)。當愛國情感與本土情結(jié)在片中“合理沖撞”時,后者成為兩者之間的優(yōu)先選項,本應崇高的愛國情感瞬間顯示出了它的“樸素性”。
即便到了1995年的《紅番區(qū)》中,影片也試圖通過敘述一名美國華人青年由于鉆石搶劫案被迫與流氓聯(lián)手對付黑幫的故事,來彰顯這種愛國情感與域外地理空間嫁接時所體現(xiàn)的適應性。此前,他的《快餐車》《龍兄虎弟》等影片也立足于表現(xiàn)正義善良的華僑華人在國外揚眉吐氣的旨趣。如果把成龍電影比喻成一輛能夠裝載不同價值觀念的“卡車”,那么從這一時期之后,它開始滿載著愛國主義思想、本土主義情結(jié)與傳統(tǒng)倫理觀念在華語影壇里昂然奔馳。其創(chuàng)作模式就是,利用功夫喜劇的外衣與易于理解的情感邏輯來支撐影片的精神內(nèi)核,并且嘗試將這一理念向外國輸出。例如,在中美合拍的《功夫夢》中,美國小孩德瑞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學習功夫,發(fā)現(xiàn)中國與國外宣傳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這名美國小孩在向成龍學習中國功夫的過程中,領悟了中國武術(shù)的魅力和高深的處世哲學。這部影片無論從電影工業(yè)合作或文化競合輸出的角度來看,都可算是成龍電影中較早的“標準件”。可以說,這部影片在產(chǎn)業(yè)上佇立于中美合拍的前哨之位,同時也是理解此時成龍電影創(chuàng)作模式的絕佳范例。
接著,以他執(zhí)導并主演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獻禮影片《辛亥革命》所構(gòu)建的宏大歷史敘事為顯著轉(zhuǎn)折,從《十二生肖》開始,他在影片中通過主人公保護文物的經(jīng)歷來揭露民族的慘痛創(chuàng)傷歷史,闡釋并輸出主旋律價值觀。由于當年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導致中國大批珍貴的文物流落海外,該片圍繞四尊十二生肖獸首的海外公開拍賣展開劇情,最終成龍使文物全部回歸中國并上交給中國政府。在后來的《天將雄師》中,已經(jīng)當選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成龍則開始在影片中聚焦“一帶一路”概念并為之進行宣傳,虛擬了一場古代中西文明相互摩擦沖突的大戰(zhàn)。但是,片中“中西對立”的矛盾在影片開始不久,就通過成龍的角色與代表善良正義的西方人聯(lián)手而轉(zhuǎn)換為“正邪對立”,并且“邪不壓正”,正義的漢人、少數(shù)民族以及羅馬人以生命的代價保障了絲綢之路的和平與安寧。
如果說成龍在他的早期影片如《A計劃》中試圖通過愛國情感的宣泄來激發(fā)觀眾的民族主義情感,那么很顯然他在近期的影片中對這一操作邏輯已有所保留。因為在“正邪對立”的敘述框架下,如果以國別為陣營來分配正邪屬性,則勢必使影片的價值觀愈顯得狹隘,不能適應他近期電影充分體現(xiàn)政府所提倡的主旋律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但這一“愛國主義”并非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主旋律乃至重大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要求下,也不應將中國與西方作為截然對立的兩個立面進行塑造,形成過于尖刻的文化與民族對立。成龍顯然能夠在影片中妥善處理這一“二元對立”。如《功夫瑜伽》中反派角色印度“王子”蘭德爾雖然最初一心只想要奪取寶藏,不惜以殺人、搶劫來達到目的,但是蘭德爾最后卻通過與杰克的一番諧趣打斗,認同了杰克倡導的“歷史是屬于全人類的”價值理念,皈依向善并與大家和諧共舞。另外,《鐵道飛虎》雖然將影片故事置于抗日戰(zhàn)爭的大背景下,卻以“功夫喜劇”的方式適當軟化了對立與仇恨情緒。一言以蔽之,在成龍電影的主旋律創(chuàng)作中,那些十惡不赦、面目猙獰、兇暴殘忍的敵人形象幾乎是缺席的。成龍似乎不需要用霍元甲、陳真或者葉問這樣“戰(zhàn)意昂揚”的元素就能框定在主旋律創(chuàng)作中的“安全區(qū)域”,并且也無意在片中體現(xiàn)某種令人亢奮的種族主義圖譜。這意味著,在香港與大陸電影合拍的趨勢之下,成龍以創(chuàng)作來摸索嘗試,找到了用他所擅長的“功夫喜劇”與當下意識形態(tài)宣傳進行融合的方法與路徑。
從另一方面來看,從《神話》開始,成龍的影片里就不斷出現(xiàn)考古、盜墓以及保護文物等元素,成龍幾番在片中塑造了愛國的考古學家與良心發(fā)現(xiàn)的“古墓大盜”。《天將雄師》通過一場跨國古代遺跡的考古活動展開敘事,《十二生肖》保衛(wèi)十二銅獸首的故事自毋庸贅言,《功夫瑜伽》的主要線索亦是尋找作為古代中印兩國友好見證的失落寶藏。更重要的是,成龍通過在電影中對盜墓行為和文物保護之間價值觀念沖突的講述,找到了一條不必制造戰(zhàn)爭沖突等尖銳對立就能使觀眾對“愛國”與主旋律價值觀進行認知的便捷途徑。
成龍電影是從香港走向內(nèi)地與世界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香港電影的文化精髓在成龍作品中得到了絕佳體現(xiàn),“功夫喜劇”的生命力即是明證。回顧歷史,香港經(jīng)歷了英國一百年的殖民歷史,導致香港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大眾化、通俗性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聚集形態(tài)④。其中,中國文化在香港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但是,香港回歸前由于港英政府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偏差,使香港人對內(nèi)地在一定程度上抱有成見,他們也隨著地方經(jīng)濟建立起了本土意識。1984年,經(jīng)過中英談判解決了持續(xù)百年的歷史遺留問題,使香港人的族群身份體認得以明確。1997年回歸之后,即便“雜音”偶爾喧囂,但香港人卻從法律上擁有了更為確切的國籍和身份歸屬。我們可以從此發(fā)現(xiàn)成龍電影與歷史相互照合的理路:成龍在《A計劃》中塑造了對英國人貪污腐敗恨之入骨的馬如龍以及《快餐車》里勇救外國美女的正義華僑的愛國形象,雖然在1998年的《我是誰》中經(jīng)歷了暫時的身份迷惘與“失憶”,但最近成龍卻以《警察故事2013》中的內(nèi)地公安干警以及《神話》《功夫瑜伽》里的愛國考古學家等承載著厚重卻煥然一新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身份再度登場。成龍電影中的主人公身份轉(zhuǎn)換,可以說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人身份認同變幻的微縮景觀。香港人文化身份歸屬的變化脈絡,同時也成為成龍電影中價值轉(zhuǎn)型與意識形態(tài)重構(gòu)的深層文化動因。
可見,自成龍以《蛇形刁手》《醉拳》等片蜚聲影壇以來,他的影片中所承載的價值內(nèi)涵與主題思想經(jīng)歷了兩次較大的轉(zhuǎn)變。第一次轉(zhuǎn)變以20世紀80年代的《龍少爺》《A計劃》與《A計劃續(xù)集》為代表,影片的核心內(nèi)涵從以往所側(cè)重的傳統(tǒng)俠義觀念轉(zhuǎn)變?yōu)闃闼貝蹏楦小5诙无D(zhuǎn)變則是在他執(zhí)導并主演《辛亥革命》之后,成龍電影開始注重以宏大的歷史敘事來倡導主旋律,《十二生肖》《天將雄師》《鐵道飛虎》《功夫瑜伽》等影片盡皆如是。需要指出,影片在核心價值上的轉(zhuǎn)變并非驟然轉(zhuǎn)向,而是有一個相對緩和的過程。同時,轉(zhuǎn)變也并非意味著對前者顛覆,因為這些能夠相互協(xié)調(diào)、包容的價值觀念之間并沒有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另外,我們還需要注意,成龍電影主要是以獲取票房利益而制作的商業(yè)電影,其最終目的是通過各種產(chǎn)業(yè)運作的手段來實現(xiàn)盈利,它的功能并非專注于宣傳某種思想主題、提倡某種價值體系,不可能無休止地在每部影片中都充斥著關于意識形態(tài)的辯護與言說。但是,如果將所有成龍電影作品看做是一幅可供延展觀賞的卷軸畫,那么各個作品所蘊含的不同主題內(nèi)涵正如散點透視般布局于畫中,它們之間所構(gòu)成的景深差異,形成了能夠聯(lián)動、定位、輻射其他作品的“價值生態(tài)”。
從更大意義上而言,成龍電影中價值轉(zhuǎn)向與重構(gòu)的系譜,與香港人在本土意識、地域身份、家國體認
[ ][ ]等方面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同構(gòu)性。20世紀80年代后,成龍電影開始在香港、內(nèi)地與世界獲得極高的聲譽,幾乎同時,香港社會上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逐漸向“分離主義”靠攏與演化。此后,成龍電影中所表達的基于本土情結(jié)的樸素愛國情感,也恰是在香港本土意識中埋藏至深的對祖國的向往的精神底流。近來,成龍的主旋律創(chuàng)作,正是對彌漫在香港社會上的“失敗主義”與“分離主義”思想上的有力駁斥,代表了涵蓋“建制派”“溫和民主派”以及內(nèi)地移民在內(nèi)的更廣大香港人的價值取向與思想觀念。大而言之,對成龍電影中主旋律價值觀的形成路徑進行研究,是導正香港本土意識,并將之與“分離主義”思想剝離的通途之一。
不過,從成龍電影在主旋律創(chuàng)作中的局限性來說,“功夫喜劇”或是“考古題材”都不一定是價值宣貫的最優(yōu)選項。例如,《功夫瑜伽》中本來惡貫滿盈的印度“王子”蘭德爾跟隨眾人在一曲《神話》之下棄惡向善、翩翩起舞,使這一突如其來的善惡轉(zhuǎn)向誠如“神話”般不可思議。又如,《天將雄師》中的古城考古行動,卻因兩名隊員因霍安事跡所感動而決意不令古城“受到文明的污染”,使古城再次塵封,用來為虛構(gòu)的故事披上歷史真實的外衣。需要指出,影片應使用更為圓滑并且符合邏輯的影像風格和敘事手法來對這些情節(jié)進行處理,才能使得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藝術(shù)上更有說服力和感染力。
【注釋】
①Paul S.N. Lee. The absorp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foreign media cultures a study on a cultural meeting point of the east and west: Hong Kong[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1(1):56.
②賈磊磊.成龍:用動作改變世界[J].當代電影,2014(3):38-42.
③陳墨.功夫成龍:從港島走向世界──成龍電影創(chuàng)作歷程述要[J].當代電影,2000(1):72-78.
④周毅之.從香港文化的發(fā)展歷程看香港文化與內(nèi)地文化的關系[J].廣東社會科學,1997,(02):20-24.
本文系中國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項目《中國電影的國家理論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5BC037)階段性成果。
翟莉瀅,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