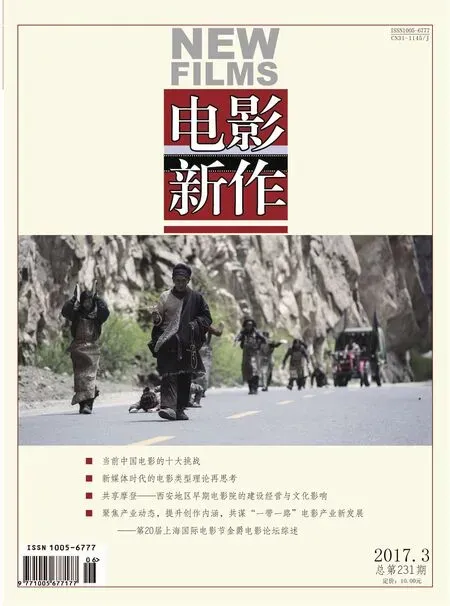新常態下對“互聯網+電影”的產業生態的再思考
郭海洋
新常態下對“互聯網+電影”的產業生態的再思考
郭海洋
當下互聯網正推動著電影產業從創意選題、融資制片到發行放映各個環節的生態變化,面對眾籌、大數據、IP改編、網生代導演、多屏傳播等“互聯網+電影”的熱門話題,我們應如何保持冷靜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斷?當“互聯網+”成為新常態,我們逐漸發現:電影作為有靈魂的藝術有機體,一定會包容、吸納、融合互聯網技術的種種優勢,其最終的發展和繁榮依然要訴諸藝術內容的創新,“講一個好故事”和“講好一個故事”的基本要求依然是電影所要堅守的審美底線。
“互聯網+” IP改編 網生代導演 電影形態
近兩年,最直觀的幾個感受提示著我們:互聯網正在不斷地改變著電影產業的生態格局。電影片尾的字幕越來越長,滿屏都是網站的標志;20歲左右的“網生代”群體成了電影院的觀眾主力;《失戀33天》《狼圖騰》《捉妖記》《滾蛋吧!腫瘤君》等網絡IP電影收獲了不俗的票房;大數據、眾籌、彈幕、IP資源、點映這些飽含互聯網思維的名詞應接不暇。其實,互聯網與電影的滲透融合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作為文化載體的互聯網一直以來都是電影文化的宣傳載體和電影內容的播出平臺。2010年,騰訊就已入股華誼兄弟;2011年,樂視影業成立時聲稱要做“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公司”。互聯網和電影產業的全面結合始于2014年,因由網絡團購而帶動電影營銷層面的互聯網化,并逐步向電影產業鏈的其他環節蔓延:由網絡眾籌的客戶思維延伸至網絡IP內容的產品思維,由點映、預售延伸至制作的數據分析以及映后的衍生品開發。互聯網與電影在選題、融資、制作、發行、銷售、放映等多個環節的融合構成了一個更為年輕化、更加具有活力的電影生態。2014年我國票房接近300億,2015年已突破400億,實現了48%的增長。然而,寄予厚望的2016年,票房實際只有457億元,同比增長3.73%,增速大幅跳水。所有這些都讓我們在歡欣鼓舞之余,不得不保持冷靜的理性和思考,并對“互聯網+”電影的產業新格局進行一番重新的審視。
一、“互聯網+”電影:到底誰為誰打工?
互聯網,這個曾經只是電影宣傳營銷和版權播出的平臺,而今,正在推動著電影產業從創意選題、融資制片到發行放映各個環節的生態變化。客觀上,互聯網的確延伸了電影的產業鏈條,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電影創作者、作品、觀眾之間的互動關系。電影也似乎因由互聯網的介入而更趨現代,更加時尚。線性的發展史觀往往讓我們無比驚異于這種新變的同時又極力地贊同并呼喚它的“更新”“更奇”。在互聯網制造的大眾狂歡和票房奇跡之下,我們通常會暢想一番電影的未來,人人爭做預言家:“在未來,電影公司可能都將為BAT打工”①,未來“電影院一定會消失”②。甚至有人言稱:“中國電影要做到3000億,如果脫離了互聯網,那是天方夜譚的囈語;如果將之置于‘互聯網+’時代的語境之下,一切皆有可能。”③如果前兩個預言還可以作為防止過度互聯網化的警醒,那么建立在“虛妄假設”基礎上的推斷就顯得十分可笑。這個時代誰還離得開互聯網呢?未來,互聯網將會深刻影響電影的變革,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目前電影產業鏈上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身影,“還不是二者的‘化學反應’,而只是傳統電影產業鏈的升級罷了”④。當這些身影成為新常態時,當我們習慣于電影片頭互聯網企業的LOGO,習慣于依據評分在線購票和選座,習慣于網絡熱門IP搬上銀幕,此時,我們才發現,觀眾最關注的依舊是電影的藝術質量。我們要做的正是基于電影本身的冷靜的思考,而真正的“互聯網+”電影的產業融合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電影的投融資環節中,網絡眾籌開辟了一條不同于傳統的“自上而下由少數資源控制者主導”⑤的投資模式。然而,與美國的電影眾籌項目多集中在中小成本的藝術電影相比,我國的眾籌項目大多是針對熱門的網絡IP,眾籌的對象也多是粉絲群體。實際上,作為熱門IP,網上開籌的那些電影大多是不差錢的。其眾籌的思維還是互聯網的“用戶思維”:將營銷的端口前置,在產品生產之前,預先確定目標用戶并進一步探測市場;另一方面也借助粉絲群體產生的話題效應進行推廣和宣傳。其主要目的不是籌集資金,而是穩定并拓展客戶群。這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眾籌”是缺少誠意的。尤其對電影產業的投融資渠道來說,它并不是給那些真正需要資金的電影以雪中送炭的創作鼓勵,而只是給那些不差錢的影片以錦上添花的吶喊助威。資金不是目的,用戶才是王道。與其說眾籌是一種投融資手段,不如說它是一種營銷策略。熱門的IP早已聚集了優勢的資金、導演、演員和宣發資源,而小眾的藝術電影依舊得不到任何資金上的支持。所以,如何讓眾籌真正具備電影融資的本能特性,讓互聯網真正助力電影的多元化創作,這才是我們要進一步思考的。
大數據被認為是當下最熱門的互聯網思維。2013年,美國Netflix公司推倒的第一張“紙牌”⑥迅速在全世界的影視行業引發多米諾效應。大數據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觀眾對影片的映前期待和映后觀感,其所表現出的“讓用戶掌握決定權”的互聯網精神也是值得電影創作者和制片人借鑒的。但是,過分依賴網絡數據進行創作將是非常危險的。復雜的網絡環境,各種人為的、商業的語言泡沫和鋪天蓋地的信息流,往往會讓數據的真實性、可靠性大打折扣。“計算機的處理方式是自下而上……它總是從‘要素’或‘成分’出發,得到這些成分所能組成的一切可能的‘結合’……這是計算機之所以永遠不能替代人腦的最大局限”。⑦人們都說《小時代》憑借大數據獲得了高票房,這是一個不言而喻的簡單數學題,有郭敬明和楊冪、郭采潔等偶像明星的粉絲作為目標觀眾群,幾億票房的保證是不足為奇的。也有人說《老男孩之猛龍過江》通過大數據分析出“音樂”“夢想”“青春”等幾個關鍵詞,從而指導電影的創作。將動態、海量的數據固化在幾個抽象的關鍵詞上,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如果電影創作可以靠幾個詞就能決定觀眾的喜好,那么“愛情”這個關鍵詞估計永遠不需要大數據來分析吧?“大數據”打著“符合最大數量網民意愿”的幌子,成了一張貼在影片上的金字招牌。要知道,數據再大,云計算再強,“也無法計算出人生圖景中的詩意;心靈和情感才是詩意的發源地”。⑧所以,如何將數據的針對性和創作者的藝術審美判斷結合起來,這才是互聯網數據服務于電影創作的重點。
其實,“互聯網+”對電影工業最大的影響和改變應該體現在促進電影工業整體升級上,而目前國內的“互聯網+”還遠未達到這一點。同樣,互聯網思維真正作用于電影創作,如《盜夢空間》《源代碼》《云圖》等影片那樣拓展電影的敘事能力和表現能力,目前還尚未出現。所以,我們不僅應看到互聯網與電影制片、營銷、放映等環節結合的新現象,還應該分析互聯網思維對電影構思、創作、制作的新影響,并從深度和效度上評價這些新現象和新影響。只有我們對互聯網大潮帶來的機遇和危險有著充分的認識,才能使電影產業的生態保持更加健康、更加良性的成長。
二、IP資源:作品素材還是產品原料?
網絡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是互聯網對電影內容和創作最貼近的影響之一。電影界購買著作權進行改編早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情,只是近年來帶有互聯網基因的IP開始成為電影創意的新寵。電影企業不外乎看中的是網絡IP的高點擊量、多用戶和高人氣,加上靚麗的數據支持,似乎熱門IP就一定是高票房的保證,于是蜂擁而上,爭相囤積。如果拋開互聯網基因,我們會發現電影很早就和各種IP結了緣:喬治·梅里愛的《月球旅行記》(1902)改編自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1915)改編自托馬斯·迪克森的暢銷小說《同族人》;中國早期電影《難夫難妻》(1903)、《黑籍冤魂》(1916)來源于文明戲;《紅粉骷髏》(1921)改編自法國偵探小說。在其后的百余年里,電影強烈地依賴著戲劇和小說的文化資源,并對神話傳奇、彈詞話本、戲曲漫畫等觀眾感興趣的IP資源表現出持續的關注,各類改編作品成為電影史中歷史最悠久,數量最龐大,成就最突出的創作形態。
我們今天對熱門IP的追捧仿若歷史某一時段的重現:20世紀20年代,徐枕亞的《玉梨魂》、包天笑的《空谷蘭》改編成電影后,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成為搶手的IP,一時洛陽紙貴;《火燒紅蓮寺》掀起了武俠神怪片風潮后,各大公司紛紛從神話傳奇、古典小說和連載武俠小說中尋找“IP”資源。僅1927年,就有“復旦”“孔雀”“亞美”三家公司同時拍攝《紅樓夢》;最強“IP”《西游記》就改編有《孫行者大戰金錢豹》(1926)、《盤絲洞》(1927)、《豬八戒招親》(1928)等多部電影;“明星”和“大中華”因《啼笑因緣》的“雙胞案”對簿公堂;民新公司精心制作的《木蘭從軍》還是被天一的同名電影搶先上映。各大電影公司在爭搶優質IP資源的同時,也都在加快出片速度,搶時間,趕進度,不顧質量,已然成風。一時間神怪片大行其道,影壇烏煙瘴氣、群魔亂舞,“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效應開始顯現。為與小公司競爭,大公司亦采取惡劣之制片策略。尚處于起步階段的國產電影在這場IP的爭奪戰和粗制濫造的惡性競爭中走上了歧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掌握了優秀的IP資源并不必然意味著電影營業上的成功,重要的不是占有了什么樣的IP資源,而是如何將其轉化為電影的藝術創造。當下許多熱門IP改編成電影后口碑和票房均遭遇了慘敗。《落跑吧,愛情》《何以笙簫默》《誰的青春不迷茫》《爵跡》《爸爸去哪兒2》《奔跑吧,兄弟》等影片唯奇觀和娛樂至上,唯市場和粉絲是瞻,喪失了人文情懷和藝術特性,其失敗是不出意料的。網絡IP固然有其新質,它的背后的確是年輕而龐大的“網生代”群體,但這在本質上和20年代熱衷報刊連載的市民階層相比并沒有太大區別,他們都是電影最具潛力的觀眾群體。網絡IP的確涵蓋了游戲、綜藝節目、小視頻等更新、更多樣的內容,但不管是傳統的改編戲劇小說還是當下的改編網絡游戲,它們最終都是作為電影的素材,在本質上它們都將受制于電影創作的藝術規律,而不是小說的、游戲的規律,更不是商業運作的規律。“每種藝術形式都依賴其自身的特定規律。……重要的是盡可能充分地探討、揭示電影與文學的互動。”⑨“小說與電影像兩條相交的直線,在某一點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點上,小說和電影幾乎沒有區別,可是當兩條線分開后,他們不僅不能彼此轉換,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點。”⑩可見,從小說到電影,改編必須是在確認和熟悉兩種文體形式的特征和屬性的前提下,由一方向另一方的轉化,網絡IP的改編也不例外。
然而,當下網絡IP改編所遵從的大眾文化邏輯和消費主義特性讓電影創作流于對網生代群體的屈就和迎合,其敘事碎片化、臺詞網絡化、場景戲謔化以及價值觀的“草根性”,一方面迎合了網民的審美意圖;另一方面也傾向于價值上的虛無和美學上的粗鄙。電影創作主體精神極度萎縮,個性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的影像風格也大為削弱,電影因缺少了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思考生活的深度感,而成為即時性、快餐化的商品。所以,如何在“游戲化、碎片化”的網生代趣味中找到一種“個性化、哲理化”的獨特表達;如何在滿足網生代價值取向的基礎上獲得最大通約的觀眾的情感共鳴;如何把網絡IP看做是作品的素材而非產品原料;如何依照藝術創作的規律挖掘其價值而非簡單的“照單抓藥”,這才是當下IP改編電影應該努力的方向。
三、網生代導演:創作者還是產品經理?
當下的電影格局呈現出數“代”共生的局面。“第五代仍在以個人品牌吸引大眾眼球;第六代繼續著‘長大成人’式的艱難轉向;而年輕的新生代以其類型化的嫻熟創作和與年輕觀眾之間天然具備的‘對話’能力,強勢擴張著自己的電影版圖。”11呼應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浪潮,越來越多的跨行業、跨領域的人才進入電影業。2014年央視舉辦的“中國電影新力量推介盛典”上韓寒、郭敬明、肖央、鄧超、俞白眉、陳思誠等11位新銳導演集體亮相,作為中國電影導演的新生力量,他們體現出強烈的互聯網環境下資本、媒介和版權聯手共謀的特征。他們得益于互聯網獨特的文化生態環境,依靠自帶的明星光環和博客、微信的粉絲效應,借助文學網站的高人氣閱讀以及草根視頻的廣泛傳播,從而擁有眾多的網民擁躉。“跨界”是網生代導演的共同特征,他們一方面利用并延展了個人的品牌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將其在網絡上的人氣價值變現為一種商業利潤。
由演員、攝影、編劇甚至美工轉行做導演的“跨界”在電影史上并不少見,僅第五代以來就有姜文、徐靜蕾、陳建斌、顧長衛、侯詠、薛曉璐、非行等,他們都是在多年的電影從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熟悉電影的創作規律,有著自己的創作觀念和美學追求。相比較而言,同是“演而優則導”的趙薇、鄧超、陳思誠、蘇有朋等人的成功更多是靠粉絲的市場號召力。《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分手大師》《北京愛情故事》《左耳》等影片雖然也收獲了不俗的票房成績,但口碑與票房明顯兩極分化。從文學向電影跨界的韓寒、郭敬明有著多年來從新概念作文到暢銷小說再到博客罵戰而積累的強大人氣。《后會無期》和《小時代》系列在雙方粉絲群體以忠誠捍衛自己精神偶像的方式下輕松賺取數億,而電影本身所表達的年輕人對“尊嚴、名利、金錢以及自我實現”的困惑也引發了人們的諸多爭議。還有從電視主持人轉行做導演的何炅、電視制作人謝滌葵、網絡紅人筷子兄弟、歌手崔健等,他們多以超高的電視收視率和名人的話題效應來制造營銷賣點,《梔子花開》《爸爸去哪兒》《老男孩之猛龍過江》《藍色骨頭》等影片要么投目標觀眾興趣之所好,以粉絲熱衷的娛樂元素為配方;要么憑借著電視節目的余熱而票房大賣,其商業成功只是現象,不是電影的常態。
網生代導演的優勢在于能夠將時代風尚和商業理念巧妙對接,在三四線城市的“小鎮青年”中形成強大的票房號召力。他們的共性是:“視覺狂歡和圖像沖擊力、市場意識、消費精神、娛樂姿態、粉絲文化、話題制造式的營銷手段、網絡語言與日常語言的無差別,對網絡、粉絲力量的有效利用。”12他們之于電影的關系并非是導演之于作品,而更像是經理人之于產品;他們不再是藝術作品的創作者,而是產品的項目經理;是“以網絡青年為用戶群體,以互聯網思維為產業理念,將技術與商業高度融合的項目策劃者、執行者和推介者。”13藝術的創造必然要傳達創作者的主體精神,表達作者對于現實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如果電影的生產退化為大批量的可復制、可調配的一種配方工藝的話;如果導演個體的藝術創造完全喪失而只突出了一種集體化的技術制造的話;如果導演不再是故事的講述者、風格的掌控者、思想的傳達者的話,那么電影就不再是一門藝術,而只是一種工藝,只是網絡(機械化)作用于人(網生代)進而生產出的網絡產品,藝術作為人類對抗異化的最后一塊領地也將不復存在。
四、電影形態:影院消失離我們有多遠?
今天,互聯網把電影放映引向了一個“多屏傳播”的時代,電視、PC、平板、手機等眾多視頻終端,讓電影的放映不再僅僅局限于影院。2011年,樂視網、騰訊網、PPTV、迅雷、暴風影音、激動網等7家互聯網公司就聯合成立了“電影網絡院線發行聯盟”,助推互聯網成為電影的第二發行渠道。網絡院線的最大價值就是使那些無緣院線的中小成本電影獲得發行放映和資金回籠的機會。然而,“電影是電影人觀察世界、感受世界、表達世界的一種方式,互聯網作為新力量進入電影,應當對一百二十年來在觀眾中形成的目光之網和心靈之網保持足夠的敬畏和尊重。”14電影形態無論怎么變化,都不會破壞電影最基本的觀看機制;觀影模式無論如何創新,也一定是建立在觀眾與銀幕“認同”“共鳴”的基礎上。
在電影的觀看機制中,“看(窺視)”的行為包含了電影的諸多奧秘。從柏拉圖的“洞穴”到拉康的“凝視”,帶著欲望的“觀看”始終是所有觀影的潛在動力。銀幕和觀眾之間的默契正是以認可這種“窺視”的合法性為前提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和奇觀化的影像構成了“看”的內容,電影的視聽慣例和影像系統不斷引導觀眾與銀幕形象的“視線融合”和“認同”,流暢的敘事和無縫的剪輯則保證了這種“融合”和“認同”的持續性。不僅是好萊塢商業片具有這樣的“認同”機制,就連那些試圖打破夢幻的藝術電影也在用某種“真實”的方式促使人們思考,以達成觀眾與銀幕間的另一種“認同”。所以,不論電影是為觀眾繪制的一幅夢幻的畫,還是為觀眾打開的一扇現實的窗,它都不愿意有異質的成分涂抹其上,它都不愿意在與觀眾產生聯系的過程中受到外界的干擾。從這個意義上講,看電影是孤獨的、個人的行為,而影院的環境:黑暗的觀影區,一人一座,保持靜默,都是在強化著這種私密性和獨享性。
在某種程度上,基于互聯網技術的觀影模式的創新正強化了電影觀看機制“窺視”“認同”的特征。浸入式電影,VR體驗式電影和基于情節的互動式電影(AB劇),不僅制造身臨其境的真實效果而且創造敘事劇情的個性體驗,它們延續電影的3D數字技術和網絡游戲的多場景選擇,不斷向巴贊所說的“機械復現現實”15的完整電影演進。它們都是在遵循百余年形成的觀影機制的基礎上,探索電影的新形態。然而,“彈幕”“跨界直播”嘗試凸顯影院的集體性和參與性,讓看電影像參加綜藝節目那樣充滿即時的交流與互動,這種創新溢出了傳統觀影模式的邊界,并非常態。“彈幕”中斷了觀眾和銀幕之間的認同,本質上是一種集體圍觀和吐槽;“跨界直播”播的已然不是電影,影院彰顯的是其聚集的劇場特性,是作為“城市會客廳”的交際場所,本質上是影院功能的變化;銀幕是通往觀眾心靈的窗口,“看電影”是觀眾和影片的交流。當“多屏共存、跨屏傳播”倒逼我們思考“什么是電影”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堅持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創造的“超越現實、批判現實”的審美本性;更應該堅持電影是被觀眾對象化的審美客體,是期待觀眾欣賞、接受并轉化為心理能量的視聽存在。
這是一個“產業融合”的時代,這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這是一個“跨屏傳播”的時代,同樣,這也最應該是“電影回歸電影”的時代!電影,這個商業與藝術、工業與文化的綜合體,在誕生之初就決定了其不斷吸收各種藝術手段,融合各種媒介資源,吸納各種技術革新的巨大包容性。戲劇、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文學,不斷為電影供給著藝術的營養;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介一次又一次為電影插上騰飛的翅膀;聲音、色彩、寬銀幕、數字技術,每一次技術革新都為這個綜合體增添巨大的生命活力。而電影自身也進行著各種形式的商業探索和藝術創造,一次次尋找更新穎、更自由的表達方式,尋找與文化和時代相融合、相對話的視聽建構。當“互聯網+”成為電影產業的新常態,我們堅信,“互聯網+”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和短暫的商業繁榮是無法遮蔽電影的藝術光環的。不管時代潮流如何變化,觀眾對于好電影的需求永遠都不會變,電影作為訴諸人類心靈的藝術有機體,也絕不會被機械化、工具化的網絡所取代。
【注釋】
①于冬、陳鵬:《理解電影革命:“互聯網+”與電影相遇后的內容全環節創新模式》,《當代電影》,2015年第7期。
②龔宇:《龔宇:電影院一定會消失》,《科技日報》2014年10月15日。
③李三強:《“互聯網+”時代我國電影面臨的沖擊與挑戰》,《當代電影》,2016年第4期。
④黃昌勇:《互聯網遇上電影的冷思考》,《光明日報》,2015年6月26日。
⑤[美]安德魯·基恩:《網民的狂歡——關于互聯網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譯,海南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19頁。
⑥《紙牌屋》的創作成功很大一部分得益于Netflix公司海量的用戶數據積累和分析。
⑦[美]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滕守堯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頁。
⑧張宏森:《抵達電影光榮的目的地——在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新常態:互聯網+與產業升級”論壇上的發言》,《當代電影》,2015年第7期。
⑨[蘇]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時光》,陳麗貴、李泳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
⑩[美]喬治·布魯斯東:《從小說到電影》,高駿千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版,第69頁。
?陳曉云,鮮佳:《難以定義的電影格局——對當下導演群體及其創作現象的一種觀察與批評》,《當代電影》,2014年,第12期。
?陳旭光:《猜想與辨析——網絡媒介背景下的“中國電影新勢力”》,《文藝研究》,2014年,第11期。
?戰迪:《“網生代”導演群體的文化轉型芻議》,《文藝爭鳴》,2015年,第8期。
?同⑧。
?[法]安德烈·巴贊著,崔君衍譯,《電影是什么?》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頁。
本文系2016年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互聯網語境下中國電影產業生態的轉型與升級》(項目編號2016-gh-022)階段性成果。
郭海洋,許昌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