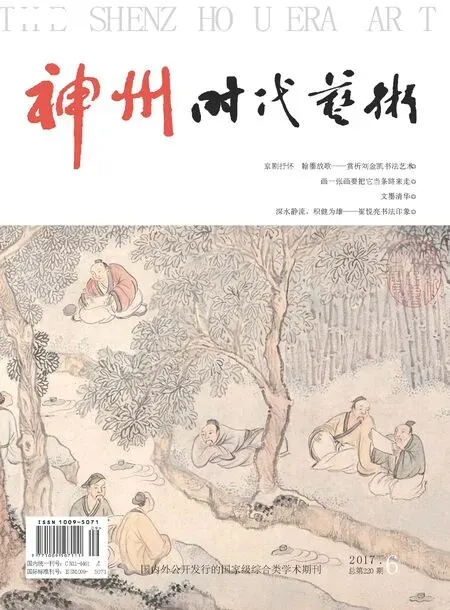假如民國大師走進今天的課堂
賀有德
中國歷史上,民國時期復雜而又特殊:軍閥混戰(zhàn),時局動蕩,但政府包括軍閥在內,一直尊師重教,且能落到實處,使得當時的中國教育走在了世界前列,不能不說是個奇跡;更讓人稱奇的,是雖逢亂世,仍出現(xiàn)了一批當之無愧的大師,形成了類似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面。
這些大師們大多與教育有緣,且其課堂文化與教學方式特色獨具,教育趣事空前絕后,讓后來者捧腹之余,再看看當今的教育、教師、教學,不能不深思之。
突發(fā)奇想:假如這些大師們走進今天的課堂,又將如何?
“狂人”劉文典講課前,先備好茶水和煙袋。講到痛快處,一邊抽煙一邊講課,下課鈴響了還在繼續(xù)。更有趣的,講《月賦》之時,居然還選擇明月當空之夜,擺上一圈座椅,自己坐在中間,對著一輪皓月“頌明月之章”。
若在今天,如此教法豈能容忍!喝茶尚可考慮,抽煙是絕對不行了,拖堂也不受歡迎。至于《月賦》式的授課,像極了孔子講學,印度詩人泰戈爾也喜歡這樣,但在今天的教育者聽來,無異于“天方夜譚”,一笑置之,敬而遠之!
在課堂上,黃侃每講到精彩處,往往戛然而止:“這里有個秘密,僅僅靠北大這幾百塊錢的薪水,我還不能講,你們要我講,得另外請我吃飯才行。”平時只管講課,從不布置作業(yè)。期末考試,不看試卷,也不打分。教務處逼急了,便寫紙條:“每人80分”
在今天的課堂上,教師敢這樣公開“索飯”那還了得,不被吐槽者的口水淹死才怪。至于“每人80分”式的“創(chuàng)舉”,還不是特大丑聞?不被學校開除,也會被家長轟走!
錢玄同總在課前趕到,門外等候,鐘聲一響,即上講壇,用鉛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然后開講。口講指畫,滔滔不絕,從不帶書本,也不考試,每學期批定成績時,按點名冊的先后,60分、61分……如果學生有40人,最后一個就得100分,40人以上,就重新從60分開始。
老錢這樣子,在今天可是喜憂參半:準時進教室,點贊;口講指劃難能可貴,滔滔不絕讓人欽佩,不帶書本內容爛熟,再次點贊;可不考試、亂打分,可是犯了應試教育大忌,要知道:考考考,教師的法寶——法寶怎么能丟?
吳宓教學非常認真,必提前十分鐘趕到教室,從不缺課、早退。尤其“憐香惜玉”,對女學生百般呵護,在西南聯(lián)大講《紅樓夢》時,見有女生站著聽,立即停下來,從旁邊教室搬來椅子,等女學生坐好,才繼續(xù)講課。
這樣的教學熱情與敬業(yè)精神,在今天看來,完全是頂級優(yōu)秀的樣板。可“憐香惜玉”之舉,不好說了——如果不會對男生“一視同仁”,恐怕就“難平民憤”了……
學貫中西的王國維,上課不遲到,上完課就走。上課時,有一說一,實事求是,絕不弄虛作假。講《尚書》時,當堂告訴學生:“這個地方我不懂。”講到研究有素的內容時,底氣十足:“我的研究成果是無可爭議的。”可惜課堂氣氛沉悶,又是一口方言,真正聽課的學生很少。
無疑,即使在今天,不遲到、不拖堂、不作假、有底氣,都難能可貴。但滿口方言,課堂不生動,在厭學成風的教學環(huán)境里,肯定不受歡迎,領導、同事、學生、家長,都會反感,甚至鄙視,其處境不容樂觀。
“老頑童”金岳霖上課提問,學生太多難得叫上名字。于是喊“今天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回答問題”,這樣一來,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同學又緊張又興奮,因為能夠流利地回答出金教授的提問那可是大出風頭。
如果在今天,課堂上如此提問,那可是大大的笑話了,甚至會“班上大亂”;學生會笑話,同行會笑話,領導呢?結局就不美妙了。何況,當老師的,原本應該記住學生的名字,課堂上叫出學生名字,學生挺高興,因為,聽到別人叫自己的名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聲音。
課堂上,葉公超一上來便讓坐在前排的學生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段落,大喝一聲:“停!”然后問大家有問題沒有,如果沒有,學生繼續(xù)。后來,學生們摸出了規(guī)律,誰愿意朗讀就坐在前排,否則就往后坐。
聽、說、讀、寫,是課堂上需要培養(yǎng)的四種能力;不能面面俱到,也得分個主次。一味強調朗讀,一如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做詩也會吟”,那可就“四缺三”了,能力的培養(yǎng)大打折扣;而且,教學方式單一、枯燥,氣氛不活躍,效果很可能不理想,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每當學期結束,評定學生成績,林語堂坐在講臺上,拿出學生名冊一一唱名,學生依次站起來。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學生一看,便定下分數(shù)。對沒有十分把握的學生,他就請對方到講臺前,略微談上幾句,然后定分。還未到學期結束,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程度,他已心中有數(shù),敢于“相面打分”。
“相面打分”?不能不說很“新潮”。今天一次統(tǒng)考,從學校的監(jiān)考安排到老師們的監(jiān)考、閱卷、統(tǒng)分、登記,到寫評語發(fā)通知書,那可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環(huán)環(huán)相扣,一氣呵成。老師們好累——林語堂先生的做法,是真正的解放自己,也解放學生了,可在今天,走到哪都行不通……
史學大師蒙文通,把考場設在了茶鋪,讓學生出題。學生按指定分組去陪先生喝茶,學生提問,先生回答。先生根據(jù)學生提問的水平,判定學生的專業(yè)水準。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即能考出學生的學識程度。如此考試,讓人叫絕。
今天,如此考試,只能“絕跡”;別說今天不會有,以后也不會有。至多,也得面試那般,先生問,學生答。何況,今天的學生提問,自然選擇簡單的、有把握的,于先生毫無意義;先生答問,輕而易舉,似乎也難知學生深淺。更何況,倘若學生提問難了,先生答不上來,豈不斯文掃地、大煞風景?
梁思成講完最后一節(jié)課,問道:“課講完了,為了應酬公事,還得考一考吧?諸位說怎么考好?”見無人答話。梁先生又說:“反正是應酬公事,怎么都可以,說說吧。”還是沒人答話。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那就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請選課的舉手。”還是無人舉手。梁先生笑了:“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謝謝諸位捧場。”說著,向講臺下作一個大揖,飄然而去。
今天的考試,“鄭重其事”,如臨大敵,保密、監(jiān)控、屏蔽、機動監(jiān)考,齊派上用場,豈是“應酬公事”?考試命題,豈能問學生?“謝謝諸位捧場”?然后“飄然而去”?在今天看來,可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
大師們的教育趣事,異彩紛呈,特色獨具,讓人大開眼界;若走進今天的課堂,這些名副其實的大師們,可就不合格,難免淪為庸師,甚至慘遭解聘……
然而,百思不解的是:那樣的大師在那樣的課堂用那樣的方法,偏偏培養(yǎng)出了大師;今天的名師在今天的課堂用今天的教法,卻再也沒有培養(yǎng)出大師來。于是,有人憂心忡忡地感慨:大師遠去,再無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