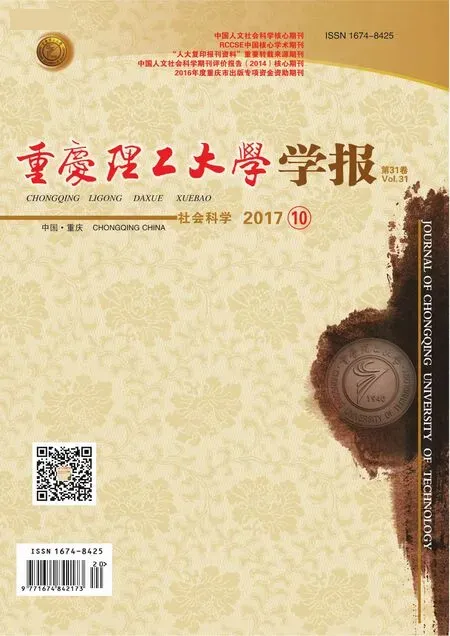從標準化到精準化: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轉向
趙 超, 金華寶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 400041)
從標準化到精準化: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轉向
趙 超, 金華寶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 400041)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主要根據決策者的偏好而非民眾的需求作出,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失衡導致“供給過剩”和“供給真空”現象并存。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是構建以民眾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大數據具有的全樣本化、精準化、個性化等特點與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具有耦合性,有助于實現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的精準匹配與無縫對接。將大數據技術嵌入公共服務供給的輸入、轉換、輸出、反饋等環節,構建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有利于拓展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領域的理論研究,且為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公共服務供給;大數據;標準化供給;精準化供給;民族地區
隨著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對口支援邊疆民族地區政策和精準扶貧各項工作的深入推進,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總量顯著提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明顯增強,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地區之間公共服務的非均衡分布格局。然而,民族地區“大水漫灌”式的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忽視了不同地區和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個性化公共服務需求,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較為明顯的結構失衡問題[1-2]。公共服務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和錯位,不僅使有限的公共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導致“供給過剩”和“供給真空”現象并存,而且長期忽視民眾的需求可能會造成政府合法性資源流失。大數據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技術支撐,有利于優化公共治理的外部環境,拓展制度設計的彈性空間[3],為公共服務的精準化供給提供核心技術和治理思維支撐。因此,如何運用大數據構建精準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新模式,以便破解民族地區“大水漫灌”式標準化供給產生的“供給過剩”和“供給真空”并存難題,助力精準扶貧向縱深發展,確保民族地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問題的提出:基于綜述的視角
概念界定是問題研究的邏輯起點,國內外學者對“公共服務”的概念界定可謂眾說紛紜。筆者比較傾向于陳振明的觀點:“公共服務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共部門運用公共權力,通過多種機制和方式的靈活運用,提供各種物質形態或非物質形態的公共物品,以不斷回應社會公共需求偏好、維護公共利益的實踐活動的總稱。”[4]13政府及其公共部門提供公共物品的過程就是公共服務供給,而供給的出發點是回應民眾的公共物品需求。近年來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及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戰略的提出,諸多國內學者高度關注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創新問題。尹華、朱明仕認為現有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有效供給不足,供給缺位、越位和錯位并存,要建立一主多元型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5]。陳娟發現公共服務供給是根據決策者偏好而非公眾需求,提出要建立以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6]。陳水生則認為公共服務存在重供給、輕需求表達的傾向,要實現公共服務供給決策與需求表達的對接[7]。這些研究指出了公共服務供給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即標準化供給忽視了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供給缺乏精準性。
公共服務供給是公共行政領域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國內外學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研究成果,似乎該領域的研究空間已相當狹小。然而,大數據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技術革命”及其引起的治理思維變革和政府流程再造,為公共服務供給引入了新的“變量”,開辟了公共服務供給研究的新領域。大數據作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日漸成為許多國家搶占精準化治理話語權和政府信息化高地的戰略選擇,被廣泛應用于公共服務供給領域,使公共服務供給趨于精準化。從實踐層面來看,在發展中國家,埃及政府使用大數據挖掘技術提升公共服務供給;印度借助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普及利用率,基于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普遍建立公共服務中心,使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度得到提高。在發達國家,澳大利亞通過大數據分析系統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增加服務種類,并與其他政策和技術配合,為公共服務的精準化供給提供了更好的政策指導;德國建設大型基礎數據庫和地方數據庫,在公共治理過程中運用大數據資源幫助作出公共服務供給決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內學界關于大數據作為政府治理工具和治理思維支撐的研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些研究成果中一部分涉及大數據與公共服務供給及其精準化問題。如:陳潭認為大數據具有量化、全面、精準的分析功能,運用大數據技術能夠精準感知公共服務的公眾滿意度,提供更加個性化和便利化的公共服務,還可以對不同社區的差異化需求進行分析,從而提供精準化的公共服務[8]。郭建錦、郭建平認為大數據可以對公共服務對象的細微行為特征進行分析,精準把握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推送個性化、精細化的公共服務產品[9]。鄧念國提出大數據技術通過公共服務供需信息及時匹配,使公共服務供給更具“匹配性”和“錨向性”[10]。薛曉東等則認為大數據為公共服務打造信息共享平臺,有利于整合政府各部門和各層級所掌握的數據,從而打破職能部門間的界限[11]。陳自強是為數不多關注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的學者,他認為大數據可以促成國家和社會的良性互動,使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呈現出個性化、精準化、智能化等特點[12]。
總體而言,近年來,學界對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以及大數據背景下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獻基礎。但學界對區域性、特殊性、差異性突出的民族地區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的關注明顯不足。因此,在深入探討大數據與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具有耦合性的基礎上,運用政治系統分析方法,構建基于大數據平臺的民族地區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不但可以擴充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領域的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實踐層面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提供理論支撐。
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務、教育服務、基礎設施服務、公共醫療和社會保障服務等與少數民族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領域。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既包含同其他地區一樣的共性問題,又具有自身的特殊問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過多年的發展建立了相對完備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供給總量得到了顯著提升,其公共服務供給的重點主要是調整供給結構,使公共服務供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進一步提高。然而,受到歷史條件、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廣大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總量處于先天劣勢,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公共服務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可能會成為民眾國家認同的潛在或者現實障礙,因此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不僅要解決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還要解決供需結構失衡的問題,精準回應民族地區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進而提高民族地區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換言之,優化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為增強少數民族民眾的國家認同提供了一條有效路徑。
二、民族地區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現實困境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民族地區公共服務的供給問題,尤其是在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背景下,諸多公共資源向民族地區傾斜,民族地區貧困落后的社會面貌得到顯著改觀。在“大水漫灌”式的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下,公共資源的大量投入帶來了前期的高效產出,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總量得到了顯著提升,但隨著資源投入到達“拐點”,邊際效益遞減現象和差異化公共服務需求難免凸顯出來。這就要求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必須向精準化方向發力,從而有效回應民眾的差異化、個性化公共服務需求,使資源投入收益得以優化。“共享發展”理念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通過各種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使民眾能夠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在非均衡化發展的民族地區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公共服務的精準化供給確保民族地區民眾能夠平等地共享發展成果,縮小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是民族地區民眾增強國家認同的重要渠道。
(一)同質化公共服務供給忽視需求差異性
“公共服務精細化供給必須以需求為導向,避免公共服務資源的浪費與重復,才能實現效益的最大化。”[13]在多元化、異質性突出的現代社會,不同地區、職業、年齡、性別、民族等群體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顯然存在差異。同時,公共服務需求具有明顯的結構性,可分為民生型需求、文化型需求、發展型需求、生態型需求[14],各類型需求之間具有一定的優先次序。民族地區由于地域面積遼闊、居住分散、生活習慣不同、文化差異較明顯等,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表現出更為顯著的差異性。相比而言,民族地區對關系到生存和發展問題的民生型公共服務需求更加突出。然而,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或缺乏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機制,或缺少有效的公共服務需求感知系統,或直接忽視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進而導致“供給過剩”和“供給真空”并存。這種缺乏彈性的供給模式難以滿足民眾多樣化、差異化的公共服務定制需求,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性不足。長此以往,勢必會影響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進而影響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和認同,正如有學者指出,任何政治體系都應盡力滿足民眾的需求,據此獲得民眾的支持和認同[15]77。
(二)供給主體間缺乏聯動協作機制
在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下,各層級政府、部門之間公共服務信息流動不暢,缺乏公共服務信息交互與共享的整合平臺,公共服務政策五花八門,難以實現縱向與橫向的合作。信息資源的交互和共享受到管理體制和技術條件的制約,導致政府部門孤軍奮戰、資源分散、多頭管理、重復供給以及信息孤島等現象嚴重。在這樣的模式下,公共服務需求信息在逐級上報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人為障礙”導致信息損耗,在漫長的“上報與下達”過程中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極有可能已發生改變,或者政策執行所需的條件已發生改變,進而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無效。比如衛生醫療領域一些流行病和傳染病的集中爆發,若按照傳統模式逐級上報,可能會因耗時過長導致決策滯后,進而加重病情的蔓延。如果基于大數據平臺建立病情檢測和應急系統,可以有效提高防控病情的反應速度,為病情的防控和治理贏得更多的寶貴時間。
(三)公眾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決策不足
在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下,信息技術落后及監管體系不完善,公共服務供給決策者難以獲得進行科學合理決策所需的信息充分條件,致使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決策以靜態、封閉的方式在抽樣數據的基礎上作出,從決策信息的采集、篩選、加工到最后決策不僅耗時過長、滯后性明顯,而且樣本的代表性存疑。同時,決策過程中公眾的參與不足。公眾的積極參與不僅是決策者作出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重要信息來源,而且是民眾產生政策認同不可或缺的渠道。因此,必須實現各層級政府以及橫向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讓決策者更加及時、全面、準確地掌握公共服務信息資源,實現公共服務的動態管理;建立跨層級、跨部門的公共服務供給聯動機制,對部門化、分散化的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實現“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無縫隙運作顯得尤為必要[16]。大數據的快速發展為破解民族地區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的各種困境提供了核心技術支撐,“無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還是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個性化特色都異常明顯,個性化需求以大數據應用為載體獲得了配送和滿足”[17]。
三、大數據與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的耦合性
大數據并不只是技術層面的創新,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人們的治理思維,讓人們從過去重點關注“為什么”到“未來應該是什么”轉變[18]1,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差不多思維”[19]329。大數據具有的全樣本化、精準化、個性化等特點重塑公共服務的外部治理生態,再造公共服務流程,為精準回應民族地區民眾多樣化、個性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和思維支撐。
(一)大數據有利于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科學化和精準化
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受到技術條件和管理體制等因素的制約,在公共服務供給決策過程中往往以“局部代替整體”的隨機抽樣方式獲取信息。這種隨機抽樣方式要想獲得較為準確的信息,需要滿足許多條件,一旦隨機采樣過程受到客觀環境過多的影響或者主觀上存在偏見,就難以得到精準的結果。公共服務信息充分是精準化供給的基礎,大數據時代舍棄樣本分析方法而代之以全樣本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分掌握民眾公共服務需求信息,彌合供給與需求的裂縫。利用各類新媒體的公眾數據流、公開的公共數據庫、商業數據庫等,準確掌握民眾的公共服務行為偏好,并建立公共服務人口基礎數據庫、公共資源地理分布數據庫和經濟社會發展基礎數據庫,為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提供精準的數據信息。另外,運用大數據還可以精準匹配公共服務需求,通過網絡平臺促進公共服務供給方和需求方的雙向互動,破解信息不對稱的難題,使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更具科學性和精準性。具體而言,合理運用以人口特征為核心的基礎數據、公共服務資源地理分布數據、公共服務機構空間分布數據等作為信息支撐,使決策者直觀精準地掌握公共服務資源的分配情況。這樣可以避免公共服務資源配置“大水漫灌”式的平均主義現象發生,實時精準定位公共服務對象的地理位置,使公共服務供給能夠精準推送給民眾。
(二)大數據有利于精準分類公共服務需求
不同地區、民族、性別、年齡、職業等群體的差異對公共服務可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需求。在收集大而全的海量公共服務需求信息數據后,還需對其進行細化分類,挖掘數據背后的規律,才能分門別類作出精準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比如,深圳建立了大量的社康中心,通過人口、法人、房屋信息集成系統獲知全市人口的地理分布情況,直觀掌握醫療資源的空間分布。通過大數據技術對不同人口特征的服務對象進行大而全的數據采集、篩選、整理、統計等,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偏好數據進行精準分類,并根據預設的公共服務供給方案精準推送公共服務。又如,成都網絡理政平臺依托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統計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分布和其他訴求、辦理情況、滿意度等,精準分析問題的類型和發生的地點。在收集和進行公共服務需求信息分類時,不再采取傳統的入戶調查、信息逐級上報等方式,避免了耗時長、效率低等缺點,大數據時代只需對各層級政府的信息數據庫進行匯總、分析、分類,就可以全面且高效地精準掌握公共服務需求。
(三)大數據有利于建立公共服務動態精準化管理機制
受到信息不充分、資金有限等客觀條件以及主觀上人的有限理性制約,外部條件的改變可能會導致現有公共服務供給決策難以適應。原先公共服務資源不足的地區經過一段時間的持續供給后可能已經達到既定目標,若繼續供給則邊際效用大大降低,甚至會造成資源浪費。因此,需要及時調整甚至終止現行的公共服務供給政策,而調整和終止的前提是對現有公共服務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科學評估。通過大數據設定公共服務供給數量、質量、產生的效應、分布等的評價指標體系,實時動態地監測公共服務供給情況,因時因地作出調整,建立公共服務供給進入和退出的動態精準化管理機制。同時,利用大數據技術建立的每一個公共服務對象數據庫,都可以動態追蹤公共服務供給的最新狀況,一旦偏離政策目標便及時進行矯正或終止,提高公共服務的精準度和有效性。這種公共服務動態精準化管理機制能夠有效克服以往政策執行過程中靜態管理和滯后調整的弱點,還可以對公共服務資源的去向進行動態追蹤,精準掌握每一項公共資源的使用情況,保證公共服務資源的高效投入。
(四)大數據有利于公共服務過程的公眾參與
在缺乏有效監督和公眾參與不足的情況下,公共服務供給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很有可能會依據個人偏好而非公共需求,制定對其職位晉升或獲得其他利益最有利的政策。許多公共服務供給決策依賴直覺判斷與主觀經驗,公眾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20]。比如,將大量公共服務資源投向更易獲得關注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忽視“以人民為中心”的差異化和個性化公共服務需求。公共服務過程公眾參與不足或者參與的有效性低,不僅會導致公共服務資源的浪費,加重公共資源分布的非均衡性以及民眾因發展差距可能產生的相對剝奪感,長此以往還可能會削弱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和認同。通過大數據技術可以實現與互聯網、移動端APP、自媒體等多種平臺的無縫對接,公眾能夠通過多種新的渠道進行網絡民主協商直接表達公共服務需求,省去不必要的中間環節,縮短需求信息送達決策中心的空間距離,減少需求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損耗。
四、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的構建
戴維·伊斯頓把政治生活看作是政治系統與所處環境互動的過程,創造性地構建了政治系統分析的理論框架,把政治系統運行的過程主要分為輸入、轉換、輸出、反饋等環節[21]3-15。這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洞與微觀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局限,有助于理解政治行為與所處環境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一分析方法對公共服務供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也可以看作主要由公共服務需求表達(輸入)、公共服務供給決策(轉換)、公共服務供給(輸出)、公共服務動態監管(反饋)等環節構成的一個閉環系統,將大數據技術嵌入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就構成了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見圖1)。

圖1 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的分析框架
通過大數據收集、識別、分析民族地區公共服務需求是實現精準供給的前提和邏輯起點。一方面,民族地區民眾通過諸如帶有GPS定位功能的公共服務需求表達系統以及其他集成地理信息的需求表達移動終端,自下而上主動表達公共服務需求的過程,為此需要大力建設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相應的大數據配套設施;另一方面,決策主體運用大數據平臺整合傳感器網絡數據庫、用戶行為數據庫、互聯網數據庫等自動收集和調查公共服務需求,自上而下準確掌握民族地區不同人口、年齡、性別、消費水平等群體的需求及其分布狀況。將與“民族”密切相關的變量,比如民族文化、民族風俗習慣、民族經濟等納入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制定過程之中,使決策更具有精準性。公共服務需求輸入完成后,鋪天蓋地的海量公共服務需求數據并不能直接為決策服務,還需要對其進行篩選與整合。不同目標群體的公共服務需求有差異,需要通過云計算等技術進行大數據分析,對目標人群的公共服務需求進行分層聚類。民族地區對民生型公共服務的需求相對較多,需要政府供給更多兜底性質的公共服務,不斷提高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總量。與此同時,切實保障少數民族在公共服務領域的知情權和參與權,以便政府在進行相應的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時,能夠將不同民族群體的需求吸納進去,拓寬少數民族民眾公共服務需求表達的渠道。比如:可以發展族際民主協商、網絡民主協商收集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數據,然后通過大數據智能優化技術將分散的公共服務需求整合起來,使需求信息能夠充分有效地傳遞到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系統。
如果少數民族民眾的公共服務需求信息被阻隔在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系統之外,沒有被納入政策之中,需求信息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系統進行具有科學性和精準性的決策,首先要將篩選和整合后的公共服務需求吸納進來,實現公共服務供需信息的精準匹配與融合。這就要求政府在進行公共服務供給決策的過程中要重視少數民族民眾的參與權、話語權,使民族地區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模式由行政權力過度集中向多元參與、共同協商對話轉變。只有公共服務需求信息還不足以幫助決策者作出具有科學性和精準性的決策,還需要對備選決策方案進行成本測算,并計算備選方案與現有可調配的公共資源的匹配度。基于大數據平臺,運用云計算等技術測算出每一個備選決策方案的成本,然后將符合預期成本的方案與可調配的資源進行精準關聯,從而選出成本低、操作性強的最優決策方案。作出公共服務供給決策以后,還需要通過大數據構建跨部門、多層次、全方位的公共資源配置聯動機制,打破各層級政府及其橫向部門之間的行政壁壘,實現信息互通和資源共享。民族地區占據的土地面積龐大,各級政府之間受到地理因素等影響,資源、信息流通不暢,單兵作戰的現象并不少見,基于大數據實現民族地區公共服務資源、信息的共享和流通勢在必行。
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方案確定、資源調配啟動后就進入公共服務供給(輸出)環節。單個小范圍的公共服務需求可根據其GPS定位信息由屬地公共服務機構直接供給對應的公共服務;區域性的公共服務需求可以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數據,明確供給主體和確定最優的公共服務組合與資源組合方式,精準輸出公共服務,有效實現公眾需求與公共資源高效配置的雙向融合。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菜單式”公共服務需求成為可能。公共服務政策輸出后并不會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還需要對政策的執行情況、實施效果等進行持續追蹤,可以基于大數據平臺建立公共服務政策執行和實施效果數據庫,實現對公共服務過程的實時、動態監管。在公共服務政策輸出過程中,可以根據既定的指標體系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精確評估,一旦偏離政策目標便及時進行矯正或終止,避免因政策無效而導致公共資源浪費。如果公共服務供給效果不佳甚至無效,民眾就會進行新一輪的公共服務需求表達,經過一次或多次循環直至其公共服務需求得到充分滿足。一個經過民族間不斷進行民主協商和平等對話而形成的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可以獲得各民族民眾的普遍支持和認同,進而為公共服務相關政策的執行提供有效的政策認同基礎,也為增強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結語
在民族地區標準化公共服務供給模式下,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失衡,導致“供給過剩”和“供給真空”并存。大數據具有的全樣本化、精準化、個性化等特點為破解這一難題、實現民族地區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提供了技術支撐。運用政治系統分析方法,將大數據技術嵌入公共服務的輸入、轉換、輸出、反饋等環節,在理論層面構建了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層面上的嘗試,其合理性還需實踐進一步檢驗。再者,大數據的發展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不僅要加強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著力培養大數據專業人才,不斷提高公共數據開放意識,逐漸增強大數據思維等,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結合大數據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應用實踐,對現有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模式進行修正和完善,從而使這一模式更具有解釋力。
[1] 郭小聰,代凱.供需結構失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中的突出問題[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140-147.
[2] 曹愛軍.公共服務“供給管理”的邏輯與進路[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23-28.
[3] 唐皇鳳,陶建武.大數據時代的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建設[J].探索與爭鳴,2014(10):54-58.
[4] 陳振明.公共服務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 尹華,朱明仕.論我國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協調機制的構建[J].經濟問題探索,2011(7):13-17.
[6] 陳娟.“雙向互動”: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角色定位與路徑選擇[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2):53-59.
[7] 陳水生.城市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機制研究:一個分析框架[J].復旦公共行政評論,2014(2):110-128.
[8] 陳潭.作為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大數據×”[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7-8.
[9] 郭建錦,郭建平.大數據背景下的國家治理能力建設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5(6):73-76.
[10] 鄧念國.公共服務如何實現精準化供給[N].學習時報,2015-12-07.
[11] 薛曉東,張立佧,薛飛.大數據下公共服務的特點及趨勢[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6):1-4.
[12] 陳自強.大數據視野中的西部民族地區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J].社會科學家,2017(4):70-76.
[13] 王正攀.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公共服務精細化治理邏輯——基于重慶南坪的個案分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2):56-62.
[14] 胡家,尚明瑞,陳思明.西北民族地區農民公共服務需求表達機制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2016(2):129-132.
[15] 夸克.合法性與政治[M].佟心平,王遠飛,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16] 王正攀.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公共服務精細化治理邏輯——基于重慶南坪的個案分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2):56-62.
[17] 陶鵬.大數據與微時代:虛擬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雙重建構[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106-111.
[18]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9] 涂子沛.大數據[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
[20] 王法碩,王翔.大數據時代公共服務智慧化供給研究——以“科普中國+百度”戰略合作為例[J].情報雜志,2016(8):179-184.
[21] 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M].王浦劬,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FromStandardizationtoPrecision:theTurnofthePublicServiceSupplyofEthnicAreasinBigDataAge
ZHAO Chao, JIN Huabao
(Party School,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ongqing 400041, China)
For a long time,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n ethnic areas is based on the decision makers’ preference rather than public dem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leads to “over supply” and “supply vacuum”.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conundrum is building a public service-oriented precise supply mechanism which base on the public demand. Big dat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ll-sample, precision and personalization, which is coupling with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It is helpful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matching and seamless connection betwee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Embedding big data technology into the input, transformation, output and feedback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process, and 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 precision supply mechanism of ethnic areas,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ield of public service precision supply,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e of public service precision supply in ethnic areas.
public service supply; big data; standardized supply; accurate supply; ethnic areas
2017-07-09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科研項目“基于大數據平臺的公共服務精準化供給機制構建研究”(CQDA2016A—004)
趙超(1990—),男,貴州三穗人,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民族政治; 金華寶(1973—),男,河南固始人,編審,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治理。
趙超,金華寶.從標準化到精準化:大數據時代民族地區的公共服務供給轉向[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10):92-98.
formatZHAO Chao,JIN Huabao.From Standardization to Precision:the Turn of the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Ethnic Areas in Big Data Age[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10):92-98.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10.012
D633;C931
A
1674-8425(2017)10-0092-07
(責任編輯鄧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