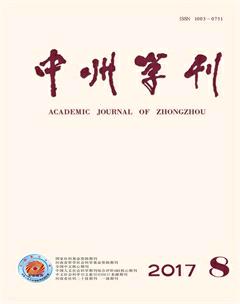現代中國文論轉型的四種路向
賀昌盛
摘 要: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基本樣態是在晚清時期古今中西交會互生的情境中誕生并演進而來的,追溯其源頭,大體可以概括為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和梁啟超所代表的“人文、修辭、審美、社會”四種路向。這四種路向除了各自都有其或隱或顯的延續之外,也與當下的“文化研究”“形式理論”“審美主義”及“社會批判”等文學理論取向,有著潛在的呼應與對接。重新發掘這些既有的資源,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轉型具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現代中國文論;文學;理論;轉型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8-0147-05
有學者將中國文論現代轉型的源頭追溯至梁啟超的工具主義式政治書寫與王國維的自主主義式審美書寫兩種基本理論模式的確立上①,這種看法無疑是深刻而富于洞見的。但僅僅停留于此,也容易陷入“革命/審美”式此消彼長的既定思維框架之內,進而忽略或遮蔽了以其他形式存在并延續著的文論探索。事實上,晚清時代中國文學思想的轉變,首先應歸因于由日文“文學”一詞逆向輸入漢語語境之后所引發的多重層面的變化與重新定位。作為日制新詞的“文學”②,在進入漢語語境后,一直在尋求能夠得以生根的土壤,以便獲得必要的本土理論資源的滋養與護育。由此,對于文學特性與功能等的界定就成為晚清學人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概而言之,晚清有關文學的理論闡發有四種主要路向:一是章太炎的廣義文學論,可視為現代“人文/文化”研究的源頭;二是劉師培的“修辭/文章”論,可歸為文學之“語言/修辭”研究一路;三是王國維的超功利“詩性/審美”說,已被看作中國現代文學審美論的發端;四是梁啟超的“文以致用”論,它沿襲并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文以載道”思想,可以看作是向現代文學社會學研究的轉換。新文化運動后,中國文學的總體面貌雖然與傳統已經形成迥然的差異,但文學思想上對于人文學、修辭學、審美論和文學社會學等不同重心的趨向與選擇,與晚清時代所確立的基本路徑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從某種程度上說,現代中國的文學思想也正是由這四種基本的路向共同建構呈現出來的,只不過因其各自形態的或隱或顯而常常容易被忽略與遮蔽而已。
一、“人文/文化”研究
在晚清學人中,章太炎一直被公認為傳統經學的末代大師。一般認為,章氏治經學宗于漢學考據,以小學為本,這種看法忽略了章氏在西學影響下對于傳統經學的根本性改造。這種改造的核心表現,一是借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章太炎譯,商務印書館,1902)中所闡發的“創造進化”思想確立起重建民族學術的自覺意識;二是不再獨尊儒學為經學的唯一正統,而將諸子并列為民族文化的正源。前者呼應的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強調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后者轉換的則是知識的一般形態,區別于儒學、道學、理學、君學等。章氏曾明確表示:“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③其于1910年刊行于日本的《國故論衡》即是以“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個部分的結構設計而成,其中的“文學(七篇)”可以看作是由語言向真理的過渡,“文學”以小學追溯其語言源頭,而以諸子為“文學”指歸,即所謂“鉤汲眢沈”以“熔冶哲理”。正是基于這樣的知識設計,章太炎給予“文學”一個總體的定義。他認為:“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闋,施之筆札謂之章。”④章氏所定義的“文學”實際指的是研究“文”的形制原則的“學問”,既包括“說/寫了什么”(思想觀念),也涵蓋“怎么說/寫”(語言)和“為什么說/寫”(作為緣由流脈的歷史依據)。這里的“文學”雖然表面上借用了日制新詞的“文學”,實際呼應的卻是漢語語境中“文章博學”的原初意味,而且特別強調“文”屬于“人”留下來的“痕跡”,這樣就打破了偏于辭采的“彣(紋)”與循于規矩的“章(彰)”之間的界限,同時與漢民族所固有的“人文/文史”傳統形成對接。
中國傳統學術一直遵循的是以儒家經學為主脈的思想取向,到清康熙時代才出現經、史、子、集分類并舉的格局,但仍然以經學為核心。章學誠的重大貢獻在于以“六經皆史”相號召,將經學重心轉移到史學上(仍保留儒家的中心地位)。章太炎則更進一步,視子學為學術之最高范疇,“諸子并舉”動搖的正是儒家正統的中心地位,這是他的創舉。回到先秦諸子有利于重新展示中國人文傳統多重路向并存的豐富面相,而以“文字/痕跡”本源為基礎,經“言說”以明辨“真理”的構想,與西式語言哲學之“言說/存有”論的思維模式并非毫無通融之處。但遺憾的是,章太炎只專注于“族裔同聲”層面上的逐本溯源,嘗試以恢復民族“本真言說”來重建漢民族的精神傳統(道統與學統),最終就只能退回到復古的老路上。所以,胡適才評價說,章太炎的“文學”定義推翻了“古來一切狹隘的‘文論”⑤,但是,“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輝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⑥,“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⑦。
章太炎之“文學”定義的關鍵啟發在于,如同“天文”(天相)、“地文”(地貌)所呈現的痕跡一樣,“人文”即人所留存的痕跡,最主要的就是“著于竹帛”及金石紙木等載體物之上的“文字”,研究這些“所著所作”即為“文之學”,這一定位恰與西文“Literature”在其詞源意義上的“著述/書寫/文法”⑧相吻合。就目前東西方學界已經普遍認可的文學的文化研究轉向來看,以文學為平臺的研究早已突破純文學的既定范疇,開始向多重維度形成輻射式的跨界延伸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章太炎所開辟的“大人文”視野需要引起我們的重新重視。
自章太炎以后,以文學面貌出現的現代形態的人文研究并沒有完全中斷。胡適“以文學求真理”的思路即與章太炎暗相呼應,朱希祖所謂的“文學為人類思想之樞機”⑨,謝無量的“大文學史”觀,錢基博對于“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構想,程千帆在其《文論要詮》中對于章太炎的推崇,錢穆對于“文學/文化”實乃一體兩面的定位,乃至徐復觀對于文學與心靈世界關系的探索等,其中都可以窺見超越于純文學之外的更為博大的人文關懷,“人文/文化”研究并沒有因為學科的界限而消逝。
二、“修辭/文章”研究
章太炎認為,“文”在其本源意義上就是“著”,“夫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文者不皆彣,是故推論文學,以文字為準,不以彣彰為準”⑩。也就是說,“文”所強調的既不是潤色,也不是采飾,“文”之所立,重在明道而不在修飾。但與章太炎并為晚清經學代表人物的劉師培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典籍稱之為“經”,正是“編織”的結果,正所謂“經緯相錯乃成文”。所以,真正的文學恰恰需要修飾。劉師培認為:“散行之體,概與文殊。……言無文藻,弗得名文;以筆冒文,誤孰甚焉。”?劉師培對于文學的定位源于阮元的“沉思翰藻”,“沉思”即言之有物,思有所得;“翰藻”則要求將所思、所得用最為恰當的方式傳達出來。以“沉思翰藻”為標準本于《文選》,《文選》不收經、史、子之類的著述,因為它們不屬于“文”;凡“文”,不僅要求有所悟得,更需要富有文采。阮元雖然將“沉思”與“翰藻”并舉,其重點是在強調“翰藻”的音韻辭采。由此,修辭層面的裝飾性就成為衡量“文”之高下的核心尺度。
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言:“中國文學,至于周末而臻極盛。莊、列之深遠,蘇、張之縱橫,韓非之排奡,荀、呂之平易,皆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詞,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惟文學臻于極盛,故周末諸子,卒以文詞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傳勿失。”?據此,劉師培認定,“文”在魏晉六朝之所以能夠崛起,正是出于它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華采、藻飾的自覺意識。這種修飾才是前代之“文”得以流傳的根本,同時也是文學最需要研究的問題。因此,《文選》之于劉師培才顯得至關重要。與周、漢時代相比,六朝“文學”空前繁榮,既有以“美飾”為目的的詩賦駢文,也有以實用為特征的論傳奏記;惟其紛紜錯雜,才會出現“文”“筆”之辨或“韻”“散”之分。劉師培重“沉思翰藻”的《文選》一途,是在突出“文”的修辭特質。在“文”的基本定位問題上,劉師培以“修飾”為準繩,與章太炎及桐城文法劃出了界限。
從現代語言學的角度看,“彰韻律”而“輕文字”似乎有以語音中心抵制文字中心的意味,這一點實際也是“辭達”與“翰藻”的分界。“辭達”者立意在“明道”,多以尚質/樸實為目標,章太炎所崇尚的“魏晉文”,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等,都可成為研習“辭達”一路文章的典范;“翰藻”者偏于性情,除了自身所固有的天分才干以外,更需要顯示出創造性的語言組織能力,所以更重視語詞表述自身形式上的美感,蕭統的《文選》即被此派中人奉為楷模。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認為:“尊重理智的修辭決定了成為中國文學中心的,與其說是所歌詠之事,所敘述之事,倒不如說是如何歌詠、如何敘述;換言之,往往常識性地理解素材,卻依靠語言來深切感人,這可說是中國文學的理想。”?在清季學人中,劉師培的文學理念確有其創見,使人對駢儷之文所蘊含的形式/修辭特性有了一種新認識。但遺憾的是,與阮元持論相似,由于劉氏過于強調文辭自身在音節、韻律、駢偶等表層形式上的美感,所以只能形成一種“翰藻”有余而“沉思”不足的理論格局。
劉師培所偏重的以文章為文學的路向可以看作是對章太炎的“無所區分”的“文”的定位的反撥。出于多方的抵制,《文選》一派在清末漸至頹逝,但從修辭/文體的角度來研究文學的思路卻一直有所延續,顧實的《文章學綱要》、汪馥泉的《文章概論》、馬宗霍的《文學概論》、蔣祖怡的《文章學纂要》等,所取的也正是這一路徑。在充分汲取傳統文章學資源的基礎上,最終奠定了后世“文學語言學”及“文學修辭學”的學理基礎。
三、“詩性/審美”研究
如果說劉師培主要強調的是“文”的外在形式的修飾性的話,王國維則是從文學自身內在的感性審美特質上對文學重新界定。王國維依據焦循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思想,將不同時代的特定文體并舉為文學呈現的多樣形態,楚騷、漢賦、唐詩、宋詞等,“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這樣就不必再糾纏“韻”“散”或“文”“筆”的問題,同時元之雜劇、明之傳奇、清之小說等,也都可以合理地納入到正統的文學研究范圍。當文體不再作為“文”之高下的價值判別標準時,作為“文”的精神內質的美感因素就被凸顯出來。
事實上,將“美感”視為文學的本質特性,完全是一種被強行移植的觀念。在古典形態的中國學術研究中,為了維護正統經學系統中“道、體、心、性、理”等核心范疇的地位不受到損害,純然感性的“美”常常被視為有害的因素而被排斥在學術之外。也正是因為如此,劉師培才會生出以形式層面的“文采/修飾”為文章正名的想法。與劉師培有別,王國維直接移植了康德、叔本華等人的西式觀念,以“真、善、美”并置,從根本上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以真為本施之以善”的“學統”格局。
作為一種舶來的觀念,“美”要在本土生根,就必然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滋養憑據。王國維的思路是依著觀念自身的本質性規定,從中國本土既有的資源中去尋找那些“附合”于這種“觀念”規范的具體例證。“美”作為一種先驗的存在形式,其功能首先在于“無用而有大用”,即它與求真、至善一樣,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實際的用途,但同時它又是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以詩、詞、曲、賦等樣態出現的文學,對于實際生活而言不過是“余裕之物”,但對于精神本身卻有超越之功,其正“附合”于“無用而有大用”的一般特性。由此,將“美”確定為文學的核心特質也就順理成章了。王國維認為:“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斗,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王國維將“美”的理念移植灌注在了文學之中,“美”作為一種全新的范疇徹底置換了傳統文學的既有內核——“道”。至此,文學才以一種獨立的面目走出經學的陰影。也正是因為審美成了文學新的內核,王國維才以《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文學小言》《屈子文學之精神》《紅樓夢評論》《人間嗜好之研究》《人間詞話》等一系列創造性的論述,建構起了包括“優美、古雅、宏壯、眩惑、悲劇、游戲、嗜好、境界、第一形式、第二形式”等在內的一整套有關文學的現代審美知識系統。
王國維的“詩性/審美”研究取向,可以看作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西論中據”的學術策略。從積極的一面看,這種策略從根本上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學術的基本面貌,并且促使中國學術本身初步完成了向現代學術的轉型;以西式美學理論為準繩來重新檢視中國傳統文學藝術,迄今已經形成某種相對普遍的對于審美主義的認同(包括海外“漢學”的諸多研究取向)。但從消極的一面來看,“西方中心論”的傾向自身所蘊含的弊端也已經逐漸暴露出來。當然,作為文學研究的路向之一,“詩性/審美”模式仍有相當的潛在資源可資開掘。
四、“啟蒙/致用”研究
與王國維類似,梁啟超也是援西學以治中國文學者。如果說王國維借助審美為文學提供了內質層面的理論定位的話,那么,梁啟超則主要是借助受進化論啟發所帶來的“(新)史學”轉型,使文學的外部功能獲得進一步的拓展。這種拓展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從“以史為鑒”到“以文啟智”的轉移。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完成的是傳統學術由經學本位向史學本位的重心轉換,但“文”的“載道”功能并沒有發生變化,儒家正統的思想仍然是“文”需要傳達的核心,只不過作為儒家思想的“道”從理學式的觀念灌輸變成了“有史為證”,即以“證據”為本位而不是以“說法”為本位,但“觀點/思想”本身并沒有變化。梁啟超將進化論引入史學,把中國傳統史學所固有的興亡更迭式的封閉性循環歷史形態,改造成了“今勝于古”“未來勝于今”的直線式歷史進化形態。所以,他才堅信:“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歷史學。”?他認為,由社會—歷史的進化可以順理成章地推導出文學的進化。“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自開展,靡不循此軌道。”?正因為如此,對于梁啟超而言,“新”“未來”就成為最具有說服力的價值尺度,“新小說”(政治小說)、“新詩體”(歐語入詩)、“新文體”(報章時文),乃至“新中國”(共和政體)等的出現,都可以歸于進化的必然。在“器物、制度、思想”循序演進的序列結構中,思想才是改變一切的核心,而要改變思想,“文”就當然地成為可資利用的最佳平臺。梁氏舉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目的并不像王國維那樣嘗試提升小說本身的文學地位,而恰恰是想利用小說自身的大眾化特性,來完成其“啟民智”進而“新國民”的政治設計。小說寫得怎么樣不重要,借小說以傳達新的“觀念”(如民權、共和、憲政等)才是核心。在梁啟超看來,“文”仍然需要延續其“載道”的功能,只是依據進化的思路,這里的“道”必須給予更新和置換,即從單純的儒家之“道”轉變為現代的觀念。“文”在此仍然只承擔著“具”的作用。
二是以進化史觀開辟了文學史書寫的新格局。除了線性進化式歷史形態的轉換以外,進化史學有別于章學誠者,還在于一者求其“動”,一者求其“靜”。求“動”者傾心當世亟變,以我觀史,終趨于“以論帶史”;求“靜”者徹察世道人心,以史觀我,有利于“論從史出”。章學誠與梁啟超的分途,大抵確定了后世文學史論形態的原初取向。清末民初,受日本學者的影響,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漸成風氣,但在總體上仍未超出“文章流別乃各擅其勝”與“后勝于前故演化推進”這兩種基本的模式。就后世大量出現的文學史著述而言,“以論帶史”,即以確定的觀念(如啟蒙、革命)為先導來展開歷史敘述的趨向,已經成為文學史書寫的主流,由此就不難看出梁啟超的深遠影響。
“文以啟智”和“以論帶史”強調的都是觀念本位,在功能上突出的主要是“文”所蘊含的思想對于社會、歷史所發揮的實際效用,所以仍然屬于傳統“文以載道”的變體。從某種程度上說,“五四”新文學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廣泛的影響和支持,與梁啟超等所倡導的進化觀念的普及密不可分。“今勝于古”的演繹思路為“白話文學”的生存和推進提供了強有力的學理支持;而“白話文學”本身也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文以啟智”的“載道”思路。只是在梁啟超的基礎上,白話的新文學進一步擴大了“觀念/道”的范圍,而將“個體、權利、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理性、邏輯”等更多的現代意識,帶入以“白話”為載體的“新文學”之中。而以“觀念”的演化為核心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史的書寫,也逐步被確定成一種特定的典范樣式。
吉川幸次郎曾指出:“文學具有政治性,是貫穿中國文學的極大特點,這種傳統一直聯系到現代文學。作為覺悟的現代文學與過去的文學是不連續的,但現代中國的小說在目的小說很多這點上,與過去的文學又是連續的。”(21)文學偏重于描繪現實,文學也就成為映射社會的鏡子和工具,文學的目的既然主要在“致用”,那么研究文學實際上也就是在研究社會了。從這個角度說,“文學社會學”取向在中國能夠一直興盛不衰,其根源也正在中國文學自身“文以載道”傳統的延續上。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如果社會的種種問題需要尋求各式的答案,那么文學自身呈現和嘗試解答社會問題以求變革改造社會的責任就不會消逝。因此,梁啟超等所開啟的“啟蒙/致用”的文學取向即使在當下也仍然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基本樣態是在古今中西交會互生的情境中誕生并演進而來的,追溯其源頭,大體可以概括為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和梁啟超所代表的“人文、修辭、審美、社會”四種路向。這四種路向除了各自都有其或隱或顯的延續之外,也與當下的“文化研究”“形式理論”“審美主義”及“社會批判”等文學理論取向有著潛在的呼應與對接。余英時曾說:“研究傳統是在不斷成長和發展之中的,甚至往往發生所謂‘革命性的變動。章炳麟、王國維等上承乾、嘉學統,然而最后更新了這個傳統。”(22)探索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如果僅僅著眼于當下現實的實際需求,或者所謂學術前沿的最新成果,恐怕都可能只是暫時的切近的一時之便利;真正回歸現代中國文學自身所已經形成的典范向度,也許是走出困境的最佳方案。
注釋
①參看余虹:《革命·審美·解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②參看[日]鈴木貞美:《文學的概念》,王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③章太炎:《致國粹學報社書》,《國粹學報》己酉年第十號,1909年11月。
④⑩章太炎:《國故論衡》,陳平原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50頁。
⑤⑥⑦胡適:《文學論略·序論》,章太炎:《文學論略》,群眾圖書公司,1925年,第1、7、11頁。
⑧[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李平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22頁。
⑨朱希祖:《文學論》,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5頁。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論文雜記》,舒蕪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0、110頁。
?(21)[日]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陳順智、徐少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9頁。
?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07頁。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一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頁。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6頁。
?王國維:《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姚淦銘、王燕編:《王國維文集》(第三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1頁。
??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36、739頁。
?飲冰等:《小說叢話》,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65頁。
(22)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538—539頁。
Four Patterns of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He Changsheng
Abstract:The basic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re shap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 mixtur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since late Qing Dynasty. Tracing the source, it can be generalized as Humanity, Rhetoric, Aesthetics, and Society, which was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Wang Guowei, and Liang Qichao. Besides their own obvious or obscure development, they potentially echoed "culture research", "formal theory", "aesthetic doctrine", and "society criticism" which existed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ories. Re-exploring the existing value is undoubtedly instructiv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research.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literature; theory; trans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