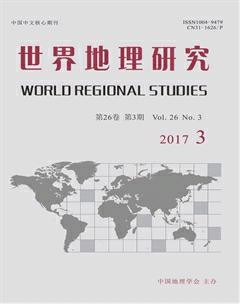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空間分布格局演變特征
代歡歡++陳俊華++方尹



摘 要:作為中東大國之一,亦是中國戰略合作伙伴的伊朗是“一帶一路”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交通樞紐,科學合理測度其人口空間分布格局演變特征可提升對伊朗國內發展態勢的認知,對加強中伊政治經濟合作具有現實意義,也可豐富世界地理研究領域中東區域的典型案例。運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重心分布、密度等指標,結合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和偏移-分享分析法等研判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變特征,結果表明:伊朗人口空間分布極不均衡,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原西北部、里海沿岸平原;人口密度整體上呈西北高東南低的特征,人口分布與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呈顯著正相關;伊朗的人口流動以鄰域地區和城市之間的流動為主,主要流向經濟發達的北部和西北地區,這也與人口重心在西北地區的空間路徑依賴慣性趨勢吻合;伊朗人口分布的空間格局演化分異呈顯著空間自相關性,人口密度較高和較低的區域均出現空間集聚特征,密度高高集聚區位于北部、西北部山地和德黑蘭周邊與中央高原交界處,且逐漸向東南方向延伸;密度低低集聚區主要分布于東部山地和西南地區,且變化甚微。
關鍵詞:人口;分布格局;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偏移-分享分析;伊朗
中圖分類號:K912 文獻標識碼:A
人口、資源、能源、糧食和環境是當今世界面臨的五大問題,人口是核心問題之一[1]。其增長帶來較大的資源環境壓力,受到學者們長期關注[2-3]。隨著中國與中東戰略伙伴關系的深化,中東工業經濟格局、城市化、可持續發展以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機制探討等問題研究逐漸升溫。同時,近年中國加強世界地理研究的呼聲日趨升高[4],伊朗作為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經濟帶上重要的節點國家,中伊兩國經貿領域合作不斷擴大,使伊朗成了地學視域導控下中東地理研究的焦點。已有研究主要涉及法律[5]、石油資源[6-7]、核問題[8]、地緣政治[9-10]、早期文化[11]等領域,對人口的相關研究僅涉及人口政策[12-13]、城鎮體系[14]、歷史時期人口研究[15]等方面,采用定量化指標來系統評價人口分布格局空間演化特征的分析較為鮮見。
現有研究雖初步刻畫了伊朗人口發展相關方面的特征及部分影響因子,但未能有效解釋伊朗省域尺度人口空間分布格局演化的總體軌跡與態勢。為此,本文借助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法和偏移-分享分析法等,采用伊朗省域人口密度、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和人口重心分布等指標明晰省域人口空間格局分異,嘗試測度伊朗人口空間格局分異軌跡。科學研判伊朗人口分布空間格局,對進一步了解伊朗人口及經濟發展態勢,維護中伊政治經濟穩定性具有現實意義。同時作為中東區域典型案例,希冀對豐富世界地理領域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1 研究區概況及數據來源
伊朗地處25-40°N,44-63°E,是文化歷史悠久、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以亞熱帶干旱、半干旱氣候為主,國土總面積164.9萬km2。截至2016年,伊朗共有31個省份,總人口達8004.31萬人。北接北高加索、中亞、俄羅斯,東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靠阿拉伯世界,南依波斯灣,是重要的地理節點,其不僅是中亞、東歐國家進入印度洋的必經之地,也是我國“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同時作為波斯灣沿岸石油產量貢獻極大的國家,巨大的油氣儲量與特殊的交通區位對全球戰略格局具有重要意義[14]。改革開放以來中伊兩國關系和平穩定發展,兩國在經濟、文化以及外交等領域開展了較多的合作交流。
本研究的人口統計數據來自《伊朗統計年鑒》及世界城市人口統計網站,選取1986年、1996年、2006年、2016年4個時期作為研究斷面。行政區劃矢量數據及輔助分析數據如DEM、水網密度、路網密度數據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省會城市的坐標用Google earth來獲取,1986年~2016年伊朗分離新建省份7個,為保證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采用2016年伊朗31個省域行政區的土地面積與人口數量比例對其他三個時期的行政區劃進行歸一處理。
2 研究方法
2.1 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
運用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U,分析區域人口的集中或分散趨勢[16],其值越大,人口分布越集中,反之則趨近平衡。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研究單元個數;xi為研究單元i的人口占研究區總人口的比重;yi為研究單元i的土地面積占研究區土地總面積的比重。
2.2 人口空間格局變化分析
2.2.1 人口重心分布
人口重心指以研究區中各研究單元的人口數量為權重而得到的空間質心,是分析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變特征的重要方面。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X和Y分別表示人口分布重心的經緯度坐標,Pi表示各研究單元人口規模,Xi、Yi為各研究單元重心坐標。參考已有研究[17-19],本文取(Xi,Yi)為研究單元行政中心坐標。
2.2.2 偏移-分享分析
借助偏移-分享法可分析區域內部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化,將特定時期某一區域的人口增長分解為“分享”和“偏移”分量,前者增長指該區域以整個地區人口增長率增長時所獲得的增長量,后者增長指該區域人口增長對分享增長量的偏差數額,其值>0,表明較平均水平而言人口向該區域集聚;其值<0,表明人口由該區域向外擴散。設研究期為[0,t],代表區域為伊朗的西北部、中部、東南部3大區域①,具體模型[20]如下:
式中:ABSGRi、SHAREi、SHIFTi分別為i地區在(to,ti)時段中的絕對增長量、分享增長量和偏移增長量,VOLSHIFTintra為子區域內不同地區間總偏移增長量,VOLSHIFTintraj為子區域之間的偏移增長量,VOLSHIFTtotal為區域總偏移增長量,r為省域單元數目,n為地區數目,m為子區域數目。
2.2.3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本文用來描述伊朗人口密度省域差異的空間集聚特征,計算公式[21]為:
式中:n為31個省份數,wij為第i個和第j個省份的鄰近權重矩陣,xi和xj分別為它們的屬性值,x為均值,Z(I)為標準差,E(I)為I的期望,Var(I)為方差,Ii為第i個省的空間自相關方程。(7)、(8)式為全局和局部空間自相關,前者描述伊朗總體相關性,后者為每個省的相關性,與LISA圖結合可形成高-高、高-低、低-高、低-低集聚區。兩種方式均通過I值即空間自相關程度判斷空間差異,愈接近1空間差異愈小,愈接近-1空間差異愈大,等于0時不相關。本文分析結果以置信度>95%時可信,即概率<0.05時為顯著特征,因此Z的絕對值應>1.96,為顯著空間自相關。
3 結果分析
3.1 人口空間分異
3.1.1 人口數量及增長態勢
以修訂后的4個斷面31個省份的人口數據為基礎作圖1②,可以看出,伊朗人口增長態勢的總體特征較為明顯,近30年以來人口總量不斷增加,總人口由1986年的4944.5萬人增長至2016年的8004.3萬人。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快于總人口的增速,年均增長率持續下降,總人口增長速度放緩。
分階段來看,人口數量變化受伊朗人口政策和城市化發展影響明顯。根據曲線特征可以看出,1986年~1996年伊朗人口增幅較大,年平均增長率為2.15%;1996年~2006年總人口增加了1044.59萬人,年平均增長率下降為1.74%,增長率的下降趨勢與此階段生育率下降密切相關,伊朗在1988年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
伊朗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快,城市人口近30年增長5634.25萬,城市化率在1996年時就突破了60%,至2016年時增至74.3%。伊斯蘭城市文明歷史悠久,在中世紀時期其城市化水平已超越歐洲[22]。二戰前,中東地區的城市也主要集中分布在伊朗和東地中海沿岸,因此伊朗的城市化起步早。二戰后,伊朗國內政局穩定,開始大力發展石油工業,城市的經濟結構向以石油經濟為主體轉變,由此帶動相關的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城市雇傭人口增加。尤其是伊朗共和國成立之初,國際石油價格上漲,伊朗利用充足的資金推進城市建設,形成許多新興城市,城市化水平居發展中國家前列。另外,伊朗的土地改革、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計劃等國家政策對城市化發展也有刺激作用。因此,伊朗的高度城市化是歷史、經濟、政策、傳統觀念等多種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但高度城市化帶來的各方面壓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增長,由此抵消了一部分2012年伊朗廢除控制人口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也使得近幾年人口增長速度較為緩慢。
3.1.2 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
運用公式(1)可得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不均衡指數(圖2)。近30年來,伊朗人口不均衡指數呈先上升后下降態勢,其中1986年~2006年增長幅度達18.33%,這一階段人口流動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以石油開發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外來人口不斷向第二、三產業發達、就業崗位多的大中城市遷移聚集,主要包括德黑蘭省、厄爾布爾士省、伊斯法罕省、法爾斯省等工業產值高的地區。這不但加劇了人口地域空間分布的不平衡性,且造成了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德黑蘭一度成為中東乃至全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港口眾多的西南波斯灣沿岸因人口快速聚集,生態環境破壞也逐步加劇[23]。近10年不均衡指數略有降低,人口分布不均衡狀態有所緩和,是由于2006年至今伊朗經濟發展速度和城市化進程速度放緩。從全國范圍來看,與人口吸引力強的西北地區相比較,東南地區和中部地區位于伊朗高原,受限于其較高的海拔和干旱的氣候,人口分布從古至今較為稀疏。
3.1.3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1986年伊朗全國人口平均密度為30人/km2,2016年全國人口平均密度達49人/km2。根據伊朗人口普查數據③,以省域尺度為研究單元,得到伊朗人口密度分布圖(圖3)。
從圖3可以看出,伊朗人口密度空間分異顯著。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區分布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西部和北部的都市圈以及沿海港口地區,并呈半環狀向外圍遞減,出現以德黑蘭為中心的單核集聚態勢。此外,港口城市也是人口密度極高的地區,包括波斯灣沿岸的布什爾、阿巴丹、阿巴斯、霍梅尼和里海沿岸的安薩利赫諾莎爾港。2016年人口高度集聚的核心區主要包括德黑蘭省、厄爾布爾士省、吉蘭省以及馬贊達蘭省,人口密度分別達到了935人/km2、515人/km2、182人/km2、135人/km2,人口分布密度較低的區域則集中在中部及東南部地區,31省中有9個省的人口密度低于全國平均人口密度,其中南呼羅珊省和塞姆南省人口密度低于10人/km2,為全國人口分布最為稀疏的地區。
總體來看,伊朗人口密度整體上呈現西北高東南低的空間特征,人口密度分布與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呈顯著正相關[24]。伊朗西部山區和里海沿岸受地中海氣候及西風影響顯著,年降水量較大。此外,波斯灣沿岸人口密度也較大,這是由于其油氣資源分布密集,港口城市交通優勢突出,經濟發達。而極少數城市位于沙漠或年降水量不足100mm的南呼羅珊省、北呼羅珊省、塞姆南省、恰哈馬哈勒-巴赫蒂亞里省、科吉盧耶-博韋艾哈邁德省環境惡劣,長期以來經濟落后,人口密度低。
3.2 人口空間格局演化
3.2.1 人口重心移動
運用公式(2)計算得到伊朗四個時期的人口重心坐標(表1),并用ArcGIS軟件做出重心移動軌跡圖(圖4)。伊朗人口分布重心始終位于伊斯法罕省的西北部(約33°N,51°E)。以伊斯法罕為中心的“十字形”地帶和阿塞拜疆地區,即包括胡齊斯坦、伊斯法罕、呼羅珊、馬贊達蘭、德黑蘭、法爾斯的“十字形”帶狀區域,人口均高于300萬,是全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其土地面積僅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33%,卻集中分布著全國56%左右的人口。
在研究時段內,伊朗人口重心盡管變化幅度不大,但演化態勢較為明顯,從重心移動軌跡上看,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重心呈現緩慢穩定地向東部移動趨勢,在東西方向上向東移動了19′34″,南北方向上移動了42″。經度方向的移動幅度明顯大于緯度方向,這是由于位于東部的呼羅珊省和西北部偏東的伊斯法罕省,人口總量在31個省中的排名分別為第二和第三。除德黑蘭省外,西北地區各省人口總數明顯少于呼羅珊省和伊斯法罕省,但由于西北部各省地域面積狹小,導致人口密度較高,人口流入西北地區的比重較大,呈現出聚集態勢明顯。地域廣闊的呼羅珊省和伊斯法罕省人口密度較小,但人口基數大,使得人口增長數量高于許多省份,東部的呼羅珊省近30年人口密度增加了2倍,人口增速也僅次于德黑蘭。其次,近30年以來城市化的發展,東部地區省份城鎮經濟得到一定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大造成人口集聚,加之交通條件不斷改善,對人口重心向東部方向移動也有拉動作用。此外,1996年~2006年人口重心的移動幅度在東西和南北方向均為最大,表明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伊朗人口大量流動特征最為顯著。
3.2.2 人口偏移增長
區域內部各地區人口偏移增長會導致人口分布變化。由偏移-分享分析法計算得到伊朗人口各個大區內部及三個大區之間在1986年~1996年、1996年~2006年和2006年~2016年三個時段的偏移增長量。
從表2可以看出,近30年間,伊朗西北地區、中部地區和東南地區的偏移增長量變化均較明顯,且偏移增長量空間差異顯著,以西北地區表現最為典型,1986年~2016年其大區之間的偏移增長量下降幅度達76.82%。而在1986年~1996年內部的偏移增長值和大區之間的偏移增長值均高于1000萬,約占起始年總量的21%,遠高于中部地區和東南地區,顯示出西北地區人口聚集的趨勢尤為明顯。1996年以前伊朗經濟尚未受到西方國家經濟制裁的影響,德黑蘭城市圈迅速崛起,伴隨著經濟發展,其人口規模迅速增加。就區域層面而言,東南地區在1996年~2006年人口集聚程度最高,而2006年后則急劇下降。中部地區偏移增長量先正后負,先增后減的變化趨勢,表明由于伊朗城市化和交通的發展,人口在一段時間內集中地偏向中部部分省份聚集,自2006年這種趨勢得到緩解,人口也開始由此大區向外流動。
總體來看,三個時段中后兩個時段伊朗的大區內部的偏移增長總量遠高于大區之間的偏移增長總量,表明21世紀以來伊朗人口偏移主要是區域內部之間的人口流動,即以鄰近的省份和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為主,以德黑蘭省、厄爾布爾士省、馬贊達蘭省、哈馬丹省這幾省之間人口流動最為突出。其次是波斯灣沿岸城市與西部地區城市之間的人口流動。西北地區是伊朗的經濟重心,其一直領先的偏移增長量,表明研究時段內伊朗國內大部分流動人口主要流向經濟發達的西北部,這也與人口重心在伊朗西北地區的空間路徑依賴趨勢吻合。
3.2.3 人口分布的空間全局自相關分析
基于鄰接(Contiguity)關系的權重矩陣,利用GeoDa軟件計算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密度分布的全局 Moran's I,得到全局空間關聯統計值(表3):全局Moran's I估計值均為正值,且檢驗結果顯著,表明伊朗31個省人口密度在空間上有較高的正相關性,人口密度較高和較低的區域均出現空間集聚特征。就變化趨勢角度,Moran's I值呈現持續減小后稍有增大,說明空間集聚隨時間推移而不斷減弱。原因主要在于:1987年伊朗政府開始將油氣資源收歸國有,大量引進外資并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以石油經濟聯動國民經濟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將其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資本;伊朗交通網絡通達性提高以及省域間基礎設施建設差異日趨縮小;各省域間人口流動加劇;中央高原東南部、東部山區南部以及阿曼灣沿岸平原北部開發以后人口承載能力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東、西部人口密度的差異。但2016年人口密度大和人口密度小的省份集中分布現象再度凸顯,說明人口密度較高的省份逆前20年變化趨勢而向西北地區更加集中,主要包括德黑蘭、厄爾布爾士、吉蘭、馬贊達蘭、加茲溫以及哈馬丹6省。
3.2.4人口分布的局部自相關分析
為深入辯明伊朗人口局部空間特性,用LISA集聚圖表示空間鄰接或空間鄰近區域單元人口密度特征的相似程度(圖5)。
從整體上看,近30年中,伊朗的西北部地區始終是人口密度的高高集聚區,從德黑蘭、馬贊達蘭省向西北、東南方向延伸至吉蘭、加茲溫、中央、庫姆、戈勒斯坦和厄爾布爾士等省份。由于德黑蘭省的極化效應,加上較為適宜的氣候環境和便利的交通,形成環首都德黑蘭的塊狀集聚格局。人口密度的低低值集聚區集中在東南部,地形上包括中央高原的東南部、阿曼灣沿岸平原北部以及東部山地,從最初的錫斯坦-俾路支斯坦、克爾曼、霍爾木茲甘、南呼羅珊和布什爾等省增加至法爾斯等6省份,形成鮮明的人口密度集疏演化的冷點帶即伊朗東南部地區。低高值和高低值基本集中在塞姆南、伊斯法罕、贊詹、哈馬丹、北呼羅珊地區,主要受交通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推動該值由1986年~2016年間不斷出現擴展,可見伊朗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密度空間分布及其集疏格局在全國范圍內逐漸縮小,其人口密度差距在不斷縮小。
4 結論與討論
運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和偏離分享分析法等研判1986年~2016年伊朗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變特征,發現:(1)1986年~2016年人口分布空間格局差異較大,同稟賦地區差異較小,人口與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呈顯著相關。(2)伊朗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化分異呈顯著空間自相關性,空間逆馬太效應初現;伊朗西北地區人口偏移增量始終領先,與人口重心在西北地區的空間路徑依賴慣性趨勢吻合。(3)西北部多數省份人口總數遠低于東部的呼羅珊省和西北部偏東的伊斯法罕省,前者因地域面積狹小,人口密度高,經濟發達吸引人口不斷聚集。后者地域廣闊使得人口密度較小,但人口基數較大,自然增長數量較多且增速快,加上經濟和交通發展的輔助推動作用,使得人口重心呈緩慢東移趨勢。(4)全局Moran s I指數持續減小后稍有增大,表明伊朗人口呈現先分散后趨于集中的態勢。局部Moran s I指數揭示高高集聚區主要分布于北部、西北部山地和德黑蘭周邊與中央高原交界處,且逐漸從該區域向東南方向延伸;密度低低集聚區主要分布于東部山地和西南部區域,且變化不大。(5)總體而言,近30年來伊朗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化總態勢呈以德黑蘭、厄爾布爾士、加茲溫和吉蘭等為核心的高水平城市為主導的增長軌跡。
通過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法,將地理鄰近因子融入空間演化特征中,并通過偏移分享對比修正分析了一般意義的量化方式,有助于厘清伊朗人口分布時空格局演化特征。而人口分布空間格局演化與人口遷移成本、遷移距離、交通網、水域范圍、農村人口耕作半徑等因子也有關,需對其他因子如資源環境、歷史范疇等系統考量。因此,未來對伊朗人口方面的研究工作應盡可能地細化研究單元,依據多方面影響因子,對不同尺度單元人口現象和人口行為演化的階段性特征等領域進行研究,并注意結合自然地理環境稟賦為前提的社會經濟系統持續發展動態,嘗試分析人口分布演化機制及人口流動的深層原因。
參考文獻:
[1] 陳學剛,楊兆萍. 基于GIS的烏魯木齊市人口空間分布模擬與變化規律研究[J]. 干旱區資源環境,2008,22(4): 12-16.
[2] 廖一蘭,王勁峰,孟斌,等. 人口統計數據空間化的一種方法[J]. 地理學報,2007,62(10):1110-1119.
[3] 左永君,何秉宇,龍桃. 1949年~2007年新疆人口的時空變化及空間結構分析[J]. 地理科學,2011,31(3): 358-364.
[4] 毛漢英.世界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建所70周年世界地理研究成果與發展前景[J]. 地理科學進展,2011,30(4): 433-441. [5] 馬龍君. 伊朗1979年《憲法》:神權政治與民主政治的二元體[D].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14.
[6] 劉增潔. 伊朗油氣資源現狀及對世界石油市場的影響[J]. 國土資源情報, 2015(11):41-43.
[7] 萬雪. 伊朗石油資源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2010.
[8] 岳漢景. 伊朗核問題的本質探析[J]. 西亞非洲,2006(6):18-23.
[9] 王京烈. 伊朗核問題與中東地緣政治[J]. 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4):3-10.
[10] 江琳. 基于伊朗國際戰略地位的美伊博弈關系分析[D]. 南京:中共江蘇省委黨校,2013.
[11] 劉拓. 伊朗舊石器考古簡史及早期文化的發現與研究[J]. 人類學學報,2016,35(4):1-13.
[12] 冀開運,冀佩琳. 伊朗人口政策的演變及特點[J]. 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6(1):84-88.
[13] 馬壽海. 伊朗人口政策與計劃生育[J]. 人口與經濟,1996(6):54-57.
[14] 呂薇. 伊朗城鎮體系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2008.
[15] 張超. 巴列維王朝時期的伊朗人口[J].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2(3):44-49.
[16] 張善余. 人口地理學概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265-323.
[17] 周崇經,李建新. 新疆人口重心的移動特征[J]. 干旱區地理,1988,11(3):55-59.
[18] 徐建華,岳文澤. 近20年來中國人口重心與經濟重心的演變及其對比分析[J]. 地理科學,2001,21(5):385-389.
[19] 張海峰,白永平,陳瓊,等. 基于ESDA-GIS的青海省區域經濟差異研究[J].干旱區地理,2009,32(3):454 -461.
[20] 馬穎憶,陸玉麒,張莉. 江蘇省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特征[J]. 地理科學進展,2012,31(2):167-175.
[21] 石英,米瑞華. 陜西省人口空間分異研究[J]. 干旱區地理,2015,38(2):368-376.
[22] 車效梅. 中東城市化的原因、特點與發展趨勢[J]. 西亞非洲,2006(4):42-48.
[23] AkbariH,Moradi H V,SarhangzadehJ,et al. Population status, distribu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Chinkara, in Iran (Mammalia: Bovidae)[J]. Zoology in the Middle East, 2014,60(3):189-194.
[24] Mojtaba G M, Reza B H. Population dynamics in geographic regions of Iran and itsconsequences[J].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Quarterly, 2014,45(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