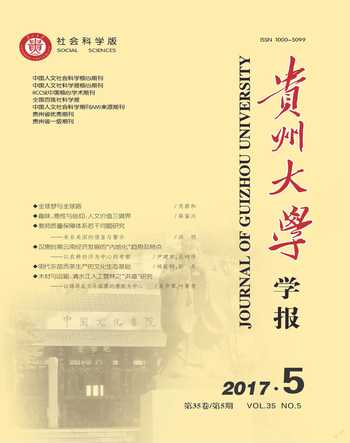礦業(yè)與邊疆治理:清朝對云貴地區(qū)礦業(yè)衰落的調控
楊亞東
摘 要:清代云南和貴州分別為全國銅礦和鉛礦的重要產區(qū),清代中后期,滇銅和黔鉛由盛轉衰,造成這一轉變的原因是復雜而深刻的,有成本增加,官價過低;燃料短缺,運輸困難;私采泛濫,課稅沉重等。為挽救滇銅黔鉛生產日益下滑的頹勢,清廷采取了控制成本、改善運輸;提高官價、補助資金;蠲免廠欠、降低課稅等措施。這些調控手段短期內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終無法遏制云貴礦業(yè)衰落的勢頭。清廷運用多種經濟和政治手段對滇銅黔鉛衰落問題進行的調控,反映了王朝國家對邊疆地區(qū)經濟和社會問題治理的思路與對策,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現代政府對經濟和產業(yè)調控的理念、思路。
關鍵詞:
清朝;邊疆;礦業(yè);衰落;調控
中圖分類號:K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7)05-0103-08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7
云貴地區(qū)礦產資源豐富,清代云南和貴州分別為全國銅礦和鉛礦的主要產區(qū),其后,出現了由盛轉衰的趨勢,清廷
采取了一系列調控手段,但最終無法挽回頹勢。學界對清代云貴地區(qū)礦業(yè)衰落原因的探討,由于史料缺乏,未形成定論。徐斌認為,云南銅業(yè)的衰落與封建政府礦業(yè)政策的桎梏及其自然條件限制有密切關聯,能源緊缺與交通運輸困難是造成云南銅業(yè)衰落的重要原因。[1]文思啟認為云南社會生產力落后與礦冶業(yè)發(fā)展不相適應的矛盾是造成銅業(yè)衰落的重要原因。[2]劉朝輝認為在自然原因背后,官發(fā)銅本與產銅成本之間日益加劇的矛盾以及銅政弊端是導致云南銅業(yè)衰落的重要原因。[3]李中清認為面對產銅成本的飆升,政府補助金的減少是造成云南銅礦業(yè)衰落的致命原因。[4]287-295肖本俊認為,清乾嘉時期的“山荒”及隨之而來的“薪柴價高”“炭路日遠”等問題是造成滇銅業(yè)衰落的重要原因。[5]羅時法認為,沉重的課稅是造成貴州礦業(yè)凋敝的主要原因。[6]袁軼峰認為清代貴州大定府鉛銅業(yè)由盛轉衰的原因主要是流民問題、糧價問題、私采濫采、貪污等。[7]學術界針對清廷應對和調控云貴地區(qū)礦業(yè)衰落問題的研究并不多見,李中清對清代云南地方政府為遏制滇銅生產衰退所做的努力進行了闡述。[4]282-286劉朝輝就清廷面對滇銅供應不足、成色低潮等問題采取的調劑措施進行了論述。[3]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清代滇銅黔鉛衰落的原因進行再認識,同時分析闡釋清廷應對礦業(yè)衰落的調控措施,從而管窺王朝統治者在治理邊疆過程中對礦業(yè)衰落等經濟和社會問題治理的思路及對策。
一、
盛極而衰:清代中后期滇銅黔鉛的衰落
清代在中國礦業(yè)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一時期以銅、鉛開發(fā)為代表的礦業(yè)取得了較大成就,無論從礦業(yè)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遠遠超過之前任何時期,“一百年的增長率大大超過了此前二千年”[8]。清代中期以前,云南的銅礦業(yè)和貴州的鉛礦業(yè)開發(fā)取得重要進展,對國家的貨幣鑄造、槍械彈藥生產、生活器皿制造等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清代中后期,滇銅和黔鉛由盛轉衰,留下了中國礦業(yè)發(fā)展史和西南邊疆開發(fā)史上濃重的一筆。
(一)滇銅由極盛到衰落
銅是清代鑄幣所需的重要原料之一。云南銅礦資源豐富,史料記載:“蓋鼓鑄鉛銅并重,而銅尤重。秦、鄂、蜀、桂、黔、贛皆產銅,而滇最饒。”[9]980云南銅礦開采歷史悠久,“產銅礦區(qū),元時為大理、澂江,……明、清兩代發(fā)現礦苗者八十三屬,開辦者三百余廠,歲供京、滇鑄錢及八路采辦之需。當乾隆三十八、九兩年,每歲產銅約一千二百數十萬斤,額課九百余萬,而商販不與焉,可謂空前之極盛時代矣”。[10]129
研究清代前期云南礦業(yè)開發(fā)的政策,不得不提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貴總督蔡毓榮在《籌滇十疏》中建議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勵和稅收優(yōu)惠措施,招攬“本地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投資開發(fā)云南礦業(yè),同時對招商開礦成效顯著的官員給予優(yōu)先提拔,甚至“酌量給與頂帶”,
參見《云南通志》第29卷《藝文三·籌滇十疏》。
清廷采納了蔡毓榮的建議。但由于銅業(yè)開發(fā)前期資金投入比較大,且開發(fā)過程中存在較大風險和不可控因素,加之云南地僻民窮,如蔡毓榮所期待的“殷實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賈”鳳毛麟角。面對云南銅礦開發(fā)中的資金問題,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貴總督貝和諾上奏對云南銅業(yè)實行“放本收銅”,即“于額例抽納外,預發(fā)工本,收買余銅”[11]4977。這一政策的實施,一方面使官府實現了對貨幣鑄造的主要原料——銅的生產壟斷,有效保障了國家貨幣的穩(wěn)定,另一方面在客觀上刺激了云南銅業(yè)的發(fā)展。
隨著“放本收銅” 政策的實施,云南銅礦開發(fā)的規(guī)模不斷擴大,產量迅速增加。“康熙四十九年(1710)云南產銅不到50萬斤。到雍正三年(1725),銅的年產量達到100萬斤。乾隆二年(1737),又上升到1 000萬斤。在不到20年的時間里,云南的銅產量增長了20倍。其后,在18世紀余下的時間里,云南平均每年的銅產量都保持在近1 000萬斤的水平上。直到19世紀中期,銅產量仍未明顯衰減。那時,云南銅礦已經生產了超過50萬噸的銅,相當于同期世界銅產量的五分之一,中國銅產量的一半。”[4]269可以說,“滇省銅政,累葉程功,非他項礦產可比。”[9]980
然而,云南的銅產量并未一直保持上升勢頭,甚至年產一千萬斤左右的水平也未能長期維持。嘉慶九年(1804)七月,云南巡撫永保在奏書中感嘆:“每見各廠月報,辦銅多不足額,辦理時形掣肘。雖京運勉強不致有誤,而各省采買,即間有不能隨到隨撥者,迥非二十年前之情形可比。”參見《宮中檔朱批奏折·財政類》云南巡撫永保奏折(嘉慶九年七月二十日)。雖然經過多方調劑,勉強辦足京運所需銅斤,但卻無法保證采買滇銅的其他各省的供給,以致“各省委員到滇,均不免稍為守候”。[8]178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三年(1823),廣東、湖北、浙江、貴州、湖南、福建等六省的八運委員因云南無銅供應,在滇連年滯留守候,無銅濟鑄的各省不得不采取停爐減卯、采買商銅接濟等措施來臨時應對。
劉朝暉認為:“相對于滇銅供應數量的問題,其成色問題更為嚴重”,及至嘉慶、道光年間,陳滇銅成色不足的問題已非常嚴重,“京局不得不設爐改煎,所需火工銀兩由各廠店員及運員賠補。”[3]從辦銅數量的持續(xù)下滑和滇銅成色不足等問題來看,嘉道年間開始,云南銅礦衰落已成不可阻擋之勢,盡管部分年份余銅出現一些波動,但下滑趨勢已不可逆轉。
(二)黔鉛由興盛到凋敝
鉛是清代鑄幣的重要原料之一,也有部分用于制作火器的彈丸。貴州鉛礦儲量豐富,清代時是全國重要的鉛鋅礦的產區(qū),雍正、乾隆年間,隨著礦禁的開放,貴州鉛礦開采取得了較大發(fā)展,黔鉛生產運銷在全國居于重要地位。
康熙五十七年(1718),貴州威寧府猴子銀鉛廠、五十九年(1720)威寧府觀音山銀鉛廠相繼獲準設廠開采,參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乾隆朝·卷49)《戶部·雜賦上》。短短幾年,貴州鉛廠就有了較快發(fā)展,雍正、乾隆年間,黔鉛產量有了較大提高。“威寧州的朱砂廠,雍正時期年產鉛 20—30萬斤,乾隆時達100萬斤以上。綏陽月亮巖廠也由30余萬斤到 100 余萬斤。年產鉛100萬斤的有丁頭山、達磨山、榨子廠、大雞、小洪關等地的廠礦。各鉛廠產量最高的是蓮花廠,年產量達 500—600 萬斤之多。全省各府廳州縣產鉛量最大的是威寧州,年產為 1 000 萬斤以上。乾隆年間貴州全省年產鉛在1 400 萬斤左右。至道光時產量大減,僅及乾隆時的1/3。[12]170
嘉慶以后,貴州許多鉛廠紛紛封閉,嘉慶《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貴州鉛廠僅有福集、蓮花塘、濟川、天星扒泥洞、永興寨、水洞帕等處,
參見《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194)《戶部·雜賦》。
與乾隆年間興盛時已無法比擬。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貴州巡撫李慶棻奏報:“黔省福集、蓮花二廠,歲供京、楚兩運白鉛六百余萬斤,每年所產有一百余萬斤缺額,自乾隆四十五年始,俱以舊存余鉛湊撥,日形支絀。”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11),乾陵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道光八年(1829)十二月,道光帝諭內閣:“黔省媽姑、福集等鉛廠因開采年久,峒老山空,砂丁采取匪易。新發(fā)白巖子廠夏間雨水過多,漕峒被淹,招丁車水,需費不少,爐戶倍形疲乏。” 參見《清宣宗實錄》(卷148),道光八年十二月戊子。由此可見,嘉道年間開始黔鉛開發(fā)以無法阻擋之勢步入衰落期。
二、
本非一端:滇銅黔鉛衰落的原因分析
(一)滇銅衰落的原因分析
《新纂云南通志》對滇銅衰落的原因有如下分析:“滇銅幾遍全國,后廠情盛極而衰,原因本非一端,然最大困難其故有五,屬于采辦方面者:(一)官給銅價,難再議加。(二)各路取給,數難議減。(三)大廠逋累,積重莫蘇。(四)小廠收買,渙散莫紀。”[10]133歸結起來,導致清代云南銅業(yè)極盛而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成本驟升、采煉艱難
銅礦開發(f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生產成本非常驚人,清代云南銅礦開采隨著開采規(guī)模的日益壯大,礦區(qū)聚集了大量的礦業(yè)人口。乾隆十一年(1746)五月,云南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允隨奏稱:“現在滇省銀、銅各廠,聚集攻采者通計何止數十萬人” 參見《張允隨奏稿》(卷7)云南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允隨.奏報遵奉查奏云南永順東南徼外卡瓦輸誠納貢情形,并備陳億萬廠民生計折(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馬琦根據滇銅產量及人年均產銅量推算出“清代滇銅礦業(yè)人口平均約7.6萬人左右,乾隆朝年均為9.3萬人,最高時達14.2萬人。”[13]131盡管清代云南銅業(yè)的從業(yè)人口準確數量無從查考,但無疑是非常龐大的。如此眾多的人口,需要消耗的生活物資非常巨大,僅以糧食一項,就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對此問題,早在雍正五年(1727),云貴總督鄂爾泰在奏疏中就有如下分析:“開采礦廠,動聚萬人,油米等項,少不接濟,則商無多息,民累貴食。” 參見《清世宗實錄》(卷52),雍正五年正月壬子。
乾隆十三年(1748),針對日益上漲的米價,張允隨認為:“米貴之由,一在生齒日繁,一在積貯失劑,而偏災商販囤積諸弊不與焉。……乃近年米價亦視前稍增者,特以生聚滋多,廠民云集之故。”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是年六月,云南巡撫圖爾炳阿在奏折中亦認為:“米價之貴,總由于生齒日繁,歲歲采買。……(云南)糧價亦不甚賤者,由于出產五金,外省人民走廠開采,幾半土著;且本省生齒亦繁故也。”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六月壬午。由此可見,由于大量的礦業(yè)人員聚集,導致米價的不斷上漲,而米價的上漲,又進一步增加了銅礦開發(fā)的成本。
除此之外,清代云南銅礦采絕大部分依靠薪炭焚燒加熱,燒煤加熱的礦廠很少,這樣一來,礦廠周圍的樹木大量被砍伐。在剛開始生產時,炭薪還可以就近砍伐林木取得,“初辟之礦,入必不深,而工不必費。” 參見《滇南礦廠圖略》(卷2),王太岳《論銅政利病狀》。
隨著銅礦生產規(guī)模的日益壯大,礦廠周圍的樹木被砍伐殆盡,勢必向更遠的地區(qū)砍伐林木,于是,薪炭產地范圍不斷向外擴展,與礦廠的距離不斷增加。史料記載:“凡廠槽多日久,遂至附近山木盡伐,而炭路日遠,煎銅所需炭重十數倍于銅,成銅之后再需煎掲,運銅之費必省于運炭。” 參見《滇南礦廠圖略》(卷1附),王昶《銅政全書·咨詢各廠對》。
獲取薪炭日益艱難,勢必導致薪炭價格上漲,進而增加生產成本。到了乾嘉時期,為了滿足云南銅礦生產的薪炭需求,大量森林被砍伐,普遍出現了“炭價日貴”“柴薪路遠”等問題,這不僅給當地生態(tài)自然環(huán)境造成巨大破壞,而且大幅度增加了銅礦采冶的成本。
2.運輸困難、工本不敷
云南屬于多山地區(qū),自古交通條件惡劣,幾千年來物資運送均靠人背馬駝,尤其是銅礦多位于深山老林中,運輸極為困難。到了嘉道年間,“開采既久,窩路遠而且深,廠丁背運礦砂,往返不能迅速,是以數日所得,尚不及從前一日之獲”。
參見《道光朝軍機處錄附奏折》,云南巡撫陸建瀛奏折(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窩路”指的是通往礦山山腹的狹窄的通道,廠丁在里面只能匍匐爬行,經過長年開采,各礦山的“窩路”越來越遠,以至于運輸礦砂異常艱辛,另外,從成品銅的運輸過程來看,云南銅業(yè)運輸也極其困難。由于運輸路途遙遠,運輸周期長,嚴中平先生感嘆:“我們估計大部分京銅,從產地到京師,非經兩年的搬運不能到達。若以路程最遠的回龍廠而論,三年怕還不夠云南銅產區(qū)域,全在深山峽谷之中,在云南境內,銅產幾乎連一尺的水道都無從利用,每年那一千二百萬斤的銅料,主要靠人的肩頭,馬的脊背和和最簡陋的牛車來輸送”。[14]34嚴先生提到的水運“時時有沉沒之虞”的例子不勝枚舉。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七月,“云南委員黃澍領運京銅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余斤,行至四川大湖灘、大黑石灘暨湖北江陵縣馬家賽地方,三次遭風沉溺,除撈獲外,共計未獲銅二十萬余斤。”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34),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戊子。
同月,“云南委員漆炳文領運五十三年三運一起京銅七十六萬一千七百九十三斤,在湖北歸州沉溺銅七萬斤……”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一月之內就有兩起沉船,可見事故之頻繁,由此也不難看出,清代滇銅運輸的難度是無法想象的。
官府提供的“工本”已無法支撐廠民包括運輸等在內的各種開銷,這從“廠欠”的大量出現可窺見一斑。所謂廠欠,高其倬在奏折中是這樣解釋的,銅廠“各種雜用,亦系價外開銷”“更有將打出之銅偷賣花銷、懸項無交者,雖現在而赤貧,或逃亡而無著,懸項累累,名曰‘廠欠,此系銅價外虧折之項。”
參見《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二輯)》,云貴總督高其倬、云南巡撫楊名時,查奏銅斤利弊情形折(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盡管造成“廠欠”的原因很多,但“廠欠”既然為“銅價外虧折之項”,但大量“廠欠”的出現,表明“不敷成本,則爐戶等不特無利之圖,而先領之工本,不能繳還”,
參見《宮中檔朱批奏折·財政類》,云南巡撫永保奏折(嘉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這亦反應了銅廠的衰落。
3.盜賣私銅、追欠遺癥
清朝規(guī)定,礦民“不論領與不領工本,產銅一概不許私自出賣,私賣的叫做‘私銅,查獲了,其銅沒官,其人罰役。”[14]7嘉道年間,云南私銅現象較為嚴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礦政的實施,是滇銅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道光三年(1823),御史龔綬奏請“查禁私銅以裕鼓鑄”,道光帝諭旨:“滇省奸商盤踞各廠,鑄銅為鑼鍋,轉發(fā)各處行銷……。各衙門胥役多與勾通。地方官欲查拿私錢,鋪戶徒受其累,而奸宄之徒,從無一人獲案。” 參見《清宣宗實錄》(卷52),道光三年五月己巳朔。
以上足見私銅泛濫,影響官銅生產和解運,清廷要求嚴行查禁,于各省采辦可期無誤。
另外,追繳廠欠亦是造成滇銅衰落的重要原因。李中清統計了云南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嘉慶十九年(1814)近一百年間部分年份銅礦廠欠損失情況,廠欠累計最高值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527000兩白銀,是年蠲免廠欠398000兩白銀,年平均損失白銀79000兩。到了嘉慶十九年(1814),蠲免廠欠9665兩白銀,年平均損失白銀9665兩。[4]285可見,嘉慶年間云南銅礦廠欠較乾隆年間有較大下降,嘉道兩朝廠欠數額也呈逐年減少的態(tài)勢,這一變化源于嘉道時期對廠欠的大力整頓和追繳,嘉道年間,針對乾隆后期廠欠數額逐年遞增的狀況,清廷制定了追繳廠欠的嚴格規(guī)定,將廠欠追繳與經放廠員個人利益直接掛鉤,督促經放廠員全力追繳廠欠,據史料記載,規(guī)定甚至嚴格到“再有著廠欠,舊例如爐戶故絕、停歇,無可著追,即于經放之員名下追賠。如經放之員家產盡絕,無力完繳,照例取具歷過任所并無隱寄財產印結,由司加具總結,詳咨原籍,提請豁免。”[15]824也就是說,經放廠員承擔廠欠的無限責任,就算銅廠“故絕、停歇”,也要經放廠員以個人資產賠付廠欠。除非經放廠員“家產盡絕,無力完繳”,才能辦理相關手續(xù),“提請豁免”廠欠。在這樣嚴格的規(guī)定之下,廠員懼怕賠累,要等見銅后才愿意發(fā)放工本。
廠員既然已不敢預發(fā)工本了,“放本收銅”政策刺激開礦的效用也就無法發(fā)揮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爐戶缺少資金開采銅礦,清代云南“廠衰”問題只能是越來越嚴重了。
(二)黔鉛衰落的原因分析
清代貴州鉛礦開發(fā)從康熙末年至乾隆中期一路增長,成為全國重要的鉛礦產地。到了嘉道年間,黔鉛生產和運銷成急劇下滑之勢,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
1.生產成本增加、官定價格過低
與滇銅衰落的原因相似,不斷增加的生產成本以及官府定價過低成為黔鉛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中糧食價格始終是影響礦廠生產成本的重要因素,礦產開發(fā),需要聚集數量龐大的從業(yè)人員,進而出現糧食供不應求,結果必然導致糧價上漲,糧價上漲又反過來增加礦廠生產成本,這是市場規(guī)律所決定的。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貴州按察使介錫周奏報:“米貴之由……加以銀、銅黑白鉛廠,上下游十有余處,每場約聚萬人,數千人不等,游民日聚。”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以糧食價格為代表的諸多生產、生活資料上漲,必然導致生產成本增加。而反觀官定鉛銅價格則增長緩慢,雍正八年(1730),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稱:“(貴州)各廠所費工本多寡不一,其收買價值議定每百斤一兩四五錢不等,另加馱腳盤費,運往永寧、漢口等處銷售,現在時價三兩七八錢及四五兩不等,除歸還買本腳價,每百斤可獲息銀一兩四五錢不等”, 參見《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18冊),貴州巡撫張廣泗,奏為奏明事(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應該說雍正年間官定價格已經很低了,但勉強能夠維持生產。到了乾隆年間隨著各項生產成本增加,低廉的價格導致鉛廠獲利甚少,鉛廠自然也就缺乏生產動力了。
2.官員腐敗沖擊、私采偷賣泛濫
官員腐敗虧空是造成黔鉛衰落的另一條重要原因。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威寧州知州劉標虧空大案被查處,乾隆皇帝痛心疾首地說到:“貴州劉標虧空銅、鉛價本至二十余萬之多,自來侵虧帑項犯案,從未有若此之甚者。……黔省吏治狼藉至此,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伊等嚴加治罪,以示創(chuàng)懲”。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852),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庚申。
另外,官府不如期向鉛廠發(fā)給工本,對礦廠正常生產也是極大的打擊。如“威寧州知州高瑋管理鉛廠,支放廠員工本并不如期給發(fā),以致廠員張祥發(fā)所辦新舊白鉛俱有虧短……”。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874),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庚辰。
私采偷賣行為是礦業(yè)開發(fā)中的“痼疾”,很難根除,這也是造成礦廠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貴州鉛礦開發(fā)中的私采偷賣現象也非常嚴重,咸豐五年(1855),清帝諭旨:“四川、云南、貴州各省多有產鉛之區(qū),所采鉛斤,半歸官賣,半歸商銷,向無例禁之文。惟黑鉛有關軍火,若任令行店市商照常販運,輾轉銷售,莫究歸宿,流弊滋多,必當嚴行禁止” 。
參見《清文宗實錄》(卷172),咸豐五年七月壬申。
以上史料足見清代販賣黑鉛現象日益嚴重,必將進一步加速黔鉛衰落的步伐。
3.自然災害破壞、硐老山空封閉
自然災害往往導致礦廠遭受重大損失,比如在生產過程中漕硐被淹和運輸途中運船沉溺。前者如道光四年(1824年),云貴總督明山奏報:“黔省威廠額辦鉛斤,因近年產礦不旺,爐戶繳鉛濡滯,又值上年夏間大雨,漕硐被淹,不能燒辦,遞相積壓,共有爐欠鉛一百八十九萬九千五百一十斤,核計銀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兩零。”
參見《清宣宗實錄》(卷74),道光四年十月丁丑。
運輸途中沉船事故多有發(fā)生,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貴州委員朱毓炯、薛清范領運京鉛,遇風沉溺,俱經陸續(xù)撈獲五萬三千余斤。”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426),乾隆五十八年四月己巳。
硐老山空是礦廠生產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很多礦場不得不因此封閉,大量礦廠封閉勢必影響礦業(yè)發(fā)展。乾隆五十三年(1788),貴州巡撫李慶棻奏報:“黔省福集、蓮花二廠,歲供京楚兩運白鉛六百余萬斤,每年所產有一百余萬斤缺額,自乾隆四十五年始,俱以舊存余鉛湊撥,日形支絀。查廠產不旺之故,實緣開采已久,漕峒日深,且挖取時遇山泉,常需雇工淘水,工費更增……。”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三、
杯水車薪:清廷對滇銅黔鉛衰落的挽救與調控
(一)對滇銅衰落的挽救與調控措施
針對清代中后期云南銅廠日益衰落的嚴峻形勢,清朝統治者采取了控制成本、廣覓子廠;提高銅價、補助資金;改善運輸、蠲免廠欠等手段進行應對和調控。
1.控制成本,廣覓子廠
銅廠采煉成本不斷增加,是造成滇銅衰落的重要原因。其中,米價上漲是導致成本增加的重要因素。鑒于此,清代云南督撫采取各種措施平抑礦區(qū)米價:一是采取積極措施擴大礦區(qū)耕地面積、新修水利設施,發(fā)展農業(yè)生產,提高糧食產量。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云南總督愛必達奏請:“云南東川府蔓海開河招墾,建壩蓄泄,……擬開渠引注蔓海,可溉熟田,荒蕪亦資墾辟。邊徼民夷無力,借帑興工,來秋征還。”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507),乾隆二十一年二月戊辰。
二是調運其他地區(qū)的糧食緩解礦區(qū)糧食緊張形勢,進而平抑米價。乾隆九年(1744)三月,云南總督兼管巡撫事臣張允隨就昭通、東川兩府平糶之事上奏乾隆帝:“因上年昭通、東川兩府秋成歉薄,恐春夏之交民食不無掊據,奏明動發(fā)銅息銀二萬兩,令駐扎永寧轉運京銅之同知谷確,于東川一帶購買川米,以供青黃不接時平糶之用。”三是規(guī)范糧食交易,提倡公平售賣。張允隨提出:“地方官勸諭有米之家運米如市,公平售賣,仍動常平倉谷出糶,以平市價,并通查各屬,如有米價昂貴、民食不敷之處,令地方官加意體察,借給籽種,以助春耕;應行平糶者,即詳請平糶,總期有濟民食,毋拘成例;其余蒸熬糜谷等弊,亦嚴加査禁。” 參見《張允隨奏稿》(卷6),云南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允隨,奏報籌買川米于昭通、東川兩府平糶折(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
為彌補大礦課額之不足,清廷還實行“廣覓子廠”的措施。所謂“廣覓子廠”也就是在大礦周圍找尋開采小礦,這些小礦不另納課,其出產用于彌補大礦課額之不足,這一措施也對緩解滇銅衰落問題發(fā)揮了積極作用。據史料來看,乾隆年間開辟的子廠數量最多。如東川湯丹銅廠就有多個子廠,“九龍箐子廠,在湯丹廠西南一百里,乾隆十六年開采,年獲銅三四十萬斤。聚寶山子廠,在湯丹廠西七十里,乾隆十八年開采,年獲銅五六十萬斤。”[15]638
2.提高銅價,補助資金
提高銅價對刺激銅廠生產具有重要作用,清代銅價由國家定價。“中央政府制定銅價主要根據礦石的品質和開礦的難度。各礦的產銅額根據礦床的大小規(guī)模而變化。盡管有一系列的變化因素,每個礦普遍的趨勢還是非常清楚的:在年產銅額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銅本數額越大,價格必然逐漸上升。”[4]281清代曾多次提高云南銅價以幫助銅廠渡過生產困難,同時也刺激銅廠的生產。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五月,乾隆帝諭旨:“滇省各銅廠前因馬騾短少,柴米價昂,每銅百斤,準其暫加價銀六錢,俟軍務竣后停止,嗣后加恩展限一、二年。今念該省頻歲雖獲有秋,而米糧、柴炭等價值,仍未即能平減,著再加恩展限二年,俾各資本寬余,踴躍開采,庶于銅務有裨,而廠民亦得資充裕。該撫仍留心體察,俟廠地物價一平,即行奏明停止。”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908),乾隆三十七年五月甲辰。
以上史料說明,清廷此次提高銅價是為了暫時幫助云南銅廠渡過難關,待“物價一平,即行奏明停止”。
除了提高銅價之外,清朝統治者還通過發(fā)放補助金的形式幫助銅廠渡過困難,發(fā)展生產。乾隆三十六年(1771),云南地方官府要求各個銅廠在每個礦的附近儲備半年的谷物、一年的油料和煤,以備不時只需,銅廠無法負擔儲備這些糧油所需的數額巨大的費用,云南地方財政給予了補助。這一舉措取得了明顯的效果,東川礦區(qū)稻米價格立即降了下來。[4]284另外,云南地方政府還通過向銅廠發(fā)放“水泄工費”補助金,以彌補洪水浸淹對銅礦生產造成的損失,降低銅廠生產成本,刺激生產。對于“水泄工費”,史料上是這樣記載的:“各廠采辦銅斤,并未酌給水泄銀兩。嗣因開采年久,漕硐深遠。產硔之區(qū),一至夏秋之際,即被水浸淹。廠民無力提拉宣泄,采取維艱。所有義都廠水泄,經總督楊、巡撫湯奏準,于順寧局鑄息銀內,自(乾隆)三十一年起,每年酌給銀三千兩。……三十七年,巡撫李條奏,水泄銀兩,應按照實獲銅數酌給,以免糜費。義都廠,每辦銅一萬斤,給予水泄銀六十五兩二錢一分七厘四毫。奉部復準,于省局鑄息銀內動支。”[15]820補助金的發(fā)放,對刺激銅礦生產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通過這些政策和措施(補助金制度),云南省級地方政府又把銅產量推回到1 000萬斤以上,1767年銅產量攀升到700萬斤,1780年又上升到1 100萬斤。就我們所知,從1765到1805,平均每年的銅產量至少和以前時期持平”。[4]286
3.改善運輸,蠲免廠欠
銅斤運輸上的極大困難是造成滇銅衰落的重要原因。清朝中期,統治者先后疏浚、修鑿多條通往省外的水陸通道,為改善云南銅斤外運條件提供了支撐,如開通金沙江、鹽井渡、羅星渡三處通川河道,就為節(jié)省運通費用產生了積極作用。乾隆五年(1740),云南總督慶復、云南巡撫張允隨奏請開鑿通川河道,七月底經軍機大臣鄂爾泰等議準,動帑興工金沙江。云南督撫制定分段次第施工、委員專管、寬籌工價、安設草房站船運儲物資、采辦川米川鹽、請領工本等多項措施,以保證工程順利進行。[16]47-49歷時六年半,金沙江工程完工,該工程為緩解滇銅京運威寧道的運輸壓力,降低運輸成本起到了積極作用。史載:“開金沙江,將滇省銅斤改由水運,每年可省陸運之半,則威寧及昭通兩路余出馬匹,辦運自見敷裕”。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221),乾隆九年七月戊戌。
乾隆十一年(1746),張允隨奏報:“查三處河道(金沙江、鹽井渡、羅星渡),……自完工以來,運發(fā)京銅,就現在辦理,較從前陸運,每年實可節(jié)省銀一萬五千五百余兩。”
參見《張允隨奏稿》卷7,云南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允隨,遵旨奏覆通川河道較先前陸運節(jié)省銀兩數折(乾隆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為挽救日益衰落的云南銅業(yè),清朝統治者還采取了蠲免廠欠的措施。廠欠的蠲免意味著由官府承擔了銅廠的債務,從而造成官府的財政損失,但該舉措的實行對減輕銅廠生產壓力確實起到了作用。乾隆、嘉慶年間,清廷多次蠲免云南銅廠廠欠,李中清先生統計了1720—1814年間部分年份云南銅礦廠欠損失情況,茲節(jié)錄如下:
(二)對黔鉛衰落的挽救與調控措施
針對清代黔鉛日益衰落的形勢,清朝統治者積極采取應對措施,對其進行挽救和調控。
1.控制成本、清查私礦
米價是影響礦廠生產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有效控制不斷上升的米價,貴州當地官員提出:“崇儉禁奢,清查酒肆,通都郡邑官為定數,新疆村寨一概禁止。尤在勸開墾、懲奸民、興水利以開其
源。”與此同時“飭令地方官凡遇報墾荒山,務即親復勘明,給照為業(yè)。其無力引水之田,則照例官借工本,限年完項,分別升科。”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
除此之外,貴州地方官員還提出了“賑糶”的對策,乾隆十三年(1748),護理貴州巡撫布政使恒文復奏:“……現貯(米)百四十萬石,即遇偏災,足備賑糶。”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317),乾隆十三年六月壬午。
從以上史料來看,清代貴州官員對控制米價的措施是得法的。
雍正初年,貴州地方官府對私礦進行大力整頓,將其納入官府監(jiān)管之下。雍正二年(1724),貴州巡撫毛文銓奏:“尚有丁頭山、齊家灣等處鉛廠,昔日俱屬私開,即前折奏聞之濫木橋水銀廠,從前亦無分文歸公之處,今逐一清查,現檄藩司議定抽收之數”。
參見《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3冊),毛文銓,奏請查私開礦廠酌議抽收款項歸公折(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經過此次大規(guī)模整頓,大部分私廠開始抽課納稅,成為國家監(jiān)管的合法礦廠。
2.提高鉛價、降低礦課
提高銅價能有效調動礦廠的生產積極性,清朝統治者注意到了此問題。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貴州巡撫李慶棻奏準“黔省福集、蓮花二廠,……日形支絀。查廠產不旺之故,實緣開采已久,漕峒日深。……而福集廠每鉛百斤價一兩四錢,蓮花廠價一兩五錢。又每百斤抽課二十斤,計爐丁得數,每百斤僅獲工本一兩一二錢,自難踴躍赴采。請照滇省加增銅價例,每百斤加價三錢,即于解運京鉛節(jié)省水腳銀六萬余兩內撥補養(yǎng)廉等項外支給。”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戊午。
又如,乾隆八年(1743)二月,貴州總督監(jiān)管巡撫張廣泗奏準:“蓮花、砂硃等廠,礦砂既薄,食物俱昂,爐民無利可圖,人散爐停,出鉛日少。請將每斤一分有零原價定為一分五厘,一面收買,一面發(fā)運。”
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85),乾隆八年二月辛亥。
除了提高銅價外,清朝統治者還采取降低礦課來刺激生產。如道光八年(1829)十二月,道光帝諭內閣:“黔省媽姑、福集等鉛廠因開采年久,峒老山空,砂丁采取匪易。新發(fā)白巖子廠夏間雨水過多,漕峒被淹,招丁車水,需費不少,爐戶倍形疲乏。……所有該廠等應抽二成課鉛,準照滇省新銅抽課一成之例,暫減一成,以紓廠力。” 參見《清宣宗實錄》(卷148),道光八年十二月丙寅。
四、余 論
清代“滇銅”和“黔鉛”都共同出現了“盛極而衰”或是“由盛轉衰”的變化,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主要有生產成本的急劇增加、開采難度的日益加大、自然災害破壞、“銅價”“鉛價”增長幅度比不上成本增加速度,私礦泛濫等。清廷采取了一些列諸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價格、查禁私礦、發(fā)放補助金、蠲免廠欠等措施,短時間內使礦業(yè)衰落問題得到緩解,但這些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遏制云貴地區(qū)礦業(yè)衰落的趨勢,隨著清朝后期政治日益腐敗和西方殖民者入侵,滇銅和黔鉛的衰落勢不可擋。
加之礦民及其與采礦相關的從業(yè)人員紛紛失業(yè),這些失業(yè)者逐漸演變成為一支反抗官府的力量,在與清代后期風起云涌的民變結合之后,共同加劇了清朝后期的邊疆統治危機。
回望這段歷史,“滇銅”和“黔鉛”的興旺,一定程度上促進和帶動了西南邊疆地區(qū)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造成“滇銅”“黔鉛”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也有政治的原因。清廷對此采取的調控策略和措施有其可取之處,一是清廷注重綜合施策、多管齊下,將挽救礦業(yè)衰落當做一項“系統工程”來看待,并不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通過經濟和政治的手段,一段時期內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二是清廷注重因時因事,分類指導,針對“滇銅”和“黔鉛”衰落的不同原因,分類采取了不同的調控措施,當然這些措施的實行是與兩省地方大員的礦政理路相匹配的。三是清廷尤其注重運用經濟的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礦業(yè)衰落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經濟問題,當然傳統社會之下經濟往往受制于政治。在清廷挽救礦業(yè)衰落的措施中無論是降低成本、提高價格、降低礦課、補助資金,都體現了現代政府對經濟和產業(yè)調控的理念、思路。這樣的理念和思路出現于19世紀對中國西南邊疆礦業(yè)的調控和治理上更有其可貴之處。
參考文獻:
[1]徐斌.試析清中后期云南銅業(yè)衰落的原因[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4):50-55.
[2]文思啟.林則徐與云南礦冶業(yè)[J].思想戰(zhàn)線,1985(4):85-89.
[3]劉朝輝.嘉道時期滇銅供應問題探析:兼論嘉道時期云南銅礦之衰落[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77-83.
[4]李中清.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經濟(1250—185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肖本俊.清代乾嘉時期云南礦區(qū)的“山荒”與滇銅業(yè)的衰落[D].昆明:云南大學,2011.
[6]羅時法.清代前、中期貴州礦業(yè)略考[J].貴州社會科學,1986(4):59-64.
[7]袁軼峰.清代大定府鉛銅業(yè)衰落的原因探析[J].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1(3):5-9.
[8]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與檔案系,中國政治制度教研室.清代的礦業(yè):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志九十九:食貨五:礦政[M]//清史稿:卷124: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縮印本.
[10]鹽務考三[M]//龍云. 新纂云南通志:第七冊:卷149.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11]張廷玉.清朝文獻通考:卷14[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2]貴州通史:第3卷[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
[13]馬琦.國家資源:清代滇銅黔鉛開發(fā)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4]嚴中平.清代云南銅政考[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5]云南通志:藝文志:云南銅志[M]//方國瑜.云南史料叢刊:卷12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
[16]劉若芳, 孔未名.乾隆年間疏浚金沙江史料:上[J]. 歷史檔案, 2001(1):47-61.
(責任編輯: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