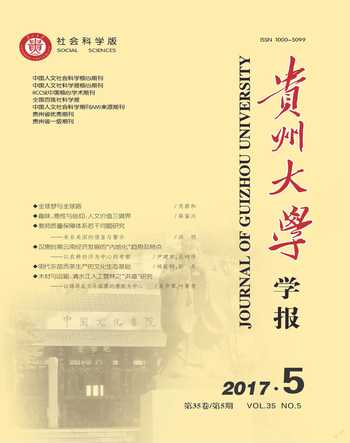貧困地區農戶對扶貧效果評價的影響因素分析
張自強 伍國勇 徐平
摘 要:基于貴州關嶺縣的農戶調查,區分農戶是否感知扶貧實惠和感知扶貧幫助程度的2個層面,將影響因素劃分為農戶特征、社會保障、政策認知和政策評價4個方面共15個變量,分別運用二元與有序logit模型,實證分析各變量對農戶感知扶貧政策實施效果的作用機理。結果表明,盡管物質給予能夠增強貧困地區農戶對扶貧實惠的感知,但包括農村低保、農村養老保等農村社會保障措施在內的制度完善才有利于提高扶貧政策的幫助程度,基于農戶可行能力塑造的社會網絡建設是扶貧開發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
貴州;扶貧;可行能力;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7)05-0070-05
國際DOI編碼:10.15958/j.cnki.gdxbshb.2017.05.11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快速增長,使得中國農村減貧取得了顯著成效。盡管貧困線多次提高,2011年中國農村貧困檢測報告顯示,農村貧困人口仍從1978年的2.5億下降到2010年的2 688萬人,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2.8%。據《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2012—2015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9.2%,農村貧困人口減少6 663萬人。然而, Zaman等針對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國家的研究發現,盡管經濟增長有助于貧困的下降,但收入不平等卻會加劇貧困的發生,作用正好相反。[1]以縣為單位的扶貧策略有利于縣域經濟的良好發展,但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2]值得注意的是,隱形貧困的存在使得脫貧的群體很容易再次陷入貧困,即家庭的貧困脆弱性。顯然,通過個體自身能力的修復來擺脫貧困存在瓶頸,多維制度設計與社會網絡構建成為新時期扶貧開發的著力方向。
根據Sen的觀點,貧困的實質在于可行能力的喪失,包括教育、技能、健康、機會等內容,扶貧重點從消除物質貧困向緩解能力貧困轉變。扶貧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貧困線標準忽視了包括教育、衛生、福利在內的非收入特征的制度安排。在扶貧資金不斷增長的情況下,一些地區的脫貧卻越來越困難,[3]即存在“越扶越貧”的現象。
扶貧措施開始從單純地關注援助資金的規模到全面地考慮制度建設轉變,國際發展援助開始“制度轉向”[4]。新時期貧困性質的轉變包括:一是地域性貧困,由自然環境條件所致;二是個體性貧困,即素質性貧困,由個體健康、勞動能力等條件所致;三是體制性貧困,如二元經濟體制引發的貧困。[5]扶貧開發也開始從“粗放式”向“精準式”轉變,2013年,《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要求“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建立風險、脆弱性預警機制,提高扶貧效率。[6]
對能力貧困而言,農村社會保障是直接針對收入貧困,應具備顯著的減貧效應。[7]農村“新貧困”特征的原因在于農民經濟、政治與社會權利的缺失或被排斥。[8]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抵消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陳立中在實證分析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對貧困減少影響的基礎上,建議開發式扶貧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為重點的社會保護式扶貧政策轉變。[9]蔣選和韓林芝基于灰色關聯分析發現,農村義務教育對貧困消除具有顯著影響。[10]薛惠元運用倍差法實證分析發現,新農保政策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11]樊麗明和解堊實證檢驗中國公共轉移支付對家庭貧困脆弱性的影響發現,教育程度、家庭規模、就業狀態、工作性質及地區變量同時同方向地影響到貧困及脆弱性。[12]
在關注政策減貧客觀效果的同時,現有研究還注意到了貧困地區農戶的主觀滿意水平。肖云和嚴茉基于全國多個省份的農戶調查,分析了農戶對扶貧政策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包括農戶家庭特征、扶貧政策及其實施情況等。[13]王宏杰和李東岳基于湖北省農戶調查實證分析發現,農戶對扶貧政策的了解程度對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14]陳小麗運用層次分析法,從社會發展、扶貧投入等多個方面評價了扶貧效果的影響,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影響權重較高。[15]
現有研究注意到了新時期農村貧困特征的轉變,強調扶貧政策或措施不再僅僅是物質給予,而更側重于基于制度保障的脫貧能力塑造;實證分析了貧困地區農戶對扶貧政策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然而,貧困表征多維,在側重于貧困率、貧困戶收入增長等客觀成效的同時,也需要關注農戶對貧困狀況改善的主觀感知。對此,本研究基于貴州關嶺縣的農戶調查,結合農戶稟賦與能力塑造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在分析影響農戶是否享受扶貧福利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農戶評價扶貧效果程度的影響,探討農戶扶貧效果認知的影響因素,為提高扶貧政策或措施的實施效果提供參考借鑒。
一、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1.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中國扶貧開發戰略和政策研究調查》課題組2016年5—6月對貴州省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農戶問卷調查。關嶺縣隸屬于貴州省安順市,是國家級貧困縣,調查樣本選取具有代表性。問卷調查采取隨機入戶形式,主要集中在頂云鄉、永寧鎮、斷橋鎮等多個鄉鎮的10多個村,結合訪談進行。共發放問卷310份,收回問卷260份,其中有效問卷252份。
2.變量選取
基于以往研究對影響農戶貧困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為農戶特征、社會保障、政策認知、政策評價4個方面共15個影響因素。其中,農戶特征包括年齡、受教育年限、是否常年外出打工、是否經常生病、土地面積;社會保障包括是否享受農村低保,是否享受農村養老保;政策認知包括扶貧對象是否準確,扶貧資金使用是否公正,扶貧政策是否真正需要;政策評價包括政府對扶貧的重視程度,扶貧政策實施滿意度,農村“低保”效果,農村“養老保”效果,“新農合”效果(如表1)。
自變量中,年齡x11、受教育年限x12和耕地面積x15為連續變量,其他變量均為分類變量。受訪農戶年齡最低為17歲,最高達91歲;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最小為0公頃,最大為1.07公頃;農戶受教育年限的均值為6.59,受訪農戶的教育程度比較低。需要說明的是,調查問卷中涉及到“農戶是否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問題,受訪農戶基本都參與了,所以在社會保障的變量中未納入這一因素。
3.模型設定
二、實證估計
運用stata 12.0統計軟件估計得出表2。從表2可知:二元logit回歸結果中,LR chi2(15)值為49.25,相應的p值為0<0.05,模型整體擬合度較好,Pseudo R2值為0.41;有序logit回歸結果中,LR chi2(15)值為136.01,相應的p值為0<005,模型整體擬合度也較好,Pseudo R2值為056。二元logit回歸結果中,社會保障中的變量影響不顯著,政策評價中的變量影響比較明顯;有序logit回歸結果中,變量影響顯著性較小,社會保障與政策認知中的變量影響均不顯著,各變量的具體影響如下:
第一,農戶特征變量的影響。一是農戶“受教育年限”x12變量的影響系數為-0.05,且統計上不顯著。農戶受教育程度越高,認為獲得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低,這可能與自身人力資本未得到發揮有關。如果只是救濟性扶貧,農戶脫貧能力未得到自我塑造,人力資本作用效果較小。需要注意的是,在對扶貧政策帶來幫助的有序logit回歸結果中,受教育年限的影響系數為0.11,也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作用方向為正,作用強度較高,表明當扶貧政策或項目實施如何利用到農戶自身的人力資本時,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資本發揮的作用相對越大,對扶貧政策產生幫助的作用評價也就越高。
二是農戶“是否常年在外打工”x13變量對是否享受扶貧實惠的影響系數為1.50,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表明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戶享受到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高,這可能與地方政府鼓勵勞動力轉移有關。然而,該變量對扶貧政策幫助的有序logit回歸結果的系數為0.56,且統計上不顯著。即常年在外打工農戶對扶貧幫助評價越高的可能性越小,表明常年不在家的農戶對扶貧政策了解程度有限,對扶貧政策效果的評價相對就低。勞動力轉移不僅能改善家庭貧困,還有利于城鎮化建設,地方政府積極性較高,農戶享受到的政策紅利越大。
三是“是否經常生病”x14變量對是否享受扶貧實惠的影響系數為0.48,且統計上不顯著。即農戶健康狀況越差,能夠享受到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高,健康狀況越差的農戶享受政府救濟相對越多。該變量對扶貧政策幫助的有序logit回歸結果的系數為-1.79,且在5%的水平上統計顯著。即健康狀況差的農戶確實能享受到扶貧實惠,而且認為扶貧政策帶來的幫助越大。顯然,農村醫療制度的完善對于扶貧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性,但農村缺乏大病救濟制度,越是嚴重的疾病,能夠享受到的扶貧幫助越是有限,“因病致貧”時有發生。相比于其他變量,該變量的影響系數非常大,可見農戶對此的重視程度。
第二,社會保障變量的影響。農戶“是否享受農村低保”x21變量和農戶“是否享受農村養老保”x22變量,對y1和y2的影響系數均為正,但統計上均不顯著,表明農戶能夠享受到農村低保或養老保的政策福利。但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大,認為扶貧政策幫助的程度越小,說明農村低保與養老保仍處于較低水平,這兩項政策的實施對農戶感知扶貧效果的提升作用有限。
第三,政策認知變量的影響。一是“扶貧對象是否準確”x31變量對y1和y2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77和-0.47,且統計上均不顯著,說明扶貧對象準確與否對農戶扶貧政策實惠的感知不存在必然相關性。
二是“扶貧資金使用是否公正”x32變量對y1的影響系數為0.47,且統計上不顯著,表明扶貧資金使用越公正,農戶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大,農戶了解具體扶貧政策項目的實施,甚至參與相關扶貧政策與項目的討論,對扶貧實惠的感知水平相對就越高。該變量對y2的影響系數為-0.38,即農戶認為扶貧資金使用公開、公正,對扶貧政策帶來實際幫助評價高的可能性越大。由此可以認為,扶貧資金使用的公開、公正,不僅能增強農戶對扶貧政策的感知,了解到存在“實惠”,而且能影響農戶感知政策“實惠”的大小,“公開”有利于提高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至少避免“流失”,農戶能理性地對待扶貧資金的使用。
三是“扶貧政策是否真正需要”x33變量對y1的影響系數為2.36,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該變量對y1的作用強度與顯著程度都比較大,即農戶認為扶貧政策越是真正需要的,對扶貧實惠的感知程度越高,表明扶貧政策在滿足當地農戶實際需求上更能影響農戶對扶貧效果的判斷。而且該變量對y2的影響系數為0.69,也具有比較大的正向作用,但不顯著,表明盡管扶貧政策是自身需要的,但認為政策產生的幫助較小。由此可知,農戶不僅關注扶貧政策是否滿足自身需求,更重視得到滿足的程度,“救濟式”扶貧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戶需求,但農戶更需要脫貧能力的塑造。
第四,政策評價變量的影響。一是“政府對扶貧重視程度”x41變量對y1的影響系數為-3.6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政府對扶貧的重視程度越低,農戶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表明政府重視貧困戶識別、農戶需求、扶貧資金使用等方面,能夠提高農戶享受扶貧政策的實惠。且該變量對y2的影響系數為0.91,統計上不顯著,進一步表明在強制性制度變遷的背景下,政府對貧困的關注與重視程度決定了扶貧效果與效率。
二是“扶貧政策實施效果”x42變量對y1和y2的影響系數分別為2.93和3.17,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農戶越滿意扶貧政策,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高,對扶貧政策產生幫助評價高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三是3項農村公共服務中,只有“‘新農合效果”x45變量對y1和y2的影響分別在10%和5%的水平上顯著,且影響系數分別為-105和120。即農戶認為“新農合”效果越低,感知扶貧政策實惠的可能性就越低,對扶貧政策產生幫助評價低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表明農村醫療制度建設對農戶脫貧更具有建設性價值。而且健康影響農戶人力資本,保障農戶健康的制度越完善,農戶人力資本提升可能性越大,脫貧能力也就相對越強。
三、結論與啟示
1.結論
基于貴州省關嶺縣的農戶調查數據,將影響農戶對扶貧效果的評價從2個層面展開,即是否感知扶貧實惠和感知實惠幫助的程度,結合以往研究成果,將影響因素劃分為農戶特征、社會保障、政策認知和政策評價4個方面共15個變量,分別運用二元logit回歸和有序logit回歸,分析了各變量對農戶感知扶貧實惠與實惠幫助程度的作用機理,結論如下:一是農戶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常年在外打工、經常生病和擁有的耕地面積越少,農戶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高;二是享受農村低保、農村養老保的農戶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越高;三是扶貧資金使用公正、政策符合自身真實需要,農戶對扶貧實惠感知的可能性就越高;四是政府對扶貧工程重視程度越高,農戶對扶貧政策實施越滿意,“新農合”實施效果越好,農戶感知扶貧實惠的可能性就越高。
2.啟示
從實證估計結果看,影響因素中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農戶人力資本的作用,包括教育、健康、農村醫療變量均具有顯著影響。“救濟式”扶貧難以滿足新時期農戶脫貧需求,自身能力的塑造才是擺脫貧困的關鍵。其中,人力資本的提升能顯著改善農戶生產與創收能力,避免物質脫貧的脆弱性。從對扶貧政策產生幫助的影響結果看,有關人力資本的變量才是影響農戶對扶貧效果判斷的依據,對此,包括基礎教育、職業技術培訓在內的教育服務對于地區和農戶脫貧具有深遠意義。二是扶貧公開透明的重要性。由于制度依賴與權力尋租的存在,部分貧困地區存在“越扶越貧”的脫貧怪圈,扶貧項目實施與扶貧資金使用的公開并不一定能顯著改善扶貧效果和扶貧效率,但能增強社會監管與監督,至少能避免扶貧資金使用的“使命漂移”,在“公開”的基礎上逐漸引入市場參與機制,擴寬扶貧資金使用的市場化途徑,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的幫扶程度。三是新時期貧困特征對扶貧攻堅提出了更高要求。社會網絡的制度建設對農村貧困兜底尤為重要,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在兼容地區環境優勢或特征的同時,也需要切合農戶脫貧需求。制度設計需要農戶參與,強制性政府干預盡管能帶來扶貧實惠,但農戶感知實惠的程度較低,扶貧效果有限,引入農戶參與途徑后構建農戶參與扶貧建設平臺,制定滿足當地農戶需求的扶貧政策或制度,體現了扶貧“精準”的內在要求,有利于保障地區脫貧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1]ZAMAN K, SHAH I A, KHAN M M, et al. The growth, inequality and poverty triangle: new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SAARC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Business Research, 2012, 4(5):485-500.
[2]王志凌,鄒林杰. 國家級貧困縣“精準”扶貧效率評價:以廣西27個縣為例[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102-106.
[3]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R].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
[4]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Chapter 6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J].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005, 1(5):385-472.
[5]呂煒,劉暢.中國農村公共投資、社會性支出與貧困問題研究[J].財貿研究,2008(5):61-69.
[6]黃承偉,王小林,徐麗萍. 貧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測量方法[J].農業技術經濟,2010(8):4-11.
[7]阿馬蒂亞·森.論社會排斥[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3):1-7.
[8]段文娟. 論“社會排斥”與農村“新貧困”[J]. 重慶工商大學學報(西部論壇),2005(6):11-14.
[9]陳立中. 收入增長和分配對我國農村減貧的影響:方法、特征與證據[J].經濟學(季刊),2009(2):711-726.
[10]蔣選,韓林芝.教育與消除貧困:研究動態與中國農村的實證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9(3):66-70.
[11]薛惠元. 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減貧效應評估:基于對廣西和湖北的抽樣調研[J].現代經濟探討,2013(3):11-15.
[12]樊麗明,解堊.公共轉移支付減少了貧困脆弱性嗎?[J].經濟研究,2014(8):67-77.
[13]肖云,嚴茉.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對扶貧政策滿意度影響因素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12(5):107-112.
[14]王宏杰,李東岳. 貧困地區農村居民對扶貧政策的滿意度分析[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44-49.
[15]陳小麗. 基于多層次分析法的湖北民族地區扶貧績效評價[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76-80.
(責任編輯:鐘昭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