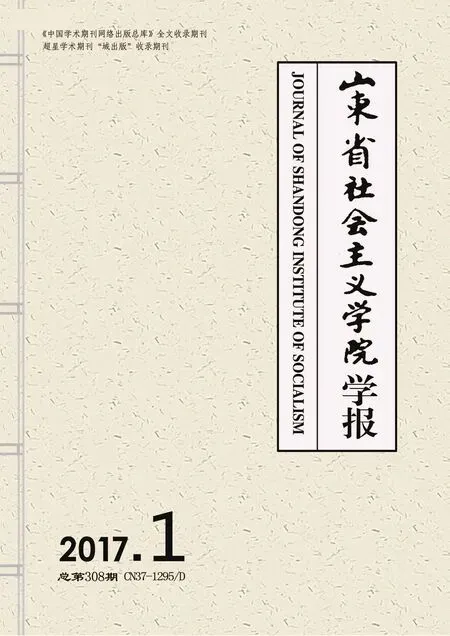《史記·五帝本紀》與中華共同體的形成
陳戰峰
《史記·五帝本紀》與中華共同體的形成
陳戰峰
《五帝本紀》是《史記》的第一篇(卷),在中國歷史與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反映了司馬遷卓著的史學眼光與時代意識,對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史學與理論基礎。其中的“五帝”及其關系清晰而鮮明,顯示了史書編撰者的主動調整和自覺建構努力。“五帝”既反映了歷史一脈相承,又有重人文、重理性的思想文化特征。在客觀與邏輯意義上,《五帝本紀》通過歷史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與心理認同,反映并促進了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為建立和鞏固具有民族多樣性、文化多元性的統一的新型國家提供了重要歷史依據和經驗智慧,影響深遠,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史記》;《五帝本紀》;中華共同體;認同
《五帝本紀》是古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的第一篇(卷),在中國歷史與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司馬遷面對當時百家稱“黃帝”而文辭不雅馴①“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史記·五帝本紀》)本文所參考《史記》為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后同。,實地考察,對傳聞“五帝”現象進行重新的思考和研究。盡管《史記》已經做到“擇其言尤雅者”(《史記·五帝本紀》),但畢竟記載了不少傳說故事,錯訛與矛盾的地方也比較多,不能作為判定客觀史實的唯一依據。然而史學作品具有歷史重構的本質屬性,本身便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文化現象,需要對其進行思想文化的分析。如果將《五帝本紀》與其緊接著的卷二《夏本紀》、卷三《殷本紀》以及卷四《周本紀》結合起來分析,則反映了司馬遷卓著的史學眼光與時代意識。簡言之,《五帝本紀》對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史學與理論基礎。
當然,這里所說的中華共同體具體包括歷史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以及心理共同體,四個方面融會在秦漢以來以華夏民族(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與多元文化的統一的國家形成進程中,促進了國格意識的形成與思想文化的發展,對后世影響深遠。中華民族是一個多元統一體[1]。
一、“五帝”的排序與《五帝本紀》中“五帝”的變化
“五帝”并不是中國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或提法,而是在戰國時期逐漸形成和發展完善的。但是,據龍山文化遺址等考古發現,相當于“五帝”時期的歷史時代是客觀存在的。
“五帝”大多指稱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上古時期歷史人物的合稱,具體包括三種說法,即“太皞(伏羲)、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戰國策》《呂氏春秋》),“少昊(少皞)、顓頊、高辛(帝嚳)、堯、舜”(《偽尚書序》),“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等,三種關于“五帝”的排序反映了不同的譜系特點和時代烙印,也體現了“五帝”在戰國中晚期至秦漢之際的調整變化的特質。《史記》中的《五帝本紀》與《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順序一致,與《偽尚書序》也比較接近,是對此前五帝順序與譜系的重新建構與整合。
二是五方上帝(或五方神)的合稱,即中央黃帝(軒轅,屬土)、東方青帝(伏羲、屬木),南方赤帝(炎帝,一說蚩尤,屬火),西方白帝(少昊,屬金),北方黑帝(顓頊,屬水),自然這里的五方上帝帶有明顯的五行思想和觀念,而且反映了黃帝已經居于中央統攝地位,對四方神具有支配與指導作用。《呂氏春秋·應同》以五行思想解釋黃帝、舜、湯、文王以來的歷史演變規律,判斷代周而興的當屬“水”德。這些都是秦漢之際大一統歷史趨勢在思想觀念上的曲折反映①郭沫若先生認為:“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黃帝的子孫,那便完全是人為。那是在中國統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為消除各種氏族的畛域起見而生出的大一統的要求。”(《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2-223.)。
《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及其關系很清晰與鮮明,顯示了史書編撰者的主動調整和自覺建構,其中蘊藏的時代感和問題意識值得人們注意。
二、《五帝本紀》歷史傳承的特色
《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分別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他們之間具有密切的血緣聯系,“黃帝”是始祖,“顓頊”是“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帝嚳”是黃帝之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堯”是帝嚳之子(名放勛),“舜”是昌意的七世孫(即黃帝的八世孫),當然,《夏本紀》記載繼承“舜”大位的“禹”是昌意的三世孫(即黃帝的四世孫),其間顯有錯訛與矛盾,則是另一問題,也愈益突顯了這個世系與譜系的重構本質。
《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形象克服了此前“五帝”世系的紛雜與矛盾,而代之以同宗共族的特色,均是共祖“黃帝”的嫡系后裔。雖然這個譜系還有不少歷史的空白,有間隔,不連續,但所選取的主要歷史人物與歷史節點,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涵。顯而易見,《五帝本紀》中的“五帝”帶有濃郁的血緣屬性和人文屬性,“五帝”重視德行與功業,通過個人的努力、發明和百姓的共同勞動,逐步改善生存生活的環境和境遇,促進文明的進步和發展,而不是依靠上天的恩賜或神的庇佑,這都反映了較天命思想以及圖騰崇拜、上帝崇拜與祖先崇拜進步的思想意義,具有深刻的人文價值與實踐功能。因此,《五帝本紀》中的“五帝”既反映了歷史一脈相承,又有重人文、重理性的思想文化特征。這些記載雖然與《詩經》《尚書》記載的在殷商時期依然保留著厚重的圖騰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崇拜(《詩經·生民》《詩經·玄鳥》等)不完全一致,卻深刻反映了秦漢時期歷史敘述重構的思想本質。
這種重構的影響因素大致來源于三個要素,分別是:戰國中晚期炎黃信仰的形成發展與黃老之學的興起,新型國家統一趨勢在思想上的訴求和反映,陰陽思想與五行思想的匯合與交融等等。
三、《五帝本紀》在中華共同體形成中的文化功能
在客觀與邏輯意義上,《五帝本紀》反映并促進了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歷史認同
歷史認同是歷史建構與歷史重構的基礎和前提。炎帝、黃帝等上古帝王,不見于《詩經》《尚書》的記載。炎帝、黃帝的記載,在流傳文獻中最早見于《國語·周語》①“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國語·晉語》)。司馬遷重新梳理勾勒歷史。以黃帝為首重建上古史的譜系,既是對五方上帝神觀念的揚棄,也是對人文歷史認識的自覺化與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啟迪意義。
關于這種歷史重構中的諸多復雜問題,例如如何處理神話與歷史的關系問題,司馬遷嘗試所做的“神話的歷史化”和“歷史的神話化”[2]努力,恰恰反映了對神話傳說歷史價值尊重和對現實歷史價值賦予的雙重努力,其中的矛盾與沖突不僅僅具有表面的史料或觀點的不一致,更深層次反映了歷史重構在面對歷史文化資源與現實社會需要時的多重考量和曲折努力。當然,《史記》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具有多種演變[3],其中班氏家藏本的改變應被充分考慮在內,這有助于判斷和厘清表面沖突后的歷史實質。
(二)民族認同
“五帝”時代是氏族部落不斷發展和融合的時代。古老部落與新興部落的結盟、分化與融合,在神話歷史傳說中表現為世系相傳與更迭,反映了氏族部落的延續和變化。部落的首領或盟主帶有“共主”的特點,世代相沿不替,所以流傳的英雄首領名稱便是“共名”,如炎帝和黃帝等,這有助于理解上古傳說帝王長壽的故事,盡管荒誕不經,但卻蘊藏著對歷史的追溯與體認,凝聚著氏族部落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民族認同。“歷史記載的長期連續性,即是我們民族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證”“中華民族這種強烈的歷史感,其實質意義即是重視民族自身的由來、發展,并且自覺地將它傳續下去”[4],中華民族也是在這個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的。
《五帝本紀》以人文化的視野重新審視傳說歷史,將“五帝”構筑為一個世代相傳、綿延不絕的歷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歷史,其中的民族認同,為后世歷史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五帝”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體現了對歷史的選擇和重構,確認和凸顯黃帝的歷史地位,是民族歷史發展的必然反映。
《五帝本紀》以家譜的形式重新梳理歷史,既反映了民族認同的加深加劇,“五帝相繼作為部落首領而出自同一家族,前后綿綿數百年,這就為一個家族的歷史譜系做了最充分的材料準備”[5],也體現了家國觀念的發展以及家國一體格局進一步完善的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趨勢。
以華夏民族(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奠定了秦漢以后多民族融合又保持鮮明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體的基礎,影響深遠。
(三)文化認同
《五帝本紀》具有濃郁的人文色彩,標志是重視德行,重視功業,重視教化。《五帝本紀》記載五帝的功業,都有教化的寫照。黃帝“淳化鳥獸蟲蛾”①“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史記·五帝本紀》),顓頊“治氣以教化”②“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史記·五帝本紀》),帝嚳“撫教萬民而利誨之”③“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史記·五帝本紀》),堯“能明馴德”④“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史記·五帝本紀》),舜“使布五教于四方”⑤“日以篤謹,匪有解”“內行彌謹”“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史記·五帝本紀》)。“五帝”均能夠德化四方,教化萬民⑥其他如《史記》敘述商始祖契重視教化與功業:“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史記·殷本紀》)。這些奠定了內外兼修、本末賅備、體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觀念基礎。這并非是意味著歷史上的氏族首領—五帝客觀具有的思想特征,而是生活在漢代,受秦漢思想哺育的史學工作者進行自覺的理論審視與歷史重構、文化認同的必然結果。當然,這種文化認同在古史體系上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被認為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古史體系”[6]。相傳黃帝的大臣倉頡造字、殷代始祖契改進文字書寫辦法等,也曲折說明文化認同的進一步發展,包括對語言文字符號的發明和改進,促成了穩定有序的文明傳承體系的形成,這也是文化認同的表現。
《史記》在《三代世表》中明確強調,以黃帝為首的“五帝”與“三代”天子均是秉承修養德行而代代相傳,即使有的時候需要假托“天命”的觀念,“天命難言,非圣人莫能見”,也反復申述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后世”,子孫能夠“皆復立為天子”,關鍵是“天之報有德”(《史記·三代世表》)。重德是司馬遷自覺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意識。“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史記·五帝本紀》),司馬遷對“五帝”德行的建構和敘述,形象化地表達理想的道德人格和價值理念,其中呈現的人文精神是中華民族亙古不衰的主體價值觀念,也是中國哲學史與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征。
這種現象在《史記》的其他各篇也有顯著的反映,如關于先周的歷史,同《詩經》《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文王》等比較,《史記·周本紀》對是否具有“令德”①“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谷。’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記·周本紀》)當然,這里的史料除來源于《詩經·生民》外,還來自于《尚書·堯典》。的行為很重視,并且作為書寫歷史貫穿前后的一條主要線索,這既是對《詩經》上述六首英雄史詩的系統把握和深入體會,同時也展示了史學家個人史學建構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四)心理認同
《五帝本紀》與《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是一個有機的系統,雖然其中還有不少齟齬之處。
《夏本紀》將“禹”作為昌意的三世孫(黃帝→昌意→顓頊→鯀→禹),是直接繼承黃帝而來。《殷本紀》與《周本紀》中記載的殷始祖契、周始祖棄(后稷)分別是帝嚳的次妃簡狄吞燕卵與元妃姜嫄(原)履跡所生,事跡分別見于《詩經·玄鳥》②“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詩經· 商頌·玄鳥》)《楚辭·天問》③“簡狄在臺嚳何宜, 玄鳥致貽女何喜?”(《楚辭·天問》)與《詩經·生民》④“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詩經·大雅·生民》),帶有圖騰崇拜的深刻烙印,當然也交織和混合著上帝崇拜與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嚳則是黃帝的曾孫。這樣,將歷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過心理認同系結在“黃帝”的主干上,“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史記·三代世表》),從而使三代成為相互因革而在血緣與文化上又具有連續性的共同體,促使人們在心理上對國家統一性的認識逐漸加強。
《秦本紀》追溯的秦的始祖大業也直接肇源于顓頊的苗裔⑤“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史記·秦本紀》),《高祖本紀》將漢高祖的降生與神奇的“大澤之陂”的“蛟龍”⑥“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聯系在一起,形成與黑帝似有似無的聯系⑦當然,《史記·高祖本紀》在漢的統系上有不同認識,同篇高祖被酒斬蛇,后老嫗稱蛇為白帝子所化,為赤帝子所斬,作為漢代秦的論證,漢則屬“赤帝”系統(“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愿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后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 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終漢一代,人們在“黑帝”與“赤帝”系統上糾葛不清。。
這些都是有意識地論述“五帝”“三代”“秦漢”一脈相承,都是黃帝的子孫與苗裔①“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史記·三代世表》)這說明司馬遷對《詩經》記載與流傳神話故事的矛盾性有所覺察,而自覺進行了歷史的重新建構。。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意義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國家不會滅亡,民族不會滅亡。后來明清時期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國”與“亡天下”實際恰恰是朝代更迭與亡國的區別②如顧炎武說:“保國者保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卷13“正始”條)。這種歷史與文化的獨特性也保證了中國歷經戰亂兵燹而綿延不絕的存在狀態。
四、結語
司馬遷關于“五帝”歷史建構和歷史敘述的方式,是對漢代國家“大一統”觀念的表征,這種“大一統”,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國家民族形成的基本規律,也是歷史、民族、文化、心理等認同的結晶和影像。“大一統”的共同體的形成具有時空性,但也是物質和精神、主觀和客觀、歷史和現實的有機統一。在這種意義上,“五帝”譜系所昭示的歷史與文化的大一統的共同體觀念是與秦漢社會歷史與思想意識的發展息息相關的。
《五帝本紀》奠定和反映了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和發展。《史記》以后,歷代官修史書與民間史書在反映這個歷史時段時,大多保留或沿襲了《五帝本紀》的基本脈絡和譜系框架,保持和鞏固了歷史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促進了中華共同體的形成和具有民族多樣性、文化多元性的統一的新型國家的建立和發展,為奠定歷史上綿延不斷、源遠流長的中央集權國家提供了重要歷史依據和經驗智慧,影響深遠,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1]費孝通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1.
[2]劉書惠,李廣龍.《史記》感生神話矛盾性論析[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95.
[3]李開元.解構《史記·秦始皇本紀》—兼論3+N的歷史學知識構成[J].史學集刊,2012(4):48-58.
[4]陳其泰.史學與民族精神[M].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6.
[5]徐軍義.《史記·五帝本紀》的主體性構建[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4(14):9.
[6]陳其泰.史學與民族精神[M].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207.
陳戰峰,男,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儒學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