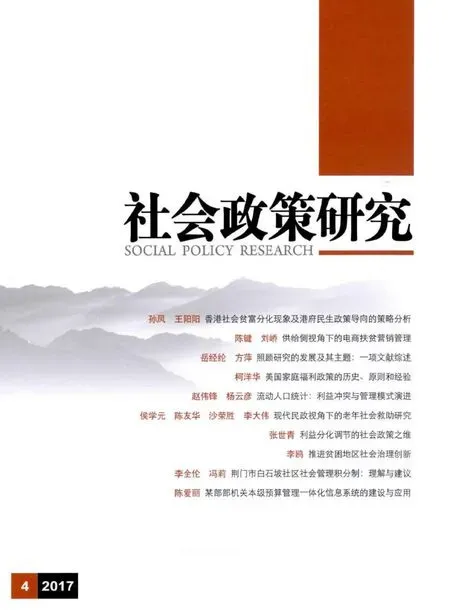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的歷史、原則和經(jīng)驗(yàn)
柯洋華
一、引言
作為一個(gè)“不情愿的”(Bruce. J.,1988)福利國(guó)家,美國(guó)政府對(duì)家庭福利的政治承諾非常之少,主要表現(xiàn)為:至今沒有聯(lián)邦層面的家庭政策,沒有普遍性的兒童津貼,沒有全國(guó)性的帶薪產(chǎn)假安排,也沒有專門的家庭政策部門,在全球各類家庭政策子項(xiàng)目排名中幾乎都處于末位,還是唯一一個(gè)在憲法中未提及“家庭”的國(guó)家(R.L.Corrow,2001)。由此看來,在家庭政策方面,美國(guó)似乎并不是一個(gè)理想的研究和學(xué)習(xí)對(duì)象。然而,與其據(jù)此認(rèn)為美國(guó)政府輕視家庭,不如說美國(guó)社會(huì)對(duì)于政府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尚未形成共識(shí)。系統(tǒng)的家庭政策在社會(huì)福利體系中缺席,并不意味著其在美國(guó)政界、學(xué)術(shù)界及社會(huì)公眾中缺乏關(guān)注度,事實(shí)恰好與之相反。按照家庭政策分析類型學(xué)來劃分,美國(guó)的家庭政策可以歸類為含蓄型(implicit)家庭政策,即“包括在其他領(lǐng)域所采取與家庭無關(guān),但對(duì)于家庭有重要影響的政策,例如所得稅措施,含蓄型家庭政策可延伸至明確型(explicit)家庭政策以外,包括任何政府或私營(yíng)部門從事的工作”(呂亞軍,2010)。本文將從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的歷史沿革、變遷背景及當(dāng)前內(nèi)容出發(fā),探討美國(guó)含蓄型家庭福利政策的特點(diǎn)、規(guī)律及其對(duì)中國(guó)的啟示。
二、變化中的家庭——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變遷的一般性背景
(一)持續(xù)變化的美國(guó)家庭:家庭形式和兒童生育環(huán)境日趨多樣
盡管美國(guó)社會(huì)從來都不存在一個(gè)所謂主流的家庭模式,但是與20世紀(jì)50年代相比,非婚同居者、非婚生育者、同性婚姻/同居者等多種婚姻和家庭形式大量出現(xiàn),如今的美國(guó)男女對(duì)于配偶、結(jié)婚時(shí)間、是否結(jié)婚、是否生育小孩等有了更多被社會(huì)認(rèn)可的選擇。具體而言,數(shù)十年來美國(guó)社會(huì)的婚姻和家庭形式主要表現(xiàn)出如下變化:1.結(jié)婚率下降,2014年,美國(guó)有50%的成年人處于在婚狀態(tài),這一比例在1960年為75%;2.同居取代結(jié)婚成為性伴侶間結(jié)成親密關(guān)系的主要方式,但同居日趨不穩(wěn)定和短暫;3.非婚生育的子女比例大比例攀升,由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的21%上升到了2009-2013年的43%;4.中年夫妻的離婚率有增高趨勢(shì),2010年,約有50%的50歲及以上的結(jié)過婚的美國(guó)人有過離婚或分居的經(jīng)歷;5.同性婚姻數(shù)量大幅增長(zhǎng),從2013年的近23萬對(duì)增加到了2015年的超過48萬對(duì);6.越來越多的兒童生活在不穩(wěn)定的家庭環(huán)境中,他們頻繁地隨著單親、非婚同居的父母或者繼父母遷居。
(二)女不再主內(nèi):女性逐漸參與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家庭內(nèi)部分工發(fā)生變化
美國(guó)家庭內(nèi)部分工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為美國(guó)女性大量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從傳統(tǒng)的家庭照料者變身為“養(yǎng)家糊口者(Bread Winner)”。這一趨勢(shì)顯現(xiàn)于二戰(zhàn)時(shí)期,彼時(shí)由于男性大量參與戰(zhàn)事,一方面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大量勞動(dòng)機(jī)會(huì)空出,另一方面女性需要承擔(dān)起養(yǎng)育家庭中的兒童和老年人的職責(zé)。這個(gè)階段,美國(guó)家庭的男女分工模式被迫逆?zhèn)鹘y(tǒng)而動(dòng),但戰(zhàn)爭(zhēng)的特殊性使其也獲得了廣泛的社會(huì)認(rèn)可。戰(zhàn)后初期,美國(guó)家庭經(jīng)歷了兩個(gè)截然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在冷戰(zhàn)早期,戰(zhàn)后美國(guó)年輕人開始選擇了“回歸家庭(homeward bound)”的生活方式,美國(guó)人的結(jié)婚率相對(duì)更高,結(jié)婚年齡也更低,而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家庭分工模式也被順理成章地接受了(Elaine Tyler May,2012)。進(jìn)入到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和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興起的60年代,無過錯(cuò)離婚得到法律許可①1969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家事法(California Family Law Act of 1969),支持無過錯(cuò)婚姻,成為美國(guó)乃至西方世界第一個(gè)適用無過錯(cuò)離婚的州。,離婚及非婚生育成為個(gè)性解放和婚姻獨(dú)立的標(biāo)志。婚姻和家庭生活在年輕人中被追求的程度下降,隨之而來的是離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女性市場(chǎng)勞動(dòng)參與率上升。而從有數(shù)據(jù)可查的1975年開始比較,有18歲以下孩子的女性的勞動(dòng)參與率已經(jīng)從當(dāng)時(shí)的47%增長(zhǎng)到了2014年的70%,其中家有學(xué)齡前兒童(6歲以前)的女性的勞動(dòng)參與率則從39%增長(zhǎng)到了64%。這些加入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的女性中,有3/4左右從事的是全職工作。
(三)價(jià)值多元:美國(guó)民眾對(duì)家庭及家庭政策的認(rèn)識(shí)變化
從上文可以看出,隨著美國(guó)高離婚率漸趨穩(wěn)定,美國(guó)民眾對(duì)于性取向、配偶、是否結(jié)婚生育子女、什么時(shí)候結(jié)婚/生育子女等有了更多獲社會(huì)認(rèn)可的選擇。Thornton et al.(2010)研究了20世紀(jì)60年代到90年代美國(guó)家庭觀念的變遷趨勢(shì),指出當(dāng)今美國(guó)對(duì)婚姻、孩子和家庭生活的高度重視和負(fù)責(zé)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持續(xù)特征,青年人和老年人都非常重視婚姻和孩子,并打算把他們生活的重心放在孩子和配偶身上;然而美國(guó)民眾心中婚姻和孩子的意義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雖然絕大多數(shù)美國(guó)人仍重視婚姻、孩子和家庭生活,但這些社會(huì)機(jī)制與以前相比,自主性更強(qiáng),而強(qiáng)制性更弱了。這種婚姻和父母身份的自主性作為一長(zhǎng)期趨勢(shì)延續(xù)到了90年代,人們選擇親密關(guān)系和家庭生活方式明顯比過去更被理解和更自由了。進(jìn)入21世紀(jì),前述觀念繼續(xù)變化。2015年皮尤中心(Pew Center)的一項(xiàng)調(diào)查顯示,絕大多數(shù)受訪者將孩子和締結(jié)婚姻視為一個(gè)家庭的要件:無論父母是單親還是非婚狀態(tài)、是異性或同性結(jié)合,只要他(們)有孩子,他們都可稱為一個(gè)家庭,一對(duì)結(jié)婚無孩的伴侶也可視作一個(gè)家庭,但是沒有孩子的同居者不能算作家庭。如果我們以家庭主義者所定義的“家庭”——一男一女組成的合乎法律規(guī)定的、終生的、性關(guān)系上排他的婚姻形式,他們通常有孩子而且男性是主要的掙錢養(yǎng)家者——作為考察美國(guó)家庭觀念和形式變化的基礎(chǔ),可以發(fā)現(xiàn)這幾乎是一個(gè)對(duì)前述“傳統(tǒng)”家庭多重背離的過程。
三、20世紀(jì)30年代以來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的變遷
美國(guó)家庭及美國(guó)民眾家庭觀念的變遷,主要在以下領(lǐng)域形成社會(huì)問題,需要公共政策對(duì)此作出回應(yīng):“復(fù)雜家庭(complex family)”①“復(fù)雜家庭”,是相對(duì)于“簡(jiǎn)單家庭(simple family)”而言的,后者通常是指單純由兩個(gè)生物學(xué)意義上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組成的家庭,而除此以外的家庭形式都是“復(fù)雜家庭”,通常表現(xiàn)出家庭關(guān)系復(fù)雜、不完整、高沖突、高流動(dòng)等特點(diǎn)。援引自:AG. Vanorman & P. Scommegna. (2016).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FAMILY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原文鏈接:http://www.prb.org/pdf16/prb-population-bulletin-71.1-complex-families-2016.pdf 。中的兒童照料和發(fā)展問題、以單親媽媽家庭為代表的脆弱家庭的貧困問題、多樣化的婚姻和家庭形式對(duì)所謂傳統(tǒng)美國(guó)價(jià)值觀的挑戰(zhàn)問題以及家庭責(zé)任與市場(chǎng)勞動(dòng)之間的平衡問題。這些問題在種族、階層和地區(qū)因素?fù)诫s之下,又在現(xiàn)實(shí)情境中表現(xiàn)得更加復(fù)雜,但不同歷史階段家庭政策對(duì)這些問題的回應(yīng)程度和方式不盡相同。美國(guó)社會(huì)福利從免遭匱乏的福利建設(shè),到“向貧困開戰(zhàn)”的福利擴(kuò)張,再到“向福利開戰(zhàn)”的福利改革,從終身福利到工作福利,最終形成了一個(gè)低福利、高市場(chǎng)和補(bǔ)救型的福利模式(嚴(yán)敏、朱春奎,2014)。而家庭福利作為社會(huì)福利的一支,也起落于這樣一個(gè)大的潮流之中。
(一)以“家庭中的個(gè)人”為對(duì)象的家庭福利創(chuàng)制時(shí)期(1930年代-1945年)
20世紀(jì)30年代,羅斯福新政時(shí)期家庭福利政策集中體現(xiàn)于1935年《社會(huì)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簡(jiǎn)稱SSA)的規(guī)定,“本法旨在增進(jìn)公共福利,通過建立一個(gè)聯(lián)邦的老年救濟(jì)金制度,使一些州得以為老人、盲人、受撫養(yǎng)的和殘疾兒童提供更為可靠的生活保障,為婦幼保健、公共衛(wèi)生和失業(yè)補(bǔ)助法的實(shí)行做出妥善的安排。”聯(lián)邦政府逐漸承擔(dān)起無力為繼的家庭、社會(huì)組織和州地的責(zé)任,與家庭相關(guān)的具體福利服務(wù)制度則包括:有需要撫養(yǎng)的兒童補(bǔ)助(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簡(jiǎn)稱ADC)和老年救助項(xiàng)目(Old Age Assistance,簡(jiǎn)稱OAA),對(duì)16歲以下無依無靠的受撫養(yǎng)的兒童、殘疾兒童和盲人進(jìn)行救濟(jì),對(duì)各州救濟(jì)受撫養(yǎng)的兒童之補(bǔ)助金和各州的婦幼福利補(bǔ)助費(fèi)規(guī)定了撥款,對(duì)需要撫養(yǎng)未成年子女的單身母親家庭提供資助;聯(lián)邦政府向各州撥付資金用于支持各州為母親和孩子提高健康水平,尤其是那些身居貧困地區(qū)或面臨經(jīng)濟(jì)壓力的群體,同時(shí)資助兒童事務(wù)局與其他公共福利部門開展合作來執(zhí)行、擴(kuò)大和強(qiáng)化兒童福利項(xiàng)目。1939年,社會(huì)保障法進(jìn)一步將工人的妻子、寡婦、退休者的孩子納入保障范圍,此時(shí)的社會(huì)保障已經(jīng)從單純的勞工保險(xiǎn)變?yōu)榧彝ケkU(xiǎn)。可以說,1935年社會(huì)保障法奠定了美國(guó)社會(huì)福利制度的立法基礎(chǔ),其后的家庭福利項(xiàng)目與規(guī)模變化都以此為基點(diǎn)。
相較于進(jìn)步時(shí)代①進(jìn)步時(shí)代(progressive era),大約是指19世紀(jì)90年代到20世紀(jì)20年代這段時(shí)期,是美國(guó)國(guó)家建設(shè)歷史上的一個(gè)重要時(shí)期,也是美國(guó)的社會(huì)行動(dòng)和政治改良運(yùn)動(dòng)風(fēng)起云涌的一段時(shí)期,這種行動(dòng)和改良涉及國(guó)家、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的多個(gè)方面。以州和地方為責(zé)任主體的福利供給,羅斯福新政時(shí)期的這一系列舉措標(biāo)志著,聯(lián)邦政府一改對(duì)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事務(wù)不干預(yù)的立場(chǎng),轉(zhuǎn)為多領(lǐng)域、主動(dòng)插手,聯(lián)邦政府扮演各種福利項(xiàng)目的決策者、協(xié)調(diào)者和主要的籌資者角色。與此同時(shí),社會(huì)保障不僅保障工薪勞動(dòng)者,而是擴(kuò)展到他們的家庭。這很大程度上反映和回應(yīng)了公眾的需求,也相應(yīng)地改變著公眾對(duì)于聯(lián)邦政府在社會(huì)福利事務(wù)中角色的心理認(rèn)知,政府深度介入家庭事務(wù)獲得了民意基礎(chǔ)。
(二)以福利立法擴(kuò)張為主要內(nèi)容的家庭政策改革時(shí)期(1945年-1969年)
雖然二戰(zhàn)的爆發(fā)打斷了美國(guó)家庭福利的建設(shè)歷程,但戰(zhàn)后美國(guó)的繁榮依然為社會(huì)福利提供了財(cái)政基礎(chǔ)。在二戰(zhàn)后的二十多年間,美國(guó)政府出臺(tái)了一系列家庭福利項(xiàng)目,同時(shí),《社會(huì)保障法》在此期間進(jìn)行了多次修訂,包括增加“終身殘疾與完全殘疾救助(1950年)、社會(huì)服務(wù)(1951年)”等等,包括家庭福利在內(nèi)的社會(huì)福利受益面不斷擴(kuò)展、受益水平不斷提高。從具體安排來看,與家庭福利最息息相關(guān)的主要包括教育政策、住房保障政策和以促進(jìn)就業(yè)為主要手段的反貧困政策。
首先來看以促進(jìn)基礎(chǔ)教育公平為宗旨的一系列教育福利為例,包括初級(jí)與中級(jí)教育法 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Act, 簡(jiǎn) 稱ESEA)、兒童早期發(fā)展的開端計(jì)劃(Head Start)、高等教育之前的“跨越計(jì)劃”(Upward Bound),等等。其中,開端計(jì)劃是美國(guó)歷史上第一次以法案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聯(lián)邦政府要為貧困的學(xué)前兒童提供補(bǔ)償教育,時(shí)至今日仍然是美國(guó)兒童早期發(fā)展方面的重要政策。兩位民主黨總統(tǒng)的系列措施使得20世紀(jì)60年代成為美國(guó)歷史上各類教育事業(yè)大發(fā)展期,也使得教育福利成為美國(guó)家庭福利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是一系列食品和營(yíng)養(yǎng)保障計(jì)劃,包括為在校學(xué)生提供的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計(jì)劃及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食品券。此段時(shí)間啟動(dòng)的全國(guó)學(xué)校午餐計(jì)劃(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簡(jiǎn)稱NSLP)、食品券項(xiàng)目(Food Stamp)、學(xué)生早餐(Breakfast Program,簡(jiǎn)稱SBP)和學(xué)校牛奶供應(yīng)計(jì)劃等不僅在當(dāng)時(shí)意義重大,且構(gòu)成了當(dāng)前學(xué)齡兒童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最后再看肯尼迪總統(tǒng)“向貧困宣戰(zhàn)”和約翰遜總統(tǒng)“偉大社會(huì)(Great Society)”①偉大社會(huì)時(shí)期(Great Society),是指1960年代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tǒng)提出的施政目標(biāo),該詞源于其1964年發(fā)表的演說,“美國(guó)不僅有機(jī)會(huì)走向一個(gè)富裕和強(qiáng)大的社會(huì),而且有機(jī)會(huì)走向一個(gè)偉大的社會(huì)”。這一時(shí)期通過了許多公共政策,如“向貧困宣戰(zhàn)”、Medicare等,其中有很多項(xiàng)目存續(xù)至今日并發(fā)揮功能。時(shí)期的一系列計(jì)劃,這些計(jì)劃主要通過促進(jìn)貧困人群就業(yè)而非福利救濟(jì)來擺脫貧困,比如1962年《社會(huì)保障法》修正案第5條中首次將日托服務(wù)定義為一種政府向貧困兒童提供的公共服務(wù),以緩解單身母親的就業(yè)或?qū)ふ夜ぷ髋c照顧孩子的兩難選擇。
如果說羅斯福打下了美國(guó)家庭福利的基礎(chǔ),那么約翰遜則是在一個(gè)極短的時(shí)間內(nèi)擴(kuò)展了它的范圍。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總統(tǒng)執(zhí)政期間在公共政策或者福利政策方面的立法數(shù)量之多和范圍之廣前所未有。然而,對(duì)立法的偏好并沒有帶來相應(yīng)的財(cái)政投入,“偉大社會(huì)”時(shí)期的社會(huì)支出并未大幅增加。比起實(shí)施,約翰遜表現(xiàn)出更強(qiáng)的立法意愿和能力,而越戰(zhàn)爆發(fā)也使得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支出的份額被壓縮。
(三)家庭福利在保守與變革之間搖擺時(shí)期(1969年-1993年)
進(jìn)入20世紀(jì)70年代,美國(guó)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出現(xiàn)一個(gè)復(fù)雜的局面。一方面,宏觀經(jīng)濟(jì)面臨嚴(yán)重滯脹、失業(yè)率大幅上升,而60年代的福利擴(kuò)張導(dǎo)致美國(guó)家庭稅收負(fù)擔(dān)增加和政府財(cái)政危機(jī);對(duì)政府福利的依賴導(dǎo)致“福利陷阱”;東西方世界的冷戰(zhàn)進(jìn)入緩和政策下的對(duì)抗時(shí)期,美國(guó)國(guó)內(nèi)對(duì)社會(huì)福利的“社會(huì)主義”屬性的警惕和批判此起彼伏……這些現(xiàn)象和社會(huì)思潮都促使聯(lián)邦政府縮緊社會(huì)福利供給。而另一方面,美國(guó)社會(huì)人口狀況發(fā)生顯著變化,未婚生育增加、單親母親家庭比例猛增、離婚與分居率大幅升高,這一趨勢(shì)在90年代進(jìn)一步發(fā)展,它帶來的兒童和女性貧困問題集中擺在了尼克松和其繼任者面前;與此同時(shí),女性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參與度繼續(xù)攀升,雙職工家庭和單親家庭兒童養(yǎng)育問題也引發(fā)廣泛的社會(huì)關(guān)切。
這種矛盾局面看起來動(dòng)搖著三位相對(duì)保守的總統(tǒng)——尼克松、福特和卡特對(duì)家庭福利供給的態(tài)度。一方面,在此期間,多項(xiàng)圍繞家庭開展的福利項(xiàng)目確實(shí)得到通過和實(shí)施,比如,尼克松執(zhí)政時(shí)期,1965年開始的開端計(jì)劃因其有著極高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度,是極少得到擴(kuò)展的福利項(xiàng)目之一,擴(kuò)展后的該計(jì)劃專門為低收入家庭的學(xué)齡前兒童提供早教強(qiáng)化及其他服務(wù);1972年的面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稅抵免計(jì)劃(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簡(jiǎn)稱為EITC)及1980年的收養(yǎng)援助和兒童福利法案也獲得通過。但另一方面,也有多項(xiàng)重大家庭福利改革因?yàn)閳?zhí)政者自身的保守或者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派之爭(zhēng)等原因,要么沒能通過,要么僅停留于紙面或者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持因而效果打折,其中,尼克松批評(píng)和取消了“偉大社會(huì)”時(shí)期的一系列福利政策,還否決了國(guó)會(huì)兩黨均表示支持的全民日間照料補(bǔ)助和1971年兒童全面發(fā)展立法項(xiàng)目,理由是認(rèn)為此類立法會(huì)破壞家庭制度,將兒童養(yǎng)育的責(zé)任推給機(jī)構(gòu)。
里根總統(tǒng)執(zhí)政是包括家庭福利在內(nèi)的社會(huì)福利總體趨向保守的轉(zhuǎn)折點(diǎn)。里根總統(tǒng)采信供應(yīng)學(xué)派經(jīng)濟(jì)政策,在公共政策領(lǐng)域表現(xiàn)為盡可能減少提供、合并或取消福利計(jì)劃,盡力把福利成本從聯(lián)邦轉(zhuǎn)移給各州,同時(shí)強(qiáng)制福利申領(lǐng)者參與一些義務(wù)工作。喬治·布什當(dāng)選后,家庭福利發(fā)展有進(jìn)有退。收縮方面,作為貧困家庭主要轉(zhuǎn)移支付來源的AFDC項(xiàng)目也隨著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的出臺(tái)而發(fā)生轉(zhuǎn)向,重點(diǎn)幫助貧困的單親母親參加培訓(xùn)以獲得工作,從而擺脫經(jīng)濟(jì)上對(duì)政府福利的依賴。但是,由于這些單親母親通常受教育程度相對(duì)低、缺乏必要的就業(yè)技能,她們只能獲得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作,這就使得她們的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受AFDC資助時(shí)期;1991年,部分女性團(tuán)體等試圖通過參議院提議向嬰兒生產(chǎn)前后的職場(chǎng)父母提供帶薪假期,但保守主義反對(duì)派認(rèn)為此舉對(duì)企業(yè)不公。進(jìn)展方面,1990年兒童照料與發(fā)展基 金(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簡(jiǎn)稱CCDBG)項(xiàng)目通過,這是美國(guó)家庭政策在上世紀(jì)90年代早期的一個(gè)重大突破,它建成了一個(gè)由聯(lián)邦政府向州層面提供資金用于發(fā)展兒童服務(wù)等項(xiàng)目的渠道,這也意味著兒童照料成為聯(lián)邦政府責(zé)任范圍內(nèi)的事項(xiàng)。
(四)家庭政策全面改革時(shí)期(1993年至今)
改革的全面性首先表現(xiàn)為進(jìn)一步促進(jìn)救濟(jì)福利向工作福利轉(zhuǎn)變。1996年,美國(guó)頒布了《個(gè)人責(zé)任與就業(yè)機(jī)會(huì)協(xié)調(diào)法》(簡(jiǎn)稱PRWORA),開始實(shí)行困難家庭臨時(shí)援助(Temporary Assistant to Needy Families,簡(jiǎn)稱做TANF)。該法批準(zhǔn)各州使用自己的綜合補(bǔ)助(block grant)①美國(guó)聯(lián)邦政府對(duì)州和地方政府的經(jīng)費(fèi)補(bǔ)助,主要有適用于特定計(jì)劃的分類專項(xiàng)補(bǔ)助(categorical grants)、適用于廣泛特定功能計(jì)劃的綜合補(bǔ)助(block grants)和未特別指定用途而用于加強(qiáng)各州及地方政府財(cái)政能力與條例地區(qū)間財(cái)政差異的一般收入共享(general revenue sharing)三種方式。援引自:李珍、柯卉兵,《美國(guó)政府間社會(huì)福利權(quán)責(zé)劃分及其轉(zhuǎn)移支付》,《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07年,第5期,第166-169頁。的一定比例來“鼓勵(lì)組成和維持雙親家庭”。聯(lián)邦法律規(guī)定該制度目標(biāo),并對(duì)各州參與該計(jì)劃提出某些要求,理論上各州可自愿決定是否參加該計(jì)劃,但所有州實(shí)際上都加入了。
其次還表現(xiàn)在促進(jìn)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政策方面打破長(zhǎng)期僵局②利益相關(guān)各方對(duì)家庭假法案的爭(zhēng)議焦點(diǎn)主要有三個(gè):(1)休假期限長(zhǎng)短;(2)休假期間是否有報(bào)酬;(3)適用對(duì)象的范圍。,通過了家庭與醫(yī)療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簡(jiǎn)稱為FMLA)。在此之前,全職工作者尤其是全職女性在面臨分娩、養(yǎng)育或家庭緊急醫(yī)療事件時(shí),不能享受假期來照顧家庭。女性團(tuán)體和勞工組織長(zhǎng)達(dá)八年的的奔走在克林頓執(zhí)政時(shí)期產(chǎn)生了作用,最終形成了一個(gè)多方妥協(xié)的、福利水平有限的結(jié)果:雇傭人數(shù)超過50人的雇主,在雇員因合理的家庭和醫(yī)療原因需要離開工作崗位時(shí),要提供最多12星期的假期。作為全世界僅有的三個(gè)沒有有償育嬰假國(guó)家①2014年5月13日,國(guó)際勞工組織(ILO)發(fā)布“雙親就業(yè)狀態(tài)”(The State of Maternity and Paternity at Work)報(bào)告,只有美國(guó)、巴布亞新幾內(nèi)亞和阿曼3個(gè)國(guó)家不保證婦女享有帶薪產(chǎn)假。之一,美國(guó)1993年通過的家庭和醫(yī)療休假法案可以說已經(jīng)具有里程碑意義。
親家庭的奧巴馬當(dāng)選總統(tǒng)后被賦予眾望,在八年任期內(nèi),奧巴馬在家庭政策上的努力包括:積極地推動(dòng)家庭友善的工作方案,簽署總統(tǒng)備忘錄敦促在聯(lián)邦層面實(shí)現(xiàn)至少6周的帶薪產(chǎn)假制度;為L(zhǎng)GBT群體增權(quán),奧巴馬在其第二次就職典禮上提到了同性戀者權(quán)益問題②這是美國(guó)歷史上同性戀一詞出現(xiàn)在總統(tǒng)就職演講中,體現(xiàn)了奧巴馬對(duì)性少數(shù)群體的支持。,他在此方面實(shí)現(xiàn)的承諾則包括聯(lián)邦層面的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將無薪的兒童照料家事假擴(kuò)展至收養(yǎng)了兒童的同性伴侶;采取措施強(qiáng)化家長(zhǎng)尤其是父親責(zé)任,包括為低收入家庭和新手父母提供專家咨詢和家訪服務(wù),奧巴馬夫人還發(fā)起了一系列兒童營(yíng)養(yǎng)和健康促進(jìn)運(yùn)動(dòng);積極開展青少年健康性觀念和性行為教育。
然而,2009年的美國(guó)遭受全球金融危機(jī)導(dǎo)致的經(jīng)濟(jì)衰退重創(chuàng),這也使得家庭福利被殃及。與此同時(shí),隨著在國(guó)情咨文中誓言要在任期內(nèi)解決帶薪家產(chǎn)假和事假問題的奧巴馬總統(tǒng)在結(jié)束任期時(shí)未能如愿,美國(guó)的全職工作者們兼顧工作和家庭的期望再一次落空。此外,盡管2015年美國(guó)最高法院已宣布同性婚姻在美國(guó)全境合法,然而,5:4的投票結(jié)果不僅反映了九位大法官之間的意見分歧,也反映了美國(guó)社會(huì)整體輿論在此問題上的長(zhǎng)期分裂;在實(shí)際執(zhí)行層面,同性締結(jié)婚姻在那些保守的、宗教色彩濃厚的州依然阻力重重。隨著親市場(chǎng)的商人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上臺(tái),本就不甚明朗的美國(guó)家庭政策的走向更加難以預(yù)料。
四、美國(guó)當(dāng)前家庭政策的主要內(nèi)容
(一)家庭政策行政
作為施行“含蓄型家庭政策”(Kamerman& Kahn,1978)的國(guó)家,美國(guó)并未設(shè)立專門負(fù)責(zé)規(guī)劃與實(shí)施家庭政策的部門,它的家庭政策融入福利、稅收和就業(yè)等政策體系之中,有不同政府部門分別管理或聯(lián)合管理(呂亞軍,2010)。在這些并不明確地以提升家庭福祉為宗旨的部門中,健康與人類服務(wù)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簡(jiǎn)稱HHS)承擔(dān)起了與家庭福利服務(wù)提供有關(guān)的主要工作。健康與人類服務(wù)部成立于1979年,是維護(hù)美國(guó)公民健康、提供公共服務(wù)的聯(lián)邦政府行政部門。HHS和各州、地方政府保持著緊密聯(lián)系,許多由HHS資助的服務(wù)實(shí)際上由地方層面或私營(yíng)部門提供。HHS有11個(gè)業(yè)務(wù)部門,其中8個(gè)提供公共健康服務(wù),3個(gè)提供人類服務(wù),其中與家庭福利供給緊密相關(guān)的有兒童與家庭管理局(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簡(jiǎn) 稱ACF)、醫(yī)療保險(xiǎn)和醫(yī)療救助服務(wù)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簡(jiǎn) 稱 CMMS)和老人事務(wù)局(Administration on Aging,簡(jiǎn)稱AOA)。以美國(guó)兒童與家庭管理局為例,其1991年成立時(shí)訂立的目標(biāo)包括:增進(jìn)家庭和個(gè)人能力,建立堅(jiān)實(shí)、健康的社區(qū)支持環(huán)境,以弱勢(shì)群體的的需要為導(dǎo)向,等等,它的主要任務(wù)是為州和有關(guān)機(jī)構(gòu)提供運(yùn)作資金與政策。美國(guó)兒童和家庭局2016年的預(yù)算額為530億美元,是健康與人類服務(wù)部的第二大預(yù)算部門,這筆龐大的財(cái)政支出主要流向困難家庭臨時(shí)援助項(xiàng)目(38%)、開端計(jì)劃(17%)和兒童收養(yǎng)項(xiàng)目(15%)。
(二)美國(guó)當(dāng)前家庭政策的主要項(xiàng)目
1.以減少單親家庭及其貧困問題為目的的政策
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對(duì)婚姻和家庭的影響更多的是間接的,通過規(guī)定家庭和家庭成員的定義,對(duì)家庭成員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進(jìn)行明確,以減少單親家庭數(shù)量同時(shí)減緩單親家庭兒童貧困程度。此類間接家庭福利項(xiàng)目包括:(1)兒童撫養(yǎng)費(fèi)強(qiáng)制征收政策(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簡(jiǎn)稱CSE),國(guó)會(huì)通過兒童撫養(yǎng)費(fèi)執(zhí)行制度,聯(lián)邦據(jù)此要求各州建立兒童撫養(yǎng)費(fèi)執(zhí)行機(jī)構(gòu),以幫助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收到兒童撫養(yǎng)費(fèi),避免因離異導(dǎo)致的父母經(jīng)濟(jì)撫養(yǎng)責(zé)任缺失。(2)以健康婚姻計(jì)劃(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簡(jiǎn)稱HMI)為代表的婚姻促進(jìn)項(xiàng)目,這項(xiàng)計(jì)劃的潛在假設(shè)是,即便是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的經(jīng)濟(jì)狀況也可能隨著父母締結(jié)婚姻改善。在健康婚姻倡議計(jì)劃下,青少年學(xué)生、未婚伴侶、訂婚伴侶和已婚夫妻等被分成不同類型開展活動(dòng),通過媒體宣傳、學(xué)校教育、典型示范、社區(qū)服務(wù)等多樣化的方式,促使他們建立起維持健康婚姻和健全家庭的理念、知識(shí)和技巧(胡杰容,2014)。(3)開展對(duì)青少年的全面性教育,減少未婚生育,比如青少年家庭生活(Adolescent Family Life ,簡(jiǎn)稱為AFL)項(xiàng)目,這些項(xiàng)目旨在通過培育青少年禁欲的價(jià)值觀、提供預(yù)防婚外懷孕生育的信息和工具、樹立婚內(nèi)忠誠(chéng)的一夫一妻制關(guān)系規(guī)范等方式,推遲與節(jié)制青少年的婚前性行為,避免未婚媽媽大幅出現(xiàn),同時(shí)也減少因不健康性行為等導(dǎo)致的性傳播疾病。
2.與家庭照料者支持相關(guān)的福利政策
與家庭照料相關(guān)的社會(huì)福利政策主要圍繞對(duì)家庭照料者的支持展開。(1)全國(guó)性家庭照料者支持項(xiàng)目(National Family Caregiver Support Program,簡(jiǎn)稱NFCSP),這是一項(xiàng)為家庭以及其他非正式照料者提供多種支持的計(jì)劃,以緩解他們?cè)诰蛹艺樟霞彝コ蓡T時(shí)的經(jīng)濟(jì)、信息和心理等各種困難,從而避免或者延遲對(duì)機(jī)構(gòu)照料的需求。NFCSP提供的支持主要有三類:提供協(xié)助性服務(wù)的渠道、咨詢和培訓(xùn)服務(wù)以及喘息照料服務(wù)。(2)兒童和被撫養(yǎng)人照料減免計(jì)劃(Child and Dependent Care Credit,簡(jiǎn)稱做CDCC),該計(jì)劃面向有13歲以下兒童及其他不能自理的撫養(yǎng)人的家庭,用于減少撫養(yǎng)者因?yàn)楣ぷ骰驅(qū)ふ夜ぷ鞫仨氈Ц兜膬和樟腺M(fèi)用負(fù)擔(dān)。(3)親職假政策,截至2016年,已經(jīng)有四個(gè)州——加利福尼亞、新澤西、羅德島和紐約通過了有償?shù)募彝ゼ儆?jì)劃,還有一個(gè)州——華盛頓州雖然早就通過了有償家庭假法案,但由于缺乏資金一直未執(zhí)行。
3.有兒童的家庭收入支持項(xiàng)目
此類項(xiàng)目主要包括:(1)兒童稅收抵免計(jì)劃(Child Tax Credit,簡(jiǎn)稱為CTC),CTC是美國(guó)當(dāng)前最接近于普惠制兒童津貼的福利計(jì)劃,它用于減輕有兒童的家庭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簡(jiǎn)單來說,如果納稅人有一個(gè)符合條件的兒童,那么他/她可以減免一部分聯(lián)邦所得稅。(2)收入稅抵免計(jì)劃(EITC),面向有孩子的中低收入工作者的可返還的稅務(wù)優(yōu)惠,是一種將社會(huì)福利與所得稅相結(jié)合的制度。除了聯(lián)邦層面的EITC之外,美國(guó)還有多個(gè)州推出了自己的EITC政策,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稅收減免政策的福利性,EITC已經(jīng)成為美國(guó)支出最龐大的社會(huì)福利制度之一。(3)其他面向因父母失業(yè)等原因造成的家庭經(jīng)濟(jì)困窘的收入補(bǔ)償項(xiàng)目,主要是困難家庭臨時(shí)援助計(jì)劃,通過提供現(xiàn)金援助和支持服務(wù)、以支持育有子女的困難家庭,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社會(huì)援助。
4.與兒童養(yǎng)育有關(guān)的家庭政策
此類項(xiàng)目主要包括兒童早期發(fā)展支持和兒童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兩類計(jì)劃:(1)開端計(jì)劃為低收入家庭0-5歲兒童提供學(xué)齡前服務(wù),促進(jìn)其全面發(fā)展。根據(jù)當(dāng)?shù)厣鐓^(qū)的不同需求,開端計(jì)劃與兒童早期開端計(jì)劃提供多種服務(wù)模式,許多項(xiàng)目以中心或?qū)W校作為服務(wù)推廣基點(diǎn),還有的項(xiàng)目則利用兒童福利中心或是家庭托管所開展服務(wù)。有的項(xiàng)目制指定成員每周為兒童提供上門服務(wù),與家長(zhǎng)共同合作,完成兒童早教工作。(2)兒童照料和發(fā)展基金(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Fund, 簡(jiǎn)稱CCDF),該基金為努力兼顧工時(shí)制度的兒童及其家庭提供高質(zhì)量的發(fā)展支持,并讓其參與適合家庭需求的兒童照料計(jì)劃,同時(shí)幫助兒童在學(xué)校取得好的表現(xiàn)。兒童照料和發(fā)展基金還通過提高護(hù)理質(zhì)量來支持兒童健康發(fā)展,并通過支持兒童照料許可、制定質(zhì)量改善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來幫助項(xiàng)目達(dá)到更高標(biāo)準(zhǔn),并為幼兒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培訓(xùn)和教育支持。兒童照料和發(fā)展補(bǔ)貼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補(bǔ)貼以幫助獲得兒童照料,以便家長(zhǎng)可以從事或參加教育或培訓(xùn)活動(dòng)。(3)兒童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和保障系列計(jì)劃,有婦女、嬰兒和兒童營(yíng)養(yǎng)項(xiàng)目(WIC)、校園早餐項(xiàng)目和校園午餐項(xiàng)目,等等。
五、當(dāng)前美國(guó)家庭政策的原則和特點(diǎn)
(一)政策決策方面,政府重視立法、各方多元參與
從政府決策的動(dòng)機(jī)角度看,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也走過了一個(gè)被動(dòng)型和壓力性決策走向主動(dòng)型和發(fā)展性的歷程。其中,立法先行是包括美國(guó)家庭福利在內(nèi)的社會(huì)福利政策的重要規(guī)律。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立法和改革決策相互銜接,前者引領(lǐng)和推動(dòng)后者。相關(guān)立法中都具體地規(guī)定公民的社會(huì)福利權(quán)利和義務(wù),同時(shí)依據(jù)變化的外部環(huán)境對(duì)法律進(jìn)行相應(yīng)的修訂使之適應(yīng),并通過不同層級(jí)的法律約定家庭福利和服務(wù)的傳遞方式等內(nèi)容,增強(qiáng)家庭政策的透明度和操作性。羅斯福新政時(shí)期開始聯(lián)邦政府逐漸主導(dǎo)確立并完善了家庭政策立法體系,同時(shí)輔之以全國(guó)層面和對(duì)州和地方家庭政策項(xiàng)目的資金支持,但美國(guó)家庭政策決策和實(shí)施過程體現(xiàn)出明顯的多元參與特點(diǎn):學(xué)術(shù)界以持之以恒的研究發(fā)現(xiàn)個(gè)人和家庭福祉出現(xiàn)了哪些問題,引起公眾討論和決策者關(guān)注,同時(shí)提出政策建議;社會(huì)組織和社會(huì)工作者通過政府購(gòu)買等形式提供家庭福利服務(wù),同時(shí)透過福利服務(wù)實(shí)踐實(shí)現(xiàn)反向的政策倡導(dǎo)和改進(jìn);女性團(tuán)體、工會(huì)、企業(yè)等利益相關(guān)團(tuán)體則為各自代表的利益相關(guān)者在立法等事務(wù)上博弈。
(二)政策目的方面,以維持和擴(kuò)展家庭功能為主
美國(guó)的家庭政策領(lǐng)域一直以來就充斥著政治的和倫理的爭(zhēng)議,但是在家庭政策的目的這一問題上,美國(guó)政府、公眾、學(xué)術(shù)界、市場(chǎng)部門和其他利益相關(guān)團(tuán)體一定程度上達(dá)成了一個(gè)基本共識(shí),即美國(guó)家庭政策總體而言主要回應(yīng)的是家庭在社會(huì)變遷中弱化和失去某些傳統(tǒng)的功能這一問題。作為一個(gè)總體而言崇尚自由主義、對(duì)政府介入家庭事務(wù)保持警惕的國(guó)家,美國(guó)的公共家庭政策重點(diǎn)在于在家庭規(guī)模、結(jié)構(gòu)和內(nèi)部分工發(fā)生變化后,由制度搭建起安全網(wǎng)兜住家庭功能弱化之后落入困境的人群,同時(shí)發(fā)展家庭的某些功能增強(qiáng)家庭保障其成員的能力,而非有意維持某種特定的家庭形式或以公共政策替換家庭。
因?yàn)槊绹?guó)家庭政策的非系統(tǒng)性和隱性的特點(diǎn),它們?cè)跒榧彝ピ瞿芎唾x權(quán)之外還有一系列間接的政策目標(biāo),或者說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huì)公平、社會(huì)輿論和公眾意識(shí)等領(lǐng)域,實(shí)現(xiàn)了某些正的外部性。具體包括:(1)增進(jìn)性別平權(quán),主要是減少女性就業(yè)的歧視性條件、提升女性在就業(yè)和家庭之間的自主選擇權(quán),減少女性貧困;(2)促進(jìn)社會(huì)包容,包括對(duì)不同形式和結(jié)構(gòu)的家庭、LGBT群體、移民家庭、兒童和老人等社會(huì)中的少數(shù)或弱勢(shì)社群的理解和包容,減少基于種族、性取向、出生地、婚姻狀況、年齡等因素的社會(huì)排斥和仇恨;(3)加大人力資本和社會(huì)投資,主要包括為孕產(chǎn)期婦女提供育嬰咨詢和營(yíng)養(yǎng)服務(wù)、為學(xué)前兒童提供發(fā)展性服務(wù)、為學(xué)齡兒童提供營(yíng)養(yǎng)補(bǔ)充計(jì)劃、為殘疾兒童等特殊需要兒童提供可融入社會(huì)的服務(wù)等項(xiàng)目,通過提升兒童和女性的質(zhì)量,為整個(gè)社會(huì)的未來投資人力資本。
(三)政策對(duì)象具有選擇性,家庭福利供給中的“兒童優(yōu)先”取向明顯
美國(guó)大部分家庭福利都是選擇性的,即只有福利對(duì)象需要滿足收入、身心狀況、居住條件等一系列資格才能獲取公共政策的支持。從上文對(duì)美國(guó)家庭領(lǐng)域的發(fā)展變化和公共政策的回應(yīng)可以看出,從20世紀(jì)30年代美國(guó)家庭福利建制之始,以“家庭中的個(gè)人(people in family)”如老人、兒童和殘疾人等為主要的政策對(duì)象。20世紀(jì)60年代后,家庭政策的對(duì)象重點(diǎn)逐漸轉(zhuǎn)為“關(guān)系中的家庭”,如單親媽媽為戶主的家庭和雙職工家庭,主要考慮的也是此類家庭的兒童照料和經(jīng)濟(jì)安全問題。在各類福利服務(wù)對(duì)象的資格條件規(guī)定中,往往是社會(huì)中最不幸的群體才能獲得這些服務(wù),普遍性家庭福利只在特定領(lǐng)域偶有體現(xiàn)。在這些被選中重點(diǎn)關(guān)照的群體中,兒童又被置于最優(yōu)先的地位,兒童經(jīng)濟(jì)安全、營(yíng)養(yǎng)保障、兒童青少年性教育和兒童早期發(fā)展項(xiàng)目等都是家庭福利中支出較大的領(lǐng)域。
(四)福利內(nèi)容和形式上,重服務(wù)和實(shí)物支持、推崇工作福利
美國(guó)當(dāng)前形成的是分散于多部門的多層次家庭政策體系,總的來說以服務(wù)和實(shí)物類補(bǔ)助為主,重視為有需要的家庭和個(gè)人提供信息咨詢、服務(wù)提供、就業(yè)培訓(xùn)等項(xiàng)目,而盡量避免直接為政策對(duì)象提供現(xiàn)金補(bǔ)貼。即便是經(jīng)濟(jì)支持性項(xiàng)目,也設(shè)置各種條件避免這種轉(zhuǎn)移支付變現(xiàn),比如開支龐大的食品券項(xiàng)目和兒童營(yíng)養(yǎng)保障項(xiàng)目額服務(wù)券不可提現(xiàn)和轉(zhuǎn)讓,而兒童稅抵扣和低收入稅收優(yōu)惠等項(xiàng)目雖然是直接的收入補(bǔ)償項(xiàng)目,但它們都要求政策對(duì)象參與一份可持續(xù)的工作。從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些舉措都意味著美國(guó)家庭政策的取向是盡量避免福利陷阱,作為一個(gè)有著自由主義偏好的國(guó)家,美國(guó)聯(lián)邦政府為福利改革而進(jìn)行的法律和制度變革的直接目的,通常都是要減少個(gè)人和家庭對(duì)政府提供的援助項(xiàng)目的依賴、并最終實(shí)現(xiàn)自立。
六、小結(jié)及啟示
家庭政策本身是一個(gè)充滿政治和倫理爭(zhēng)議的議題,美國(guó)家庭福利政策之所以形成了碎片化的基本形態(tài),主要在于以下重要問題爭(zhēng)議不絕:家庭的界定問題,即家庭的形式、結(jié)構(gòu)和功能等是否應(yīng)有特定的規(guī)定;公共家庭政策的必要性問題,家庭失去或弱化的某些功能是否應(yīng)該由公共部門來負(fù)責(zé),這涉及到歸罪于誰和公私領(lǐng)域的邊界問題;政策優(yōu)先性問題,即家庭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眾多議題中,哪些問題(人口問題、婚姻問題、福利問題、社會(huì)性別問題等)和哪些群體(依據(jù)身心條件還是經(jīng)濟(jì)水平還是種族狀況來分,等等)具有何種程度的優(yōu)先性;福利供給責(zé)任分配問題,即各級(jí)政府、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分別在政策供給中扮演何種角色的問題;公共政策的外部性問題,即社會(huì)政策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規(guī)律、與傳統(tǒng)價(jià)值倫理、與政黨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
作為社會(huì)的基本單元,家庭在中國(guó)一直以來扮演人口再生產(chǎn)、養(yǎng)老扶幼、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重要角色,同時(shí)間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控制和穩(wěn)定。但是,這些功能發(fā)揮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隨著計(jì)劃生育政策變革和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發(fā)展,年輕一代中國(guó)夫妻和父母的流動(dòng)性和思想的多元性等也使得婚姻和家庭的組成方式日趨多元,家庭形式及其功能的變化從未停止向后現(xiàn)代社會(huì)過渡。上述爭(zhēng)議點(diǎn)的充分討論和考量是美國(guó)制定家庭福利政策的前提,其中一些也是中國(guó)政府和社會(huì)需要重視的。盡管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觀、人口和家庭形態(tài)等背景迥異,美國(guó)已經(jīng)實(shí)行的家庭福利政策之中依然有許多可供中國(guó)借鑒之處,如予以家庭照料者尤其是職場(chǎng)女性照料者必要的支持、兒童優(yōu)先以及立法與服務(wù)并行,等等。
參考文獻(xiàn)
[1]何歡,《美國(guó)家庭政策的經(jīng)驗(yàn)和啟示》,《清華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1期,第147-156頁。
[2]胡杰容,《美國(guó)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趨勢(shì)及其啟示》,《青海社會(huì)科學(xué)》2014年,第1期,第85-90頁。
[3]黃安年,《當(dāng)代美國(guó)政府社會(huì)福利保障政策的歷史演變》,《史學(xué)月刊》,1996年,第1期,第97-103頁。
[4]黃安年,《克林頓政府改革美國(guó)家庭福利保障的對(duì)策》《美國(guó)研究》,1997年,第2期,第87-104頁。
[5]黃安年,《美國(guó)政府的住房福利保障政策——從羅斯福新政到約翰遜“偉大社會(huì)”時(shí)期》,《山東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98年,第4期,第13-17頁。
[6]黃安年,《當(dāng)代美國(guó)的社會(huì)保障政策》,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8年。
[7]李珍、柯卉兵,《美國(guó)政府間社會(huì)福利權(quán)責(zé)劃分及其轉(zhuǎn)移支付》,《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07年,第5期,第166-169頁。
[8]呂亞軍,《戰(zhàn)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綜述》,《河北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 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 年,第5期,第12-16頁。
[9]瑞貝卡·魯倫,《美國(guó)的家庭政策——“自由國(guó)土”上的精英文化價(jià)值觀障礙》,金一虹、史麗娜編,《中國(guó)家庭變遷和國(guó)際視野下的家庭公共政策研究》,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年。
[10]王三秀,《美國(guó)福利權(quán)保障立法價(jià)值重心的轉(zhuǎn)移及其啟示》,《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7-144頁。
[11]許寶友,《美國(guó)社會(huì)福利制度發(fā)展和轉(zhuǎn)型的政治理念因素分析》,《科學(xué)社會(huì)主義》,2009年,第1期,第141-146頁。
[12]嚴(yán)敏、朱春奎,《美國(guó)社會(huì)福利制度的歷史發(fā)展與運(yùn)營(yíng)管理》,《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4年,第4期,第88-94頁。
[13]姚建平、朱衛(wèi)東,《美國(guó)兒童福利制度簡(jiǎn)介》,《青少年犯罪問題》,2005年,第5期,第57-61頁。
[14]伊萊恩·泰勒·梅、傅琳,(2013)《冷戰(zhàn)時(shí)代的美國(guó)家庭》,《復(fù)旦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3年,第3期,第34-41頁。
[15]張永健,《家庭與社會(huì)變遷——當(dāng)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動(dòng)向》,《社會(huì)學(xué)研究》,1993年,第2期,第97-10頁。
[16]鄭麗嬌,《美國(guó)「家庭與醫(yī)療假法」政策形成過程之研究》,《政治科學(xué)論叢》,1999年,第11期,第265-294頁。
[17]A·桑頓、L·揚(yáng)-德馬斯,《美國(guó)四十年家庭觀念的變化趨勢(shì)——從20世紀(jì)60年代到90年代》,胡玉霞摘譯,劉汶蓉校,《婚姻與家庭雜志》,2001年,第63期。
[18]Anderson, J. R.& Wilde, J. L. 《美國(guó)的家庭政策概述》,中國(guó)家庭研究網(wǎng),2008年,原文鏈接:http://www2.sass.org.cn/familystudy/articleshow.jsp?dinji=628&artid=62482&sortid=17 76。
[19]Andrew J. Cherlin (1985). The Changing American Family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2), 495-497.
[20]Berkowitz, E. (1994). The undeserving poor: 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by michael b. katz.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9(3), 385-386.
[21]Bhushan, N. (2012). Work-famil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J.l. & Pub.poly.
[22]Blank, R. M. (2002). Evaluating welfar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40), 1105-1166.
[23]Boling, P. (2002). Redefining family policy:implic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Mathematics, 5(4),674-690.
[24]Carlson, L., & Harrison, R. (2010). Family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30(4), 320-330.
[25]Cascio, E., & Reber, S. (2013). The k-12 education battle. Legacies of the War on Poverty, 77.
[26]Dzodin, H. C. (1980),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Familie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A Report to the Association of Family Conciliation Courts. Family Court Review, 18: 1–8. doi:10.1111/j.174-1617.1980.tb00047.x.
[27]Gauthier, A. Family Polici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s There Convergence? [J].Population, 2002.
[28]Gerson, K. (2010).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How a new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family, work, and gender 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Giele, J. Z. (2013). Family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safety net.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30]Heckman, J. (2011). The American Family in Black & White: A Post-Racial Strategy for Improving Skills to Promote Equality. Daedalus, 140(2), 70-89.
[31]Jansson, B. S. (1997). The reluctant welfare state: American social welfare policies--past,present, and future. Pacific Grove, Calif: Brooks/Cole Publishing.
[32]Jennifer M. Randles ?. (2012). Marriage promotion policy and family inequality. Sociology Compass, 6(6), 671–683.
[33]Kamerman S & Kahn A. 1978. Family Policies: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14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47.
[34]Lichter, D. T. (2001). Marriage as public policy.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Pew Center, (2015). Parenting in America,Retrieved from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17/1-the-american-family-today/#
[35]Popenoe, D. (1993). American Family Decline, 1960-1990: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5(3),527-542.
[36]Smock, P. J., & Wendy D. Manning. (2004).Living together unmarried in the united states:demographic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for family policy. Law & Policy, 26(1), 87–117.
[37]Theodora Ooms. (1990). Families and government: implementing a family perspective in public policy. Social Thought, 16(2), 61-78.
[38]Rebecca L. Corrow.(2004) . Shaping the American Family by Inac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The Fami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1788-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