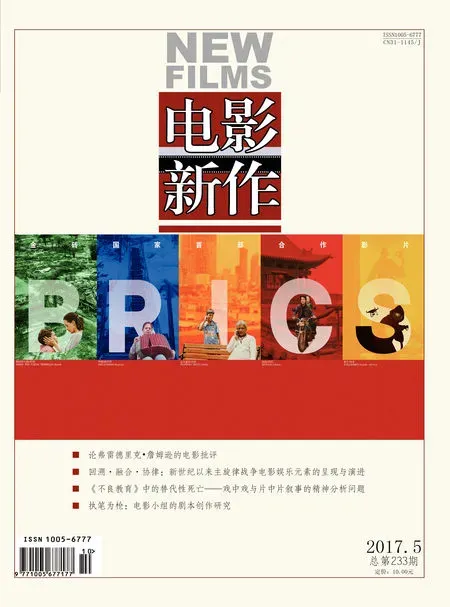徐浩峰武術電影的作者化敘事
高金利
武俠電影作為中國電影史上最成熟也最具代表性之一的類型,已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在美學形態、敘事策略等方面,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形態。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時代環境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武俠電影的樣態發生了一定的轉向。特別是新世紀以來,以《臥虎藏龍》《英雄》為代表的一批“武俠大片”,以名導、明星、大制作、打破類型邊界等多種方式相結合,對傳統武俠電影進行重構,體現出中國電影界尋求武俠電影新形態,突破發展瓶頸的探索性努力。然而,由于一時間創作觀念過于多元且批評話語對其探索意義的理論總結嚴重滯后,這一階段的“新武俠”創作并未能為華語武俠電影的發展指明方向。在21世紀初的“武俠熱”風潮漸息之后,武俠片創作一度式微,只有極少數武俠電影能夠取得不錯的成績,這與武俠電影在中國電影史上曾經占據的位置嚴重失衡。
2011年,徐浩峰以電影導演處女作《倭寇的蹤跡》為中國武俠片帶來耳目一新的“紀實”氣象,重新提振了電影界對于武俠電影的興趣和期望。基于“在東方世界里,械斗一定是大于拳打腳踢的,兵器是一個習武之人尊嚴的象征”①的世家觀念,徐浩峰熱衷于拍攝中國冷兵器時代的各種兵器,以電影影像構筑中國武術的“兵器譜”。②徐浩峰依循日本武士題材電影傳統,將這類拍攝各類兵器械斗的影片稱為“劍戟片”(劍與戟分別為短兵器和長兵器的統稱,二者概括了所有冷兵器)。③
本文運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通過分析徐浩峰執導的三部電影《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所表現出的共同的敘事策略和敘事手法等特色,以求探究徐浩峰電影的反類型特征,確認其作者化風格。對于“武俠電影”的類型定義,學界尚沒有絕對的標準,廣義上的“中國武俠電影”,作為一切以表
現武術與武林人士為主的一類電影的統稱,包含許多特定的次類型,例如大陸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武俠神怪片、新時期的武打片和武術片等,以及港臺地區的表現古代兵器打斗的武俠片和表現近代拳腳打斗的功夫片。④而徐浩峰電影所體現出的特征,明顯有別于傳統武俠電影和拳腳功夫電影,且導演有意識對傳統該類型影片注重觀賞性、主題內涵單一的特點進行反撥,而注重展示中國武術及其兵器的精神內涵、思想價值,故本文選擇以“武術電影”來指稱徐浩峰的電影作品。本文中作為一個成熟而發展完備的類型所談到的“武俠電影”,指代廣義上的包含武俠片和功夫片在內的所有涉及武術打斗的類型影片。
一、對經典敘事母題的揚棄
武俠文化源起于中國民間,“俠客”在傳統俠義小說或武俠文學中,通常活躍在與“廟堂”相對的“江湖”,即在官府體制管轄范圍之外的地域。“江湖”的概念絕不僅僅是行政上的,而更多的是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它意味著在此領域內,“俠客”們以高超的武功和高尚的道德品質,重新建立一套不同于官方統治和律法行為準則的社會秩序。因此,傳統的武俠敘事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以英雄敘事作為基本母題。
在武俠電影創作方面,無論是早期武俠神怪片的經典正邪對立模式,還是“黃飛鴻”電影的任俠模式、李小龍電影的“敵外”模式,主人公無不作為正義的代表,完成鋤強扶弱、懲惡揚善,甚至重塑民族尊嚴的道德任務。及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娛樂化時代,以成龍電影為代表的功夫喜劇電影仍然致力于塑造小人物中的平民化英雄。新世紀的華語電影“武俠熱”,同時也是對于“英雄”形象的再定義,《英雄》《天地英雄》等作品僅從片名上就可看出張藝謀等名導重塑華語電影英雄形象的創作意圖。對于華語武俠電影中“英雄”形象的分析,陜西師范大學孫昊明的碩士論文⑤有較為系統的論述。
然而,在“后現代”消費時代,曾經盛產英雄的中國武俠電影也呈現出了消解英雄甚至反英雄的趨勢。《投名狀》《繡春刀》等影片,開始將武林人物與廟堂政治相結合,呈現出江湖式的俠客在龐大復雜的政治體制下的渺小和無力,初見消解傳統英雄的意向。徐浩峰的三部電影作品,重新將人物投入民間江湖的土壤中,但卻同樣表現了他們在強大的既定規則、紛亂的時代背景中的彷徨和無奈。甚至《師父》中由廖凡飾演的主人公師父陳識,最初是以陰謀家的形象出現的,完全顛覆了傳統深刻浸潤父權文化的武俠作品中“德高望重”的“師父”形象,表現出明顯的反英雄傾向。

圖1.《箭士柳白猿》
傳統武俠電影中的“英雄”,由于產生于儒家文化的意識形態土壤,必然要追求“忠孝兩全”的完美形象。古裝刀劍武俠電影中,因為俠客浪跡江湖,遠離官場,以“忠君”為核心的主題時常被以“盡孝”為核心的復仇主題所取代。⑥民國以來,面對內憂外患的歷史和現實,社會上掀起“習武救國”的風潮,在近代拳腳功夫片中,以霍元甲、陳真和李小龍電影中的主人公為代表的“武林英雄”,通過擊敗外國武士的方式弘揚中華武術、樹立民族自信,完成了武俠電影人物“大忠”形象的塑造。在這類傳統武俠電影中,“忠”與“孝”的形象通常通過比武行為建構起來,主人公通過比武完成鋤強扶弱或重塑民族尊嚴的敘事任務。徐浩峰的電影作品,繼承了傳統的復仇、敵外、比武等經典母題,但同時三部影片又無不對這三種母題的意義進行了消解,使之無法完成“英雄敘事”。
(一)“復仇”母題
影片《箭士柳白猿》涉及兩次復仇,分別為混血女二冬為父報仇和柳白猿為姐姐報仇。柳白猿最終并未殺死強奸姐姐的地主王老爺,而是以向水中射箭的方式完成自省(水等同于鏡子,代表著“自省”的文化意義。影片中提到的“射回來的箭”可理解為射向自己內心的自省之箭),認識到自己對姐姐的傷害可能比王老爺更大。由此復仇的對象成為復仇者本人,復仇行為實際上并未完成,而成為一次自我反思。二冬為父報仇,由于與懷有政治目的的軍官過德誠(趙崢飾)合作,而具有政治意義。以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式⑦分析,二冬通過發布復仇“命令”,將復仇行為主體的身份轉移給接受“命令”的柳白猿。但復仇是一種私人行為,柳白猿對于復仇行為客體楊乃興(馬君飾)并無直接情感上或利益上的對立,因而不具備強烈的復仇欲望,其行為的目的性被極大地削弱。而二冬的復仇計劃在另一重意義上卻等同于過德誠的政治刺殺陰謀,使得復仇行為被極大地遮蔽。此外,二冬的混血身份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在內憂外患的民國時代背景下,一個“異族”女性對中國軍政界人士的復仇行為,實際上象征著一種民族侵犯,使得復仇行為的正義性隨之降低。由此,柳白猿替二冬復仇,在行為動機和合法性方面均被削弱。加之柳白猿最終放棄了刺殺行為,卻轉而殺死了謀劃這場刺殺的過德誠,使得這場復仇最終走向了“為復仇對象復仇”的反諷式結局,復仇的敘事意義也被消解。柳白猿作為行動的失敗者和放棄者,始終沒有完成“英雄”行為。
《師父》中的復仇行為,在行動主體的選擇上,即完成了對傳統的反叛。上文提到,賈磊磊認為,傳統武俠電影中的敘事母題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盡孝”倫理道德,這與大量武俠作品中的復仇行為表現在為父母、師父等父輩人物報仇的現象相符。但《師父》中的復仇卻表現為師父為徒弟復仇,直接剝奪了該行為的“盡孝”倫理。影片中的“盡孝”體現在陳識北上以拳揚名(“我沒給家人盡過責,也沒給師父盡過責。”“因為拳法揚名,成敗都快,就想先報師恩,再整家業。”),但此行為卻以陰謀的形式展開,消解了其道德正義。
《倭寇的蹤跡》中,于承惠飾演的第一高手裘冬月,有過一瞬間的邪念,意圖設計使通奸的夫人和護衛自相殘殺,這可以看作一次復仇行為。但該行為很快被裘冬月自己終止,復仇行為成為一次邪念的閃現,而其失敗意味著善念的復生,這一設計同樣使復仇行為不具備正義立場。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三部影片中的復仇行為,都不具備塑造英雄的功能,甚至起到消解英雄的客觀效果。
(二)“敵外”母題
《倭寇的蹤跡》所敘述的故事,發生在倭寇已被剿滅,抗倭將領俞大猷、戚繼光逝世之后,作為敵對異族勢力的“倭寇”始終不曾真正出現,反而是戚家軍遺族、抗倭軍士被當作倭寇進行剿殺和驅逐,而本應負責對抗外敵的海盜防官兵,身處“和平時期”,守備松懈、戰斗力低下。海盜防首領夢寐以求的“鐵鎧甲”本應是軍功的象征,異族舞女原本象征著異族勢力的威脅,但最終沒有任何真正的入侵,海盜防“無處立功”,無法得到皇帝賞賜的鐵鎧甲,卻只能接受異族舞女的饋贈(“皇上不給你,我給”),形成荒誕的反諷。“和平”的時局使流落民間的戚家軍抗倭“英雄”主人公梁痕錄(宋洋飾)基于“戰時思維”的各種測試顯得不合時宜,更無從樹立英雄的形象。
《師父》中的異族危機表現在白俄舞女的“肌肉運用之妙近乎拳理”,而中華武術界卻囿于門戶之見,拳術秘傳,導致“洋人早晚研究出來,我們的子孫要挨打”。但由于這種擔憂屬于“未來”,白俄舞女作為尋求娛樂和消遣的對象,無法與中華民族、武術界和主人公形成沖突,最終只能由金士杰飾演的鄭山傲“阻止不了洋人破解我們的拳術,就把洋人娶了”的荒誕方式取得對抗異族的“勝利”,這顯然不是傳統“英雄”的行為邏輯。
在《箭士柳白猿》中,除了上文分析的混血女復仇的行為,沒有其他的異族對抗類情節,中華民族與異族之間的沖突主要體現在不同文化元素之間突兀的并置,例如楊乃興的道士服和手風琴、門口小巷上的教堂與寺廟,以及柳白猿落水被二冬救回后,身著西方教士服裝立于東方佛像之前。這些造型元素上的沖突,象征著一定歷史時期內西方文化對本土文化的沖擊,但卻不在敘事進程之內,也就無從在敘事中發展和解決,成為溫和但卻不可調和的矛盾,圍繞在主人公周圍。主人公無法克服他們,也就無從構建“英雄”的行為模式。
(三)“比武”母題
《箭士柳白猿》中,楊乃興被殺后,柳白猿與于承惠飾演的匡一民有一場比武,幾乎不具有敘事上的意義,而是“為比武而比武”。這種敘事“閑筆”式的比武,在徐浩峰的三部電影作品中多次出現,同樣表現出與傳統武俠電影極大的不同。
在傳統武俠電影中,比武作為一個經典母題,常常承擔著鋤強扶弱或重塑民族威嚴的敘事功能。而在《倭寇的蹤跡》中,梁痕錄輸掉了與裘冬月的比武,卻仍然被允許開宗立派;在《箭士柳白猿》中,過德誠與匡一民以比武賭楊乃興死活,過德誠輸掉比武卻仍然部署暗殺了楊乃興;在《師父》中,徒弟按規矩打贏八家武館,卻被武行與軍界聯合驅逐。在徐浩峰的電影里,很多時候,比武在敘事上的作用既非目的性的,如主人公為了比武而習武,最終完成自我實現;也非功能性的,如通過比武達成某種目的。比武的勝利或失敗,在徐浩峰的電影中,常常無法影響情節發展或改變主人公的處境。因此,主人公通常也無法通過比武的勝利構建英雄形象。
由此,武俠電影中的三個經典母題復仇、敵外和比武,在徐浩峰的電影中被一一消解,最終否定了在傳統武俠電影中幾乎處于文化核心地位的英雄敘事母題。
在《箭士柳白猿》中,匡一民在要求和柳白猿比武時,有一句自我評價:“我自己就是個無才無福的人,我有的只是武功。”這幾乎可以理解為徐浩峰作品一以貫之的主題——真正的武術不同于傳統武俠電影中的假想,武術既無從救國,也很少能造就出真正的英雄人物,甚至不能改變事態的發展——這一主題無疑構成了徐浩峰電影作品一種迥異于傳統的作者化表達。
二、對類型敘事結構的超越
關于類型電影的定義,通常涉及某些固定的特征和敘事模式。作為一種類型所出現的傳統武俠電影,也具備這種模式化特征,其中最為普遍認可的莫過于其正邪對立模式。學者倪駿認為,武俠電影“最簡單最基本的模式是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起沖突,并以‘打斗’的方式解決沖突”,而諸如復仇、報恩等情節,都是編導“為正反兩派人物設計開打的理由”。⑧學者劉郁琪也認為,盡管在新浪潮武俠之后,如徐克的《新龍門客棧》、李安的《臥虎藏龍》等新武俠影片通過引入第三方甚至第四方勢力,將沖突的形態由二元擴展至多元,但“對立沖突本身的存在,卻是一個永遠不變的事實”。⑨但是,在徐浩峰的電影中,卻從來不存在這種正邪對立模式。無論是《倭寇的蹤跡》中的“打過四個門口”,還是《師父》中的“踢過八家武館”,比武行為都并不意味著“對抗”,因為主人公的最終目的不是打敗對方,而是尋求被對方“接納”。郄佬所統轄的“四大門”和鄭山傲領導的天津武行,其中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絕對的“壞人”,而是代表著一種江湖中的“體制”。主人公與其對抗,不是正邪不兩立的傳統沖突模式,而是展現了個人與體制之間的關系;其結果也并非傳統模式的“邪不勝正”,而是主人公被“體制”所接納或被其驅逐。《箭士柳白猿》中阻礙主人公柳白猿行動的高手匡一民,顯然也不具備“壞人”的特征,柳白猿的“刺殺”行為與他的“保護”職責相沖突,是一種“各為其主”式的觀念沖突,而非善惡對立的道德沖突。
關于武俠電影中的沖突類型,劉郁琪在《中國武俠電影的雙序列敘事結構及其文化意味》中有著較為系統的分析。文章認為,中國武俠電影中普遍存在雙序列敘事結構:一個序列講述正反力量的對立沖突,另一序列講述正面主人公的個人故事。第一序列是人類各種欲望沖突的象征性外化,第二序列是人因尋求主體性的滿足而與外界發生的沖突。這符合我們對大多數武俠電影的直觀印象。然而下文將通過論述加以證明,在徐浩峰的電影中,不存在大多數傳統武俠電影中的上述圍繞主人公所展開的“雙序列敘事結構”,轉而采取一種更為復雜的“雙線交織式結構”,在主體情節線之外往往存在著一條完整的副線。而且,設置副線的目的不是推動主線的敘事進程,而是展示(而非干預)故事世界中的某種現實。

圖2.《師父》
在《倭寇的蹤跡》中,敘事主線是戚家軍遺族“左偏使”和主人公梁痕錄因想將戚家軍刀技流傳民間,與霜葉城武行發生沖突,最終通過與第一高手裘冬月比武而獲得認可;副線為年邁的裘冬月因逃避夫人和侍衛通奸上山歸隱,又因“城里鬧倭寇,后輩小子打不過”而回城,實則是為了捍衛“第一高手”的榮譽,從而引出霜葉城兩大高手的爭霸局面。《箭士柳白猿》中,主線為主人公雙喜做“跳墻和尚”成為柳白猿,被軍官過德誠和混血女二冬選中為其刺殺政敵楊乃興,但柳白猿放棄了刺殺,最終卻殺死了過德誠;副線展示了武功高手匡一民為成就自身價值,在亂世中尋主護主的一系列恩怨艱辛。《師父》的主線為主人公陳識欲在天津開武館揚名,需先收徒“踢過八家武館”,但徒弟踢館后被軍界所殺,師父放棄開館的計劃,為徒弟報仇后逃離天津;副線為天津武行頭牌鄭山傲被做了督軍副官的徒弟所敗,武行面臨被軍界接管的危機,武行人士借陳識之手除去林副官,在亂世中逃避被軍界接管的命運。
可以看到,三部影片中,副線情節均非圍繞主人公展開,而幾乎是另一個與主人公毫無關系的故事。兩條敘事線索之間的關系,除在極少數場景中形成“交織”(如《師父》中陳識殺死林副官)以外,主人公幾乎不干預副線的敘事進程,而只作為線索人物引出副線情節,主線與副線之間大多數情況下不存在較強的因果聯系。同時,副線情節雖然有時放棄了因果邏輯連接,而只按照時間進展組織事件,但每部影片的副線大體都可以構成自足的情節線,且其主要情節大部分不與主人公發生關系。
由以上分析可以判斷,副線的主要情節既不是關于主人公的故事,也幾乎不受主人公行動的影響,而是有其自足的語境、人物和情節走向。無論是《倭寇的蹤跡》中的民間武行紛爭、《箭士柳白猿》中武行人士在軍政界尋求發展,還是《師父》中武行與軍界的沖突,實際上都暗示著一種龐大的社會現實,一種江湖體制或江湖體制與政治體制的交纏或沖突。“體制”的世界在電影中總是先驗存在、自足發展,而且主人公總是無法進入也無法改變副線所代表的體制世界。
學者李顯杰在分析交織式結構時認為,這是一種對比的結構,意在表達電影作者的某種觀念。⑩在徐浩峰的電影中,兩條線索間的對比,體現在體制與個人、龐大與渺小,或江湖體制與廟堂體制的對比。徐浩峰通過這種對比,完全顛覆了以往武俠電影中“江湖”廣闊,任俠客放浪形骸的“武俠烏托邦”,而展現了一個有著一套固定的行事規范、不可撼動的江湖體制。而且在徐浩峰的電影中,展示了江湖不可能完全逃離廟堂的現實處境,作為個體的主人公(及其他武林人物)身處兩種體制的夾縫中,只能顯得更加渺小和無力。這種在傳統武俠題材電影中融入現代意識的表達,也成為徐浩峰極為鮮明的個人風格。
三、對傳統敘事手法的反叛
武俠電影作為一種類型在中國發端較早,發展充分,已形成較為固定的美學風格。其敘事手法經過歷代導演的發展革新,形成了一條較為明顯的發展軌跡。大體而言,初期的武俠神怪片主要通過早期特效手段制造視覺奇觀,“黃飛鴻”時代的武打片大部分停留在以比較簡單的紀錄式手法表現完整武打動作。20世紀60年代起,一批有才氣的新人導演(胡金銓、張徹等)的加入,大大提升了武俠片的藝術水準,從此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美學風格。賈磊磊認為,中國武俠動作電影的美學風格在于其標志性的剪輯語法,并且揭示了由剪輯手法所制造的武打場面的節奏特征。
根據賈磊磊的研究,中國武俠電影自60年代成熟以來,武打場面的剪輯節奏總體上呈不斷加快的趨勢,并在90年代的繁榮時期形成了平均每秒鐘一個鏡頭的“暴雨式”剪輯,從而既能保證畫面的清晰連貫,又能制造出激烈緊張的視覺效果。但是,通過對徐浩峰電影中武打場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徐浩峰放棄了這種基于長期歷史積累而形成的剪輯手法,而形成了一套有著明確個人風格的敘事手段。
對于徐浩峰三部電影作品中比較重要的武打場面,下文以表格形式進行分析:

表1.
由上表可以看出,徐浩峰電影的武打場面普遍放棄了以快速剪輯為主的節奏,而大量使用較長的鏡頭以表現完整的武術動作。通過計算這些武打場面中平均每個鏡頭的時間長度可以大體看出,徐浩峰電影中武打場面鏡頭的長度要遠遠大于上文提到的90年代以來形成的成熟風格(詳見附表1)。
進一步分析徐浩峰電影的武打場面,發現在場面內部,其結構也呈現出鮮明的獨特風格。以《倭寇的蹤跡》中裘冬月與梁痕錄的比武為例,從裘冬月提醒“不要看我的槍,要看我的腳”之后兩人斗步的鏡頭開始,至裘冬月擊敗梁痕錄的鏡頭為止,段落長度近3分鐘,共25個鏡頭,但其中真正展現兩人交鋒的鏡頭只有最后一個,且交鋒時間幾乎只有兵器相碰的一瞬間。該段落的前110秒(1:36:33-1:38:23)共19個鏡頭,都在展現二人的斗步、互相試探和觀戰者;繼而又用了52秒(1:38:23-1:39:15)共5個鏡頭,展現二人各自的準備和觀戰者;只有最后一個鏡頭,約7秒鐘(1:39:15-1:39:32),展示了二人最終的對決和梁痕錄失敗后走向前景,而其中兩人兵器相接的時間只有一瞬間,最終的“比武”只有一招。這顯然不同于傳統武俠電影將武打段落作為核心進行展示的結構特征,這一“比武”段落的重點不在于兩人招式的較量,甚至不在意其較量的結果(梁痕錄輸了比武卻仍獲準開宗立派)。從三個部分的時間比例上可以明顯看出,這一段落的重心在于展示兩人武功步法的精妙、兵器的特點,以及以之前“漫長”的試探和準備過程,更反襯出兩兵相接決出勝負的速度之快。
同樣的結構也出現在《箭士柳白猿》中的師徒長槍對決。從過德誠說“我悟出了更好的”開始進攻的鏡頭始,至匡一民展示回馬槍止,共約106秒,19個鏡頭。前39秒(1:04:59-1:05:38)共5個鏡頭,是師徒二人以長棍互相了解和試探;中間18秒(1:05:50-1:06:08)共2個鏡頭,換過槍頭之后是二人真正的勝負對決;后37秒(1:06:08-1:06:45)共10個鏡頭,是匡一民打敗徒弟后,以“師父”身份向徒弟展示“老祖宗的東西”,這一部分已經不具備敘事上的意義。真正的長槍對決只用了2個鏡頭表現,亦即匡一民在摸透了徒弟的槍法后,只用了2個鏡頭(其中第一個鏡頭是徒弟進攻,師父防守反擊,第二個鏡頭是師父進攻。相當于仍是一招制勝)即戰勝了徒弟。
以上兩個場景無疑是寫實的,但又不同于傳統武俠電影中,以記錄精心設計的武打套招為特征的“寫實”,而是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武術的實戰情景。真實的武術搏擊,顯然沒有那么多表演性的華麗動作,而往往勝負只在交手的一瞬間。徐浩峰電影的武打場面,將電影中的“功夫”由充斥銀幕的觀賞性“表演”,還原為真正的具備實戰功能的“武術”。不難看出,徐浩峰電影對于武打場面的表現,旗幟鮮明地對傳統武俠電影的娛樂性和“觀賞性”進行了反叛。
除結構的特殊之外,在以上所分析的兩個場景中,各有一個采用人物腰部以下景別、展示武術步法的鏡頭(類似鏡頭在徐浩峰電影的其他武打場面中也曾出現),這種帶有明顯敘事者痕跡的鏡頭,有著明確的展示性目的。結合前文所述,在徐浩峰的電影中很多武打場面不具備敘事上的意義,我們不難斷定,徐浩峰電影的武打場面,在很多情況下,并非為了觀賞目的或推動敘事進展,而是為了展示真實的武術及其實用性搏擊樣態。展示即目的——可以判定為徐浩峰武術電影在敘事手法上的鮮明作者化風格。
結語
武俠電影作為中國電影中的一個重要類型,幾乎見證了中國電影的每一個發展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武俠電影創作呈現出紛繁多樣的文化和審美樣態,也曾一度陷入衰微。如何突破發展瓶頸,使基于傳統題材和文化的武俠電影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重新煥發吸引力,順利實現“現代轉型”,是武俠電影在現階段的發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徐浩峰的武俠電影創作,基于現代紀實美學風格,立足于民間江湖的社會文化背景,展示了真正的傳統中華武術的精微,也書寫了武林人士在時代中的彷徨與掙扎。可以說,徐浩峰的電影,實現了傳統題材與現代視角的結合,為武俠電影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創作思路,同時也在表現手法上做出了革新和探索。確認并闡發徐浩峰電影的作者化風格,不僅有利于豐富華語電影武俠創作的風格特征,相信也會為武俠電影的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和啟發,從而促進武俠電影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的轉型和重新繁榮。

表2.賈磊磊《“暴雨剪輯”——中國武俠動作電影的剪輯技巧及“標志性”節奏》對60年代以來武俠電影武打場面的節奏分析圖。
【注釋】
①滕朝.專訪徐浩峰:動作片最頂尖的是特工化的武術[J].電影,2015(12):74-81.
②吳冠平.武之美學,器之精神——徐浩峰訪談[J].電影藝術,2013(3):44-50.
③徐浩峰.坐看重圍——電影《師父》武打設計[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75.
④陳墨.中國武俠電影史[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2.
⑤孫昊明.華語功夫武俠電影中“英雄”形象的文化身份書寫[D].西安:陜西師范大學,2014.
⑥賈磊磊.武舞神話:中國武俠電影及其文化精神[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7:60-62.
⑦[法]阿爾吉達·朱利安·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M].蔣梓驊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257-261.
⑧倪駿.中國武俠電影的歷史與審美研究[D].北京:中央戲劇學院,2005:54.
⑨劉郁琪.中國武俠電影的雙序列敘事結構及其文化意味[J].江西社會科學,2011,31(10):190,189-193.
⑩李顯杰.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378.